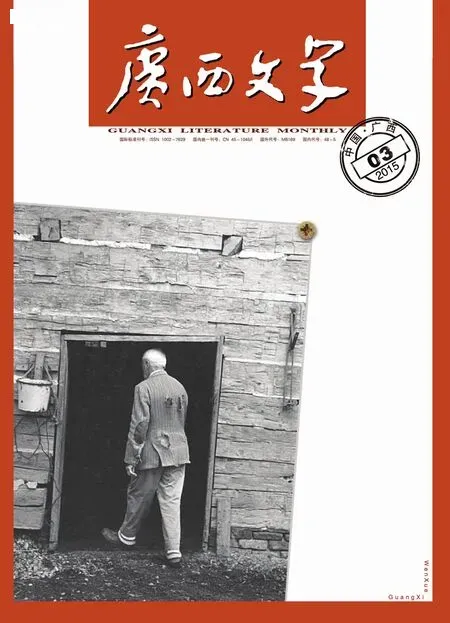夜行人咖啡馆
短篇小说·陶丽群/著
老史晚上十一点十分到达他的夜行人咖啡馆,比平时要早差不多一个小时,平时都是十二点。丽妃朝他笑笑,他的体贴,她懂。这个跟着他六年的三十四岁的女人,有一张圆圆的娃娃脸,柔顺的披肩发永远温情脉脉地垂在肩上。老史从没见过她束发,哪怕她刚洗完澡从卫生间里出来时。不过他挺喜欢她这个样子。她对老史笑时,永远都带种不设防的明朗。可以从她的笑里轻易看出她对他的信任和依恋,那样干净而温顺的眼神,是老史人生中一盏暖意融融的灯火。不过,当她安静沉思时,她的整个人会被一种老史很陌生的神情罩住。老史无法准确形容那种神情,仿佛一个人陷入某种悲伤回忆时的沉痛,或者对未来不知所措的迷茫。那时候的丽妃他感觉跟他毫无关系,一个陌生的丽妃。他知道她心里肯定端着放不下的东西,但老史从来不问,并不是不在意,毫无疑问,他是爱这个女人的。
此时她坐在柜台后面,亮紫色风衣搭在椅子靠背上,米色针织开衫把她细长的脖子和瘦而窄小的双肩暴露无遗,瞅着令人顿生怜爱。她的面前放着一杯琥珀色的普洱茶,对老史的笑脸上带有些许倦色。他们的夜行人咖啡馆是二十四小时营业,老史从晚上十二点到早上十点,之后丽妃会来接他的班,一直到十二点。他们有两个服务员,一男一女,上班时男跟老史,女跟丽妃。咖啡馆不大,二十平米,也不在主街道上,甚至还有点儿偏僻。当初选在这里时,老史的几个朋友很有些担心,但老史毫不犹豫看上了。结果还不错,真的不错,总会有些人避开喧闹遁入这个安静的角落喝杯咖啡、茶,吃点点心。这是个令人能暂时放下心事和情绪的地方,当然,也可以放下疲劳,以及当作无处可去时的消磨之地、避雨避风之地。一年当中老史和丽妃会在春末和初秋这两个不冷不热的时间段出去旅游十多天,把“休息中”的牌子悬挂在夜行人咖啡馆门脸上。大体来说,老史和丽妃是满意这种生活现状的,当然包括他们之间这种关系的现状。
丽妃从柜台后的椅子上站起来,她只是笑,并不说话,看来白天的生意不错,她确实累了。她从靠背椅上取下紫色风衣穿上,老史走过去帮她把头发从衣领里轻轻拿出来。她又朝他笑笑,顺便捏一下他的胳膊。女服务员站在柜台边上,头上戴着黑色三角帽,满脸羡慕嫉妒地看着两个老板表达落落大方的性感亲昵。她对于他们之间的关系很模糊,说是夫妻,好像又有那么点儿生疏和客气夹杂其间;说不是夫妻,有眼睛的人都看出他们是夫妻,这怎么说好呢?女服务员遮着嘴巴打一个哈欠的当儿,老板娘就裹着风衣出门了。他们家离咖啡馆有好几个站,他们没买车,在这件事上他们的态度惊人一致。大多数人认为车是生活的必需品,在他们看来却成为一种负担或累赘。
老史站在咖啡馆玻璃门前,一直看着丽妃上出租车。因为今晚提前来了,老史在路上时就给司机打了电话。这个出租车司机接送丽妃六年了,每晚十一点五十分准时在他们咖啡馆门前等,只有在风雨大得实在不便行车时才进入他们的咖啡馆喝上一杯,并且拒绝他们请客,咖啡钱很低调地压在咖啡杯下。他在白天和晚上给他们拉来过不少神情忧郁的无处可去的顾客,这些顾客后来成为他们的常客,有些则是第一次来也是最后一次来,极为自然。
“你也回去吧。”老史环顾一下咖啡馆,只有一对小情侣安静地坐在最角落的一张桌上。他对女服务员说。女服务员朝那对小情侣望了一眼。
“没事,我在就行。顺便给小米带个话,今晚放他假。”老史说。小米是上夜班的男服务生,天塌下来也能笑得出的阳光青年。
“啊,谢谢老板。”女服务员风一样转进小里间,二十来岁的动作轻快敏捷。老史宽容地笑了。很快女服务员就换掉工作服出来,工作时盘起来的头发也放下了,整个人顿时如夜色一样不动声色地生出一种不可名状的惆怅风情。她朝老史做一个飞吻动作告别,旋风一样出了玻璃门,带进一股湿润冰冷的空气。老史惊觉过来后,想叫住那毛躁孩子,告诉她带把伞,眨眼间老史只来得及望见一把黑发一闪,如同夜色撕开的一线裂缝,很快就弥合如初了。老史有些无奈,不过他是欣慰的,黑夜里匆忙的身影和脚步代表方向和归宿,有方向和归宿的人是幸福的。小情侣不一会儿也结账走人了,咖啡馆顿时和外面的夜色一样安静下来。
老史并不收拾那对小情侣桌上的咖啡杯子。他给自己煮了杯咖啡,选一张靠窗的桌子坐下。这样的晚上是不会有太多的客人的,不过通常也会有个把。他安静地坐着,等着。对于这样的夜晚,老史总有种莫名的恐惧和紧张的情绪盘旋心底。这种情绪往往会使老史彻夜不安和清醒,通常下半夜四点到五点之间的困意也消失殆尽。在黎明的曙光爬上窗户时,这种奇怪情绪才慢慢平复,直到看见丽妃带着淡淡的笑容走进咖啡馆,这种恼人情绪才算彻底烟消云散,随之而来的是抽筋扒骨般的疲劳感,仿佛一整夜他都在高度集中精神提心吊胆着什么事情。其实任何事情都没有,六年来他们的咖啡馆所有的夜间经营都相对平安,偶尔会发生一些情侣之间争执的事情,不过通常很快就平息了。这不是一个热闹的地方,来的人基本上也不是喜欢热闹的人。
从玻璃窗望出去,夜色愈发深重了,几乎能听到清冷空气流动的嘶嘶声,无孔不入的寒意弥漫整个夜色。偶尔有出租车经过,车灯像是被打磨钝了,昏黄而散漫,急急移过来,又速速离开去,投下的一帘光影映衬不太密集的雨帘,并没使得咖啡馆里的光线亮起来多少。都是有目的地的夜间的匆忙过客。
雨大概是晚八点半时下的,入冬后的第一场雨。开始下时有点大,雨点急促敲打在他们卧室的玻璃窗上。老史从梦中惊醒过来,窗外已经一片漆黑,屋里的空气带着刺般蜇人的冷,恐惧和紧张的情绪开始在心底酝酿了。他在黑暗中摸索,把丽妃的枕头拽过来,夹到胳膊弯里。枕头的一角抵在他的下巴处,他闻到了洗发水的淡淡清香。丽妃总是嘲笑他这行为很幼稚,然后趴在他上头,清澈的目光深深望进他的双眼,看见他眼底隐藏的不安。她了解他的情绪,但不知道他这种情绪因何而生,她也不问。老史感激这个女人的善意。他的晚餐很简单,一碗米饭,胡萝卜炒黑木耳,一碗香菇菠菜汤,吃得很满足。老史不吃肉,连蛋奶都不吃,纯素食主义者。不过丽妃吃,她每顿饭都得有几块肉,或者煲一个排骨汤。她吃得很香,老史从不要求丽妃也跟他素食,他甚至很乐意看见她啃一块骨头时略显贪婪和享受的满足感。他希望丽妃过得随心所欲一些,奢侈一些他也接受。老史喜欢身边的人过得快乐满足,他会从中获得一种踏实感。老史出门时,雨渐渐小了,没有风,空气饱含湿冷,大街上的车已经渐渐稀少,路灯显得孤单而清寂。他大步朝咖啡馆走去,那股复杂情绪已经在他的胸口饱满得伸手可及了。他希望丽妃早一点回家,这样四处湿冷的夜晚,所有的人都应该待在温暖的家里。
四十一岁的老史在朋友眼中是个温和低调的男人,当然,他的朋友并不多。一个在嘉年华酒吧当调酒师。一个行踪诡异但秉性老实的自学成才的画家,总是引诱老史画裸体像。一个整天钻进别人书房检查网络故障的电信技术员。还有一个胖大的,看起来面目温情的超市小老板。他们有时一两个月相互不联系,好像要彼此相忘于江湖,某一个夜晚却带着高涨的热情突然闯进他的咖啡馆,通宵免费消费老史的咖啡,咖啡钱倒没花多少。他们都不怎么喜欢喝咖啡,他们喜欢喝啤酒,老史最多给他们提供一扎,之后就拒绝再给了。他因此总免不了被挖苦嘲笑一番,他们说他怕丽妃。老史宽厚地笑笑,之后给他们上咖啡,浅浅碰一两口之后,他们的咖啡常常冷却在杯子里。朋友们热情高涨地胡说八道过了上半夜后,大家都有些困乏了,但没有人提出要离开,集体沉默着朝窗外沉寂的夜色凝望,各自沉浸在无人所知的隐秘世界里。老史坐在柜台后面,这时候他会发现这些朋友瞬间变得陌生了,变成另外一些老史不认识的陌生人。调酒师神情沉静中带一点适度的忧伤,夜色于他而言并不陌生,他常常通宵工作,为各种各样的人调一杯杯口味不同的红酒。他置身于嘈杂的酒吧里,练就了一种屏蔽掉一切不想入眼入耳之事的本领,在他的眼里只有精致的酒杯和色泽透亮的酒水。他站在柜台后面,嘈杂的音乐和丑态百出的客人们在他的眼前一片空白,他们常常在酒精作祟下粗鲁地拽住他的衣服,朝柜台上吐口水的行为也被他一笑了之。刚来酒吧时他对他们深恶痛绝,但过了一阵子之后,他则以略带点悲悯的态度对付他们。他在凌晨最静谧的那段时间下班,通常是三点半到四点之间,带着一种宁静情绪静悄悄走在空旷的马路上。他喜欢夜色,高大的建筑物在夜色的笼罩下比白天看起来线条柔和许多。他觉得世间应该是这样的,柔和,柔软,白天把一切都糟蹋掉了。调酒师一般会选择几条平时喜欢的街道继续走上一阵。假如没有意外,通常会在雕塑广场附近的一个拐角,灵巧地跳出来一个清秀的和调酒师年纪相仿,但看起来起码要比他年轻十岁的清秀男子。他不是存心要吓调酒师,不,不是的,他只是想给他一个惊喜,尽管调酒师早就知道他在那里等着。男子带着腼腆的笑,在柔和的路灯下朝调酒师走来。他们面对面站着,相互凝望片刻,然后十指深情相扣,默默相伴走在下半夜里。有时候他们会说一两句话,更多时候则什么都不说,但他们的内心是欢喜的、满足的。在黎明的曙色到来之前,两个人满脸悲戚依依不舍告别,各自回到这个城市某一个安置他们的角落。他们已经交往六年,下一个六年,在他们心里如夜色般隐藏着许多看不见的定数。他们从未在白天见过面,这座城市的白天无法包容并接纳他们的深情。他们通常在调酒师休息日时在一起,每个月两个休息日,不过他们已经很满足了。
画家凝视夜色时的表情是失魂落魄的,一副拼命克制某种疼痛的表情,不一会儿他就绷不住了,脸上僵硬的表情松弛下来,嘴角一阵神经质般抽搐,然后捧住头,像个失去心爱玩具的孩子伤心抽泣起来。他的哭是压抑的、克制的,仿佛嘴里塞了一块布头。他瘦小的肩膀不断颤动,令人揪心。几个见惯了的朋友毫不动容,没有谁给他一句安慰,甚至连一只拍他肩膀安慰的手都没有。他不需要,他们知道。画家非常热爱女人,他有很多女人,他对女人好到简直是慈悲为怀的程度。他常常被那些女人搜得身无分文,有时还因为钱少而被破口大骂。但这几个朋友都知道,他不行,他和她们睡觉,实际上什么都没干。每个女人在画家眼里都是他姐姐,他少年时相认的姐姐,姐姐突然在某一天莫名其妙不见了。画家长年奔走各地,作画卖画,他希望在一个陌生的地方,他的姐姐失而复得。他偏爱夜晚,常常深更半夜在大街小巷游荡,他固执地觉得姐姐的失踪一定和夜色有关。画家五官俊朗,三十八岁。哭上一阵子之后,他常常叹一口长气,作为这场流泪事件的结束语,然后满面悲戚擦干眼泪,目光重新跌进深渊般的夜色里。电信技术员是个情绪容易激动的人,不过当他沉浸在复杂的网络检修工作中时,那些错综复杂的线路会使他变得异常专注和镇定。在并不固定的朋友聚会里,他常常无比愤慨地感叹某天下午给一户人家检查网络故障时,见到人家的房子是何等豪华舒适,据主人说他们的浴缸都是从加拿大空运来的。“操,不就一个洗屁股的盆嘛。”他说,狰狞的模样恨不得立马对什么白刀子进红刀子出,他屡次因为买不起房子而恋情告吹,在三十四岁时和一个带三岁女孩的女人结婚了。女人有一套两居室的房子,他们之间没有孩子,据说老婆不肯生了。“除了这,她还是挺好的。”他偶尔对朋友们说,朋友们望着他眉间深锁的悲愁,默不作声。每次朋友们邀请来老史的咖啡馆“过一夜”时,他总是最高兴最迫不及待的一个。他望着窗外的夜色时,像一个迷路的孩子,进退两茫然的神色使他看起来呆滞得不行。超市小老板在朋友们当中算是比较圆满的,当然,他为创建他的小超市吃过不少苦头。老婆和他一样胖而朴实,他的两个女儿在上一所不错的中学,都很有舞蹈天赋。他的脸上总是一副息事宁人的谦和表情。他从来不干短斤缺两的事情,也不计较顾客少一毛两毛。去他超市的大都是熟客,大家都认为他是个乐观厚道的小老板。只有极少数人,比如这几个朋友,才知道他隐藏极深的极少表露出来的另一副面孔。他坐过五年牢,但他是冤枉的,没得到一分补偿款。他的二女儿在他进去后的第三年诡异地出生了,但他对她很好,对老婆也很好。他凝望深夜时脸上以往那副招牌似的温情敦厚的笑脸不见了,一种被抛入无底冰窟般的绝望像厚实的寒霜挂在脸上,他专注而固执地朝黑夜偏着脸,直到微热的泪水顺着胖胖的脸颊流下。夜黑得如此博大宽厚,每个人都可以在彼此无法看得见的黑色中,找到一个暂时盛放自己的角落,剥掉白天的盔甲,和自己赤裸坦诚相对。
他们就那样坐着,咖啡馆里零散的顾客并没影响到他们。老史走过去,安静地坐在他的朋友们之间,彼此靠近。他们像一个相似的共同体,释放出一种彼此相互需要的孤独的温暖。这样的安静大约会维持半个小时,之后他们如梦初醒。从短暂的精神迷失中苏醒后,彼此相望的神情有些不自然,带一点心照不宣的害羞笑容,摇晃僵直的身体,找好舒服姿势,横七竖八歪在桌边睡了,毫不设防地睡一个好觉,没谁提出要回家。他们似乎都需要一个这样的夜晚,一个可靠的地方,把自己放空,短暂回到真实的自我当中。老史回到柜台边,当客人全部走后,他守着他的朋友们,内心宁静而满足地打发掉又一个漫长的夜晚。当朋友们带着初醒的满足表情骂骂咧咧在黎明的曙光里离去时,老史像完成了某种使命般,浓重的倦意纷至沓来。
……
这个连呼吸都会被湿冷刺痛的冬夜,老史不希望他的朋友们离开家,应该在温暖的被窝里沉沉睡去,包括丽妃。他仔细端详玻璃窗外的夜色,雨夜如此静谧,十二点半了。他精神抖擞,凝神聆听,像只机敏的猫头鹰捕抓黑夜中点滴的响动。只有雨声微弱的唰唰声透过玻璃窗传来,世界真的安静了。他的咖啡馆亮着橘色的暖和光芒,任何行走在雨夜中的人都难以抗拒这抹微弱的暖意。
老史的咖啡馆在一条巷子中间。巷子悠长曲折,像满怀心事的人。两边排满店铺,卖陶瓷和茶叶的居多,夹杂几间卖杭州丝织品,卖老北京布鞋、唐装,还有几间包罗万象般你看不出具体卖什么的店铺,里面有针头线脑,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口盅,几匹颜色华丽的少数民族布料,几件也许过了若干年后价值连城的蒙着灰尘的古旧家具。整条巷子的色泽是陈旧的,透出不动声色的哀伤沉寂,特别是夜晚。大部分店铺在晚上十点左右相继打烊,余下几家茶馆、咖啡馆也在午夜前关门。他们和老史都很熟,路过他的咖啡馆时按一下恼人的喇叭后扬长而去。他们和老史开玩笑:夜间的风景一定很不错吧?老史通常沧海桑田般宽厚一笑。他喜欢这巷子的调子和色泽,以及这些没有太多想法,甚至对生活带有点儿轻度厌倦的态度懒散的小老板。巷子尽头二十四小时值班的社区派出所也是他喜欢这条巷子的原因之一。老史从未去打扰过他们,那几个面熟的警察偶尔会在某个漫长的夜晚来他的咖啡馆喝上一杯,很客气。
老史靠在靠背椅上,一动不动凝望窗外的夜色。夜黑得如此彻底,他感觉内心也一片黑暗。但他知道有很多东西包裹在浓重的夜色里,如同他胸口暗暗涌动的情绪。情绪,老史意识到自己又会陷入过往酝酿出来的情绪之中时,他马上使劲摇头,仿佛要把脑袋里的东西全都摇晃掉。这样的夜晚对老史来说并不陌生,有时候他独自一人待到次日早晨丽妃来到咖啡馆时。丽妃脸上会有些浮肿,仿佛这样的夜她也并未睡去。有时候也会有那么一两个顾客陪他,通常两点过后就走了,他们离去时表情懒散淡定,只是来咖啡馆要一阵子深夜的安静而已。
老史站起来,若有所思地朝玻璃门口走去。已经冷却的咖啡已收拾走了。他瞟了一眼墙上的挂钟,两点十分。嗯,这是一天当中一个人离自己最近的时候,最柔软的时候,最无助的时候,他内心渐渐充满一种黑色般的心酸。他把咖啡杯子放在柜台上,坐进柜台里。老史发现每当坐在这个位置上时,他便有一种把握住什么的自信,情绪随之慢慢平复下来。他朝玻璃门外张望,咖啡馆里橘色的暖光照亮了门外一小片湿漉漉的黑夜。
是的,他听见了。迟疑而涩重的脚步声,慢慢靠近他的咖啡馆。老史安静地等待着,咖啡馆内暗淡的灯光笼罩在他的脸上,以往来顾客时童叟无欺欢迎光临的温和表情挂在脸上。湿冷的午夜把一个身材矮小、发梢上滴着雨水的小个子男人推到老史的咖啡馆门前。他提一只同样湿漉漉的扎了口的白色编织袋子,肮脏不堪。蓝色牛仔裤和黑色条纹西服污迹斑斑,湿透了,整个人透出一股令人忍不住打寒战的落魄感,看样子在雨夜里已经行走好一阵子了。他站在玻璃门外,朝咖啡馆里犹疑张望。老史发现这令人发冷的夜行人有一张非常耐看的脸,五官线条明朗,紧抿的嘴令人想到害人不浅的倔强。那张脸上,嗯,老史在昏暗的咖啡馆里端详它,看不出任何表情,死水一般,似乎浓黑的夜和冰冷的雨水并未使它受到任何影响。他就那样站在玻璃门外,那副坚定的样子仿佛在等待屋里的人请求他进去。老史叹了口气,从柜台里出来,朝玻璃门走过去。门外的夜行人往后退了两步,退进浓重的黑夜里,是戒备的姿态。老史拉开玻璃门,一股水分厚重的冷空气扑面而来。
“请进,二十四小时营业,热咖啡、热茶、点心都有,需要的话点心可以微波炉加热。咖啡一杯六块,茶一壶八块。”老史温和地说。
夜行人依旧站在那里,打量咖啡馆,也打量老史。老史很平静,脸上既没有欢迎的热情也没有拒绝的厌烦。夜行人终于还是进来了,小心翼翼地迈上两层台阶,侧身经过老史身边。身上浓重的寒气使老史忍不住打一个寒战,还带着一股令他为之一振的熟悉的气味,老史顿时心里一阵紧缩。夜行人站在咖啡馆中间,仔细打量一番咖啡馆,然后朝一张最靠里的桌子坐下,把自己缩进墙角里。一直紧抓的白色编织袋放在靠里的椅子上,不过他又极快地抓起来,放在桌子底下的地板上,同时有些不安地望着老史。老史低下头,在他望向自己之前。他倒了杯热水朝他走过去,放在他面前的桌子上。
“你需要点什么?”老史淡淡地问。
“泡面,有吗?”他飞快看了桌上那杯热水一眼,有些拘谨地问。
“有的,来两包?”老史很平静地微笑着。
“啊,我以为没有。”他显得有些欣喜。
“稍等,马上就好的。”老史拿着托盘,他朝咖啡馆里一扇装饰得极为隐秘的门指了指,“卫生间在那里。”他觉得夜行人应该换掉身上几乎可以拧出水来的衣服,假如塞在桌子底下的编织袋里装的是衣服的话,不过看样子里边的东西也该湿透了。
老史走进煮咖啡的里间,里间很小,有一扇透明的玻璃窗子,可以看见外边的顾客。老史从柜子下费劲地拽出一个并不大的纸箱,里边藏有十袋香辣红烧牛肉泡面。丽妃对泡面有种令老史不可思议的痛恨,有一次甚至因为泡面和老史吵得不可开交,然后蜷缩在角落里哭得一塌糊涂。其实老史从头到尾都没说一句。她歇斯底里又哭又闹,蓝色高跟鞋把一箱泡面踩得粉身碎骨。老史只好偷偷把泡面藏在换过头脸的纸箱里,藏起来。他们的咖啡馆并不卖泡面,老史也极少吃。某天夜晚,朋友们会要求来那么一碗,像举行某种仪式般埋头吃完。
老史麻利地烧水,撕开两包泡面放进平底锅,内心有一种因为夜行人到来而产生的感激,这不是常有的。他记得遇见丽妃时,他也产生过这样的情感。火腿肠和鸡蛋还有,犹豫了一下,老史最终什么都没加进去,一大碗开水泡面。老史把热腾腾的泡面端到夜行人面前时,发现他还穿那身湿衣服拘谨地坐在那里,仿佛还没适应这个新环境。他放下面碗,略微犹豫,把到嘴边的话咽下去了。夜行人几乎是从椅子上弹起来,快速摸索牛仔裤屁股兜。老史赶紧说,不是,你要走了再付。我是觉得你该到卫生间换掉你这身衣服,好像湿透了。夜行人的手从身后慢慢弯回来,仔细朝自己身上看,仿佛才意识到自己的衣服湿透了。他朝老史笑笑。老史觉得那笑像是强行按在他的脸上,僵硬、呆板。他拿着托盘走了。
咖啡馆短暂的插曲过后又恢复安静。老史坐在柜台里,盯住桌面的账本。其实他从来不查账本,所有收入和支出均是丽妃打点,丽妃每个月会叫他过目,但他从来没碰过账本,银行卡也在丽妃手上。假如丽妃哪一天从咖啡馆消失,老史的夜行人咖啡馆只能关门永久停业。但老史不在意,他对目前的生活状态有一种占大便宜感,既然是便宜,就不存在失去的恐惧了。他盯住账本,目光却从微垂的眼帘下飞向角落里浑身湿寒的夜行人。他在吃面,小心谨慎,毫无声响,一面吃一面向老史投来机警的一瞥,像一只饥寒交迫的小动物在警惕享用好不容易弄到手的食物。那个角落离老史坐的柜台也就七八米,隔六张桌子,泡面暖洋洋的诱人香味洋溢小小的空间,夹杂那股老史熟悉的久违的气味。看得出来,他不属于这座城市,而来自哪里,老史并不关心。
但,怎么办呢?老史此时内心无端端充满感激。不过他并不想和夜行人说上几句,他觉得和夜行人之间有一种并不需要语言的默契。他忍不住抬头,目光柔和而专注地注视角落里的夜行人。他依旧埋头在面碗里,吃的速度也变得有些狼吞虎咽起来,显然已经放松不少。突然他猛地抬起头来,似乎感觉到老史的目光,老史已经来不及收回自己的目光了。他只好从柜台里走出来,朝角落里走过去。夜行人一直盯着他,眼见他一步步靠近自己,嘴里的咀嚼也停下来了。他放下筷子,慢慢站起来,整个人透出一种拒绝但又无能为力的紧张感。原先过于苍白的脸色因为热气腾腾的补给而泛起些红晕,双眼在橘色的灯光下惊讶不安地直视老史。很年轻,不会超过二十五岁。老史走到他跟前,才为他的行为找到蹩脚的借口:你需不需要作料?辣或者醋?可能口味会好一点。哦,不了。夜行人似乎放心不少,朝老史笑笑,带一点腼腆。嗯,那就好。老史说,目光盯住桌上的碗,差不多吃完了。要不要再来一碗?我很饿时能吃四包。老史开玩笑似的,但他是认真的。啊,这就够了,谢谢。夜行人搓搓手。那你慢用。老史说,转身走回柜台,在柜台和玻璃门围成的折角里把空调打开,调到制暖。
老史呆呆地坐在柜台里,搁在柜台上的手轻微颤抖。空调吹出来的暖气一阵一阵拂过他的面颊,老史把柜台边的台灯关掉,他在黯淡的柜台里不动声色地凝视角落里的夜行人。一种久远的、熟悉的感觉在老史心里慢慢弥漫起来,陷入绝境般令人绝望的、自我羞耻和憎恶得想呕吐的感觉,极为孤独无助的感觉。这种感觉慢慢滋生出一种彻骨的痛。他的脸被疼痛弄得很僵硬,不明就里的人看到时是一副面无表情的模样,没人懂得沉寂之下焚心般的痛楚。幸好这种感觉不是常常困扰他,只是少数如今夜才凶猛袭来。他不再使劲摇头,他知道今夜自己会无可避免地沦陷进这种感觉中。这种招人恨的感觉此时就算是丽妃,也无法给予他一丝安慰。每个人总有一些这样那样的东西一辈子只能独自享有,就算是被它折磨,也无法找人分担。
安静黯淡的柜台里弥漫老史浓厚的忧伤,他靠在靠背椅上,不声不响。他极少在夜经营中睡去,就算犯困也不会。老史逐渐恢复了情绪,在角落里一直盯着夜行人。他深深地吸一口气,泡面的香味淡去了,那股老史熟悉的夜行人身上(也可能是从那个脏兮兮的编织袋里散发出来的)的味儿,变得浓烈起来,混合着暖气,平常人肯定会被熏得胸口发闷甚至呕吐,但老史和夜行人却如闻所未闻,这种熟悉的味儿甚至使他们有一种温暖的安然。角落里的夜行人靠在靠背椅子上,偶尔使劲点一下脑袋,终于睡过去了,被睡眠笼罩的面孔带着深重的愁绪。老史默默瞅着,轻轻叹了口气。老史知道当这个睡着了还带着悲愁的深夜流落人,他的人生开始脱离困境进入平稳的生活轨迹时,此时此刻的情境会蜂拥而至,占据他的夜晚,毁掉他的睡眠,别指望从安稳的生活中得到一个安稳的睡眠。老史的无数个夜晚就是这么度过的,就算床上的被子干净温暖,而丽妃温软的身体就在他的怀里,老史也会噩梦连连,无法获得一个安宁的睡眠。老史默默思索着,夜行人的睡眠安抚了他,让他感觉有睡意浓重袭来。
梦像人的心病。老史使劲奔跑,手里拎着脏污不堪的编织袋,那里面装着白天翻垃圾桶捡拾来可以换钱的破烂,脚上过大的球鞋像枷锁一样困住他飞奔的双脚。恐惧、愤怒和怨恨的心快要破胸而出了。他一路狂奔一路寻找亮光,下半夜后的城市犹如地狱般沉入黑暗的深渊中,老史几乎要绝望了。身后的脚步声越来越近,夹杂着尖叫声和起哄声。三个半大痞子像三个魔鬼,不管老史搬到城市哪个角落,都被他们轻易找到,等到深更半夜时才幽灵般出现在老史隐匿的角落里,和老史玩一种似乎已经成瘾的残酷游戏。他们追着他跑,疯狂的模样恨不得立刻把老史捏到手心里弄死。他们的手里有碎砖头块和棍子,还有砸碎的玻璃酒瓶。直到老史跑不动了,整个人瑟瑟发抖地紧贴住某条巷子的墙壁。他们叉开腿站在老史面前,喘着大气叫老史垃圾捞仔,并拧开手电筒,齐刷刷射到老史脸上。看见老史满含泪水的哀求而屈辱的双眼,两片嘴唇像风吹的薄纸般颤动时,他们瞬间集体爆发出邪恶的快意大笑,把棍子、碎砖头、碎酒瓶锋利的口子贴住老史被汗水和泪水冲刷的脸。老史彻底被恐惧和绝望击垮了,裤管一阵湿热,把这个游戏推上了高潮,也结束了。三个魔鬼从未动老史一根手指头,甚至连他口袋里卖破烂的钱他们都不要。老史宁愿被他们暴打一顿,肉体的疼痛或许能减轻心里胀满的恐惧和屈辱。游戏结束后,他们往往找一个离老史稍远的地方坐下,抽烟,骂娘,然后集体沉默,像黑暗中的一团阴谋。老史从恐惧中一点一点复苏过来,尿湿的裤子冰冷得令他牙齿打战,他从他们面前慢吞吞走过,三个魔鬼安静而淡漠地看他走远。
梦中的老史和自己卑微的灵魂相遇了,他抽搐着、挣扎着,叫却又叫不出。他疲惫不堪地渐渐清醒过来,那股浓烈的垃圾味儿仿佛就在他的鼻孔底下,他意识到了什么,没睁开眼睛。他的沉睡也许能让夜行人轻易逃掉两碗泡面的钱。他等着,那股垃圾味又渐渐淡去了,老史没听见玻璃门拉开的声音。老史又安静等待片刻,并在黑暗中慢慢睁开眼睛,夜行人还坐在那里,偏着头凝望玻璃窗外的黑夜。五点四十了,雨似乎也停了。老史瞟了眼墙上的挂钟,他动了一下,坐正身子,真正醒来了。老史拧亮柜台的台灯,夜行人很快转过头来,朝老史望了望,然后朝桌子底下摸索,拎出那只编织袋,站起来朝老史走过去。
老史朝他点点头:“不再坐会?天还没亮呢。”
夜行人笑了笑,“不了,还要干活。”他说,语气是轻快的,一夜的暖气和安静睡眠显然使他获得某种常态力量了。
老史点点头,“一共六块钱。”
夜行人愉快地从脏兮兮的牛仔裤后兜掏出钱来,一把零散的钱,仔细数出几张最干净挺括的给老史。
老史又点点头,“谢谢。”他说,真心的。
夜行人似乎愣了一下,他笑起来,挺直了一下背骨。
“欢迎再来啊。”老史说。
“看情况吧。”他愉快地说。
老史会意般点点头。夜行人转身,朝咖啡馆里的陈设再次看了看,也没和老史道别,推开玻璃门出去了。老史一直目送他消失在越来越近的黎明里。老史打算天亮时关门,提早回家,给丽妃做早餐。丽妃是老史开这个咖啡馆后不久的某一天夜里碰到的。她披头散发,满脸倦容,拉着一个坏了一只轮子的拉杆箱子。她拉开老史的夜行人咖啡馆玻璃门时,并没进来,而是像一个远游的人回到久别的家一样,靠在玻璃门上,朝老史久别重逢般地笑,很快就咕咚一声栽倒在咖啡馆门口。从此丽妃再也没有离开过咖啡馆,和老史在这座别人的城市里相依为命。
老史拉开咖啡馆玻璃门,站到门外。黎明前的空气新鲜清冷,他深深呼吸了几口。假如丽妃愿意,他打算今天向她求婚,假如她同意,他们将会在咖啡馆里举办一个简单婚礼,邀请那几个一起在孤儿院度过童年,又成功地从那儿逃出来的朋友参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