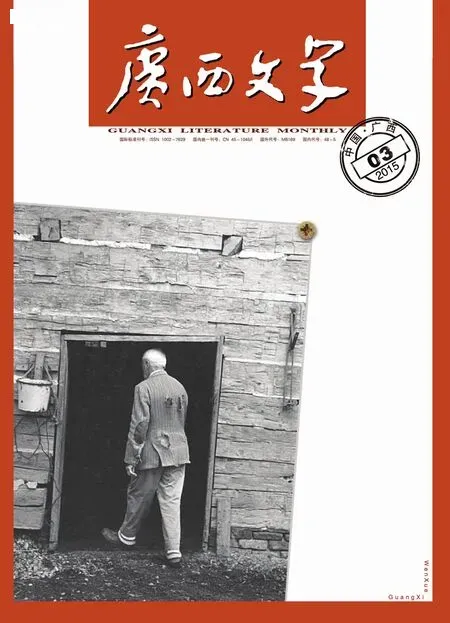鬼子中篇小说两个戴墨镜的男人
2005年5月25日中午,我突然接到一个电话,是一个美国人打来的。电话很长,打得我耳朵发烫,绕来绕去其实只是为了让我接一个活,让我给他编一个故事。但我心里拿不定主意,他很快也听出了我的犹豫,于是便说出一个不小的数目,那是有关故事的酬劳,我的脑子顿时一热,很快也发烫了起来。我在心里敲了敲小鼓,最后便答应了他。他在电话那头于是OK了一声,他说那你明天就过来吧。我说好的,放下电话就跑到了街上,买下了第二天下午到达北京的机票。那个美国人,那时就蹲在北京,在三里屯的一个公寓酒店里。那是一个三室一厅的客房,他让我住在其中的一间。房间的感觉挺好的,晚上睡觉的时候,我才发现那张床有女人用过,离去的时间肯定不到一天。
这个美国人,其实是一个中国人,清华毕业的,后来是政府把他送到了美国留学,再后来,他就自己成了美国人了。从机场出来的高速路上,他告诉我,他曾在美国的政府里工作。他说这个故事只要做得好,他可以在美国弄到一半的投资。
我问多少?
他说不少,最少几十万吧。
到底几十万就不好细问了,免得别人另眼看人。
我问美金?
他说当然!
那个时候的美金比人民币牛多了,几十万的美金就是几百万的人民币,只要故事里不存在烧钱的大场面,拍一个像样的中国故事是没有问题的,何况人家说的那只是一半。
故事里的人物与设想,他早就写在了一块写字板上,高高地立在了客厅的墙上,也就是电视机的上方。
写字板上的字很难看,每个字都写得歪歪的,就像电视里的一帮乞丐,而且都患有严重的腰椎劳损,手脚没一个是正常的。
第一行是主要人物,那是两个男人,一个叫尚海,一个叫胡男。跟着是人物的简介,尚海是瓦城人,大学毕业,原厂报编辑,工厂完蛋,人已下岗,有些心眼,但总是失意;胡男是瓦村的,老实善良,可容易上当。
他说你的很多小说我都翻过,不是瓦村的就是瓦城的,所以我把尚海给了你瓦城,把胡男给了你瓦村。我说可以,但他的那一个翻字,让我想偷偷地翻他一眼,但我没翻,我也不去看他,我只歪着头,继续看着他的那些歪字,一边看一边听着他的讲解。
人物简介的下边是故事的起因,一共两点。首先是这两个男人的妻子都怀孕了,他们都想把孩子生下来。他说尚海的妻子原来打过两次胎,这次不想再打了,打多了怕以后怀不上。胡男的妻子也是第三胎,前两胎生的都是女孩,这一胎他想应该是个男的了,所以就想留着。起因的第二点,是这两个男人的身上都缺钱。尚海缺的是生小孩时的住院费用,胡男缺的是第三胎的超生罚款。他们面对的数额都差不多,至少都在一万左右。
这个故事的点子不错,我说。他的脸上就笑了笑。他说在他的脑子里,这个故事已经挂了好几年了。
接着是故事的主要发生地,他起了一个名字叫做洪城。他说洪城听上去要比你的瓦城大得多,而且也更有气势,就相当于你们的广州或者东莞那样的城市,很大,也很乱,走到哪里都是乱哄哄的外来人。
他说的你们,其实是另外的一层意思,可当时我没有听出来。
我就说,我是瓦城的,瓦城不属于广东。
他便闪电一样白了我一眼。
他说我知道,一样!
我心想,知道了怎么还一样呢?但我没有还嘴。
他说我想过要放在你瓦城的,但是,我在你的瓦城里,怎么也找不到发生这个故事的那种感觉。我说没事,这是你要的故事,就让它发生在你的洪城吧。他就又一次朝我笑了笑,还给我点了点头,嘴里轻轻地说了一句,你这人不错。我便傻傻地笑了笑。
再往下,是故事发生的时间,他把它绑在了使用BP机的那个年代。我想了想,觉得也好。那个时候,很多城里人的腰上,都别着那么一个小东西,不时BBB地尖叫着,像山地里那些发情的小毛鼠。
最后边是几个歪歪的关键词,分别是墨镜、计划生育、性、爱情、人性、悲剧。悲剧的后边是省略号点点点。
对我来说,除了墨镜,别的都是一眼就能看穿的,尤其是计划生育,那应该是他换取投资的主要砝码。至于性、爱情、人性、悲剧,那就如同厨师手里的油盐酱醋,没一样是新鲜的。
我把目光退回到墨镜两个字的上边。我问他,那墨镜是什么意思?他猛地就呵了一声,两手狠狠地拍了一下自己的膝盖,把自己从沙发上拍了起来。他说这个特别有意思,我要让这两个男人,都戴着墨镜到洪城去,故事一开始就戴上。说着就钻进他的房间,转身拿出了两副黑麻麻的墨镜来。
那是两副不一样的墨镜,一副是宽宽的,一副却小小的,宽的是我们常见的那一种,街上也到处有卖;小的那副,我可是从来都没有见过。
他晃了晃那副大的。
他说这是给尚海的。
然后晃了晃那副小的。
他说这是给胡男的。
他再次晃了晃那副小的。
这个墨镜你肯定没见过。
脸上晃着几丝得意,得意里又藏着几分神秘。
我摇摇头,我真的没有见过那么小的墨镜。
他说我告诉你吧,这副墨镜是我专门给胡男做的,是我亲手做的,但是,在这个故事里,是胡男自己给自己做的,他用的是他母亲的老花镜做的。你知道他是怎么做的吗?他是用油漆,把里边的这一面给涂黑的。
我觉得奇怪。
我说他为什么要这样?
他说舍不得花钱买呗。
问题是用油漆涂黑了他怎么戴呀?
我说着就朝他长长地伸过了手去。
但他没有急着给我。他说你先别急,你先看看我是怎么戴的,我怎么戴,胡男在电影里到时就怎么戴,你先好好看,看看是不是很有意思。说着他把大的那副递给我,让我帮他拿着,然后,他像一个电影导演在给演员说戏一样,让我好好地看着他。他的意思我明白,看着他就是看着以后电影里的胡男。他的动作很慢,慢到我能看清他手背上的筋脉在抽动。他把胡男的那副墨镜戴上后,手没有马上离开,而是横出两根手指,从他的鼻头慢慢地往上走,然后压在了墨镜的鼻桥上。随后的画面我有点说不清楚了,我不知道是他的手指在把墨镜慢慢地往下拨,还是他的眼睛在墨镜的后边慢慢地往上爬,但爬得不多,就停住了,就像躲在窗台后的两个小偷。
说真话,那副模样挺丑的,丑得有点愚蠢。谁那样戴着墨镜,谁都会同样的又丑又蠢。为什么要让胡男做这样的事情,就因为人家是村上的?
他为什么要这样?我再一次问他。
他没有回答,他的两根手指本来已经放下,这时又抬回了眼前,他指了指脸上的墨镜,示意我再好好地看一看。他说你先告诉我,在电影里,有一个人这样戴着墨镜,是不是很有意思!
我没有回答他想要的意思。
我还是那一句,他为什么要这样?
他的眉头便在漆黑的墨镜上动了动,我知道,他那是对我在暗暗地翻眼,然后,他突然问道:
你是不是觉得你不能接受?
我点了点头。
你是不是想说你觉得这样有点假?
我又点了点头,我说是的。
他便因此忽然愤怒了起来。
他说你们的脑子怎么都这样呢!
说完把脸转了过去,分明不屑于再看我。
我便愣了一下,也就是说,在这个三室一厅的公寓里,因为这个故事,来过别的作家!他们可能是北京的,也可能是像我一样,从别的地方飞来的,但他们也都像我一样,对胡男的这副墨镜有着一样的态度,都给了他一样的脸色。
等到他的脸转回来的时候,我发现他的脸竟是歪的,像他写在纸板上的那些歪字。
他说我们不要讨论这副墨镜合理不合理好不好,因为在这个问题上,我怎么说,你们都接受不了,这样吧,我只告诉你,胡男的这副墨镜,在这个故事里很重要,如果说这个故事是一个人,那胡男的这副墨镜就是这个人的那双眼睛,这是不能没有的。你如果能够接受这副墨镜,我们就讨论下去,你如果接受不了,我就只能另外找人了。
我心里就急急地敲了敲小鼓。我想得最多的,当然是他在电话里说的那个数目。我把那个数目和这副墨镜放一起滚了滚,滚了好几个来回。也许人家花的那个数目,买的就是你对人家这副墨镜的认可?
最后我说好的,那就听你的吧,让他戴着。
他就慢慢地转了转脖子,然后盯着我,慢慢地把脸板正了。
他问真的?
我笑了笑,点了点头。
他的脸却没有跟着我笑,他还在紧紧地盯着我。
他又问真的假的?
我说真的。
他问为什么?
这一次,我哼哼地笑了笑,我说就为了合作愉快呗!你要的故事,不听你的我听谁的?
不仅仅是因为这个吧?
他用三个手指,数钱一样搓了搓。
不是。我摇摇头。
但这样的回答,心里还是有点发凉。
他说这就对了。你要是仅仅为了这个,我会小看你的人格,你知道吗?我需要的是你的真心,你要真心地爱我这个故事,你才能把我这个故事编好,你知道我的意思吗?
我说我知道。
再说了,在这之前,我也跟不少导演合作过,我知道到了最后你还是得听他们的。国外是不是这样我不知道,在国内,基本上都是这样的,否则他们就会换人,为了钱,愿意听导演的人还是很多的。听编剧的导演也有,但是极少。
他重重地就拍了一下我的肩膀。他说看来你是个聪明人,至少在你们这帮鸟作家里,你算得是聪明的。
这一次,他在你们后边还加了一个鸟字!
我心里说,你这个鸟人我估计也不是什么好鸟,如果不是为了那个高额的数目,老子看都不看你这样的鸟人。
他说完就把脸和身子都转了过去,他不再看我。我只好把身子落回到沙发上,心里正想琢磨一点什么,他突然回头吼了一声,走,吃饭去!
我便跟着他下楼吃饭去了。
那一餐,倒是吃得挺好的。下楼的时候,他用手机叫了一个女的带一个女的也过来吃饭,可没有等到她们的到来,他就抓起了筷子。我说不等等她们?他说不用。真的就先吃了起来。我心想这个美国人怎么这点又不像美国呢?可美国又是怎么等吃的,我也不知道,就提起筷子也跟着先吃了。他一边吃一边不停地吩咐我好好吃,叫我多吃一点。他说从明天开始,我们就不再下楼吃饭了,我们得把门关起来,饿了就叫外卖,什么时候把故事谈好了,我们再下楼好好地撮一顿。我笑了笑,我说没问题。他的筷子就又不停地指点着桌上的菜,那你就多吃一点,好好吃。吃到一半的时候,那两个女的到了。他抓着她们的手介绍说,她们都是北京的优秀演员。我只是点点头,我没有去抓她们的手,我只是看着她们,觉得都挺漂亮的,不管是脸还是身材,尤其是眼里流出来的那些笑,可她们都演过什么,我真的一点印象都没有。我以为吃完了他会把她们也叫到公寓去,然后跟着一起把门关起来,可是没有,吃完了他就让她们走人了。他说我们俩要谈一个故事,你们先回去吧,等弄好了再跟你们联系。那两个漂亮的女演员就朝我们笑了笑,像演戏一样,各自在低低的胸沟前,挥了挥她们的小手,然后就转身回去了。
吃饭回来,我们就真的开始了。
为了更容易接近人物的灵魂,这话是他说的,他又拿出了那两副墨镜来。从他的眼神里我能看出,他想把胡男的墨镜给我戴,但我却先开口了。
我说好呀,那我戴尚海的,你戴胡男的。
他的脸色就沉了一下,似乎想问为什么,最后没问,但他伸出了一根手指,在眼前朝我点了几下,然后把尚海的墨镜递给了我。他说我戴也好,等到你写剧本的时候,你就不用再去琢磨胡男戴墨镜的种种样子,你只要记住我是怎么戴的就可以了,但是,我得告诉你,我可没在农村待过,农村人灵魂里的一些东西,我可能不一定都能戴得出来。我没有多嘴。我怕一不小心,那副墨镜会跑到我的脸上。
就这样,两个戴墨镜的男人,在北京三里屯的一家公寓酒店里,编起了另外两个戴墨镜的男人的故事。
故事的开头是他先想好的。他让尚海一开始就注意到了胡男,那是在前往洪城的火车上,让他引起关注的,当然是胡男戴墨镜看人的那副样子。而胡男与尚海的认识,则是到了洪城了。那是他们共同的一个遭遇。从洪城火车站往外走的时候,有一个举着牌子的姑娘,把他们几乎同时拉在了一起。牌子的上边写着“招工”两个大字。举牌的姑娘很漂亮,嘴巴也很甜,她给他们每人递了一瓶矿泉水,就把他们带到了一辆小巴上。然后,她说她还要去接别的人,就转身走了。尚海和胡男以为一下车就得到工作了,就喝着矿泉水在车里等着,可喝完水就睡着了,等到醒来的时候,那辆小巴已经不见了,只剩了他们两个,被丢弃在荒郊的一堵砖墙下。尚海带在身上的钱本来就不多,醒来一摸,口袋空空的了。只有胡男的钱没有被摸走。他的钱藏在内裤的裤裆里,他老婆帮他在那里缝了个小口袋。那个女孩的手可能哪都摸了,就是没有想过要摸摸那个地方。
两个人因此像掉进了一口井里。
尚海离不开胡男了,否则喝水的钱都没有。胡男也不想离开尚海,因为尚海告诉他,他是瓦城的,还读过大学,当过报纸的编辑记者,胡男愿意像兄弟一样,让尚海分享他裤裆里的那点钱。
我说这个开头还可以。
那往下呢?他说往下我想过很多故事,但哪一个都走不下去,而且也都不是太好。
想过顺着胡男的裤裆走吗?我问。
他说想过,就是花掉他裤裆里的那点钱,可花完了呢?我说花掉那点钱算什么故事呢,那种故事一点意义都没有。那你怎么走?他说,胡男的裤裆里,不就那点钱吗?我说不,胡男的裤裆里,不仅仅只有那点钱,还有这个故事里最最重要的东西。
他的眼光便翻到了胡男的墨镜上。
我告诉他,我编故事有一个习惯,就是死死抓住故事里的某一些东西,换句话说,就是抓住点子不要乱动,然后像圆规画圆一样,从四面八方把故事画进来。
他一下就急了,说你别给我啰嗦你的什么习惯,我看过评论家对你的评论,说你最擅长的,就是给你的故事层层加码,最后让你的人物走向悲剧,但是我告诉你,悲剧是我要的,层层加码也没有问题,问题是,你千万不要把我的故事,最后只弄成了一个裤裆里的故事。
我指了指电视机上的那块写字板,让他再看看他要的那些关键词。他马上把胡男的墨镜摘了下来,但我把他给阻止了。我说你还是把你的墨镜给戴上吧,你现在看写字板的样子,就是我想象中的胡男,胡男往下找活路的时候,会看看电线杆上的那些小广告,你摘下了我就看不出他的表情了。
他就白了我一眼,把墨镜乖乖地戴了回去。
我示意他好好地看看第二个关键词,那是计划生育。我说你把计划生育放到胡男的裤裆里去想一想,看看能不能想出什么故事来。
他看了又看,看的样子真的是丑死了,明明是需要抬头的,可他却不得不把下巴往下扣,好让目光从墨镜的上边翻出去。他盯着计划生育看了好久,似乎没想出什么,就只好回头看我,我没有等他开口,就又挥挥手,请他再好好地看一看。他没有把头转回去,他只看着。他说那胡男是因为计划生育才出来的,我们又把计划生育放回他的裤裆里,你什么意思?我说那你先这样想想吧,他出来的目的是什么?打工呀。打工又是为了什么?为了钱呗,不说了是为了超生罚款吗?
我停了停。我说如果我们真的让他去打工挣钱,那是最没有意思的,最好的办法是,让他不用打工也能挣到钱。
他说这跟裤裆有什么关系?你不会是想让他杀人放火抢银行吧?那我可告诉你,你想都不用往那些地方去想,那不是我要的故事,也不是他们要的故事,他们要的故事必须是因为计划生育而发生的故事,你只能给我死死地往这里想。
我说对呀,我就是往这里想,要不让你钻进他的裤裆里去干什么呢。
他的双手便在空中不停地晃了起来,他说得得得,那你就说他的裤裆里还有别的什么故事吧,只能跟计划生育有关的,别的你就不要给我啰嗦了。他急得差点又要把胡男的墨镜给摘下来。
他急他的,我不急。我说好,抢银行的故事你们不要,真的让他去打工又不是我喜欢的。我先告诉你我喜欢什么。你喜欢什么。我喜欢意外的故事,因为只有意外的故事才是最好看的。他的双手就又挥过了头顶。
我说好好好,那我就告诉你吧,我们可以把胡男裤裆里的东西给阉掉。
他的双手便在空中停住了。
阉掉?他像被撕掉了一块肉一样惊叫。
我点点头,我说对,同时还可以让他挣到钱!
他把墨镜一把就摘了下来,眼鼓鼓地盯着我。
阉掉他裤裆里的东西,同时还能让他挣到钱?
我没有急着回答他,我只是指着他手里的墨镜,让他戴回去,我说别忘了你现在是胡男,我现在想看到的是胡男愤怒的时候会怎么样。他扬起墨镜就要摔到地上,但最后还是乖乖地戴了回去。很难想象,玩笑有时候也可以征服一个人,而且还是一个有点牛逼哄哄的美国人。
也许是他心里有点急,或许是我的说事方式让他有点烦,这一次,他的眼光翻过墨镜的样子更加丑陋。以至于我当时就想,如果胡男真的这样自己给自己丢人现眼,他的结局就应该是死在洪城。只是当时距离结局还很远,他得先活着,得先把他裤裆里的东西阉掉再说。
我告诉他,我下乡参加过计划生育工作队,把裤裆里的东西阉掉,是我们工作队的一项工作任务。
他说这我知道,阉掉裤裆里的东西是他们的义务,阉了就阉了,好像没有给钱,你说他怎么还能挣到钱呢?
我说是,义务是没有钱的,阉完了就回家,而且也不是什么大手术,听说有胆子大的,当天晚上就试着跟老婆睡了,说是照样能把老婆睡得叫吱吱的。但是有的人,而且不少人,是不愿去完成这个义务的,他们不愿意去挨这一刀,他们想留着,他们不想动。所以,他们就在私下里花钱,找人顶替他们去阉,有出三千的,有出五千的,有些有钱的甚至出到一万以上。而且这种事,已经成了一种黑市生意了。
不会吧?
他突然就激动起来。
我怎么没听说过呀,太荒唐了吧!
我笑了笑,我说比这荒唐的事还多的是。
那你们工作队不管?
工作队里都有人私下里参与,还有医院的医生,要不怎么会有这种事。
假的吧?你可别瞎编来糊弄我!
我说这是真事,不是假的!我很认真。
他冷静了一下,很快就兴奋了起来。他狠狠地拍了一下自己的膝盖,又把自己从沙发上给拍了起来。他一激动就喜欢这样,像一头发情的公猪。他说好,太好了!那我们就让他们挣这个钱吧,怎么挣?
我说不,阉胡男就可以了,尚海不能阉。尚海是知识分子,他也不会让自己去做这样的事情的,再说了,你让知识分子在计划生育中被阉掉,那会阉出另一种东西来,而那种东西也不是你这个故事想要的东西。但尚海可以是把胡男阉掉的合作者,是他说服了胡男去阉的,而且一而再的去阉。每次阉完胡男,他都把手长长地伸到胡男的面前,让胡男把答应给他的钱给他。
他说可以,这个画面不错,也算是当下那些小知识分子的一种无奈与堕落吧。我笑了笑,心里说是的,这种无奈与堕落常常是无处不在的,作为一个作家,我拿兄弟同胞们的生存短处,来帮你给他们编这种故事,又何尝不是一种无奈与堕落呢?
随后,在洪城的一根电线杆下,我们让他们在找工作的时候,碰到了一个人。那个人是张贴狗皮膏药小广告的。他看上了他们。他们看上了他。裤裆里的故事就这样开始了。
头一次打开裤裆,顶替别人挨刀,我们决定先给他三千。第二次再给五千,第三次可以考虑更多一点。头一次三千虽然有点少,但胡男听了尚海的说服后,还是接受了,因为找工作还是挺难的,弄不好一个月都得不到三千。再说了,只要有钱交了罚款,保住了老婆肚子里的男孩,以后就不用再考虑生孩子了,那么这裤裆里的东西也就无所谓了,况且,这东西迟早也是要被计划生育阉掉的。
谈完了这段裤裆里的故事,夜已经很深了,但在后来的后半夜里,他几乎都兴奋在这个裤裆的故事里。他说故事要高于生活,真的首先要来源于生活,真的!我要是有这种生活,我早在美国就完成这个故事了。说完脱下墨镜,露出了一种少见的笑。他说找你真的是找对了,真的找对了!
我只是笑笑的。那种笑,在整个故事的讨论中,其实是一种对付性的傻笑。我跟别的导演也合作过,他们的话,真真假假的,你不可能真的全放在心上,真放了你就真的傻了。说白了还是那句话,我是冲着可观的酬劳而来的,毕竟,比起辛辛苦苦地写小说,这要挣得更容易,而且也多得多。
有点堕落是吗?
但我心里明白。
第二天早上,我还没有起床,他在他的房里就吼了过来,他说下边的故事你想好了没有?听声音他的身子也还横在床上。我说还没有起床呢,想什么想。他像是没有听见。他说告诉你,你不能阉完了,让他得了钱就回家去了,那可不行,这个故事你得给我主要放在洪城,农村的戏多了不好看,人家也不会喜欢。
我说我知道。
但他还是没有起床,他继续横在床上对我说,我们把胡男阉掉了好是好,可我们还只是阉出了荒诞而已,或者叫做阉出了荒唐,我们还没有让他阉出悲剧来,往下走如果能让他阉出悲剧,那这个故事就高级了。
他不起,我也不起,我们继续横在床上。
我说你是不是想让胡男不停地阉下去,一直阉到他裤裆里的东西完全烂掉,或者让他们在洪城成立一家代阉公司,越做越大,最后被丢进大狱,震撼全国,轰动世界。他说不不不,那种故事太低劣了,我如果要那种故事,我不会找你,会编那种故事的人,北京多的是。
其实我知道他想要的是什么,我说你是不是想把胡男老婆肚子里的小孩给做掉?他说对对对,我就是这样想的,洪城这里,胡男为了孩子的罚款,刚刚把裤裆里的东西阉掉;瓦村那边,因为计划生育,他的孩子没有了,可以是被打掉,也可以是怎么流产了。
这样的故事当然是悲剧的,但我却告诉他,胡男老婆的事现在还不能动。他说那动什么?我说我们得编编尚海的故事了,否则这两个男人故事就得不到平衡。
他就又对对对的喊叫了起来。他说那我们起来讨论尚海的故事吧。我说你还是先叫外卖吧,饿着肚子,故事是出不来的。
他马上就拨通了一个外卖的电话,先是大声地点了一份回锅肉,然后又吼着嗓子要了一份子姜炒鸭。这两份菜,也都是胡男顶替别人做完手术后,我们让尚海给打的两份菜。尚海吃的是回锅肉,胡男吃的是子姜炒鸭。
但我不吃回锅肉,我把子姜炒鸭抢到了手上。
为了让我能把戴墨镜的胡男写好,吃饭的时候,他也自觉地戴上那副墨镜。他戴我自然也戴,舒服不舒服,已经不在乎了。
回锅肉和子姜鸭还没有吃完,尚海就在故事里开始倒霉了。首先是他腰间的BP机,突然响起来了。
BP机我们只配给了尚海,胡男我们不给,给了也没用,他的瓦村家里也没有电话。
尚海的BP机,是他老婆给他买的,而且就在出门的前一天,她想有事的时候好寻呼他,让他尽快跟她联系。那个女孩把他身上的钱都摸走的时候,为什么没有摸走BP机呢?那时候一个BP机好像也不太便宜,她要是摸走了,应该也能变卖几个钱。但我没有提醒他,因为BP机也是这个故事的关键词,我不想去动他的。真要动也不难,胡男给他分钱之后,又买了一个也就解决了。
尚海的老婆要他马上回到瓦城,她说你如果不马上回,我就把你的孩子从我的肚子里打掉。好像那个孩子只是尚海的孩子,而不是她的孩子。
女人不能孤单,孤单就容易愤怒!
尚海吊着脑袋,给胡男这样解释他的妻子。
胡男说那你就马上回去吧,你出来不就是为了孩子吗,如果孩子没有了,你出来就一点意思都没有了,你回去吧。尚海就决定回去了。
走的时候,我们让胡男数了数阉裤裆得到的那点钱,最后他数出了三千,后来我们觉得少了,就又让他数了一千,一共四千。他让尚海回到瓦城后帮他跑一趟瓦村,把钱先交给他的老婆,也好让老婆安安心,他怕他的老婆也会像尚海的老婆那样,如果哪天孤单了,也会想到要把孩子打掉。关于那四千块钱,我们还让他犹豫了一下怎么处理。他先是吩咐尚海,让他老婆先把那四千块钱交给村长帮拿着,因为四千是他们那里超生罚款的一半,他说交给村长的好处是,上边有人来查超生的时候,村长就可以帮他先说说话,但他又担心老婆拿去交给村长的时候,村长会不会乱摸他的老婆。他对尚海说,他们的村长色得要命,村里的女人,他看到哪一个都会流口水。最后他说算了,让我老婆收好就行了,等我回去再交给村长吧。可他哪里知道,按照这个故事的走向,我们是不会让他回到瓦村去的。有时我就想,这样的故事,是胡男那些人的命运的悲剧呢,还是我们这些编故事的人的灵魂悲剧?或者,是别的什么悲剧。
尚海就这样回家了,刚一进家,我们就让他看到老婆的肚子平平的了,他一看就傻掉了。他没有想到,他老婆是叫他回家离婚的。不知什么时候,她已经偷偷爱上了一个有钱的男人了。那个男人也说爱她,他答应跟她结婚,但有一个前提,就是必须把尚海的孩子打掉。于是她就把尚海的孩子从身上拿掉了。尚海摘下BP机让她看,他说你呼我回来原来是为了这个?就把BP机摔碎在了地上。他还想狠狠地揍她一顿,但她却不怕,她让他打,她站在他的面前,全身的皮肉抖都不抖。她说如果你是为了你的孩子,你就打吧,但我告诉你,你的孩子要是留下你能养吗?你说你能养吗?我打掉这个孩子不光是为了我,也是为了你,你知道吗?如果是为了爱情,你最好别动手,因为我们本来就没有什么爱,我们认识才半天,你就把我给睡了,我是怀了孕才不得不跟你结婚的。
女人这么一说,尚海就瘫掉了,但他咽住了哭声,他只让眼泪哗哗地流着。他转身就跑到瓦村,给胡男的老婆送钱去了。
胡男小孩的事,我们决定就放在这里。
胡男的老婆当然跟尚海的老婆一样,尚海看到她的时候,她的肚子也是平平的。他当时怀疑,她不是胡男的老婆。
女人说是,我是胡男的老婆。
尚海说那你肚子里的孩子呢?
她忽然就哭了。
她告诉尚海她流产了,而且胡男出去打工还不到一个星期。那是一个晚上,天其实都快要亮了,一辆大巴车突然停在了他们的村头。那辆车是来拉人去做结扎和引产的。以前是白天来,但白天碰不到人,他们的车子往往还没有停下,村里的人就早早地躲去了。后来就改成了晚上来,而且是后半夜,这个时候的人容易睡得像死了一样。可是他们哪里知道,人睡了,狗却一直醒着。胡男的老婆一听到全村的狗都在叫,就知道是计生工作的来了,就急急地往外跑。她说那条路她其实是很熟的,她闭着眼睛都能跑过去,可她没有想到,那天晚上他们选了一个下雨天,路好滑好滑,她只跑了一半的路,就滚到一个深深的沟里去了。
她的孩子就在那个深沟里没有了。
故事谈到这里,他突然把墨镜按了一下,把眼睛完全地露了出来。他盯着我。
他问,这种事会真的有吗?
我忽然觉得有点奇怪。
我说你不是不在乎故事的真与假吗?
他说不,就这事,就胡男的老婆流产这个事,你告诉我,是真的会有吗?
我点点头。我说我参加计生工作队时,有几次就是天快亮的时候开车到村里的,选的也是下雨的天。
他说,我说的是胡男老婆的事。
我说也会的,因为她知道,她老公出去打工,就是为了她肚子里的孩子,所以为了孩子,再大的雨她也不怕,除非天上下着刀子。
他就慢慢地把墨镜推回到眼睛上,然后一只手伸出来指着我,记住,他说,写到这里的时候,你要让尚海突然号啕大哭。他的孩子没有的时候,他只是哗哗地流着泪,但这个小孩,胡男的这个小孩,一定要让他号啕大哭。
我没问他为什么。
我只是默默地点了点头。
胡男的孩子这么一死,胡男裤裆里的悲剧就越来越大了。这是他要的,也是他们要的,所以,他觉得很好,而且相当好。我也觉得不错,因为人家要的就是这样的故事,你不这样帮人家走,人家的故事怎么去震撼人家的观众呢。
可是往下的故事,我们却走不动了。
因为起床起得晚,我们吃完了外卖,时间就过了中午了。晚上,我要了一份苦瓜牛肉,还加了一个乌鸡汤,他要了一份茄子,也点了一个乌鸡汤,但在整个吃的过程中,一个故事都吃不出来,一直到吃完,把饭盒丢进了垃圾桶,故事还一直停留在尚海的号啕大哭那里。
乱七八糟的故事,从他的嘴里倒是出来过不少,但都被我给他塞回去了。他说的那些故事,都是从外边乱加进去的,并没有从人物出发,或者是从故事的核心出发,也就是圆规画圆时的那个点。我说你不能离开那个点去乱画,你一乱画,那个圆就不是那个圆了。一个故事的好与坏,往往就区别在这里。
他说你也不能光是否定我的呀,否定我的也可以,你得拿出你的故事往下走呀。我说我的脑子白天不好用。那你的脑子什么时候最好用?我说一般在天黑以后,最好是深夜。他说靠,等到天黑可以,等到深夜就死人了。
要不我们到外边去走走,我说。
他的手马上就挥过了头顶。他说不行,说过关起门来讨论的,就得真的关起门来讨论,我把我们上一餐丢的饭盒,都让外卖帮拿下去丢了,你没看到吗?
每一次让人帮丢饭盒,他都给了一块钱。
我只好靠在沙发里坐着,动也不动。
他不坐,他在屋里不停地走来走去,还不时地脱下胡男的墨镜在手里晃着。他说胡男老这么戴着,其实也挺难受的。他把墨镜递给我,让我试一试。我不试。我连手都没有伸出去。我怕接下了就回不去了。
他说真的挺难受的。
于是他建议,往下走的时候,在故事的后半段,能不能让胡男把墨镜换掉。我说那就让他去买一副呗,他不是早就有钱了吗?他说可以,但随即又说不行,农民嘛,他还是舍不得买的,除非在故事里让他碰着了不花钱的墨镜了。只能是不花钱的,否则我们不能让他乱脱。
但故事还是走不动。
天都黑了很久了,故事还停在尚海号啕大哭那里。
故事当然不能再跟尚海走了,就是让他马上回到洪城,他又能有什么故事呢?他就是有故事,也必须是和胡男有关的故事,否则,故事就会跑到圆规的圆圈之外。
那就只能在胡男身上找故事了。
然而胡男是不能再阉了的,阉两次阉得好也还能看,如果阉三次四次,那就等于白阉了。
不能再阉的胡男,又该有什么故事呢?
让他去找别的工作?那还不如再阉他一次。
就是这样,故事怎么也走不动。
其实,走不动的原因,是我们只顾低头往故事的墙上撞,而忘了抬头看看写字板上的那些关键词,也就是回到最初想要的那些点子上,然后看看都完成了什么,还有什么还没有。
一直到了后半夜,我才想起了这个来。我说上边有一个字,我们是不是一直没有动过。他问我哪一个字,我说性。他就把头抬了过去,随即就把自己从沙发上狠狠地拍了起来。他说对呀,他们最爱的就是这个东西了,我们怎么把这个给忘了呢?没有这个东西,就像菜里没放盐,怎么吃呀!
我们的情绪就又活起来了,好像有关性的故事,都跟我们自己有关似的,我们都认真地把各自的墨镜戴回了脸上。当时我们两个,就像准备潜水的两个男人,然后猛地一扎,就深深地潜入了胡男的裤裆深处。
我们很快就给胡男找到了一个女人。
那是一个单身的女人,有钱,养着一只小狗。
为了让胡男尽快地摆脱那副难受的墨镜,我们让那只小狗也戴着一副。那小狗的墨镜当然是真正的墨镜,而且质量不是一般的好。有钱的女人嘛,她的狗就是她的亲人。那只狗的身子很小,但是它的头却很大。这一点我们是为了胡男着想的,因为那只小狗的墨镜,我们要在后边戴到胡男的脸上。
那是一场巧遇。
我们让胡男和那只小狗,同时出现在洪城的一条小街上,还有那个女人。他们的头上,太阳很好。他们的身上全都是阳光,就像梦中的黄金在流淌一样。
那只小狗没有牵在女人的手里,它只跟随在女人的四周,自由自在地玩耍着,有时离她很近,有时又离她远一些。
胡男看到那只小狗的时候,没有看到那个女人。他是被小狗脸上的墨镜所吸引,而且走的又是一个方向,就一边走一边看,一直没有收眼。他觉得好玩,他从来都没有见过狗也戴墨镜的,连想都没有想过。几个嘻嘻哈哈的小伙子,这时也注意到了小狗脸上的墨镜,他们是迎着小狗走过来的,其中一个就不停地指着小狗,走到小狗身边的时候,他突然飞起一脚,就把那只小狗踢飞到了空中,落到了边上的一个泥塘里。
这样一来,马上就有戏了。
那个女人跑过来了。她没有去追那几个小子。那几个小子也早就跑远了。那女人只是看着泥塘里的小狗,呼天抢地地喊叫着。泥塘边上的人很多,但没有人帮她下去把小狗救起来。他们只是热闹地看着。
后来是胡男跳了下去,把小狗捧了上来。
小狗一身脏兮兮的,女人碰都不敢碰。
她对胡男说,你能不能帮我抱回去。
胡男说可以,就跟在了她的身后。
后边的故事就自己走路了。
胡男帮那女人把狗洗得干干净净的,女人看了就很感动。她看着胡男也忙得脏兮兮的,就说你也洗洗吧。胡男说不用。她说洗洗吧。又说,洗完了把你的衣服也全部洗一洗。我帮你洗吧。她告诉他,她的洗衣机是可以烘干的,不到一个小时你就可以穿上了。她还拿出了自己的睡衣给他,让他洗好了先穿着。
有钱人的睡衣就是好,谁穿在身上都是好看的。
胡男从里边刚刚走出来,女人的眼睛就看呆了。
她看见胡男腰上的带子没有系好,就示意他再好好地系一系,可胡男还是怎么也系不好,她就上来帮他了,这一帮,她竟自己扛不住了。她先把脸悄悄地贴在了胡男的背上,她在等着胡男的某种反应。但胡男却被吓懵了。胡男没有动。胡男的反应只是在胡男的肉体里。最后还是她自己扛不住。她伸手突然就搂住了胡男的腰,而且搂得紧紧的。
就这样,我们让她把胡男给弄到她的床上去了。
故事编到这里,就停不下来了。我们两个就你一句我一句的,用我们的嘴巴,让那女人和胡男在床上忙了起来。他说,那个女的肯定先拿出了安全套来。我说,胡男只看了一眼,马上说,不用!那女的就说不用不行的,我怕怀孕。胡男就说不会的,你不会怀孕的。她就说怀孕不怀孕只有女人才知道,你们男人是不知道的。胡男就指着阉过的地方给她看。他说他已经做了计划生育了,而且是刚刚做的。她就摸了摸他的伤口,然后问他,那你还能用吗?胡男说不知道。她说那你阉完了你没用过吗?胡男说没有用过。她说要不你试试吧?胡男说试就试。她把安全套往地上一扔,俩人就试了起来了。
结果当然是能用,而且把她用得嗷嗷直叫。
我们还决定,在这里插一块小料,我们让她的小狗也被她的嗷嗷叫给吓了一跳。小狗以为她的主人遇到了不幸了,远远地就往她的床上扑了过来。当然,我们不会让小狗坏了他们的好事,我们让它最后把头贴在主人的枕头边,只是眼睛斜斜地看着满头大汗的胡男。它好像知道他在忙什么,又好像不知道。它一直看到胡男最后翻倒在主人的身边。
完了他又让他们来了一次。
我说再来就没什么意思了,反正就那么一点破事,电影里也不怎么好拍。问题是那个女的肯定不会让他马上走,他说,胡男刚要翻身下床,那女的把他拉住了。她说你的衣服还没有洗好呢,你没听到洗衣机还在响吗?她说可能正在帮你甩干。这个时候,电影里就可以空放洗衣机的声音,或者是洗衣机在镜头里洗衣的样子。那洗衣机的前边是透明的,看得见胡男的衣服在里边滚来滚去。
说完他摘下墨镜笑了笑,好像他就是那个胡男似的。
胡男走的时候,我让那个女的给了一百块钱,他说一百太少了,应该给三百四百,或者五百六百,那样就可以显示那个女人有钱,还证明她是真的感谢他。我说这又不是美国故事,中国故事是不会给那么多钱的。最后我们达成了合议,先给胡男四百,算是两个事,一事两百,但她只是把钱塞给他,没说是因为狗还是因为她。胡男推了两三下就收下了。
下边有段对话,对故事的流动,我们觉得至关重要。
胡男准备开门往外走的时候,那个女人的手忽然又摸了摸他的脊背。胡男的身板是真的好,平稳厚实,力量充沛。那女的忽然问道,你是来洪城打工的吧?胡男说是。她说那你在打什么工?他说还在找。她就在他的背上温柔地搓了好几下,搓得胡男麻酥酥的,又不敢把脸转过来。然后她说,那你别找了,你就当是来我这里打工吧,想来了你就来,每次来我都会给你钱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吗?胡男看了看还握在手上的钱,脸色兴奋起来。他点了点头,没说明白,也没说不明白。
第二天,胡男就敲开了她的房门。
他真的把这当成了打工挣钱的活了。
但我忽然有一点质疑。我说你觉得会吗?他说会,怎么不会呢?是我我都会。他说我告诉你吧,我有个很好的朋友,他在美国就这么干过。有什么呢?不就睡嘛,还能挣钱,为什么不做?
然后把眼光从墨镜的上边翻出来,死死地盯着我。
于是,我们就给他们设定了一些规矩和场面,比如那个女的从来不请他吃饭。他就是在吃饭的时候来了,她也不叫他吃,她只叫他看电视等她。每次给钱的时候,胡男总是在她的面前呆呆地站着,眼睛只盯着她手里的钱,就像街边那些打零工的,在盯着老板给他结算工钱。
我说真要让他把这当作打工,那就意味着他要天天来,可天天来的戏可不好写。他说那是你的事,到时你可以重新安排、重新结构,我们现在可以先把他们的事情全部谈开。只要是男人和女人的事,他就来劲,如果不让他谈,估计他会十分难受。
他所说的把事谈开,指的就是先把故事给说通了,说合理了,然后再把我们要的东西放进去。
比如这个女人为什么喜欢胡男,与爱又没有关系。
我们谈开的结果是,让那个女人自己开口问了胡男,她说你知道我为什么喜欢你吗?问话的场地可以是躺在床上,也可以是坐在沙发里。胡男的回答是不知道。她就告诉他,因为你是一个被阉过的男人。胡男就有点吃惊。他说为什么?因为你被阉过,所以你跟我做爱就不用那个讨厌的安全套啦。她说她不喜欢用安全套。她说那根本就不是跟男人在做爱,而是跟橡皮在忙来忙去,一点味道都没有。橡皮的味道是什么味道你知道吗?她问胡男。胡男傻傻地笑了笑,他说橡皮我知道呀,我给我女儿买过。她就尖叫起来,你女儿多大呀?他说刚刚读一年级。什么一年级?小学。小学一年级你就给她买这个呀?她用得着吗?用得着呀,她写作业写错了就得拿橡皮来涂来涂去,我都给她买了好几块了。她就哈哈地大笑起来,她说我的天呀,我以为你给你女儿买的是避孕套呢!
至于如何把我们要的东西放进去,这个也不难。
第二次来,我们就让那个女的告诉胡男,她要把小狗的名字给改了,而且改的是胡男的名字。在这之前,她没问过他的名字。胡男一听脸色就变了,像是被人在头上泼了一瓢粪水,有点受侮辱了。他问她为什么?她说因为你是它的救命恩人呀,如果没有你,它就死在泥塘里啦!他说我那是可怜你,不是可怜它。她说一样的,我就是它,它就是我,它是我的心肝你知道吗?把我心肝的名字改成恩人的名字,这多么好呀!他的脑子还是怎么也过不去。他说改成人的名字不好吧,你想想你跟它出去,你喊它的时候喊的是我的名字,别人听了也不好的。她说这有什么不好呢,再说了,也没人知道那是你的名字,也没人认识你,有人认识你吗?反正她死活就是要改。她说快说快说,快说你叫什么名字嘛。缠得胡男没有办法,但他却突然想起了尚海来,他想尚海那样回去肯定是不回来了,心中不由突然一笑,就把尚海的名字告诉她。她就捧起小狗,不停地叫唤着尚海尚海尚海,她说宝贝宝贝,你的名字以后就叫做尚海了你听到没有?尚海!尚海!尚海!
随后,我们又让胡男耍了一个小心眼,把小狗的墨镜也换到了自己的脸上。他对她说,我们村上有一个习俗我想跟你说一下。她说什么习俗你说吧。他说,在我们村上,如果有一个小孩,碰着了什么不好的事,被吓着了,然后家里就得去找一个爹给他,如果女的就找干妈,找好了就拿一些东西去拜访,拜访完了,干爹也要送些东西给那小孩拿回去。我的意思是,双方都得拿点对方的东西,这样以后也好有个牵挂。那女的听得有点糊涂,她说你想说什么,你直说嘛。胡男就说,我的意思就是,你看吧,我把我的名字已经给了你的宝贝了,那我想在你的宝贝身上要一样东西,要不换也可以,你看可不可以。她说你想要什么?他说墨镜,我想要它的墨镜,换也可以,把它的给我,把我的给它。
那女的看了看胡男手上的墨镜,觉得他的墨镜小小的,给她的宝贝戴在脸上也还可以,就说想换你就换呗。胡男就扑到小狗的身边,摘下了那副漂亮的墨镜,随即就戴到了自己的脸上。至于他的墨镜,他知道肯定不能戴在小狗的眼睛上,于是就用了一根小绳子,绑在小狗的脸上,让墨镜挂在小狗的眼睛下边。然后,他告诉她,以后小狗脸上的墨镜,就一直这么挂着就可以了,千万不要戴到它的眼睛上。他说它为什么被人踢到泥塘里去,你知道吗?就是因为你给它戴在了眼睛上,谁看了心里都不会舒服的,因为他们自己都没有戴呢。再说了,你不就是为了给它弄个样子吗?就这样挂着就可以了,这样人家看了也不太往心里去,因为小狗还是用狗眼在看路,而不是用墨镜在看路。她觉得也对。他就又告诉她,我给你说实话吧,我这墨镜是看不见的,你要是真的给它戴上,它马上就会发疯的。她说为什么。他就告诉她,他的墨镜是他自己用油漆涂黑的。她问他你为什么要这样。他说村上人嘛,他怕来到洪城后,城里人会从他的眼神里一眼就看出是村上的。她就觉得也是。她说来打工的和城里的,就是不同,真的一看眼神就能看透了。她因此夸了胡男一句,她说你这个农村人还是很聪明的。胡男没有再多说什么,他想的只是他天天来的事。
但我们是不会让他天天来的,天天来的戏也不好看。
这一天,她的姨妈来了,但胡男已经敲开了她的房门。她于是对他说,我们两个以后可能要改一改,不能你想来了你就来,我知道你是可以天天来的,可是我不行,我们应该改作我想你了你再来。胡男就觉得有点啰嗦了,我怎么知道你什么时候想我呢?她说那你就一个星期以后再来吧,到时我给你配一个BP机,BP机你知道吗?他说知道。我给你配一个BP机,我想你了我就呼你,看见我呼你了,你也不用找电话打,你直接过来就行了。他点了点头。那你今天不想吗?不想,想也不能要。那我走了。走吧,随便找找别的什么零工做做也可以。胡男就转身走了。那一天她可能不给胡男付钱,但我们谁都没有提起。
后边的故事,就是顺水推舟了。
我们让尚海回到了洪城,但不让他说出他的小孩没有了,也不说自己的孩子,离婚的事他也不提。他的回来,其实是为了帮助我们,把胡男尽快地推进火坑的深处。悲剧嘛,就是这样,曹雪芹是这样编的,褔楼拜也是这样编的,卡夫卡也是这样。
尚海一回来,就发现问题了。
首先是胡男脸上的墨镜。他发现胡男看他的时候,再也不是原来的模样,而是昂首挺胸的了。这一点我们没有让他问他,因为他知道胡男有钱了,换一副墨镜不算什么。可是BP机呢?他发现胡男也有了BP机时,心情是有点落差的,因为他的BP机已经没有了。于是他问胡男,这个是那个小子给你买的,还是你自己买的?胡男说是我自己买的。他就说那个小子后来还找过你吗?胡男说找过,找了好多次,但我只去过一次,后来我就再也不去了。他看见我不理他,就不再找我了。尚海就呵了一声,他说你知道吗,我其实挺担心你的,我担心我不在这里他会不停地乱找你,我怕你不懂拒绝,我怕你不停地给他接活,最后把你给弄残了怎么办?胡男笑笑的,他说不会的。尚海就问,那后来你都做什么呢?你是不是找到了什么活了?
就在这时,我们让胡男的BP机响了起来。
时间可以是晚上十点左右。胡男没有回答尚海他找到了什么活,他说他有事,他要马上出去。尚海却拉住他,他说什么事这么晚了你要出去。胡男就笑笑的扯了一个谎。他说那个BP机不是他自己买的,是前几天一个老板送给他的,那老板有一个货场,几乎每天都有货要装卸,他说他是在街上找活的时候碰着他的,那老板觉得他干活干得挺卖力的,就送了他这个BP机,说不管什么时候有车来了,或者需要装,或者需要卸,就随时呼他。尚海问他什么货呀,不会是毒品吧,人家要是深更半夜的叫你去帮接运毒品,你就死定了。胡男说不是毒品。他说真的只是上车下车的活,累是累点,但老板挺舍得给钱的。他叫尚海你放心吧。但尚海就是放心不下。他跟着胡男一起走到了街上,然后对胡男说,那你去你的吧,我去吃一碗米粉。但胡男没有走远,他就偷偷地跟在了胡男身后,一直跟到那个女人的楼下。那个女人的楼下停有很多车,但没有一辆是在等着装卸的。
附近,也没有任何货场。
尚海就睡不着了,他等着胡男的回来,然后劈头就说:你骗了我!他让胡男告诉他,到底做什么去了?胡男不说。他就说,你是不愿说还是不能说。胡男说不是不能说,也不是不愿说,是不想说。尚海说,你要是不肯告诉我,等哪天你再去的时候,我就去找警察报案,我带着他们到那里去抓你。
这一说,胡男就有点怕他了。他说他也睡不着,他想去吃一碗米粉。就对尚海说,你如果跟我一起去,我就告诉你。俩人就吃米粉去了。
米粉吃到一半,尚海就吃不下去了。
他说那你不是挣了好多钱了?胡男说是,挣了不少,跟打工可能差不多吧,也许还要多一点。看着吃得满面红光的胡男,尚海有一种说不出的难受,是那种失落后的难受。
那女的是不是很难看?他突然问道。
胡男却摇摇头,一脸笑笑的。他说挺好看的,比我老婆还好看。尚海说你老婆挺漂亮的。他说我老婆是漂亮,可她比我老婆漂亮多了。你是因为她有钱给你,你就说她漂亮吧?不是,她是真的漂亮,你要不信,明天早上我带你到洪城公园偷偷看她一眼,她每天早上都会去那里散步,但我只能在远处偷偷地指给你看,你要是想看清楚点,你就自己走到她的身边去,反正她也不认识你。她真的很漂亮,你见了你可能都会想。
尚海摇摇头,说我才不会呢。他说我现在对女人一点兴趣都没有。胡男不信,他说那你这次回去没跟你老婆睡觉?尚海就严肃了起来,低着头,晃了两晃。他说我碰都懒得碰她。但胡男依然坚信,你要是见了那个女的,你会觉得她很漂亮的,明早你就知道了。
故事因此又深入了一个台阶。
或者说,是我们找到了一个套子,把尚海也装了进去了,因为只有他,才能尽快地把这个故事带到我们想要的深处。另外,还达到了一个小小的目的,尚海会在洪城公园听到那只小狗的名字。但他如何走近那个女人,如何听到她呼唤小狗的名字,这个情节我们没有讨论,我们觉得也不需要讨论,因为太简单了,情节中也没有什么需要通过讨论来突破的,我们就一脚跨了过去了。
可是就在这里,我们突然发现了一个问题。我们觉得,那个女人付给胡男的那些钱,应该有一半左右是假钱,因为都给真钱是不真实的,当然,如果都给假钱也是不对的。
可这个假钱是如何被发现的呢?
我们的讨论在这里出现了两条路。
一条是常规的,一条是反常规的。
常规的比较自然,听上去也比较合理,但故事相当一般。就是尚海从洪城公园回来之后,狠狠地就给了胡男一脚,然后大骂胡男,怎么可以把他的名字放在了那条小狗的身上。他觉得胡男这事做得太过缺德,也做得太没有良心了。他让胡男给他一千块钱,作为精神补偿。刚刚从瓦城回来,他身上还是需要钱的,得一点是一点,总比没有强。胡男想想也有点过意不去,就拿出了那个女人的钱,数了五百块给他。那女人给的钱,胡男一直紧紧地收藏着,一直没有动过。他告诉尚海,他花的一直还是阉裤裆时得的钱。他没有把这两种钱混在一起。他觉得这样心里比较安妥。尚海看见那女人给的钱挺多的,想多要一点,胡男就是不给。尚海又给了胡男一脚,就拿着五百块钱出去了,没想到买东西的时候,被人发现那五百块都是假钱,差点被人给打了。尚海愤怒地告诉了胡男,胡男不信,就上街买回了一个验钞器,像打火机似的那一种。然后把藏着的那点钱,一张一张地验过。结果发现,差不多一半都是假的,就拿着假钱找那个女人去了。
而如果反常,那就很有戏了,就可以在人物的内心深处,挖一个很隐秘很隐秘的坑,然后让人物深深地掉到那个坑里去,去接受人性的某种最最庸常的煎熬,或者叫做考验。也就是说,尚海在洪城公园看到那个女人后,心里忽然就乱了起来了。胡男的那句话他没有忘,他说你见了你可能都会想。尚海发现自己是真的想了。他想他要不要也去试一试,看看那个女人会不会对他更感兴趣。于是就悄悄地跟随在那个女人的身后,一直跟到她拿出钥匙准备打开房门。
当然,他没有让她发现他。
他也不会让自己那么着急。
他需要自己再好好地想一想。而想的结果是,他在街上买了一个BP机,跟胡男腰上的一模一样,也就在那天晚上,他把胡男的BP机,偷偷地换到了自己的手上。第二天,他匆匆地告别了胡男。他说他不再回来了,他要自己找工作去了。胡男还因此给了他一点钱,虽然给的不是太多,但那些都是从他的口袋里数出来的,那是他阉裤裆时得的钱。尚海当时还是有些感动的。但感动之后,就到洪城的大街上游荡去了,但一整天他都没有走得太远,他一直在等待着BP机的振响,一直等到了天黑。
那女人打开房门的时候吓了一跳。
她说你是谁?尚海晃了晃手里的BP机,他说他来不了了,他回乡下去了,这是他留给我的。那女人拿过BP机看了看,又放回到尚海的手上。她知道那是她送给胡男的BP机,上边留的也是她的呼号。她说那他回去了就回去了,你来干什么?尚海说,是他叫我来的。
他叫你来干什么?
他说只要我拿着这个BP机来找你,你就会知道他是叫我来干什么的。
他是这么说的?
是的,他是这么说的。
说完尚海又补充了一句:
他来你这里的事,他都跟我说了。
那女人的脸色顿时就变了。她像是受了侮辱了。她突然就愤怒了起来。她从尚海的手上抓回那个BP机,狠狠地摔在了地上,把那个BP机给摔烂了。
她说,你们把我当成什么人啦?
尚海就吓住了,不知怎么回答。
你们是不是把我当成了傻瓜了?一个走了,另一个又来接班是不是?想天天在我这里拿钱是不是?我告诉你,老娘我可没有那么傻。反正他已经走了,已经不在洪城了,他也不可能再来找我,那我就告诉你吧,你以为我付给他的那些钱,都是真钱吗?我有那么傻吗?
尚海一听就傻掉了,转身就出门去了。
随后,他就在街上帮胡男买了一个验钞器。
后边的故事就一个方向了,胡男拿着那些假钱,就找那个女人来了。那个女人这时正好打开房门准备外出,胡男一把就把她推回了屋里,嘭的一声,把门关上了。
他把抓在手里的那些假钱,狠狠地砸在她的脸上。
他说你为什么给我假钱?
她当然不用多作任何的思考。
她说我要是都给你真钱我傻呀?
那你把我当傻瓜啦?
谁叫你天天来呀?
不都是你呼我的吗?
我呼你你就来呀?我要是不给钱,你会来吗?
那你把我当成什么啦?
你说我把你当成什么啦?
你说?
你说!
我怎么知道。
那我也不知道。
那你也不摸摸你的良心。
我为什么要摸摸我的良心?
你给了我这么多的假钱,你说你还有良心吗?你自己数一数吧,你数一数是多少,你就给我补多少,我要真钱!我带了这个来了,一张假钱我都不要。
胡男说着从口袋里拿出了那个验钞器。
女人一把就抓了过来,狠狠地把验钞器给摔烂了。
看着验钞器的那些碎片,胡男也愤怒了,他突然一脚,就把身边的小狗踢到了墙上,那小狗刚刚落地,他又抓起一张木凳,狠狠地砸在小狗的身上。与此同时,他看到了小狗脸上的眼镜,不知如何飞到了一边的沙发上。
那是他的眼镜呀,是他母亲的老花镜!
他上去刚刚把眼镜捡在手里,那个女人发疯一样朝他扑了上来。俩人因此扭打在了一起。
最后,他把她给掐死了。
后边的故事就简单了。
胡男想逃回瓦村去,他想看看老婆肚子里的儿子。我们当然不让。我们让尚海劝住他。一是告诉他,他的儿子早就没有了;二是希望他不要被抓,因为被抓是要被枪毙的,那会让他的家人很受折磨,而且还会替他背上一辈子的骂名。
尚海告诉他:
你最好是选择自己死!
而且是意外死亡,不是自杀。
还要赶在警察追捕之前,否则死了也等于白死。
胡男想了想,觉得也是,就同意了尚海的劝说。
可到底怎么死才是最好的意外死亡呢?我们让他首选了一个被人偷走了井盖的下水道,而且是洪城的市中心,也可以是市中心边上一点点,时间当然是深夜,他扛着一个沉重的蛇皮袋,走呀走呀,就掉到下边去了。但刚刚说完,我们就都沉默了下来,我们觉得这样的死一点都不好看。
最后,是他拍板作的决定,他说还是让他撞火车吧。撞火车的画面比较悲壮。什么意外不意外的,谁会去管那么多呢。我说行,那就让他撞火车吧。
就这样,胡男撞火车去了。我们最先让他去撞了一列客车,然后列车因此停了下来,车上的乘客都把脑袋挤到了车窗的外边,就像在看什么惊悚片一样,那样的场面也蛮好看的。但眨眼之间,我们就改变了这个主意,我们让他撞向了一列破旧的火车,因为破旧列车的画面不仅悲壮,而且意味深长。
这当然应该是在郊外,胡男和尚海坐在一条铁轨的边上,大约是十来步的距离。他们烧着烟,在等着破旧列车的到来。胡男觉得有点远,他说我们再往前一点吧,那样我一撞过去就能撞到火车了。尚海说不行,太近了会被人怀疑是我把你推向火车的,到时我说不清楚的。胡男只好坐着不动,看着各种各样的列车从他们面前飞过。一直等到太阳快下山的时候,一列破旧的火车终于过来了。随着火车的越来越近,胡男慢慢地站了起来,最后,他突然摘下了脸上的墨镜,递给了尚海,然后飞一样扑向火车。
浓烟过后,胡男躺在了铁轨旁的碎石上。
尚海这时站了起来,他慢慢地走向胡男,一边走一边看了看胡男递给他的墨镜,然后就戴到了眼睛上,这一戴,他突然站住了。他的眼前黑麻麻的,他看不到躺在铁轨边的胡男了,于是,他把墨镜摘了下来,可马上又戴了上去,然后又摘了下来,不停地反复着。
躺在铁轨边上的胡男,也跟着尚海手里的墨镜,黑了又亮,亮了又黑。
故事就这样基本上谈完了。
其中的时间,我们用了差不多三天三夜,嘴巴和脑子几乎没有停过,有时连吃饭的时候,我们都还在说,有时他一兴奋,米饭都喷出了嘴外,有的还飞进我的碗里。嘴巴累了,偶尔他也会把胡男的墨镜摘下来,对着房间的某一个地方胡乱地眨着眼,眨得十分使劲;有时也会转过来让我看一看他的眼,我就想笑,也许是习惯了在胡男的墨镜上往外翻,他的眼睛看我的时候,竟然也是那样的低着头,下巴往下扣着,眼睛要翻不翻的,好像不认识我一样。尤其是想出了什么故事,他的眼光总是在墨镜的上边翻得一闪一闪的,像我小时候夜里看到坟头上的那些鬼火,开始我觉得怪怪的,心里就偷偷地笑,后来看多了,我发现他那一闪一闪的眼光里,好像还藏有一点点小小的冷恶,而且有一种从门缝里挤出来的那种歹毒。看的次数多了,有时我竟然有点怕,就只好把目光移走。
我倒是没有脱过尚海的墨镜,我怕他乘机给我换掉,因此,在整个故事的讨论中,我眼中的底色,一直都是阴阴的,阴得心里有时发冷。
讨论结束后,好像是我先摘的墨镜,然后我把墨镜递给了他。我以为他会把墨镜收起来,但他没有接。等到他把墨镜摘下来的时候,他反倒把墨镜递给了我。他说,你把这两副墨镜都拿着吧,写故事的时候,也许还用得着。
完了他问,你是愿意在这里把这个故事整出来,还是拿回家去慢慢弄。这样的话谁都能听得明白,如果想让我就在那里把故事弄出来,他就不会这样问。我就说我拿回家弄吧。他说好的,那你明天就回去好好弄吧。说完就到房里提出了一个大信封,装杂志的那一种,里边装的都是钱。我接到手上掂了掂,蛮重的,可能有两斤以上。他说这是故事的钱,不算在剧本里。剧本的钱在合同中,合同要等你做好了故事我们再签,反正就是在电话里给你说的那个数,如果没有什么意外,你就可能是你们这帮鸟作家里,编剧费目前拿得最多的。我笑笑的,没说什么。我心想我能把这个故事做好的,我能做成他们想要的,当然,我更想得到那笔可观的酬劳。
我就这样回家了。不到一个星期,我就把故事给弄好了。在我写的故事里,该有的情节和该看到的细节,我都写下了清晰可见的线头,一边看一边只需随手一拉,就能拉出许多精彩的东西来。我传往他的电子信箱时,天色刚刚黄昏,天黑的时候,他的电话就打过来了。那时我刚刚吃饭。他说我写的故事他看了,写得很好,比他想象的还要好,尤其是故事的布局结构。然后他就告诉我,他会在几天内把合同给我寄过来,让我到时签完就给他寄回去,等他收到了合同,会在一个星期内给我打上头一笔编剧费,拿到钱后,我就可以动手做剧本了。结束电话的时候,他又补了一句,他说我相信你,我们会成功的。
然后就把电话挂了。
这个电话倒是不长,长的是我后来的兴奋,一直到了后半夜都收不住,整个脑子都毛茸茸的,全部都是兴奋的触须,在四面八方地舒展着,坐在哪里都像是坐在棉花上,晕乎乎的;躺在床上也不像是躺在床上了,整个身子都有随时离床而去的感觉,闭着的眼睛也像一直地睁开着,好像就站在那个美国人的身边,在看到他把我的故事梗概,传进了一个又一个投资商的电脑里,美国的、法国的、英国的,还有加拿大的意大利的,而且还听到他的电话一次又一次地被打响,而且听到他谈成了一笔又一笔的投资。因为每一笔投资里,都可能有我百分之五到十的编剧费。
我就这样等着他的合同。
可是,结果等到的竟是这个美国人死掉了。
消息是北京的一个导演告诉我的,说他就死在三里屯边上的一个酒吧里,因为喝酒的时候与人打架,最后被人打死的,手是他先动的,别人是自卫,所以死了也就死了。打架的原因是因为吵架,吵架的原因是他先出口伤了人,而且就因为那一句你们。想想他真是活该,三里屯是什么地方你不知道吗?在那个地方,你要是喝多了,你骂人家爹你骂人家娘,或者你骂人家大爷,这都无所谓,你还可以像现在一样骂人家你妹,这些也都没什么,那就像是嘴巴顺口而出的嘻嘻或者哈哈一样,真的没什么,你的嘴巴不就是你屁股的另一头吗?就当是你一不小心放了一个屁。可是,你不能随便乱拿你们和我们说事,那会叫人从骨子里感到难受,那会叫人眼睛里冒火。你不是也在中国长大的吗?就算你原来喝的都是马尿,那你血液里现在流着的也是中国的马尿呀!你怎么能动不动就说你们你们的呢?
只是,他那么一死,他们想要的那个故事,便也死掉了一样,一直在我的电脑里死死地待着。我也不再打开,只是偶尔拿出那两副墨镜来看一看,有时看到的是故事里的两个人,而有时看到的,却是故事外的另外两个人,再后来,我就找了一个深深的画框,我把它们粘在了里边,一副粘在左边,一副粘在右边,我让它们永远相互对视着。我还做了一片小小的画签,钉在画框的右下角,画签上的作品名称,是《两个戴墨镜的男人》;但作者一栏,我一直空着,我不想写上我的名字;创作时间,我想了好久,最后我写了:2005年,夏。有事没事的时候就看一看。在这之后,我写了不少东西,但我几乎都让它们在电脑里睡着,我不想拿它们出去发表。我有一种茫然,一种说不出来的茫然,茫然得有时心痛,直至今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