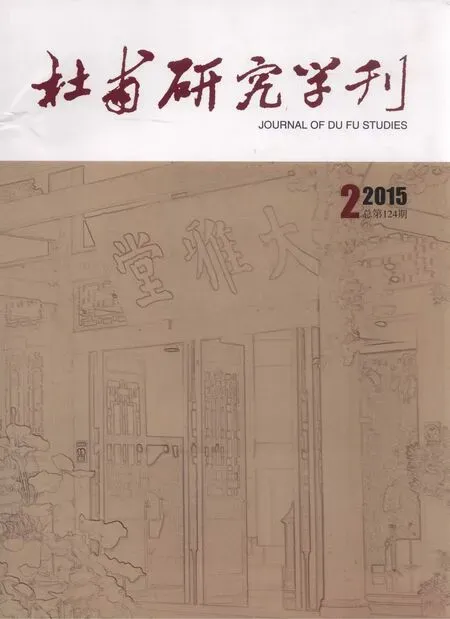沉郁顿挫背后的清狂——从任华《寄杜拾遗》看被忽略的杜甫清狂性格
莫道才
生活在唐肃宗年间的任华,是与李白、杜甫、怀素同时在世并有交游,还存有与这三位盛唐名家寄赠诗的诗人,也是唐代文学研究中被忽视与低估的诗人。他总共留下只有三首诗。由于他结交过李白、杜甫和怀素,这就使得他的诗不但具有文学欣赏价值,还具有文学史料价值。这一点使得任华的诗歌有重新审视的必要。他的《寄杜拾遗》这首诗虽然以前也有过提及,但是其对杜甫研究的文学史料见证价值尚未被重视。这首诗给我们描述了与我们文学史记载不一样的杜甫,这里有必要作一点讨论。
杜拾遗,名甫第二才甚奇。任生与君别,别来已多时,何尝一日不相思。杜拾遗,知不知?昨日有人诵得数篇黄绢词,吾怪异奇特,借问果然称是杜二之所为。势攫虎豹,气腾蛟螭。沧海无风似鼓荡,华岳平地欲奔驰。曹刘俯仰惭大敌,沈谢逡巡称小儿。昔在帝城中,盛名君一个。诸人见所作,无不心胆破。郎官丛里作狂歌,丞相阁中常醉卧。前年皇帝归长安,承恩阔步青云端。积翠扈游花匼匝,披香寓直月团栾。英才特达承天睠,公卿无不相钦羡。只缘汲黯好直言,遂使安仁却为掾。如今避地锦城隅,幕下英僚每日相随提玉壶。半醉起舞捋髭须,乍低乍昂傍若无。古人制礼但为防俗士,岂得为君设之乎?而我不飞不鸣亦何以,只待朝廷有知己。已曾读却无限书,拙诗一句两句在人耳。如今看之总无益,又不能崎岖傍朝市。且当事耕稼,岂得便徒尔。南阳葛亮为友朋,东山谢安作邻里。闲常把琴弄,闷即携樽起。莺啼二月三月时,花发千山万山里。此时幽旷无人知,火急将书凭驿使——为报杜拾遗。任华诗用回忆的笔触来写与杜甫的交往和印象,重点写了杜甫的性格和为人。在这首风格奇崛的诗里,我们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杜甫,一个潇洒豪放的诗人,一个清狂的诗人,而不是一个抑郁隐忍、郁郁寡欢的诗人。不可否认,任华这首具有投献性质的诗对杜甫的描写有一定的夸张渲染成分,但绝对不是无中生有的虚构。
一
任华生平事迹不详,大多数时间是在各地漫游,做幕僚。其在《与庾中丞书》中云:“华本野人,常思渔钓寻常,杖策归乎旧山,非有机心,致斯扣击。”任华除长安外,去过成都、桂林,留下来的许多文章多是在桂林时期做郡佐兼侍御史写的。后又辗转商州、潭州,参湖南观察使幕。其生卒年不详,但可以确定是与李白、杜甫同时代的人,与李白、杜甫均有交游,均有诗作寄赠。但杜甫在诗中未有提到与任华的交游。宝应元年(762)任华隐居绵阳。广德二年(764),杜甫为严武荐举,任检校工部员外郎,并参节度使幕。这一年任华来到成都。据陶敏、李一飞、傅璇琮所著《新编唐五代文学编年史》宝应元年(762)三月条云:“杜甫、严武在成都,游西城;本年春,二人时有唱和之作”,又,广德二年(764)条“任华隐于绵州涪城,本年来成都,上书严武。”这是根据任华的《上严大夫笺》所述得出的结论。此文初载《唐摭言》卷十一。称其“憨直”。文云:“逸人姓任名华,是曾作芸省校书郎者,辄敢长揖,俾三尺之童,奉笺于御史大夫严公麾下:仆隐居岩壑,积有岁年,销宦情于浮云,掷世事于流水。今者辍鱼钓,诣旌麾,非求荣,非求利,非求名,非求媚,是将观公俯仰,窥公浅深,何也?公若带骄贵之色,移夙昔之眷,自谓威足陵物,不能礼接于人,则公之浅深,于是见矣。公若务于招延,不隔卑贱,念半面之曩日,回亲眼于片时,则公之厚德,未易量也,惟执事少留意焉。且君子成人之美,仆忝士君子之末,岂不敢成公之美事乎!是将投公药石之言,疗公膏盲之疾,未知雅意欲闻之乎?必欲闻之,则当先之以卑辞,中之以喜色,则膏盲之疾,不劳扁鹊而自愈矣。公其喜听之,何者?当今天下,有讥谏之士,咸皆不减于先侍郎矣。然失在于倨,阙在于怒,且《易》曰:‘谦谦君子,卑以自牧。’复语曰:‘君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公之顷者,似不务此道,非恐乖于君子,亦应招怒于时人。祸患之机,怨雠之府,岂在利剑相击,拔戟相撞?其亦在于辞色相干,拜揖失节。则潘安仁以孙季获罪,嵇叔夜为锺会所图,古来此类,盖非一也。公所明知之,又安可不以为深诫乎?必能遇士则诫于倨,抚下则弘以恕,是可以长守富贵而无忧危,公成人之美,在此而已矣。念之哉!任华一野客耳,用华言亦唯命,不用华言亦唯命,明日当拂衣而去矣,不知其它。”“仆隐居岩壑,积有岁年,销宦情于浮云,掷世事于流水。今者辍鱼钓,诣旌麾”云云,可以看出任华应是原来隐居在涪城。从行文来看,通篇文字充满投献求助意味,应该是自荐求献之文。而杜甫与严武有非常密切的友情,任华凭借与杜甫在长安时就是旧友,期望通过杜甫与严武的熟识关系来获得寓居成都一份差事,这是很正常的。应该是在这个背景下,写有一篇《寄杜拾遗》的诗。诗中云“而我不飞不鸣亦何以,只待朝廷有知己……此时幽旷无人知,火急将书凭驿使——为报杜拾遗”透露出其写这首诗给杜甫的目的了。
这首诗歌写于何时何地?值得考察。这篇诗作应该是作于杜甫获得检校工部员外郎之前。因为任华在诗题和内容中称杜甫为杜拾遗而不是杜工部,应该是称呼杜甫以前做过的官职,这样容易获得其好感。《旧唐书》本传认为是上元二年(761)严武奏为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误。应该是在广德二年(764),学界已有辨析。关于写作时间,诗中“前年皇帝归长安”提供了很好的参照。《通鉴》卷二百二十一上元元年(760):“上皇爱兴庆宫。自蜀归,即居之。”一般认为这首诗写于任华到成都的宝应元年(762)。而诗中云“莺啼二月三月时”透露了具体写作在这一年初春二三月间。陶敏、李一飞、傅璇琮《新编唐五代文学编年史》(中唐卷)认为:“杜甫本年春与成都严武交密,任华诗当本年春作。”这个推论是合理的。这首诗正是任华需要帮助之时,想得到早到成都的旧友杜甫的帮助。所以总体上说,这是一首意在求助的诗。言辞中要提及往日交游的往事,难免有夸大之辞,甚或行文语气有讨好之嫌,但是基本史实可以肯定是存在的,所写的内容不会是杜撰之辞。而给严武的《上严大夫笺》应该是与杜甫见过面之后写的。看来,他写给杜甫的目的可能是为了通过杜甫来认识严武。
二
本文仅讨论这首诗提供了纠正以往我们对杜甫的很多成见的旁证。比如我们往往受杜甫“沉郁顿挫”风格的固定思路,认为杜甫性格沉郁顿挫。因为这个词本来就是来源于杜甫的自述。《进雕赋表》云:“臣之述作,虽不能鼓吹六经,先鸣数子,至于沉郁顿挫,随时敏捷,扬雄、枚皋之徒,庶可企及也。有臣如此,陛下其舍诸?伏惟明主哀怜之,无令役役,便至于衰老也。”杜甫希望通过献赋的行为获得朝廷的赏识,得到一个类似于扬雄和枚皋这样的御用文人的职位用以糊口养家,所以他认为自己对于公文写作所需的文辞才华和敏捷写作速度,完全达到扬雄和枚皋的水平了。宋人葛立方《韵语阳秋》云:“老杜高自称许,有乃祖之风。上书明皇云:‘臣之述作,沉郁顿挫,扬雄、枚皋可企及也。’《壮游》诗则自比于崔魏班扬,又云‘气劘屈贾垒,目短曹刘墙。’《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则曰‘赋料扬雄敌,诗看子建亲。’甫以诗雄于世,自比诸人,诚未为过,至‘窃比稷与契’则过矣。史称甫好论天下大事,高而不切,岂自比稷契而然邪?至云‘上感九庙焚,下悯万民疮。斯时伏青蒲,廷争守御床。’其忠荩亦可嘉矣”可以看出,前人也意识到杜甫有高估自己而至于狂傲的一面。客观来说,杜甫有浓重的书生意气,这种书生意气用在官场上则有一些愚拙、迂腐。他自己也明白自身的这些特点“老大意转拙,许身一何愚”甚至常常“取笑同学翁”(《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他对自我从政能力的认识不够。他还是有狂傲的一面,这也是杜甫能与李白性格相投,一起远游的原因吧。仇兆鳌指出关于“沉郁顿挫”的出处,前人已有使用,不过都是分开的。刘歆《求方言书》:“子云澹雅之才,沉郁之思。”陆机《思归赋》:“伊我思之沉郁,怆感物而增悲。”又《遂志赋》:“抑扬顿挫怨之徒也。”钟嵘《诗品》:“谢朓与余论诗,感激顿挫过其文。”后来评论家和文学史将“沉郁顿挫”作为杜甫诗歌的风格的概括。与杜甫《进雕赋表》原文的含义有了出入。《进雕赋表》里“沉郁顿挫,随时敏捷”连用,隐含既“沉郁顿挫”又“随时敏捷”的逻辑关系。这里是具有相对举、相互依存的关系。考虑到这篇文章是具有自荐的性质,当然是要说明自己具有做官的各种品质和素质。“随时敏捷”当然是指对时事觉察敏捷、应对反映敏捷、写作公文快捷的意思,这样“沉郁顿挫”应该是指具有对朝廷的忠诚而深沉的思想感情、才华丰富的意思,甚至更偏重于后者,说自己有满腹才华。与后来赋予的指杜甫的风格甚至诗法的含义有一定差异的。清人陈梦雷指出“杜少陵之沉郁顿挫,合而为一,不独章法布置之整,字句锤炼之工而巳”。在文学史的叙述中,杜甫逐渐被塑造成与李白完全不同的批判现实主义诗人。这样对杜甫诗歌的选择介绍更注重关注现实、揭露时弊、情感深沉的所谓强调人民性的作品。在艺术上,杜甫是讲究诗律和炼字的人。清人徐而庵说“杜工部云沉郁顿挫者,沉郁于顿挫之法也。”这是文学史的选择的结果。作为盛唐的诗人,杜甫被描述成与其他人完全不同的形象。由于与盛唐的格调有别,以至于人们怀疑杜甫能否算作盛唐的诗人,杜甫的风格能否算是盛唐的时代风格。其实这是被文学史选择过的被接受的杜甫。
清人卢世氵隺说:“子美最傥宕,自表其能,上之天子,谓‘沉郁顿挫,随时敏捷’扬雄、枚皋,尚可企及,有臣如此,陛下其舍诸?自东方朔以来,斯趣仅见,载观其《遣怀》《壮游》诸作,又谓许身稷契,致君尧舜。脱略时辈,结交老苍,于荡齐赵间,春歌冬猎,酣视八极。与高李登单父台,感慨骏骨,龙媒赋诗,流涕上嘉,吕尚传说之事,来碣石万里风。至于闺房儿女,悲欢细碎,情状尽写入《北征》篇中,与经纬密勿,收京平胡,参伍错杂,不复知有旁观,固是笔端有胆,亦繇眼底无人,古之狂也肆,子美有焉。”这番评价可以说揭示了杜甫被“沉郁顿挫”遮掩的一面,这就是他的“傥宕”。何谓“傥宕”?就是倜傥不羁、豪爽宕逸。就是“狂肆”!白居易《白氏六帖事类集》解释“古之狂也肆”时云“狂者进取”“肆:直意敢言也”杜甫就是这样一个积极进取、直意敢言的人。
正因为杜甫也有狂的一面,才可以解释他能与豪放飘逸的李白结伴而游,成为畅游天下的挚友。古人云,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杜甫或许与李白有性格相近和志趣相投才能成为游伴。其实杜甫年轻也不缺乏狂放,豪情的一面。《画鹰》里展示的“何当击凡鸟,毛血洒平芜”,《望岳》里的“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都是这种流露。而杜甫诗中反复用写到的“放歌”(如《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沉饮聊自遣,放歌破愁绝”,《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白日放歌须纵酒”)更是杜甫骨子里那种狂放的文人本性的流露。但是作为杜甫同时代的并且与杜甫有过交往的任华,他的诗《寄杜拾遗》对于了解杜甫的性格更具有难能可贵的见证意义和价值。任华总共留下三首奇特的诗作,这三首诗歌都是寄送给三位同时代有过交往的文人:杜甫、李白、怀素。从诗歌作品来看,这些寄送的对象应该说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豪放洒脱。而任华本人也是这样的人,否则就不会互引以为知音。任华《赠李白》中说“古来文章有能奔逸气,耸高格,清人心神,惊人魂魄.我闻当今有李白。”他欣赏的就是这种豁达任气的性格。那么,他欣赏杜甫的是什么呢?
一、才气与豪情。诗一开头就说“杜拾遗,名甫第二才甚奇。”称颂杜甫“才甚奇”。这里说的“才”就是才气,也就是宋人所欣赏的“才”。到宋代,杜甫获得的文学史地位被大幅提升,除了宋代需要杜甫的忠君爱民思想情怀外,在艺术方面,杜甫的诗才也是宋人欣赏的,所以才被江西诗派尊奉为诗祖。从某种意义上说,宋诗尚才学,可以追溯到杜甫。但是宋人欣赏杜甫的“才”,被解读为用典用事、无一字无来处等饾饤文字的技巧之才了。看看宋代诗话里,宋代文人讨论杜诗的话题基本上多是练字、用典、对偶、声韵之类的内容。实际上,这不是杜甫才气,只是杜甫才气的表面。杜甫的才气是无所不写,挥洒自如的抒情、纵情表达的豪放。“半醉起舞捋髭须,乍低乍昂傍若无。”这正是任华见证的杜甫的豪放潇洒形象。
二、诗风怪异奇特。诗中说“昨日有人诵得数篇黄绢词,吾怪异奇特,借问果然称是杜二之所为。势攫虎豹,气腾蛟螭。沧海无风似鼓荡,华岳平地欲奔驰。曹刘俯仰惭大敌,沈谢逡巡称小儿。”这里“吾怪异奇特”可以理解为“我认为诗风怪异奇特”,“怪异奇特”是指诗风不寻常、与一般的写法完全迥异,十分奇特,这种写法需要大手笔。在成都读到这样怪异奇特的诗作,任华认为不是一般的人能写出来的。“借问果然称是杜二之所为”,结果一问果然是杜甫所写,就不以为怪了。任华从前读过这样的诗作,诗风似曾相识,当然不奇怪,所以采用“果然”一词。这是怎样的一种“怪异奇特”呢?“势攫虎豹,气腾蛟螭。”这是比喻,是说诗也是说书法。从两个方面来说,“势”是古人论诗歌和书法常用的概念。“势”如“攫虎豹”说的是杜诗之势有力。《醉歌行赠公安颜少府请顾八题壁》:“君不见西汉杜陵老?诗家笔势君不嫌,词翰升堂为君扫。”这是说的诗。杜甫自己的诗中也用过。《戏题王宰画山水图歌》:“尤工远势古莫比,咫尺应须论万里。”这是说的画。宋人陈应行在《吟窗杂录》中“论诗势”条说“先须明其体势,然后用思取句”“诗有十势”其中就有“龙潜巨浸势”“龙行虎步势”“虎纵岀群势”“风动势”,“气”在这里与“势”同义。“气腾蛟螭”说的是其有腾越飞动之势。“沧海无风似鼓荡,华岳平地欲奔驰。”说的也是“势”。这也是比喻描述。像苍茫海面,表面看没有风,却波澜壮阔;像华山,在平地间拔地而起,犹如万马欲奔。这是说,其诗很有张力,却不张扬。这样的诗“曹刘俯仰惭大敌,沈谢逡巡称小儿。”而这个印象,与我们习见的印象是完全不同的。其实,唐人还是理解这样的杜甫的。这不正是元稹在墓志铭序称赞的“古傍苏、李,气夺曹、刘”吗?
这首诗还提供了什么我们以前忽略的信息呢?
一、杜甫在长安拥有盛名。以往我们文学史认为杜甫在长安的十年是困顿、困守的十年。
但是《寄杜拾遗》诗中说“昔在帝城中,盛名君一个。”这个“昔”就是我们文学史说的长安漂泊十年,困顿十年。文学史描述的杜甫是穷困潦倒的、狼狈不堪的、困厄局促的。“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但是同样在这首《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中,我们也看到“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赋料扬雄敌,诗看子建亲。李邕求识面,王翰愿卜邻”的豪情万丈和被追星般的洋洋自得。只是我们文学史往往断章取义地截取“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只用来说明其读书渊博。“读书破万卷”说其诗中呈现出学识渊博是因,而要炫耀的重点才是“下笔如有神”这个才似泉涌的果。这不就是豪放吗?只因为这样才达到了“赋料扬雄敌,诗看子建亲。李邕求识面,王翰愿卜邻”的效果。这不正是任华诗中所说的“公卿无不相钦羡”吗?这正是杜甫当年在长安盛名!在任华眼里,那时的杜甫在政治上也是实现了抱负的人杰,“前年皇帝归长安,承恩阔步青云端。积翠扈游花匼匝,披香寓直月团栾。英才特达承天睠,公卿无不相钦羡。”好像这并不是我们看到的那个穷困潦倒的杜甫,而是在众公卿面前志得意满的杜甫。杜甫正是具有这样的“盛名”!这个盛名除了令人羡慕的青云直上外,更应该是杜甫与人交往的豪放、豪爽、豪迈的性格。一个胸无大志的人、默默无闻的人不能称为有盛名;穷困潦倒的,狼狈不堪的、困厄局促的人也不能称为有盛名。这样杜甫在长安时期,并非我们原来解读的默默无闻之人。“承恩阔步青云端。积翠扈游花匼匝,披香寓直月团栾。英才特达承天睠,公卿无不相钦羡。”这就是众人仰慕的盛名啊!这种盛名甚至在成都时期还有“如今避地锦城隅,幕下英僚每日相随提玉壶。”而这个方面,在杜甫后期自己的诗里是被有意无意忽略了的。文学史里的杜甫留给了后人一个寒酸穷困的形象。难道我们的文学史都被“蒙骗”了?这里确实是需要深入探讨的。
二、行为狂歌醉卧。任华看到的杜甫是“郎官丛里作狂歌,丞相阁中常醉卧。”杜甫行为中的“醉卧”“狂歌”留给了任华很深的记忆。这种不拘礼法的行为,甚至任华为之辩解。《寄杜拾遗》诗中说“古人制礼但为防俗士,岂得为君设之乎?”当年在京城,任华见到过杜甫与各类郎官宴饮狂歌,在丞相阁中常醉卧。这些是以前没有见过的描述,杜甫自身描述的是“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但使残年饱吃饭,只愿无事常相见。”(《病后遇王倚饮赠歌》)杜甫自身也没有描述过“郎官丛里作狂歌,丞相阁中常醉卧”这种生活。这是任华虚构的吗?不可能!杜甫自己诗中也写到过“狂歌”和“醉卧”的形象,但是一般不被重视。比如杜甫在《寄李白》诗中写过“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留下了他与李白在一起痛饮狂歌的生活侧影。在《官定后戏赠(时免河西尉,为右卫率府兵曹)》中写道“耽酒须微禄,狂歌托圣朝。”在《陪王侍御宴通泉东山野亭》中写到过“狂歌过于胜,得醉即为家。”这里都可以看到杜甫的狂歌醉卧的形象。《望牛头寺》说“休作狂歌老,回看不住心。”《陪章留后侍御宴南楼(得风字)》说“寇盗狂歌外,形骸痛饮中。”“此身醒复醉,不拟哭途穷。”杜甫有一首《狂歌行赠四兄》,杨伦《杜诗镜铨》记云:“蒋云:胸中无限牢骚,乃兄发泄,题曰《狂歌行》。伤我羡人,一片郁勃所岀,都是狂态也。”明人王世贞在《吴长君七十长歌》诗中说:“昔日杜甫成狂歌,自言四兄巢许伦。虽然龌龊家人语,能使千载传其真。”他也认可杜甫有狂的一面。杜甫在《不见(近无李白消息)》诗中表现他:“不见李生久,佯狂真可哀。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敏捷诗千首,飘零酒一杯。匡山读书处,头白好归来。”写因为不见李白许久,很怀念在一起狂歌醉卧的情形。自己独处也要“佯狂”一番来感受回味一下。一个“佯狂”可以看出两人在一起时的真狂景象!也可见杜甫骨子里也是狂人!
杜甫的《壮游》是对他平生的自述,可以看出他的豪放情怀:“往昔十四五,出游翰墨场。斯文崔魏徒,以我似班扬。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皇。九龄书大字,有作成一囊。性豪业嗜酒,嫉恶怀刚肠。脱略小时辈,结交皆老苍。饮酣视八极,俗物都茫茫。东下姑苏台,已具浮海航。到今有遗恨,不得穷扶桑。王谢风流远,阖闾丘墓荒。剑池石壁仄,长洲荷芰香。嵯峨阊门北,清庙映回塘。每趋吴太伯,抚事泪浪浪。蒸鱼闻匕首,除道哂要章。枕戈忆勾践,渡浙想秦皇。越女天下白,镜湖五月凉。剡溪蕴秀异,欲罢不能忘。归帆拂天姥,中岁贡旧乡。气劘屈贾垒,目短曹刘墙。忤下考工第,独辞京尹堂。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春歌丛台上,冬猎青丘旁。呼鹰皂枥林,逐兽云雪冈。射飞曾纵鞚,引臂落鹙鸧。苏侯据鞍喜,忽如携葛强。快意八九年,西归到咸阳。许与必词伯,赏游实贤王。曳裾置醴地,奏赋入明光。天子废食召,群公会轩裳。脱身无所爱,痛饮信行藏。黑貂不免弊,斑鬓兀称觞。杜曲晚耆旧,四郊多白杨。坐深乡党敬,日觉死生忙。朱门任倾夺,赤族迭罹殃。国马竭粟豆,官鸡输稻梁……”从这首《壮游》的自述中,可以看到杜甫当年“性豪业嗜酒,嫉恶怀刚肠”的豪放洒脱,“气劘屈贾垒,目短曹刘墙”的自信。“裘马颇清狂”这是杜甫对自己的描述。在《七月三日,亭午已后校热退,晚加小凉,稳睡有诗,因论壮年乐事,戏呈元二十一曹长》中写道自己的豪情:“歘思红颜日,霜露冻阶闼。胡马挟雕弓,鸣弦不虚发。长钅比逐狡兔,突羽当满月。惆怅白头吟,萧条游侠窟。”仇兆鳌指出“此追论壮年乐事,亦从秋景想出。……此即《壮游》诗中‘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呼鹰皂枥林,逐兽云雪冈’事也”又如杜甫《遣闷戏呈路十九曹长》:“唯君最爱清狂客,百遍相过意未阑。”说朋友最爱清狂客,实质上是想说自己是一个清狂客。仇兆鳌说“‘清狂客’三字,旷怀豪兴,兼而有之,公之自命甚高。”他交往的也多是清狂之人,比如他崇拜的号为“四明狂客”的贺知章“贺公雅吴语,在位常清狂”(《遣兴》)。朱熹解释“贺知章‘汲汲如狂’。汲汲:勤急貎。《礼记》:“汲汲然,如有追,而弗及也。‘如狂’犹言清狂。杜甫诗‘在位常清狂’注:‘凡狂者,阴阳脉尽浊。不狂如狂者曰清狂。’”“清狂”一词可追溯到《汉书·昌邑王贺传》:“曰贺清狂不慧。”在文学里最早是在左思《魏都赋》:“仆党清狂”李善注“色理清徐,而心不慧,故曰清狂也。”
三、性情仗义直言。任华《寄杜拾遗》诗中说当年“只缘汲黯好直言,遂使安仁却为掾。”这实质上是杜甫“狂”的表现,书生意气,不顾官场规则。这可能是说救房琯事。元稹在《唐故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志铭并序》中就指出是“以直言失官”。明人邵经邦在《弘简录》中说“杜甫论房琯奏,虽狂不失谏体。”杜甫直言既是他直言不讳的勇气,也是性格坦荡无私的表现。可能正是看中杜甫的为人仗义执言,任华才来找他帮忙向严武荐举美言。清人卢世氵隺《尊水园集略》云“子美千古大侠,司马迁之后,一人。子长为救李陵而下腐刑,子美为救房琯,几蹈不测,赖张相镐,申救获免,坐是蹉趺卒老剑外,可谓为侠所累。然太史公遭李陵之祸而成《史记》,与天地相终始。子美自发秦州以后诸作,泣鬼疑神,惊心动魄,直与《史记》并行,造物所以酬先生者,正自不薄。”这里说的“为侠所累”也就是他仗义执言。这种仗义执言也是一种“狂”而不计后果的表现。卢世氵隺《尊水园集略》又云“子美性极辣,惜未见诸行事。《雕赋》一篇辣味尽露。”这里说的“辣”就是现在人们俗语说的泼辣敢说,敢仗义执言,其实也是一种狂的表现。
三
杜甫自己如何看待“狂”的呢?后人又怎么看待杜甫的“狂”呢?这个是应该弄清楚的。
杜甫在诗中自陈过“我生性放诞,雅欲逃自然。嗜酒爱风竹,卜居必林泉。”(《寄题江外草堂(梓州作,寄成都故居)》)这说明杜甫对自我“放诞”性格是认知的。《雕赋》是借神雕来寄寓自己理想与抱负的:“当九秋之凄清,见一鹗之直上。以雄材为已任,横杀气而独往。梢梢劲翮,肃肃逸响。杳不可追,俊无留赏。彼何乡之性命,碎今日之指掌,伊鸷鸟之累百,敢同年而争长,此雕之大略也。”正是以雕为自喻,抒写了自己的不凡才华和远大理想。清人陆葇《历朝赋格》评《雕赋》和《进雕赋表》云:“气雄力厚,快所欲言,不袭汉晋,何况六朝。拾遗以搏击自任,枭乌鸧鸹辈侧目之矣,岂俟救房琯乃遭贬黜。”《饮中八仙歌》写他交往的人物无一不是以“狂”著称:“知章骑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汝阳三斗始朝天,道逢麹车口流涎,恨不移封向酒泉。左相日兴费万钱,饮如长鲸吸百川,衔杯乐圣称避贤。宗之潇洒美少年,举觞白眼望青天,皎如玉树临风前。苏晋长斋绣佛前,醉中往往爱逃禅。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焦遂五斗方卓然,高谈雄辨惊四筵。”这些偶像正反映了杜甫心中对“狂”的追慕。在《遣闷》中,杜甫写道“倚著如秦赘,过逢类楚狂。气冲看剑匣,颖脱抚锥囊。”杜甫喜欢称颂别人的“狂”,说明杜甫心目中也是崇拜“狂”的。杜甫《寄李十二白二十韵》:“昔年有狂客,号尔谪仙人。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声名从此大,汩没一朝伸。文采承殊渥,流传必绝伦。”杜甫《不见(近无李白消息)》:“不见李生久,佯狂真可哀。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敏捷诗千首,飘零酒一杯。匡山读书处,头白好归来。”可见杜甫是喜欢与性情“狂”者交游的。在描写自然景物时,他也喜欢把这种对“狂”的推崇移情到自然中。如《绝句漫兴九首》:“肠断江春欲尽头,杖藜徐步立芳洲。颠狂柳絮随风舞,轻薄桃花逐水流。”“隔户杨柳弱嫋嫋,恰似十五女儿腰。谁谓朝来不作意,狂风挽断最长条。”又如《君不见简苏徯》:“君不见道边废弃池,君不见前者摧折桐。百年死树中琴瑟,一斛旧水藏蛟龙。丈夫盖棺事始定,君今幸未成老翁。何恨憔悴在山中,深山穷谷不可处,霹雳魍魉兼狂风。”这里“颠狂栁絮”用拟人手法写出内心之情。明人王九思在《与南川德一复至浒西赏杏花十首》说“莫笑浊醪频过墙,看花杜甫益颠狂。且教花下秦娥舞,绝胜人间傀儡场。”指出杜甫因为看花而更加颠狂的“狂”的性格。“狂风”也是“狂”的移情体现。而上元元年在成都写的《狂夫》更是自号“狂夫”:“万里桥西一草堂,百花潭水即沧浪。风含翠筱娟娟净,雨裛红蕖冉冉香。厚禄故人书断绝,恒饥稚子色凄凉。欲填沟壑惟疏放,自笑狂夫老更狂。”最后一句“自笑狂夫老更狂”反映了杜甫在成都时期的心态。杜甫最爱的是“清狂”,杜诗中三次提到“清狂”,他在《遣兴五首》说“贺公雅吴语,在位常清狂。”在《遣闷戏呈路十九曹长》中说“唯吾最爱清狂客,百遍相看意未阑。”在《壮游》中说“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这些都道出了杜甫对清狂的追慕,杜甫自己的沉郁顿挫背后其实是清狂。
杜甫的这种“狂”,除了任华外,唐人也有印象。比杜甫稍晚的杨巨源(755-?)就有“杜甫狂处遗天地”之说。杨巨源在《赠从弟茂卿时欲北游》诗中云:“吾从骥足杨茂卿,性灵且奇才甚清。海内方微风雅道,邺中更有文章盟。扣寂由来在渊思,搜奇本自通禅智。王维证时符水月,杜甫狂处遗天地。流水东西岐路分,幽州迢 旧来闻。若为向北驱疲马,山似寒空塞似云。”杜甫之狂在新旧唐书的本传中也有记载。《旧唐书》本传称其“甫性褊躁无器度,恃恩放恣。尝凭醉登武之床,瞪视武曰:‘严挺之乃有此儿。’武虽急暴,不以为忤。甫于成都浣花里种竹植树,结庐枕江,纵酒啸咏,与田畯野老相狎荡,无拘检。严武过之,有时不冠,其傲诞如此。”《新唐书》本传也记载云“甫放旷不自检,好论天下大事,高而不切。少与李白齐名,时号李杜。尝从白及高适过汴州,酒酣登吹台。慷慨怀古,人莫测也。”前人对这些记载或者质疑,或者忽略,其实这些都说明其清狂性格在当时是出名了的,正史编撰者都认为是其性格中很重要的方面,对其创作有重要影响,所以才记录下来。而我们的研究者、文学史家误以为这是杜甫性格的不足,往往有意忽略、回避,或者为之辩解,以为这会影响杜甫的完美形象,其实是曲解了杜甫性格的重要一面。
历代文人对杜甫“狂”的性格是持肯定看法的。北宋王禹偁在《酬安秘丞歌诗集》:“神仙负过遭谴谪,谪来人世为辞客。李白王维并杜甫,诗颠酒狂振寰宇。”一个“并”字可以看出,王禹偁认为李白、王维和杜甫都是“诗颠酒狂”,也因此都“振寰宇”。元人刘敏中在《答寓斋问》中说:“佯狂李白杜甫,寓诸歌诗,而皆终身焉。”认为这种“狂”是诗中表现出来的“佯狂”,不仅是贯穿其创作始终,也是贯穿其生活始终的。不仅李白如此,杜甫也是如此。只是我们以前往往只说杜甫青年时代如此。刘敏中这个评价值得注意。其实后人大多接受杜甫有“狂”的性格这一特点。明人潘希曾在《枕上作》中说:“忽忽梦初觉,沉沉夜未央。孤砧晴捣月,残角冷吹霜。酒醒相如渴,诗成杜甫狂。帝城惊渐远,所喜近江乡。”明人秦夔在《梅轩为荆溪任庭兰赋》中说:“轩前旧种梅千树,野雪初晴白满枝。才似广平应有赋,狂如杜甫岂无诗?”明人倪谦在《夏日游宣府李挥使北园席上步于景瞻韵二首,时天顺庚辰六月也》中说“野花园草竞芬芳,坐爱南薫透葛凉。饮量任开千日酝,醉魂犹到五云乡。原思自信贫非病,杜甫谁知老更狂。”清人潘德舆在《除夕题壁》中说:“日短心犹壮,天高首自昂。乾坤容侧陋,旋转藉文章。对策董生直,悲歌杜甫狂。呼朋勉希古,吾道未苍茫。”清人储大文在《送史先生致政归序》中说:“予尤爱少尹诗二语曰:‘王维静时证水月,杜甫狂处遗天地。’若大江而南,气盖函夏,唯采石矶巅,水月可证,而天地可遗也。若风物淸美,谢脁靑山李白楼,摩诘可静坐,子美可狂吟。”历代文人对杜甫的这种认识值得重视。杜甫这种“狂”的性格也是他的魅力所在。有了这种“狂”才有对人生理想的执着,才有创作的激情。
怎么评价杜甫的清狂呢?明人李贽在《孟轲附乐克论》中专论过“狂”与“狷”,其云:“吾且极言之:凡人之生,负阴而抱阳,阳轻淸而直上,故得之则为狂。阴坚凝而执固,故得之则为狷……君子者,大而未化之圣人也。善人者,狂士之徽称也。有恒者,狷者之别名也……若陶渊明肆于菊,东方朔肆于朝,阮嗣宗肆于目,刘伯伦、王无功之徒肆于酒,淳于髠以一言定国肆于口,皆狂之上乗者也。难之难者,其东方生乎?避世金马门以万乗,为僚友所谓古之狂也肆。其在斯人欤?其在斯人欤?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洁之人而与之,是狷也。……李谪仙、王摩诘,诗人之狂也。杜子美、孟浩然,诗人之狷也。韩退之,文之狷,柳宗元,文之狂。是又不可不知也。”他认为杜甫的“狂”是狂狷。狷者,狷介、耿介也。杜甫这种“清狂”是他坚持操守的体现,但往往是不合时宜的,不懂官场规则,不懂人情世故的。明人杨廉在《清狂山人记》中说:“清有 孟慱淸议之清,有杨伯起清白之淸。等而上之,则伯夷之清,淸之至者也。狂有贺知章狂客之狂,有杜子美狂夫之狂。等而上之,则曾点之狂,狂之尤者也。”他认为杜甫的“狂”是“狂夫”之狂。今天来看,杜甫的“狂”与李白的“狂”一样都是坚持自我个性、不愿改变自我的表现。正因为这样,才有了他对社稷的忠诚,对人民的热爱,才成就了杜甫的伟大!以往我们对杜甫的描述过于刻板,过于狭窄单一,过于强调沉郁顿挫。这样的杜甫被模式化了,太沉重太抑郁了。其实杜甫的沉郁顿挫是人生低谷和遇到挫折时诗歌呈现的风格样态。在人生相对安逸时则是另外一番景象,比如成都时期。而当人生在他看来较顺利时或者得意时,杜甫的这种清狂就展示了出来。这正是杜甫丰富的人生样态。我们也应该看到,杜甫的沉郁顿挫是压抑自身清狂的表现。那是动乱的时代和苦难的阅历带来的改变。通过任华的《寄杜拾遗》这首诗,我们应该回到盛唐的现场,复原杜甫的清狂,让杜甫的形象丰满起来,鲜活起来。
〔本文系广西特聘专家岗(编号2011B30)专项经费资助成果〕
注释:
①关于杜甫之“狂”也有一些论文作过讨论,比如刘曙初《论杜甫与中国狂士传统》(《湘潭师院学报》2005年第1期)、吴怀东《自笑狂夫老更狂——论“狂”与杜甫文化精神》(《固原师专学报》2004年第5期)、许德楠《论杜诗中的“狂顾”、“狂走”和“狂歌”》(《杜甫研究学刊》2003年第2期)、吴明贤《试论杜甫的“狂”》(《杜甫研究学刊》1996年第3期),以及任治春《试论杜甫的放浪狂歌》(安徽大学2011年硕士论文)等等,但是本文角度与之不同,故还有必要再做论述。
②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二百六十一,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2903页。
③参见殷祝胜:《论任华桂林之游及在桂林的散文创作》,《广西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4期。
④参见李德辉:《全唐文作者小传正补》,辽海出版社,2011年,第379页。
⑤陶敏、李一飞、傅璇琮:《新编唐五代文学编年史》(中唐卷),辽海出版社2013年版,第69页。
⑥陶敏、李一飞、傅璇琮:《新编唐五代文学编年史》(中唐卷),辽海出版社2013年版,第97页。
⑦董诰等编:《全唐文》卷三百七十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1689页。
⑧陶敏、李一飞、傅璇琮:《新编唐五代文学编年史》(中唐卷),辽海出版社2013年版,第92页。
⑨司马光:《资治通鉴》,岳麓书社1990年版,第924页。
⑩仇兆鳌:《杜诗详注》卷二十四,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172-2173页。
⑪葛立方:《韵语阳秋》卷八,何文焕《历代诗话》,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46页。
⑫陈梦雷:《松鹤山房诗文集》诗集卷六,清康熙铜活字印本。
⑬蔡鈞:《诗法指南》卷四,清乾隆刻本。
⑭卢世氵隺:《尊水园集略》卷六,清顺治刻十七年庐孝余增修本。
⑮白居易:《白氏六帖事类集》卷八,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影印本(据傅增湘旧藏毛样影印),帖册二,第87页。
⑯陈应行:《吟窗杂录》卷十二,明嘉靖二十七年崇文书堂刻本。
⑰杨伦:《杜诗镜铨》卷十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564页。
⑱王世贞:《弇州山人四部续稿》卷十一诗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清文渊阁四库全书,1282册,第143页。
⑲仇兆鳌:《杜诗详注》卷十五,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318页。
⑳仇兆鳌:《杜诗详注》卷十八,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602页。
㉑朱熹:《通鉴纲目》卷四十八,台湾世界书局1985年版,摛藻堂四库全书荟要,169册,第220页。
㉒萧统:《文选》卷六,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10页。
㉓邵经邦:《弘简录》卷三十三,清康熙刻本。
㉔卢世氵隺:《尊水园集略》卷六,清顺治刻十七年庐孝余增修本。
㉕卢世氵隺:《尊水园集略》卷六,清顺治刻十七年庐孝余增修本。
㉖陆葇:《历朝赋格》上集文赋格卷五,清康熙间刻本。
㉗王琦:《李太白诗集注》卷三十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清文渊阁四库全书,1067册,第571页。
㉘王九思:《渼陂集》卷六,明嘉靖刻崇祯补修本。
㉙刘昫:《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054页;第5055页。
㉚王禹偁:《小畜集》卷第十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清文渊阁四库全书,1086册,第126页;第127页。
㉛刘敏中:《中庵集》卷十六经疑策问杂著,清钞本。
㉜潘希曾:《竹涧集》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清文渊阁四库全书,1266册,第645页。
㉝秦夔:《五峰遗稿》卷十二,明嘉靖元年刻本。
㉞倪谦:《倪文僖集》卷九,清武林往哲遗著本。
㉟潘德舆:《养一斋集》卷六,清道光刻本。
㊱储大文:《存砚楼二集》卷六,清乾隆京江张氏刻十九年储球孙等补修本。
㊲李贽:《藏书》儒臣传卷二十四,明万历二十七年焦竑刻本。
㊳杨廉:《杨文恪公文集》卷三十六,明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