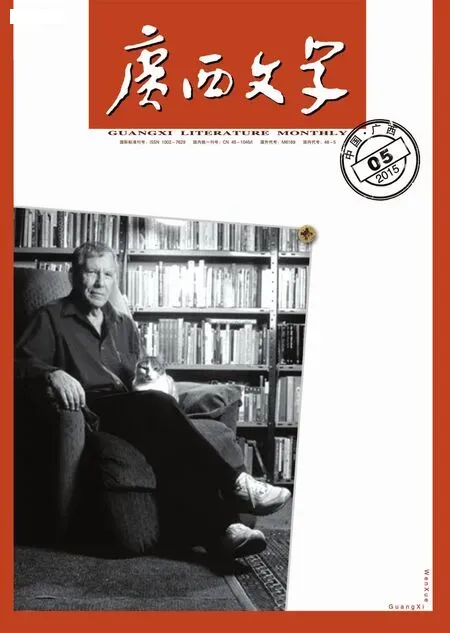阑 尾
短篇小说·陈纸/著
我不承认我有病,从出生到四十一岁,我从没去过医院。小时候,见了村里的赤脚医生陈建国,不是我躲开他跑,而是他见了我就避让,怕我这个野孩子奔狂鲁莽,撞他个人仰马翻。他侧着身子,斜着眼,对我喊:“跑开跑开,你不生病,不要妨碍我去跟别人看病!”
打死我我都不承认有病。肚子痛那叫“病”吗?记忆中,村里人没有谁把肚子痛叫“有病”。如果一个小小的肚子痛,你说生病了,会招人笑话的,会笑你挨不住痛、经不得痛。
在我们那座叫“舍陂”的小乡村里,没有哪家的孩子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去拿药吃的,大人就更不用说了。我痛过的几次,尽管印象深刻、记忆深刻、感觉深刻,尽管躺在床上剧烈翻滚,用枕头顶着肚子呻吟,连走路都不稳,我也不承认是生病,用父母的话说,是“吃了不干净的东西”。每每这个时候,他们就去商店买两袋糖果,糖果尖尖的,刻着条纹,像延安的宝塔山。他们说,吃几颗糖,然后,就会没事的。
我不承认我有病,事实上,我就是没病。吃了几颗糖,一些细长的虫子,就随着大便爬了出来。原来,是它们在我的肚子里闹的。有时,它们三四条,有时,八九条,缠绕着、拥抱着,合着伙来闹腾我,来捉弄我,这些可恶的家伙!我一边使着劲,一边勾着头,看着它们慢慢蠕动的样子,那么欢快,我也跟着欢快起来,之后,我的肚子便不痛了。我觉得肚子痛不是病,而是一部小小的童话剧。
除了一些虫子偶尔来作怪,还有,就是读书时长着的红肿冻疮和酱色疥疮了。
冻疮算病吗?疥疮算病吗?在当时,哪个小伙伴没生过冻疮、没得过疥疮?冰天雪地呀,没有取暖设备呀,来来去去走路上学呀,上课翻书呀,放了寒假帮家里做家务呀,每个小伙伴的手都通红通红,胀胀肿肿,有的溃烂了,像熟烂的小樱桃;有的结痂了,像烤煳的小面包。
读初中和高中,一离家,就一个礼拜。学校远在十几公里外,一个班,男生、女生,各一个寝室,一个寝室二三十号人,箱子呀脸盆呀塑料桶铁桶呀,还有毛巾衣服呀,都堆着,放着、寝室里,挤挤挨挨,阴暗潮湿,天冷时,有的同学夜尿都懒得起来,对着窗外乱射,异味熏天呀。我们身上,每个人都痒,特别是在有关节的地方,踝关节、臂关节、手指关节、脚趾关节……执意任性地痒,持之以恒地痒,坚持不懈地痒,兴奋激动地痒,到了晚上,大家搔呀挠呀、挠呀搔呀, “沙沙沙沙”“刷刷刷刷”——像春蚕食桑,像木匠锯树。此时,如果有明亮的灯光,一定能在下铺看到上铺的碎屑,纷纷扬扬、飘飘洒洒……但那是病吗?冻疮与疥疮算是病吗?顶多算是一种“现象”,一种集体主义现象。那时,也没人把它们当成“病”,没一位同学去涂抹什么“冻疮膏”“硫黄软膏”之类的,那两个名字,是我多年以后,来到城里,在一次偶然机会才知道的。但我没丝毫后悔,我没病,我们大家都认为没病,我们为什么要刻意去寻找什么“膏”?我们也没时间与金钱去寻找什么“膏”,更没必要去寻找什么“膏”, 一门心思,我们只有学习。拼命地学习、努力地学习,我们这些农村的学生,没有人去认真思考那是不是病,要不要治,该怎样治。
阿弥陀佛,大吉大利,四十一年了,我没有病,我平安地走过来了。
我没有病,虽然最近的肚子,时不时——有点痛,但也许是童年的反刍,是在唤醒我的记忆吧。
想不到,疼痛也记得起乡愁,时不时,从乡村赶到城里来,依然造访我的肚子。
妻子皱起了眉头:“该不会是什么慢性病吧?一定要去看看!”妻子紧张的神情,让我的肚子阵阵收紧,疼痛也一阵紧似一阵。
我倒很轻松:“没事,不是病,只是肚子痛而已。”
“‘肚子痛肚子痛’,你总是叫着农村那一套,肚子痛怎么不是病?肚子痛有好多种原因,肚子痛说不定是胃痛,说不定是肾痛,说不定是肝痛,说不定是胆囊痛……”妻子说完这些,气喘吁吁。
我承认,从小在谭城这座大城市里长大的妻子确实懂得比我多,至少在“肚子痛”上,就懂得比我多四倍。但那又有什么用?她有我的经验多吗?至少在“肚子痛”上,她的经验有我多吗?她见过的各种各样的虫子有我多吗?她肚子痛的次数有我多吗?我与她结婚十五年整,从没听她喊过一句“肚子痛”,而我,在最近不到一年,就痛了四五次——从这一点来说,我觉得她没有优先判断的发言权。何况,“肚子痛”是我的,是我肚子痛,我自己的肚子自己最清楚是怎么回事。我的肚子我做主,用不着别人管。
“别人怎么管不得?我是你妻子,我是你最亲近的人,除了你自己,就数我最了解你,有的时候,有些事,你自己不一定比别人更了解你自己。更何况,你的肚子、你的病痛不是你一个人的,至少现在不是了。你现在不比之前,你现在有了你做主的家,你有母亲、你有妻子、你有儿子,你还有工作。你的肚子、你的病痛不再是你一个人的,是你母亲的是我的是你儿子的是我们全家的,还是你单位部门和领导的,同事不过问你,领导不过问你,我们有权过问你,有权建议你……”妻子满脸涨得通红,好像谁要抢她最心爱的物件,她在拼死力争。妻子像刚吐出了鱼的鸬鹚,抻了一下脖子,然后放低,又说:“当然,你去不去医院,你去不去看病,还是你自己看着办。你又不是三四岁的小孩,你不去,我们不能拉着你、绑着你、拖着你去。”
我可不想跟妻子红脸,我可不想与她一般见识,但我还是给了她一个台阶。看着她苦苦哀求的样子,我实在不忍心,怕她流下泪来,我想了半天,于是答应了她:“那,就去社区诊所看看吧。”
社区诊所的医生叫刘代春。我是从诊所的招牌猜想她名字的。这家诊所在小区宿舍区到菜市的路上,招牌横挂着,高高在上,红底白字,大得像棺材板,死板、威严。
以前,我怎么从没留意到,这里有一家诊所呢?妻子扯着我,然后,推到一位穿着白大褂、五十岁上下的女医生面前,说:“刘医生,我爱人肚子痛一年多了,看看什么病。”
我白了妻子一眼,连忙纠正说:“没什么病,痛不到一年,一年里三四次,忍一忍,就过去了。”
刘医生嘟着嘴,把手放在我的手上,镜片后面的眼睛却定定地落在妻子脸上。七八秒钟后,她松了手,低下头,严肃而认真地说:“消化不良,开点消食片,回去吃吃。”
拿着一百多元消食片,我很想问问刘代春医生:我这算不算病呢?我想了想,还是没开口。如果有病,刘医生是不会这么轻易放过我的。如果有病,她怎么连个“病”字都未提呢?我没有病,何必问呢?这一百多块钱,算是给妻子买了个教训。
妻子却锲而不舍,好像唐僧随身携带的咒语。妻子的“咒语”是“肚子痛”,她想起什么时候要提醒我一下,便把“肚子痛”往我身上一丢,然后说:“是吧?又痛了吧?没那么简单的,算我求求你,去医院看看吧。”在读初三、正迎考复习的儿子也说话了:“爸,还是听妈的。你这么叫喊,我都没办法做试题了。”
我虽然没病,但不能影响别人。正因为我没病,所以不能影响别人。但我又不能不叫喊,因为实在太痛了。像小时候那样,我痛得在床上打滚,我学着小时候那样,用枕头顶着腹部,但无济于事。
妻子也不与我商量,拦了一辆出租车,把弯着腰、垂成姜太公的我推了进去,直接送进了谭城第一人民医院。忙忙碌碌的医生把我吓坏了。后来,我才知道,是我疼痛的样子把那些年轻的医生吓坏了,他们不由分说,说先要给我打几瓶吊针水。医生的大胆,把收费处的收费员吓坏了,那个看上去娇小羸弱的女子推了两下眼镜框,把处方毅然决然推出玻璃窗外,她的声音大得吓人:“六瓶?是给一个病人打还是两个病人打?还要不要命了?而且,有两副注射器,两只手同时打吗?!”
妻子也被女子的话吓坏了,她抓起处方单直奔医生室。医生瞪着妻子说:“到底她是医生还是我是医生?!”妻子瞪着医生,眼睛木然,她扭了一下头,见我扭成一团的身子,又毅然决然跑向收费处。
我虽然痛,但我的思维没有痛,是心痛。准确地说,此时,我心比肚子痛。我艰难地伸出一只手,另一只手紧紧地抓住椅子的扶手。我伸出的手五指张开,颤颤巍巍,在空中抖动。我使出吃奶的气力,对着妻子喊:“六瓶,两副注射器,得多少钱呀!”
妻子说:“不是钱多钱少的问题,而是这么一个肚子痛,要一次性打六瓶吊针水,而且,要两只手同时打,有那么严重吗?”
我捂着肚子,挤出了一丝笑容,说:“是吧,你也终于承认了吧。我没有什么病,至少,没有多么严重的病。我说了吧,不要来医院,来了医院,再小的问题,都会当成大病。”
妻子下定了决心,她说:“到了医院就安心治病。”我还想向她说什么。她扭回了头,又毅然决然冲进了医生室,说:“收费处不肯结账,不敢收费,说……”医生不耐烦地挥挥手,盯着办公桌的电脑显示屏,缓了一下口气,说,“再去吧,我已经改过来了。”
有点愠怒地,医生把妻子送出门,接着,示意我躺在办公室一侧靠墙的床上。他的一只手放在另一只手的手背上,用另一只手,在我肚子不同的部位按压。他不停地交换不同的部位,问话却是相同的:“这里痛吗?这里痛吗?这里痛吗……”
我的回答有两种:痛,或者不痛。痛与不痛的比例大抵是二比三,或者是三比三,又好像是三比二。我不能准确确定,因为我不记得说了几次痛,或者不痛。
最后,医生变换了问话,好像还有点生气:“这里到底痛不痛?这里呢?这里呢?这里?这里?”我分不清这里痛还是不痛,那里痛还是不痛。医生的手在我的肚子上开始杂乱无章地游走,我的感觉也是杂乱无章的,我想知道是该痛呢,还是不该痛呢。
我正犹豫间,医生大手一挥:“去抽血,取大小便吧。”
我去了一趟抽血处,又去了一趟卫生间。回到输液室,几瓶注射液已“叮叮当当”挂在架子上了。
妻子强烈要求让我住院,医生说:“等检查结果出来再说吧。”
妻子看着我蜷缩在椅子里,像头乌龟,又说了一句:“还是住院吧,住院一边观察,一边等待检查结果。”
医生说:“初步诊断为急性肠胃炎,打几瓶水,消消炎再说吧。”
妻子说:“绝不是肠胃炎那么简单。他小时候就经常肚子痛,最近一年来,又经常痛,打过几次消炎针,也吃了各种消炎药,还吃过消食片,总止不住,时不时地痛,痛得大喊大叫,严重到影响家庭生活。”
妻子见医生不理她,便退了出来,嘴里还嘀咕着:“我还从没见过这样的医院,病人要求住院还不让住。我只听过病人不要求住院医生强行要求住院的医院……”妻子嘀咕完,对正在给我打针的护士说,“他是我老公,我最了解他,他不是肠胃炎那么简单的,他要住院,他真的需要住院。你去跟医生说一下,让他开一张住院单吧……”
护士纤细的手指弹弹柔软的导管,说:“医院现在都是病人,住院部全住满了,连走廊上的加床都没有了,还不停地有人打电话来要求住院。钻后门的我们都没法安排,当多大官的我们也没办法,就是谭城市的市委书记、市长来住院,我们都没法安排。”护士在我的手背上又绕了一趟胶布,说,“打完这几瓶吊针水就不会痛的,不痛就可以回家了……”
妻子还想说什么,我忙制止她。我去拉她的衣袖,我只想随意地去拉她一下,我没有想用哪只手去拉她。我去拉她时,那根洁白而柔软的导管也斜上了她的衣袖,铁架上的瓶子也跟着晃了一下。妻子“哎哟”了一声,不管她的袖子,反托住我的那只手,惊叫了一声:“小心你的手。”
我这才发觉,是用了打吊针的手去拉了妻子的衣袖,但我的手一点都不觉得痛,我只是捂着肚子,对妻子说:“没事,打完这几瓶吊针水就不会痛的,不痛就可以回家了……”
我说了我没病,我有多大的病呢?对不起,让认真负责的医生们忙坏了,让美丽可人的护士多费口舌了,让忠贞不贰的妻子吓坏了。连医生都说我没什么大病。我打了五瓶药水(医生妥协,将六瓶改成了五瓶,尽管如此,我还是认为他坑了我),从上午十一点打到下午四点,虽然连中餐都没吃,但我一点都不饿。我觉得,那五瓶水在肚子里晃晃荡荡,在欢快地跳舞唱歌,它们把疼痛压死了,或者消失得无影无踪,再不能翻身了。
我说了,我真的没病,我又能大吃大喝了,又能读书写作了,甚至能远地出差了。我想,通过五瓶吊针水,我以前的疼痛应该彻底地消灭了。五瓶啊,我长到四十一岁,四十一年里的吊针水,总共加起来也没有五瓶啊;四十一年,最渴的一次,喝的水最多也不过两葫芦,折合成瓶,我想,最多两瓶。五瓶啊,我庆幸没有被撑死,庆幸我没病,以我健康强壮之躯,装下了五瓶吊针水,竟然一点事都没有,而且,痛感还消失了,这是多么奇特的事啊!
我差不多想唱起歌来,如果不是看到妻子阴沉着脸,如果不是看到儿子皱着眉,如果不是听见母亲自言自语,我真想放出声来。
他们什么心态呀?他们唯恐我有病,他们见我捂着肚子蜷缩成大王八才高兴?他们见我一身轻松欢天喜地倒满是忧愁,他们什么心态呀?他们要我怎样他们才舒畅呀?
我说过了,我絮絮叨叨几十年,我说过无数次了:我没病我没病我没病我真的一点病也没有,为什么大家都盯着我不放,都怀疑我有病呢?为什么大家都逼着我住院治疗呢?.
难道我真的有病吗?……真的吗?真的真的真的吗?我的肚子怎么又痛了起来了?先是一个点,一个芝麻一样、沙粒一样的点,然后,慢慢慢慢慢慢地,向周围弥漫开来,有点像用毛笔挫了一下,接着,越来越粗,弥漫成了一小片、一大片,再接着,变成了潮汐,黑暗的潮汐,铅块一样的潮汐,持续性的、阵发性的、转移性的,好像一处是,又好像整片是。不对,周围皆是,最后,我没有知觉了,一下——我晕倒在办公室的桌子上。
吊了五瓶水之后,不到两个月,我再一次进了医院。这次是住院,这是我生平第一次住院,而且,住的是省第一人民医院。
我一直坚信,我不会有病。尽管我无数次听亲朋好友说过,省第一人民医院无愧于其“第一”的称号,一定是全省最好的医院,我仍坚信,我必将与这里无缘。
然而现在,我住进了省第一人民医院。我醒后才知,我已昏迷了一个小时,是医生把我抢救了过来。我是在抢救过来后坐在轮椅上,被护士推着去做B超时,看到长长走廊两边贴着的蓝色字体后才知,我是在省第一人民医院的。我眼睛迷离,思想恍惚;我不由自主,浑身乏力。巨大的疼痛,像闷响的锣鼓,充溢我全身。
我躺在检验床上,听见医生小声而急速地说:“以前没做B超吗?一看就看出来了,是急性阑尾炎,得做手术,把它割掉。”
朦朦胧胧中,我听清楚了,是阑尾炎。“阑尾”——一个陌生而熟悉的名字,就像一个人,一个以前无数次听过、知晓过,却从未谋面过,而且认为这一生可能都不会遇见的人,现在,忽然不期而遇了。而且,现在才知,那个坚信永不会遇见的“人”,竟然“缠绕”了我一年多,或者,从我的第一次疼痛,就已经“灵魂附体”。难怪,我无视它存在,我怠慢它,轻视它,它就慢慢地折磨我,这次,来了个总爆发,它彻底发怒了。
但是,我能凭着惊人的记忆力,确定下面这段文字来自某份权威医学杂志:不少人认为,阑尾可有可无,抱着“有病坚决割、没病可以割”的态度,而研究表明,阑尾可以分泌免疫物质,能增强对癌症的抵抗能力。
而我认为,下面这段文字是一般肝肠科医生都应了解的:急性阑尾炎是最常见的腹部外科疾病,任何年龄都可能发生,以青壮年为多见。阑尾为蚯蚓状盲管,与盲管相通处开口狭小,阑尾系膜短,容易扭曲,阑尾黏膜下淋巴组织丰富,常因增生、肿胀使阑尾腔更为狭小,粪石或其他异物易在此堵塞而造成阑尾炎或阑尾穿孔。
我不是医生,对于急性阑尾炎,不需要了解太多,我需要了解的是:阑尾不是可有可无。上帝造人,每一个部位,每一个毛孔,每一个细胞,都是有用的,它们各负其责,各有分工。我的B超医生坚决说“必须切除”,我当即反对:“我要保守治疗,请勿割去。”
我和妻子争执起来。我们的争执以她的失败而告终,我听她的口气像虚脱了一样瘫软下来。她抻长脖子,盯着天花板,叹了一口气,说:“好吧,割不割,让主治医生决定。”
好吧,现在我承认,我有病,但只是小病。
“你跟主治医生说说,就说我想保守治疗,别把我亲爱的阑尾割掉。”我近乎哀求妻子。我仰着头,我从下面看到妻子又涨红了脸,她的额头还有细细的汗水。她的脚步追着护士的轮椅跑,她的语言纷乱而坚硬:“一条臭臭的阑尾,留着有什么用?不割掉它,你就有永远的痛,我们也跟着你担心。”妻子又补充了一句,“你不担心,我们担心!”
我说:“我都不担心,你们担心什么?”妻子抹了一把汗水,说:“你说我们担心什么?你照照镜子,你看看你看看,你痛得全身湿透了,你湿透了,我也没少出汗。”
我说:“阑尾真的有用,不是一般的有用,而是非常的有用……”妻子也跟我绕起了口令:“有用有什么用?发炎了溃烂了阻塞了就没用,没用不割掉它,留着有什么用?”
我不跟妻子争辩,她没痛没病,有的是力气,我争辩不过她。何况,在争辩这件事上,男人永远争辩不过女人,女人不但有耐心,而且从不讲理。
妻子也不再跟我说话,她把主治医生叫到病房。主治医生像只又老又瘦的燕尾蝶,飘到我病床前。我挣扎着坐起身,“燕尾蝶”示意我躺下,说:“不要翻身!”他的话近乎呵斥,但我不怕!我虚弱而顽强地说:“1989年版的《实用外科手术学》一书,在《阑尾切除术》一章开篇即明确说,‘不要把阑尾手术当作小手术,它带来的问题很多’……”
“燕尾蝶”放软口气,问我:“什么问题呀?”我强忍住痛,望着惨白的天花板,像陷入恐惧的泥潭中。我挣扎说:“你以为我不知道?阑尾手术后容易引起肠粘连、肠梗阻、神经损伤、伤口感染、阑尾残端炎、疤痕增生……”
“燕尾蝶”说:“你懂得蛮多嘛,你懂得这么多,早就应该到医院来做个B超,现在,你跟我上阑尾课有什么用?你知道你得的什么病吗?你左一个阑尾,右一个阑尾,听得我都糊涂了,我看你只会纸上谈兵。我现在正式告诉你,刚才看了你的片子,你的病很严重,你不要以为是什么急性阑尾炎,不是!而是胃溃疡导致的胃穿孔,必须马上手术,切除一部分,缝补一部分……”
后面的话我没听清,或者听清楚了,可现在忘了。反正,两个小时后,我被急急地推进了手术室;又两个小时后,我被推了出来。
是的,我曾经一直认为自己没病。我坚信自己不会生病。好吧,现在,我承认,我有病。我曾以为,我有病也是小病。我这么年轻,我这么强壮,我这么乐观,我怎么会生大病呢?我想到的,也是B超小姐想到的,最多也只是急性阑尾炎——这是我想到的最坏结果。即使是急性阑尾炎,我也一定会慎重对待。有炎症,就要把整段阑尾切除吗?我听说,在西方某些国家的某些地方,为了杜绝患阑尾炎,人一出生,就把阑尾割掉,这纯粹是愚昧,简直是扯淡!这纯粹是反上帝、反人类、反文明、反……
没想到,我生了一场大病。不过,庆幸的是,现在,我真的没病了。我想,我真正的病原体——我亲爱的胃,经过一年多的生长、重组、新生,早已不是以前的那个胃了,早已是另一个胃了。不管是哪个胃,总之,它是健康的、充满活力的,它能容纳和消化我吞下的任何食物。
不过,事实上,我真正想告诉你的是:如今,我成了一名没有阑尾的男人。——这是妻子半年前告诉我的,她向我道出了手术结束后的实情。
那天,手术结束后,“燕尾蝶”把妻子叫到医生办公室,他用平静而舒畅的语气对妻子说:“感谢你配合我们,他已经阑尾穿孔了,幸亏早送来,不然,晚半个小时,会引起腹膜炎,就有生命危险,手术刻不容缓。我们拗不过你丈夫,是生命重要,还是阑尾重要,我相信你能说服你丈夫。我们割了他的阑尾,而没有动他的胃……”
我不知道,当时,妻子对“燕尾蝶”说过什么没有,她的讲述到此为止。我也没有问她,一个问题都没有问她,我甚至一句话都没说。
我想:有些事情,有些话,还是不必问、不必说吧?就像手术过后,起初,我很想问医生:伤口怎么会是在右下腹?但我终究没问。
其实,问了也未必有标准答案。就像现在,我倒弄不懂——
阑尾,究竟有没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