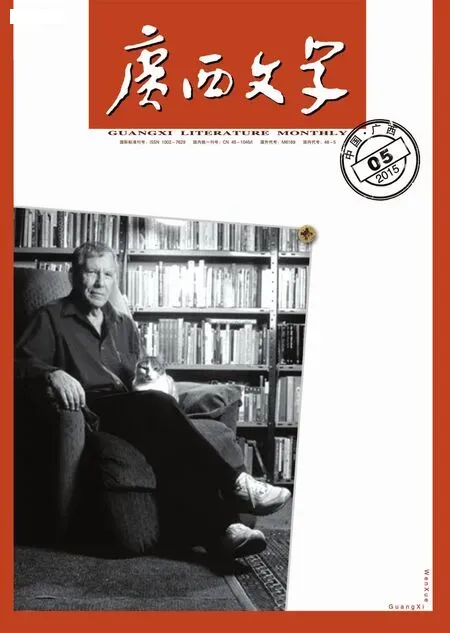凶 器
短篇小说·陈纸/著
平 原
我叫洪琦,是一名歌手。
一说到我出生的地方,眼前摇曳的尽是一望无际的紫云英与稻穗。阳光照射的角度是平的,它沿着天边,一路匍匐而来,与我对视;风吹来的角度也是平的,没有任何阻碍能让它改变方向、改变姿态,它直接拂拭在脸上,舒缓,自然。我的视线也是平的,一马平川,无所顾忌,肆意盎然。
我的道路也是平坦的。我家门前的那条水泥小马路,虽然不宽,但很妥帖,很安全,它托付着我,送我到乡里读了初中,到县里读了高中,到省城读了艺术学校。一帆风顺得让我有些诧异。
我很满足,像家乡田野上晃荡着大肚子吃草的小黄牛那般满足,它不愁苗草,还能听到溪水荡漾,听到雀燕婉转,还能看到油菜花烂漫,看到修竹轻弹。
我感觉的确应该知足。比起村里其他人家的女孩子,他们要么因学习成绩不好,初中还没毕业就出去打工了,要么因经济困难,考上大学也没上,我已算是很幸运了。
我说这些时,丝毫没有幸灾乐祸、落井下石的味道,更没有养尊处优、衣锦还乡的炫耀。我说的都是客观事实,我现在的心情平静无比、从容淡定,当然,用我父母的话说,是满足现状,不思进取。
随他们怎么说吧,他们手里能拎起多大石头,在我心湖激起多大浪波呢?
在省城艺术学校,我学的是舞蹈。
记得报到那天,我面前一位中年女子,在我身上上看下看,左瞧右瞧,一个劲地笑,笑了,还“啧啧”两声,说:“真是一比一,正好了呢,一个暑假,两个月,正好了呢。”
我当时听了,眨眼睛,以为她把我当成“金龙鱼”煮菜油呢。那位中年女子转了一下她自己的身子,伸出长长的、白藕样的手臂,搭在我肩上,说:“洪琦呀,报考舞蹈专业,准备好吃苦了没有?”
我说:“在家就吃过苦,家有五六亩田地,每年暑假都要下地干活。眼前的田地,这边看不到那头,一弯下腰,挥着镰,插着秧,一时半会儿不能直起来呢。”
那中年女子飘移过身子,搂了我一下,说:“难怪你腰身这么好,都是劳动锻炼出来的,不像城里女孩子,是天生出来的,或是吃出来的。”
我说:“再好也好不过您呢,您的腰身那才是真的好呢!”
那中年女子向我伸出手,我握了她的手,听她说:“我叫肖云燕,往后教你的舞蹈,还是你的班主任。”
我叫了一声:“肖老师好。”她应了一声,然后说:“你要记得你刚才说的话,你说你不怕苦,不怕苦好,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不怕苦好,我就喜欢不怕苦的学生。”
我走出报名处,下了几十级台阶,眼前是一块大操场,操场是一大块平坦的地,平坦的地上用绿色与红色涂了两大块,红色的部分为椭圆形,绿色的部分为长方形,红色绕着绿色。
我见过操场,还没见过这么大的操场。我小学、初中学校都建在小山坡的平地上;我上高中的学校在县城,周围的楼房挤挤挨挨,操场被挤得喘不过气来。相对之下,这里的操场真是大。
相比操场,练功房更大。说它“更大”,并不是真正的面积“更大”,而是对面的墙壁上装了一面镜子。我只能说,镜子是真正的大,我从没见过那么大的镜子。它高高地立着,长长地伸展着,把整个练功房扩大了一倍,把我们的动作全装在里面。
在练功房,在镜子前,我们没什么动作,也没什么秘密是隐藏的。即使有,老师也看得出来,因为她就站在我们面前。
老师的视线一马平川,像尖利的砂纸刷到我们的面前。我满头大汗,我浑身发颤,我大气连喘,但我还是尽量调整呼吸,镇定眼神,放松面庞。
我注视肖老师,不下百遍地听她说:“来,同学们,跟我做一个简单动作。好,非常好,没关系,很容易。来,脚掌落地,脚后跟踮起,开始走路,多配几个手的动作。对,就这样,像我这样。好,一只手放在胸前,一只手伸直,对,就这样,很好……”
我觉得,肖老师所有的目光都对着我,而我,刻意压抑住激动与自豪,我呼吸平缓。我偶尔低头,我发现前胸也一如呼吸一样平缓,我仿如穿越在整齐划一的稻田里,此时,稻花飞扬,轻风徐徐,我飘飘欲仙,美妙无比。
“来,非常好,同学们,我们换组动作。对,两只脚平移,手上下摆动。注意,看好了,像我这样,手的方向要不一样,最好柔软一点,好!像洪琦那样,洪琦做得很好……”
我看着肖老师的口型,我尽量舒展手脚,在一张大的地毯上轻歌曼舞,凌波碎步。我又听到肖老师说:“好的,像洪琦那样,脚掌落地,脚后跟踮起,走漂亮的步子。要小一点,再小一点,双手合十……来,再做一遍……”
肖老师的话像春风,将我缓缓托起。我极目四望,看到了更平坦的天地。
把我推下来的,是杨子玲。
杨子玲站在我身后,她扬起细长的腿脚,朝我屁股轻轻踢了一下,她的话也在我背后推过来:“你的头昂得比求偶的母鹅还高。”
我回过头,把位置放到她头的位置,笑了一下,说:“我没有呀,别说得这么难听,好不好?”
杨子玲的声音随着肖老师的一声“解散”,更加密集地向我撒过来:“你头昂得太高,挡住了我的视线,我光看你了,我光听肖老师说你的名字了……”
我推她一下,收住笑,说:“明天跟你换个位置,你站在我前面,总可以吧?”
杨子玲说:“你头昂得比我高,我胸不挺起来,也比你高。”
我低下头,笑起来了,我盯着杨子玲前胸,我真想伸过去捏它们一下,我“嘻嘻”两声,说:“我早看出来了,自从我俩住在同一间寝室,睡第一个晚上,我就看出来了,你的胸比我大,比我高,但我们学跳舞的是比舞姿,不比胸大小,是吧?”
杨子玲一只手搭在我肩上,说:“也是,每次跳跃时,我就感觉吃力,不像你‘太平公主’,一身轻松,所以,肖老师每次都表扬你跳得好呢。”
我说:“所以,大有大的好,小有小的好;平有平的妙,高有高的妙。”
杨子玲拍了我两下,说:“你过两年就明白了。”
一个学期形体训练后,压肩胛带,地面吊腰,杠上压腿,躺地分腿等,平静地在我身上经过,像每个月要来的那一次,不断往复,像不断造访的客人。我先是以茶酒迎接,后来,只微笑打声招呼,它们即使不期而至,我未及料想,也能从容应对。
“要学跳舞,就得这样。”我好像早就知道老师会说这句话,而且,会不停地重复,像每天早晨准时响起的闹铃。
其间,云起雨落,晨昏交错,有三四位同学还没进入到第二学期,便从舞蹈班消失了。其中两位,转到音乐专业班去了;还有两位,被父母的轿车接走了。有父母不止一次来到学校,看到自己女儿,腰弯折得不成人形,他们惊叫起来:女儿没饭吃,就是饿死,也不能吃跳舞这门饭呀!他们的表情比女儿做舞蹈动作还夸张,他们提前为自己的女儿判决了前程。看着那几位同学瞬间被解放的表情,我报之一笑。随后,我便不解。
杨子玲说:“你以后会明白的。你注意到了没有,转到音乐专业班的那两位同学比我们高挑漂亮,被父母领走的那两位同学,不但长得比你我高挑漂亮,而且,家里还有钱。”
“难道高挑漂亮就能转到音乐专业班去吗?难道高挑漂亮、家里有钱就可以不用学习吗?”我不明白。
杨子玲说:“至少可以不用学得像我们这么苦。”
我说:“学舞蹈苦,学其他,可能照样苦,说不定比这还苦。”
杨子玲眨巴了一下眼睛,说:“看来你是真的一点都不懂,她们都有杀伤力很强的‘凶器’。”停了三四秒钟,杨子玲又说,“跟你打个赌,下个学期,音乐专业的两位同学就能上台表演,获得的掌声可能会比你这一辈子得到的掌声都要多,而我们,要等到猴年马月。”
我说:“那又怎么样?”杨子玲说:“不怎么样,有了‘凶器’,她们就能早成功。”
第二个学期,我们开始芭蕾舞基本功练习。我问肖老师:“我是学民间舞的,关芭蕾舞什么事?”肖老师说:“学点芭蕾对你们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后面有整整一学年时间学民间舞呢。”我说:“不急,是吗?”肖老师笑了一下,说:“对了,不急,慢慢来。”
高 山
学期结束,举办一场文艺演出,学姐、学哥们的舞蹈确实跳得那个好呀!街舞把我的头都转晕了,探戈跳红了我的脸,如果让我跳,我肯定跳不出来。我拍着杨子玲的腿说:“快看,人家的踩堂舞跳得多好啊,还有扇子舞,唔,还有那个……那个瑶族的度戒舞,将来我们就是那样了,那身段,那动作,流水一样!”
杨子玲说:“不管怎样,我还是喜欢唱歌,嘴一张,学得容易,来钱也容易。”
我说:“那你为什么不也转到音乐专业班去?”
杨子玲说:“转得了我早转了。”
我问:“难道你没‘凶器’吗?”
杨子玲打了一下我的手臂,说:“有,但不厉害。”
我又问:“什么样的‘凶器’才厉害?”
杨子玲指着舞台上两位刚出场的女演员说:“她们那样的才厉害!”顿了一下,她斜我一眼,补充说,“你的‘凶器’最不厉害,你连‘凶器’都没有。”
我看不清舞台上刚出场的两位女演员,我今天忘了戴眼镜,眼镜放在寝室里。我眼前只有两团黑白相间的影子,杨子玲在我耳畔说:“看,她俩是我们曾经的同学呢。就是她俩,李欣仪与杨佳!”
我“哦”了一下,说:“她们歌唱得不怎么样,音乐专业就没别的学生吗?除了她一年级的,还有二年级、三年级的学姐学哥呀。”
杨子玲说:“她俩有‘凶器’,专门对付校长,还有其他男人的。”
我说:“不要乱讲,这是学校,不是哪家不正规的公司和酒吧。”
杨子玲说:“看见了吧?她们胸前那两团包子,把裙子都快撑爆了,还才包住一半。我看是故意的,干脆全扯下来得了。”
我说:“这是学校,你是女生,这样说话不好听。”
杨子玲说:“你说不好听,可人家男生喜欢听。你看他们鼓掌起哄的样子,你看他们眼珠子爆炸的样子,他们就希望我的话能兑现呢!”
我懒得跟杨子玲说话,我觉得她的话虽然有几分道理,但总体来说,还是偏激的。我想看曾经是我同班同学的李欣仪与杨佳唱歌。我的目光从杨子玲身上转向舞台。我的目光被人群完全挡住了,他们个个兴奋地站起来,耸立成了一座山峰,把我完全隔离在人浪之外。我感到压抑、窒息,有点喘不过气来。我也站起来,抻长了脖子,我的目光越过高山,眼前热浪滔天。我还听到一声声尖叫,屁股下的椅子“嘎嘎”作响。我忙低下头,用双手压住椅子,但它根本不听指挥,它执拗地要向前移动,我甚至听到骨头脱臼的声音。
舞台上,歌声越来越高,我甚至怀疑是不是那两位曾经的同学发出的声音。她们平时晃晃荡荡的样子,她们平时走进练功房懒洋洋的样子,她们平时昂着头斜着眼连话都不屑讲的样子——我对她俩的印象太深了,没想到,这会儿有那么大的能量,有那么大的爆发力,是谁、是什么赋予她们这一切?
不知何时,杨子玲跟着尖叫起来。她把两根手指放在嘴里,把两边的腮帮子塞得鼓鼓囊囊,胸脯也跟着晃晃荡荡。突然,我心里升腾起一种复杂的感觉,是不屑?不平?不甘?不忍?不愿?不服?好像什么都是,又好像什么都不是。
我心中泛起一种从未有过的波澜,眼前的一切,似不解,又陌生,像在做梦似的,我在高处飘浮,好像任何一个人,任何一种声音,任何一种力量,都能轻而易举地,把我托举起来。我飘浮在高处,烟雾升腾,什么都看不见,模糊一片。
那台晚会上,李欣仪、杨佳让我感觉到“凶器”的厉害了。杨子玲整个一天都在唠叨这件事,她的话题始终没有离开李欣仪与杨佳。“李欣仪与杨佳”成了杨子玲的口头禅,那个叫“凶器”的词也反复出现,像暴风骤雨中偶尔降临的冰雹,时不时地砸到我心窝。
我觉得这一天逃不脱“凶器”的追杀了。晚上,在寝室里,在床上,杨子玲还在讲李欣仪和杨佳,还在讲她俩合唱的那首《最炫民族风》,我的耳膜好像还没从那高山大海般的声浪中脱离出来,我捂住耳朵,对着杨子玲咆哮:“不要再说了,不要再说了,好吗?求求你了我求求你了!”
杨子玲见我松开了双手,接着说:“《天鹅湖》呀,《睡美人》呀,《胡桃夹子》呀,《罗密欧与朱丽叶》呀,听呀,看呀,能踮起脚尖走两步就不错了,学点皮毛有什么用?人家李欣仪与杨佳寒假都到酒吧、夜总会里挣钱去了,一个晚上跑两个场子,一个月能有三四千块钱的收入,而我们呢,把腿练痛了、练瘸了,也没人找你,更别说给钱了。”
我说:“我相信‘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我们学舞蹈的,还没练‘软’,还没练‘开’,就想登台,就想挣钱,做梦一样难。”
杨子玲说:“我不跟你争,我可不想练踮脚尖了,还有,我也不想学《舞蹈运动生理学》,不想学《舞蹈编排技法》和《中国舞蹈史》。我白天练得手脚痛,晚上啃那些课本,头痛,我全身上下、里里外外,哪里都痛,我痛得不想动。你还有父母心痛,我父母呢,整天在为我的学杂费担忧,还一个劲地问,毕业了能包分配吧,不包分配找不到工作怎么办呀。听得我把之前教的舞蹈动作全忘了。”
我说:“过两天,省电视台举办一台文艺晚会,听说要到我们学校来挑伴舞演员,听说,晚会请了好几位港台明星,能为他们伴舞就好了。”杨子玲说:“那也是在二、三年级学生中挑,哪轮得到我们?”我说:“肖老师说,我们班有两三个名额,要我们去锻炼锻炼。”杨子玲说:“肖老师只对你说,我却不知道,肯定是内定的名单,我肯定没戏。”我说:“到时我们一起去,你不要自卑。”
电视台来学校挑伴舞演员,整个练功房热闹非凡,像煮热的汤掀开了锅。有两个人,进练功房朝我们比画着手。看他们的脸上,不耐烦,还皱着眉头。
学校里的老师说:“各位同学,出去出去,导演说到外面去,大家站到操场上去。”
大家一边起哄,一边推推搡搡,往操场上跑。外面阳光很大,大家都用手遮住额头,留一双疑惑的眼睛,看着那两位导演。我慌忙寻找班上同学,想着面试时跳什么舞。我双腿微微发抖,声音也有些沙哑,我的目光在人群中穿梭,我只会本能地喊:“杨子玲!杨子玲!”
我看到杨子玲,被那两个人中其中一人拉住了,那个人的眼神在杨子玲浑身上下抹了一遍,然后,往前一扯,说:“就是你了,你算一个!”
我朝杨子玲走去,在快拉住她时,那两个人中的另一个人拉住了我。他的目光蜻蜓点水般地在我身上停了两三秒钟,轻轻地推我一下,说:“对不起,这位同学,请站到那边去。”把我与杨子玲隔开了。
四五分钟后,操场上的我们被分成了两个阵营。我拨开人群,想到另一个队伍里去找杨子玲。周围的同学都白着眼,嗤着鼻,纷纷散去。我的身子在零乱的人群里左右晃荡,雨打浮萍般,我的内心感到了一种急促和焦灼。
只两三分钟,周围的同学像初冬里掠过天空的小麻雀,尖厉地叫着,然后,飞快奔向自己的巢。操场上,剩下我,还有另一个阵营的十几位同学。我与他们楚汉界河,苦苦相望。接着,我像突然惊醒,四处寻找老师,寻找肖老师,寻找最欣赏我、最看重我的敬爱的肖老师。我在原地打转,我的目光转了好几个三百六十度,我没看到肖老师。而就在十分钟前,她带我们进练功房,她还拍了我的肩膀,我当时满怀希望。
这时,我看见杨子玲从那个阵营露出来,冲我意味深长地笑着。我还看见那两位电视台的人与她们嬉笑,她们的笑容一律花枝乱颤,有的还互相追打,张牙舞爪,向对方前胸抓去。
我低下头,发现我一无所有。
第二天,我见到肖老师。她迟疑了一下,向我走来,对我说:“昨天真是太气愤了,他们哪里是挑舞蹈演员?简直是选美。他们说,首先要看三围,这样,很多功底好的同学吃亏了……”
我不知道该如何面对肖老师,我觉得是我的错。我辜负了肖老师,我悲抑难平,我波涛汹涌,被一股巨大惯性推上山峰,但瞬间又被甩到平地。
接下来,还有一年,我开始真正接触民间舞。我在之前的课本上听过,民间舞中,有斗牛舞、扇子舞、夫妻跳盘王、跳神舞……还有身韵课,还有创作实习,还有毕业论文,还有工作选择……我彻底喘不过气来,感到了窒息,感到了毁灭。我周身发凉,恨不得现在就倒下,四肢摊开,缴械投降。
可我还是我吗?还是以前的那个我吗?还是那个视野一马平川、肆意纵横驰骋的我吗?还是那个自信满满的我吗?
我做出了一个惊人的举动,我也要锻造我的“凶器”!
深 谷
刚开始,是平原燃烧,残云风卷;之后,是大地撕裂,抽丝剥茧;接着,火焰渐熄,渐熄,星辰升起,月色迷蒙,慢慢酣睡,毫不知晓。
火山醒来,熔浆涌动,撕心裂肺,一片混沌,盘古开天,轰然隆起,异峰峭立,惊世骇俗。
一切冷却,我的大脑冷静了下来,万物花开,生机盎然。我既然走了这一步,便毅然决然。我觉得这不是我一个人的表演,我只是像千千万万说不明、道不白的“默认者”中的一员,世界如此,社会依然。
在医院住了七天。第八天,医院安排我们同一批做手术的女生,去一家酒店的游泳池里做了一次体验。我们站成一排,立于一人造小瀑布前,不知从哪里放下水来,流水形成水幕,铺天盖地。向我们扑来。我们尖叫着,我们的身躯不堪一击,而我们身上的某个部位坚如磐石。
我扑倒在水中,掩住脸庞。我喜极而泣,羞涩万般。
这个长假,我过得意义非凡;这个长假,我成绩傲然。我走进校园,将胸脯包裹得严严实实,但仍然裹不住怦然乱跳的心脏。我知道,这种事,在校园外是一种评判,在校园的围墙内,又是另一种眼光。
我精神恍惚,做了一场长梦,梦醒了,要回去了。我感觉自己的步子有些陌生,有些异类,我不知道其他同学看出来了没有。
杨子玲没看出来,但她从我扭捏的身材上看出了一些其他东西。奇怪的是,我对其他同学的目光闪烁,唯一在与她对视时,我是镇定的。我甚至故意强调这种情绪,我把目光定得很久,与她对视很久。我们好像是在对抗某种恒久,竞赛某种力量。
我对视着杨子玲,她张大着嘴,我对她说:“走呀,看什么看,去冲凉!”
杨子玲发现了我身上的秘密,她一声惊呼,像高山坠入深谷的巨石,在洗澡房久久回荡。
杨子玲先前那种神采飞扬、不屑一顾的目光,在与我的对视中,慢慢黯淡了,软了下来,放了下来,接着,转换成了不解、怀疑、惊奇、妥协。
接着,她的话语像夜色中射出的支支响箭,在校园每个角落徘徊。我看见校园里子弹呼啸,落叶缤纷。我按捺住心胸,但按捺不住声响。不几日,我便成了“全国校园内第一例”“全国学生第一”“开中国舞蹈界先例”“开中国农村女学生之先河”……我没想到,没想到,世界上还有那么多奇特的组合词汇,那是一顶顶冷冰冰的、沉重无比的、钢的帽子,向我头上扣来。我步履蹒跚,我踉踉跄跄,我浑身疲软,我通身发烫,我如行尸走肉,我濒临瘫痪……
肖老师把我从练功房扯出来,她的目光像手术刀,盯在我的前胸。“手术刀”在托盘里叮当作响:“是真的吗?是真的吗?怎么能这样?你怎么会这样?”接着,她缓了口气,问,“你怎么想的?”
我摇摇头。肖老师仍不走,她的目光仍不走,我又摇了摇头,肖老师也摇了摇头。她刚想往后移动脚步,身子抖了一下,却往前倾了,她说:“好吧,但不管怎样,舞蹈总还是第一重要,训练还是第一重要,学习还是第一重要。”
我说:“肖老师请放心,我会更加认真地学好舞蹈。”
没想到,医院里把我的形象放在了他们的官方网站上,什么“特殊材料”,什么“国外引进”,什么“免费赠送”,什么“无痛手术”。我无语,这是当初签订协议时规定的,我无权干涉,这是我该承受与承担的,我没意见。
我当时想得那么纯粹,但没想到有那么多污秽。我看到那么多网友的留言,网上的评论,上千条、上万条,每一条都是一种凶器,刺向我同一个部位。
我对自己说:你既然有信心让它隆起,就要有信心让它挺立。
我管得住自己,管不住别人。我听到晚上有小石子砸击寝室窗玻璃的声音。一个人,躺在床上,很害怕。我知道,那些小石子,来自哪个方向。
那几天,杨子玲很晚才回来睡觉,都是凌晨三四点,才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进了寝室,踢掉两只鞋,倒在床上呼呼大睡。
几天后,我终于问她。她神秘地说:“我在一家会所跳舞。一个晚上跳四五支,能挣四五百块钱,平均每支舞一百块钱。”
我懒得信她,不屑信她,却又不得不求她。她拉着我的手说:“与其一个人睡在寝室里担惊受怕,不如跟我一起出去跳舞。”
杨子玲又说:“我晓得,你恨我,我不是嘴贱,没守住嘛。不过,你既然做了,守得住初一,守不住十五,是吧?你就跟我去吧,也算是我对你的补偿。别的同学就是跪在我面前,我也不会带她去挣这么好挣的钱。”
“会所”是“保健城”。保健城怎么有跳舞项目呢?我好生奇怪,脚步也放慢了下来。
杨子玲顺势拉住了我,把我往里扯。越往里,越幽深,一条长廊,淡淡的粉红淡淡的黑,望不到头。走到一段,闪出个人,拉住杨子玲,一个劲地催:“快点快点,上钟了!上次那位刘老板又点了你。”
跟着杨子玲,我进了一个包厢。我还没适应里面的光线,一个瘦长瘦长的男子,拎着西装站起来。杨子玲把我往前一推,说:“老板,她是新来的,我妹,你关照她一下哦。”
那个瘦子上下看了我一眼,笑眯眯地说:“也是你学校的?”杨子玲说:“当然,我同班同学,舞跳得最好。”
我本能地点了点头。
那个走廊上闪出来的人连忙把我与杨子玲隔开,杨子玲趁机走出了包厢。走廊上闪出来的人向我堆着笑,说:“早听玲子说起过,还以为请不到你呢,想不到你肯来。你跳舞真的全班最好?”
我本能地说:“哪里?”
“为客人跳一支舞,不长,三四分钟,然后给客人推油,会吗?”走廊上闪出来的人问我。
我连续摇了三四下头。走廊上闪出来的人又把杨子玲叫进包厢,对她说:“教教她。”
杨子玲把包厢门关上,反锁,把外套利索地脱了,露出性感的裙装。没有音乐,没有伴奏,杨子玲双腿张开,半蹲着身子,腰肢左右、上下扭了起来。她一边扭,一边慢慢把文胸吊带拉开。
我瞳孔放大,嘴巴张开。我看见圆锥样的两座小山,耸立在我眼前。说实在的,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她的,以前,我一直没有勇气面对,现在,它鲜花一样盛放在我眼前,我感到惊讶。接着,一种浓浓的羞辱感涌向心头,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
这时,那个猴子一样瘦的人冲了上来,用手指弹了一下她的胸,咬着牙,狠狠地叫了三个字:“宝塔山!”此后,他身子贴着杨子玲身子,跟着扭了起来,口里一直喃喃,“宝塔山,宝塔山,你个宝塔山……”
我这才知道,杨子玲在这里的外号叫“宝塔山”,我觉得那个瘦男子是在叫唤另一个人,他在叫唤另一个世界的人,那个人根本不存在于我们的周围。
我拉过杨子玲,觉得天已塌下来。此时,头顶碎石破裂,落屑纷纷,稍一犹豫,我们便会葬身其中。
我对杨子玲怒目圆睁,我拉着她,一路狂奔。我一路拉着杨子玲,杨子玲像一只纸扎的风筝,在我手中跌跌撞撞,飘零起伏。
杨子玲哭了,她甩开我的手,大声说:“我不要你来就好了,我怎么那么、那么贱!”
我搂过杨子玲,我们倚在一棵弱小的榕树下,彼此抱着,一起痛哭。
街上的灯光无声无息、凄凉无比。无数的人流、车辆,像电影拷贝,飞速地,一格格,瞬间掠过。
我们一下子迷失了学校的方向,我们不记得哭了多久。哭着哭着,突然,杨子玲笑了。我们手拉手,她在前,我在后。我们朝同一个方向走。我们都没有提“学校”那个词,我不知道去哪里,也没问杨子玲去哪里。
我们不知道跑过了多少条街道。迷迷糊糊的,看到前面一大块平坦的地方,我说:“这座城市到处都是人,每个角落都是人,每一缕空气都充塞着人的汗渍与呼吸,怎么有这么一大块白白的、平坦的地方呢?”
杨子玲好像也看到了,她兴奋地拉着我,大声地叫喊着:“走,走!我们去那里跳舞!”
我越跑越慢,我的胸前好像绑着两团冰冷沉重的石头。我蹲了下来。
我看清了,那块大大的、白白的、平坦的地方,是一片湖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