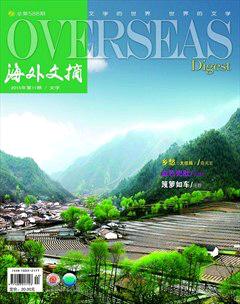老家乌桕
“莫拉克”来得那么凶猛让人始料不及,对竹乡安吉来说,它的凶猛不在于风的级别,而是引起的特大山洪暴发,就连西苕溪上的一座座石拱桥———乌象大桥、梅园大桥……也被无情地摧毁了,阻断了苕溪两岸人的通往,让人叹息不已。
我的老家就在西苕溪梅园大桥的北堍,紧贴溪边有一片可以说如今已是很难见到的乡土树种———乌桕,这次也连同惨遭厄运,“七姐妹”只剩下三棵了,如失去亲人般的伤痛,让人思念无限。
乌桕树系落叶乔木,夏日开花,黄色。结出的果子外面包着一层白色脂肪叫桕脂,可以制造蜡烛和肥皂。其种子黑色,可以榨油。它是我国特产植物的一种。我家“接管”这片珍贵的树林也属于偶然。因为当初它们并不起眼,伴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溪边土生土长的它们,经过精心的呵护而慢慢长大起来。它们结群生活,相依为伴,因它的珍贵稀少,又特别地漂亮,成为老家居住之处最动人最美丽的风景。
70年代末,乌桕树旁边的岸上还是一片当年“生产队”的老桑树,虬枝曲展,苍劲有力。每年的夏蚕过后,它们被一个个剪去上年长出的嫩枝,只剩下光秃秃的矮杆“下身”,像一个个紧握的粗糙拳头,看上去就更显得残老了。不知那片桑的特别年长还是另有什么原由,与桑结缘的乌桕又特像其貌,长得弯弯曲曲,生命顽强,倒有一种令人心仪的“资深美”。那个时候,我家已在这个村子里生活了近20年,居住的又是被称为“三进”的徽派建筑,但拥有的只有一间半上下两层带有个天井、且无出路的“偏房”。那时钞票奇缺,为了向往过上好的日子,不得已而另建新屋,与乌桕为邻的地址就这样相中了。
自认为“看中”的这块风水宝地,当初乡下的人们并不向往,有的说住在溪边经常发洪水很危险,有的说在路的“下手面”建房不好……当年我与母亲(父亲落实政策在桐庐复职了)不去顾及其他什么,也可能不懂什么可信什么,只觉得这里交通便利,开门即是路,又是村首,开阔敞亮,日照充足,很是心满意足了。农村也讲审批建房,有些老桑树也合乎情理地挖去了。其实老桑树的桑叶产量并不高,队里的人们说种下新桑生长很快,要不了两三年就是旺产期了。
这是我家自下放后第一次规划建设真正属于自己的家。用砂石、石灰、黄泥拌成的“三合土”垒成的墙身倒也坚固,被人们称之“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在上面搁上了“五孔板”,算是村里第一座“洋房”了。一家人十分欣喜。入居后,周围很快栽上了红竹、早竹、桃李、杏梅、泡桐、水杉什么的,眨眼之间就绿树成荫了。但过了数年,当时没有显山露水的乌桕“七姐妹”,此时已展现得特别吸人眼球,它们总是形影不离、姿态各异、风韵万千又亲密无间。
乌桕“七姐妹”的四季都很美。冬日乌桕树枝上虽然找不到一片叶子,但枝干上的乌桕子也完完全全脱去了外衣,身子特别洁白柔滑,它们有一簇簇的,有零零碎碎的,但顽强且牢固地缠于枝头。仰头望去,似繁星点点,像蜡梅一样“绽放”,在冬日的暖阳下犹如串串珍珠般闪亮。假如遇上雪天,它们洁白的身上形成了像雪白的朵朵棉花,显得高雅、华贵,美得精致了。
百花齐放、莺飞草长时节,乌桕好像还沉醉于长眠的寒冬,周围各种果木已如撑伞般伸展枝条着了绿装,它却与众不同,总是想把春天往后拖,不愿轻易吐出绿叶来。当它完全苏醒时,知了们也在它的周围放声歌唱了。此时,雪白的乌桕子仿佛才真正到了一个年轮,褪去了冬装而纷纷落于土壤,去寻找焕发青春的契机了。
乌桕的“春天”虽然姗姗来迟,但在冬日里孕育的生机在这个烂漫的时节更显得盎然勃发,它的全身活力四射,变得楚楚动人。“七姐妹”的探春,让周围的树木好像又把“争春”的热情让给了它们。此时,乌桕树随着片片嫩绿的绽放,继而迅速变为翠绿、墨绿……就在这片浓重的绿荫里,释放出数不尽的热烈的黄色碎花,轻风拂过,便会散发出特有的清香,让人舍不得弃花而去。就在这美妙又悄然的变化中,金灿灿的黄色碎花又会缤纷般的飘落下来,飘落到人的发梢,又从发梢间慢慢地滑落,使地面又变得火焰一般,点燃了无穷的激情,去拥抱夏日的到来。
这个时候,乌桕子也孕育完美了,结出串串绿色明珠来,掩映在盛夏的景色中。色胆的小松鼠此时也喜欢在“七姐妹”间跳来蹿去,知了们也当然有凑热闹的兴致了。金秋时节的乌桕树可谓浑身闪亮,会有别样的神韵。随着乌桕子的果型长大,内核充实,使叶片也醉得金黄起来。鲜亮的黄色叶片其形态虽然变化简单,但它不逊色于银杏叶片,同样透出珠光宝气,把整个秋天浸染得金碧辉煌,好像这个秋天要胜过春天一样,让人感觉永远不会有萧瑟、衰败的景象。
居于此又是20多年了,后来又将“三合土”改成了“八寸砖”和“琉璃瓦”,居家更加宽畅美丽了。这当中与景色相伴,心情又特别的畅美和愉悦。屈指算来,每年都有台风,每年少不了几场大水,记忆里有几次洪水的水位比“莫拉克”还要高得多,乌桕“七姐妹”还是未遭劫难,岿然不动。原想总会安然无恙的,不曾料想,今年的它们遭遇洪水侵袭,导致“死伤参半”。“莫拉克”的残酷无情所留下的遗憾,总让人难以琢磨和不得其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