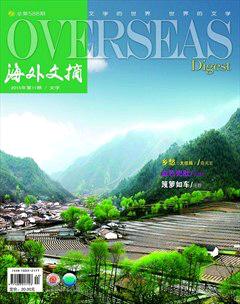血色兜肚
廖静仁
一
那一年,姐姐花儿十八岁。十八姑娘一朵花,何况她确实长得漂亮。但是漂亮有漂亮的烦恼,不仅姐姐有,就连弟弟牛儿也帮着姐姐有,他一直觉得好奇怪,不晓得傻五哥是从哪个口中学来的,“鹅蛋脸,丹凤眼,柳叶眉,嘴唇不薄不厚,嘴巴不大不小,鼻梁的线条均匀柔和,鼻尖儿微微有点往上翘。”傻五哥经常追在姐姐的屁股后面唠叨着,有时连口水都流出来了。这谁都晓得是夸奖姐姐花儿的,要是换了从另外的人口里说出来,花儿还不知会有多高兴,可偏偏是从傻老五的嘴里和着口水淌出来的,花儿就觉得特别地没有面子。
“那是老五喜欢你姐姐呢,喜欢到心里去了,心就开窍了,是有神灵在帮助老五,这是神来之笔呀!”从邵阳那边过来赊销菜刀和镰刀的张打铁就蛮爱听傻老五说这话,就在去年初夏,他还当着众人冷不丁地接过傻老五的话说:“翘里藏俏,端庄中显露出坚忍和倔强,要是我儿子能娶上像花儿这样的妹子做媳妇,我就帮他们到唐家观买一扇门面,全家人在小镇上安居乐业,一个静心刺绣,一个专门打铁,我就只乐得带孙崽。”张打铁六十岁左右,据说年轻时随老乡蔡锷将军做过侍从,难怪他能说会道,偶尔还咬文嚼字说出些让人似懂非懂的话来。他到过白驹里好多次了,是雀坪村与白驹村这一带的常客。
“你……你……”话都说到了这个分上,老五再怎么傻也是听得懂的,一开始听了张打铁上半截表扬他的话,心里还乐得怦怦跳,没想到这个打铁的,只是拿他当垫背,“你……你……”他或许也想要回敬张打铁一句什么,可一时又接不上腔来,急得满脸成了猪肝色。
“你这是凭什么呀?”没想花儿却猛一回头,似有几分娇嗔地甩过了一句话来,“以为人心也是你锤下的一块铁,随你打来打去,打圆打扁呀?我又没有见过你家儿子!”听那软软款款的话尾子,张打铁已分明感觉得出,聪明的花儿这话并不只是说给他一个人听的。
“那还不易得呀?我明年就把他带过来让你看看。他可是在宝庆府进过师范的,教他们的先生还去法国留过学呢!”一说到自己的儿子,张打铁的劲头就上来了,他又接着说:“宝庆府那只是旧时的称谓,如今早叫邵阳公署了,而邵阳师范是湖南较早开办的新学堂之一。我儿子去年毕业时还是全校文科状元,他和省主席何键都合过影。”只是当张打铁提到省主席何键这个名字时,反而就把声音压低了。
牛儿和姐姐都听得一脸疑惑,心中便有了一种想要早日见到真神的企盼。只是当着瞎眼奶奶的面,姐弟俩不好意思表现得太心切罢了。
“那就更加八竿子打不着了。”姐姐正抬首间,奶奶却先抢话了。
莫非张打铁并没有听明白奶奶话里的意思,或许是根本就没有听到?不然以他的心智和聪敏,肯定还能够说出一席让奶奶也舒心的话来。那一次,张打铁只在白驹村停留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就匆匆地赶往唐家观去了。走时还有意丢了一句话说:“我得提早去看看门面。”
在姐姐的眼里和心中,时间实在是过得太慢了。慢慢地过完去年的夏天和秋天,还有冬天……好不容易才终于盼到了今年的立夏节。
“我们明年争取早些来,最迟也不会过立夏节的。”这是去年张打铁离开白驹村时丢下的又一句话,并且他还用了“我们”这个字眼,姐姐虽然没念过几年书,但这意思她肯定是听得懂的。太阳正在慢慢地向西走,白驹村家家户户有的在磨米粉子,有的在剥水竹笋,女人们都在为男人和小孩准备一顿别开生面的风俗晚餐。一地一乡俗,白驹村人对每年立夏节是很看重的,这有民谣为证:“吃了立夏丸,能把大山掮;吃了立夏笋,长得齐楼枕。”民谣也是针对男人和孩子的。
十六岁的牛儿还只能算是一个准男人,大人们正在平秧田,他就在田塍上帮忙递送平秧田的耙子。当时只兴种一季水稻,简单有简单的好处,所以也就把农事耕作得特别精细,且还有大把的空余时间用来走亲访友串门子,用来发呆望流水,也用来想心事和想某一个人。
田垄紧挨着资江,一页白帆翻过去了,又一页白帆吻过来了,船头犁开清碧的资水,船舷两侧绽放出两股雪浪,而且呈八字形一路地开过去,把两岸青峰的倒影荡得一扭一扭的……这样的情景,是最近些天来姐姐有事没事带牛儿去村口的联珠桥时常看到的,还有傻五哥也照例跟在后面。他俩都看得特别地开心,仿佛自己的心里也绽开了一朵朵雪浪花。但是有一点牛儿却怎么也没有看明白,姐姐花儿口里说是去江边看帆船,可到了桥头却总是把目光往上游的小镇唐家观那边睃过去,还时不时把脚尖儿都踮了起来。她这是在望什么呀?就连傍晚了三个人回家里去时,也总是姐姐走后面,还不时回过头去。
此时的牛儿就在田塍上负责给大人递送平田的耙子,他又把目光向村口的联珠桥方向睃了过去,也就在这抬首的一瞬间,他就看见有一个黑瘦老头,正沿了纤道也是官道的沙石路远远地从唐家观那边走来,并且上了联珠桥,后面还跟了个挑着铁器担子的年轻人,比老人要结实一些,虎背熊腰的身板。牛儿不禁多看了一眼,见老头和后生过了联珠桥后,又向左一拐,就踏上进白驹村的那一条青石板村道了。渐渐地,他已经看得很清楚了,老头的手中还握着个铁搭子。
“是张打铁带儿子来赊销菜刀和镰刀了。”牛儿在心里高兴地说。
这时牛儿马上就联想到,姐姐原来是去桥头望张打铁和他儿子的。他想去把这一好消息告诉刚从对面山上扯水竹笋回家的姐姐,刚一起念头,却被岩山伯喊住了:“牛儿———把平田角的窄耙子递给我。”平秧田得换三次耙子,田心用宽耙,田角用窄耙,最后用铁耙收拾。
“哎———好嘞!”牛儿答得好爽快。岩山伯是在帮他们家的忙。
牛儿从小就没有了父亲,也没有了母亲,他和姐姐花儿是瞎眼奶奶一手拉扯大的。奶奶的眼睛原本是明明亮亮的,六十岁那年都还能飞针走线,尤其一手刺绣活,更是让村里的妇女和姑娘们羡慕得要死。
“首兆奶奶,能教我做刺绣活么?”爷爷首兆是驾毛板船丧命的。
“婶子,我虽然粗手大脚的,却心细呢,能当你徒弟吧?”
凡是对找上门来的大姑娘或者是哪家的儿媳妇,奶奶总是笑笑地说:“针和线也是灵性物,交道打得次数多了,心里头有它们了,针线也就会跟着你的心思走。”老人家稍顿了一下,忽然像想起了什么,又接着说:“要不这样,等牛儿他爹娘下一次送山货去汉口,我要他娘多买几尺缎子布和彩色丝线回来,总不能把花绣在麻袋上啊!”
但是,吃水上饭的牛儿他爹娘一去就没有再回来,在过八百里洞庭湖时,途中遇上风暴,人与船均未能出湖就葬送了鱼腹,连捎信的人也没有一个。往返汉口的时间已过去好多天了,又过去好多个月了,奶奶却每天站在联珠桥头望着资水下游的方向,一叶又一叶白帆从眼前翻过去,就是不见自己家帆船的影子……寒露过了,霜降来了,奶奶的老眼经不起风寒,竟然在一个下大雪的晚上突然双目失明了……
那一年,姐姐花儿不满五岁,弟弟牛儿还只有三岁。
但瞎眼奶奶毕竟还是带着他俩挺过来了。家里的两亩多水田和几亩山地,是请邻居家岩山伯耕种的。说是请,其实则是按收成总数五五分成。岩山伯是个忠厚人,伐木、解板、务农是把好手。但家里人多田少,大儿子娶妻生子后分了家,二儿子三十了,还是单身汉,小儿子老五比花儿还大,满二十岁了,四肢发达,却呆头呆脑,只知道一天到晚追在姐姐的屁股后面跑,还“花儿,花儿”地叫得馨甜,姐姐都烦死他了。可奶奶却总是帮着人家老五说话,“你看看老五多仁义。”
“嘿嘿,老五仁义,老五仁义!”傻五哥接这句话倒是蛮快的。
“只晓得仁义仁义,仁义要能当饭吃就好!”渐渐长大的花儿懂得奶奶话里的意思,那时的她要求并不高,但生儿育女总得要有饭吃呀!便把两条长辫子往后一甩,朝傻五哥说:“去,去,帮你爹做工去!”
老五只听花儿的,当真就悻悻然走了,只是没一袋烟工夫他又来了。
“做人要懂得知恩图报。”老五转背,奶奶就干脆把话往明里挑。
“你干脆哪天把我当猪狗送人算了。”这次姐姐的话说得很冲。
“那还不是把花绣在麻袋上啊!”牛儿倒是蹦出了一句经典来。
这是去年张打铁走后祖孙仨的一段简短对话,也是头一次正面交锋,姐姐花儿知道奶奶把她和弟弟拉扯大不容易,所以对奶奶也就特别孝顺,唯一在对待傻老五的事情上不那么谦让。弟弟牛儿懂事早,穷人家的孩子基本上都这样,也许就是因为懂事早,所以他特别护着自己的姐姐,“我才是家里的男子汉!”牛儿总是自豪地对花儿说。
“你呀!快些长吧,哪天姐姐我真嫁人了,你还得照顾奶奶呢。”
“姐,你真会嫁到唐家观吗?”只有牛儿最懂得姐姐的心思。
“八字还没一撇呢。”自去年张打铁走了后,花儿的心就乱了。
“那……那我也要……要去唐家观。”傻老五接话总是不择时候。
“要要要,要你个头哇蠢脑売!”花儿直气得胸脯一鼓一鼓的。
“老……老五不蠢,老五……仁……仁义!”但老五一急就结巴。
“好好好,你不蠢,你仁义。是我蠢总该行了吧?”花儿说这话是有底气的,她有着一双天生巧手,能无师自通把刺绣活做得十里八村都闻名。从十二岁那年起,唐家观镇上就有一家铺面专门经营她的绣品。她绣的富贵牡丹,花瓣上还带着欲滴未滴的露珠儿,她绣的丹凤朝阳,那展开的一对凤翅像是在凌空颤动,那一颗喷薄而出的朝阳,更是暖暖的都热到人的心里头去了……但瞎眼奶奶看不见,她也不管这些,“外地人是靠不住的。像你岩山伯一锄三棵粟,多实在。”
这也是去年张打铁走了以后,奶奶给孙女花儿的告诫。
姐姐双手搓着她那对乌黑的长辫子,埋头看了眼自己气得一起一伏的胸脯,便悄无声息地走开了,身后却始终跟了一条尾巴。“外……地人靠不住的,外地人靠不住的。”跟在后面的尾巴说。当时牛儿还真想多说几句,他不明白奶奶为什么要这么固执。人家张打铁怎么就不实在呢?牛儿从小就会唱那一首“张打铁,李打铁”的民谣,也熟悉了大人们说过的,有关于邵阳人一路赊销菜刀和镰刀的种种美谈。
“奶奶,你这样会害了我姐姐的!”弟弟牛儿也终于忍不住了。
二
白驹村的孩子们,从小就会背诵的不是《三字经》,不是《弟子规》,而是一首民谣:
“张打铁,李打铁/打把菜刀送姐姐//姐姐说她不要/转背送给嫂嫂/嫂嫂抿嘴笑笑/帮着哥哥讨镰刀//镰刀割麦又割稻/还能上山割芭茅//”
唱着唱着,话锋一转,孩子们又重新起题了,声音还会越来越响亮:
“小寒已过大寒来/满山满垄白皑皑/姐姐两眼都望呆/雪融春水桃花开//”
连三岁的小孩都会喊,童稚的歌谣就像春天的阳雀,声音亮亮的,也很婉转,又如山涧流泉,叮叮咚咚,能润泽人心……只是花儿的脸上却没有了多少笑容,还总是把一双幽幽的目光投向资水上游的远方。从秋到冬,又到了春天,冰雪化了,梨花和桃花也都开过了,紧接着就是立夏节要到了,姐姐到底是在望谁呢?远方又是在何处呢?弟弟心想,应该是过了九峡溪的联珠桥,再沿一条纤道也是官道往上走的小镇唐家观吧。
“铛———铛铛———”铁搭子清脆的声音由远而近地飞了过来,不一会儿又是一声“赊菜刀、镰刀啊———”的男高音喊响了,刹那间,满垄满村都在回应,“铛———铛铛———”,“赊菜刀、镰刀啊———”
这声音对于白驹村人而言并不陌生。每年在初夏时节,都会有从邵阳那边的铁匠过来赊销他们的产品。若不是张铁匠,就会是李铁匠或石铁匠。他们是出发前就分好了路线的,每隔三五年就相互交换一次。为什么要交换路线呢?“是为了求一个公平嘛!”这话也是张打铁说的,见人们还听不太明白,他又接着说:“我们邵阳人呐,都特别地抱团,出了门就像是亲兄弟,互换路线时结算多少也从不在乎的。”但是在这几年里,却年年都是张打铁从白驹村路过,连老人和孩子都认得他了,都和他混得很熟悉了。人们一律都称呼他张打铁。他的手中照例握着一个铁搭子,那是由两块不厚不薄的铁板串在一起组成的,形似逢年过节时打莲花闹上门讨喜钱的快板,也许是年长日久的缘故,铁搭子敲击得两头都发亮了,所以声音也特别地亮。也有人说那就是两块钢板,但无论是铁板还是钢板,人们都叫它铁搭子。
“铁搭子又敲响了,肯定是张打铁过来了。”
“也说不准今年是换成了李打铁哩!”
“不会吧?邵阳帮是有意照顾张打铁,说他儿子好到这边发展。”
“石铁匠好像已经有十多年没来过了吧?”
张打铁的喊赊声还没有亮嗓,在田垄里劳作的农人们就开始猜测了,当然还有在家里磨米粉子和剥水竹笋的主妇和伢妹子,他们中有好奇心强的,也或侧起了耳朵或伸出了脑袋来。其实后者还更有理由盼望着铁匠的到来,因为挑着一副铁器担子的张打铁或者李打铁,从将近两百里远近的邵阳那边过来,一路上得经过好几个县城,而且做铁匠的心又特别细,每次都是会顺便进一趟南杂百货店买了好几种颜色的丝线或糖粒子在身边,碰巧在哪户人家的家里寄宿或搭伙吃一餐便饭,他就会分送一些给人家当酬谢。出门在外,不能欠人情太多。
但是人们并不知道,今年最盼张打铁来的人是牛儿他姐姐花儿。
“是张打铁来了!”最先认出来人的就是站在田塍上的牛儿。“后面还跟了个挑铁器的年轻人。”他又接着补充的时候,张打铁的喊赊声便起了。“喊赊”是一个动词,但对于邵阳铁匠而言却是个名词。
这邵阳人真是会做生意,有专卖剪刀的,也有专卖菜刀和镰刀的。听说那地方山多田少,家家户户都有男人从事手艺活,而且是做铁匠的居多。但当地的销量肯定有限,于是精明的邵阳人就想出了一个大胆的销售办法———那就是冲出邵阳,走村串户满世界去赊销,这里所说的满世界,其实就是沿着资水的南北两岸往下游走,口号是质量不好来年不要钱。他们既然敢这么说,就没有质量不好的,一路过来也就没有要赖账的。这已经延续很多代了。到了后来,为了方便客户起见,铁匠们又有了新的发展,收账时也可以不付现款,用白米或稻谷代也行,他们收了抵账的粮食后,再到途经的小镇粮店去换成铜钱或现钞。这明明是给了人家方便,但邵阳人却豪爽地说:“吃了百家粮,活得寿命长。你看我们邵阳人多精神,打铁的像是铁打的。命硬!”
“赊菜刀、镰刀啊———”张打铁的喊赊声还没落音,牛儿老远就迎了过去。他跑得比狗还快。因为往年每一次都是岩山伯家的傻老五捷足先登,却不是为了给姐姐花儿讨彩色丝线,而是他自己想要吃糖粒子。这次牛儿还摔了一跤,但他并没有喊痛,爬起来又往前赶去。
“张打铁,去我们家吧!”牛儿还告诉他,姐姐在家剥水竹笋。
“还是牛儿懂事。”老打铁笑笑地说:“我帮你带姐夫哥来了。”又赶紧从布袋里拿出糖粒子给牛儿,但牛儿没有接,只在前面领路。
“真的会是我姐夫哥么?”牛儿没有问老打铁,也没有问那个年轻人,他只是在心里问自己。“我们还是快点去家里吧!”牛儿也没说姐姐在等他们。他的眼睛里还飘过了一抹云翼,稚气未褪的脸上也似乎漫涨了几许忧郁,只是这细微的变化那父子俩谁也没有觉察到。我奶奶不会又为难张打铁吧?牛儿偷偷地望了一眼英俊魁梧的“姐夫哥”,心里还真是有些七上八下不踏实,三人不觉就进了堂屋。
“嫂子你还好吧?”老铁匠一如既往地客气。奶奶照例是背靠神龛坐着,这是老人固定的位置,自从她双眼看不见以来,几乎每天都坐在那里。张打铁给奶奶先请过安,又回头说:“青儿,快叫奶奶。”
“是张打铁啊?你又———又来了!”奶奶的话冷冷的,还有意把一个“又”字重复了一遍,把音也拖得老长,而且并没有理会后面跟着的年轻铁匠,只把手中的拐杖一扫,趴在她身边的黄狗挨了重重的一杖后,猛一蹿就躲到禾坪外那棵老槐树下去了,汪汪地叫个不停。
“叫什么叫哇———你这白眼狗!”奶奶这骂声肯定是一语双关的。谁都晓得奶奶的眼睛瞎得精,虽然看不见,但她该知道的全都知道。
“你家黄狗是在欢迎我们呢!畜与人同,只是我们听不懂它的话而已。”给了一个下马威的老铁匠不但不在乎,还笑笑地回了牛儿他奶奶一句同样是一语双关的话。他毕竟是跟随同是邵阳人的蔡将军打过仗的,连死都不畏惧,更何况他后来自学徒那一天起,师傅就交代过要能吃得三坨热屎,走江湖的人什么样的委屈没有受过呢?
但没想到后面那个叫青儿的年轻人还真不愧是进过新学堂的,虽然一担铁器仍直挺挺挑在肩上,却也不卑不亢地就叫了一声“奶奶”。
“我要吃糖,我要吃糖!”这时,率先从灶屋里跑出了傻老五来。
青儿却一点也没觉得惊讶,忙放下担子,顺手就替爹将一捧糖粒子给了傻笑着的老五。姐姐花儿应该早就知道张打铁父子进了堂屋,只是在等时机罢了。老五话音未落,花儿就一手端着一杯茶水出来了。
“牛儿你还不快去拿凳子。奶奶不是从小就告诉我们,白驹村虽然是个穷地方,凳子还是有的嘛,进屋都是客,连起码的礼貌都不懂,这不是丢我们白驹村的人啊!”姐姐花儿的话很轻,音却落得很重。
像是专门过来打圆场似的,不一会儿堂屋里就挤满了人,一双双目光投向了铁器担子,女的挑菜刀,男的选镰刀,也有不挑菜刀不选镰刀只打量年轻铁匠的,“张打铁,这是你儿子吧?他比你英武多了!”
老铁匠笑出一脸自豪来:“这才叫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嘛!”又重复了一些请多包涵之类的客气话,然后话题一转,说:“他今后就留在唐家观街上打铁了。也免得我年年岁岁这么远来给你们送货哩。”
此言一出,有两个人的脸色随即就形成了反差:奶奶的脸色黑了,姐姐的脸色红了。牛儿心里鬼精得很,却没有喜形于色,暗地里怂恿傻五哥拍着手大声嚷嚷,“呵———那我就天天都去吃糖粒子!”老五倒是跟青儿特有缘分,笑笑地往他跟前一站,个头身板就像双胞胎。
“是真的吗?张打铁你有狠哩,不声不响就在唐家观买门面了!”
“哪买得起呀,是先租而已。”老铁匠回这话时看了一眼花儿。
“那以后我们就成邻居了,虽不同村,却共着一个保哎!”
“往一方走,交一方狗,你们父子俩可千万别得罪了王保长啊!”
王保长也就是这几年才当上保长的。真是说曹操,曹操到,人们正在围着张打铁父子问这问那,王保长就踩着方步也进了堂屋。王保长样子五大三粗,像个杀猪的屠夫,披着一件布纽扣黑色外套,左腋下挂着一只盒子枪,“大家都在啊?”声音嗡嗡的,算是打了招呼。
堂屋里一下就沉寂了。傻老五眼盯着王保长短枪柄上的红缨,他觉得那东西很像是花儿绣富贵牡丹的红丝线,就想走拢去试着摸一摸。他是摸过花儿绣篓里的红丝线的,那丝线的感觉真好,滑滑腻腻,就像自己小时候捧着妈妈的奶子“吃饭饭”的感觉。可惜每次他的手刚摸上去,就被花儿腾出的手啪一下给打掉了,但即便是打了,他也觉得很喜欢,因为花儿打他的手也是软软柔柔的,而且打得一点都不痛。大家正僵持着时,傻老五一蹿就到了王保长跟前,“嘿嘿,丝线线,丝线线……”他正要伸出手去摸那红缨时,王保长警觉地往后一退,大声喝道:“大胆刁民!你还想偷袭本保长不成———”说着就把短枪掏出了盒子,朝天“砰”地就是一枪,白驹村木屋的中堂是没有楼枕也没铺楼板的,空空的直通屋顶,击碎的瓦砾便应声砸了下来。
“哎哟……”有人头上就开了鲜花,这是谁也没有想到的事。
“出了人命呐!保长打死人了啊———”年近八旬的瞎眼奶奶虽然眼睛看不见,耳朵和鼻子却灵得很,她不但闻到了声音,还嗅出了火药味,她担心会闹出什么大事来,便倚老卖老地喊起冤来:“这青天白日的,是哪一个吃了熊心豹子胆呐———敢把人命当草芥啊……”还有意把声音也拖得老长老长,就差没有就地打滚发泼耍赖了。
王保长竟一时傻眼了,有人想伺机开溜。没想到真正吃了熊心豹子胆的还是年轻的张铁匠青儿,只见他从铁器担子上取过那条桑木扁担,大步上前将扁担往地上一杵,义正词严地质问道:“保长,保长,理应保一方平安,你这是哪家的保长啊?”花儿在一旁心跳得好厉害。
“就是嘛,有狠的你去打小日本呐!”
“跟老百姓动刀动枪的,也不想想是哪个在养着你们!”
一时间民情激愤,木屋的中堂里如一锅滚粥,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刁民,一群刁民!”王保长满脸横肉,人却滑头,他来白驹村是以巡查共匪为名(最近上峰有令说有共匪在这一段活动),实则想来蹭立夏丸子吃的,见有人挂了红,深知众怒难犯,好汉不吃眼前亏,狠狠地瞪了陌生的年轻铁匠一眼,鼻子里“哼”一声便灰溜溜走人了。
王保长叫王长贵,唐家观人,却管着资水两岸雀坪、余皋溪、白驹村和小镇唐家观共四个村镇。据说这保长之职是他花了大价钱买来的。而这些破事年轻的张青却似乎全都知道。他还趁热打铁跟围观的井湾里人说了很多外面世界的大事:保甲制度提出于国民党对工农红军进行军事“围剿”之时,蒋介石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身份督师江西,认为“剿”共不力的原因之一是民众不支持政府。于是在“剿匪总司令部”所属党务委员会内专门设立了地方自卫处,研究保甲制度,草拟法规,先在江西试行。1931年6月,蒋介石划定江西修水等43县编组保甲,将原有闾邻等自治组织一律撤销。次年,以蒋介石兼总司令的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颁布《剿匪区各县编查保甲户口条例》,规定10户为甲,10甲为保,联保连坐。1934年,国民党“中政会”第432次会议议决由行政院通令各省市切实办理地方保甲,据此,行政院又于同年12月通知各省,普遍实行保甲制度。但国民党当局虽对保甲制寄望极大,而保甲制的推行却收效甚微,其原因是“一般公正人士多不愿任保甲长,而一些不肖之徒又多以保甲长有利可图,百般钻营”,他接着还高声说:“正人不出,自然只有坏人的世界,良好的制度也就变成了剥削人民的工具,因此民众怨声载道。”满堂屋人竟然鸦雀无声,奶奶亦无语,姐姐花儿听得尤其入神。
“刁民,一群刁民!”老五哥被王保长“砰”地一枪给吓了一跳以后,整个人就变得更傻了,好长一段时间也不敢跟在姐姐花儿的屁股后面跑了,时不时还“刁民,一群刁民”地嚷嚷。这使牛儿很心痛。
三
这个叫张青的年轻铁匠还真是了得,初来乍到一亮相就摆平了两桩棘手的事:一是挺身而出给了横行乡里的王保长一个下马威;二是令排斥外地人的奶奶也开始对他这个有胆有识的年轻人刮目相看了。
黑瘦的张打铁,眉毛也黑,如两只卧在额下双眼之上的蚕子,这一回却显得特别地舒展。当家的女人们,一个一个忙着与他结算去年的旧账,有缺现款的照例又是带来了稻米,也有带来了谷子的,他也二话不说全都收下了。“还是张打铁好打讲。”人们的赞叹声是由衷的。挑选镰刀和菜刀的还是头一次与新人张青打交道,话也就更多一些:“我们井湾里不缺少愣头后生,缺的就是像你这种饱读诗书能晓得天下大事的年轻人!”有人就赶紧附和:“打铁哥,你若是不嫌弃,我们这里的漂亮妹子随你挑一个就是,干脆做我们白驹村的上门女婿要得啵?”老打铁在一旁听得高兴,这群上山下水的梅蛮后裔,还是头一回称呼打铁的为打铁哥,卧蚕眉又动了一动,说:“那是好事嘛!”
“我们这里最漂亮的妹子是花儿!”傻老五终于说了句清白话。
张青把目光再一次投向了花儿,花儿脸色红红的,心里也开着花。
“还不进屋煮立夏丸去,”神龛下的奶奶也发话了,“人家赶了一天的路,只怕肠子都饿得打结了。”奶奶这话也是说给其他人听的。
“首兆奶奶,那你们一家子热热闹闹过一个团圆的立夏节啊!”这话说得多暖心呀,还有意话里有话把两家人也说成了一家子。
“打铁哥,在唐家观安了家后,我们会常去你们铁匠铺的。”
大伙儿说说笑笑,推推搡搡各自回家了,傻老五却笑笑的不想走。
这一顿晚饭吃得很愉快,也很特别。主食是立夏丸子,也就是北方人说的汤丸,当然比汤丸要大,里面是用炸过的花生米拌芝麻馅。奶奶还专门交代了,要给张青的丸子里打两个荷包鸡蛋进去。新女婿过门是要吃两个荷包蛋的,这是井湾里老辈人的规矩,花儿心领神会。
那晚的月亮真圆,边上还有红晕,所以特明媚。花儿只把张打铁父子送出门口,望断了背影后,就倚着禾坪边的老槐树看月亮,她心里柔柔的,软软的,却也有些遗憾和惆怅:为什么就不肯在家里留一宿再走呢?奶奶还嘱咐她检拾了客房。可张打铁说还要赶回唐家观去,他们租下的店铺是从今天起就要算租金的,得早点去收拾,“还要重新筑炉子,真正检场开炉怕要个把月才行。”牛儿和老五却一直跟着他俩到联珠桥头才打回转。“开业那天我来吃糖粒子。”老五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