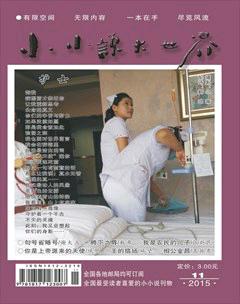父亲
陈德鸿
大青从县里回来,在门口犹豫了好一阵儿,才慢慢腾腾踱进屋里。
父亲看了他一眼,撂下饭碗,咋,没考上?
大青跌坐在凳子上,眼泪一下子流了出来。
母亲说,没考上就没考上,先吃饭吧。
大青摇摇头,哽咽着说,我,我吃不下。
那就别吃,还能省点粮。父亲说。
你这是啥话?母亲白了父亲一眼,咱大青底子好,考不上咱明年接着考。
大青抬头看了看母亲,忙又低下头去。
说得轻巧。父亲咳了一下,再考是不是那个什么复读,那不要钱?要再考不上呢?家里欠了一屁股债,农药、化肥的钱还没着落,二青在乡里住校也要钱,拿啥复读?
母亲不吭声了。
大青擦了擦眼泪,大声说,我不读行了吧?
那好。父亲苦笑了一下,明天就和我一起下地干活。
到了田里,大青也不说话,操起锄头便干了起来。父亲看了一会儿,偷偷铲掉了一棵苗,叫住了大青,你瞅瞅你是怎么干的,咋连个地都铲不好,还能干好啥?
大青的脸红了一下,继续闷头下狠力干着。
快中午时,父亲说,歇歇,该打尖了。大青不吭声,锄头仍没有停下来。
父亲说,干啥都得有时有晌,你这样使蛮力,分明就是赌气,明天就爬不起来了。往后还咋干活?
咋干也累不死。大青放下锄头,不耐烦地说。
晚上吃饭时,母亲看着大青晒得黢黑的脸和满手的血泡,心疼地直掉眼泪,在桌下偷偷捅父亲。父亲狠狠瞪了母亲一眼,母亲张了张嘴,把想说的话憋了回去。
几天后,大青铲地时速度慢慢降了下来,但技术已经很熟练了。
心气顺了,活就能干好。父亲说,我觉着吧,这高考应该和种地一个道理,该施肥施肥,该除草除草,只要精心伺弄,年景好就能丰收。
那根本就不是一码事。大青没好气地说。
咋不是一码事?父亲说,我和你妈都觉着你哪个地方可能没伺弄好,人家老师都说你是清华、北大的苗子,咋会连个啥大专都没考上呢?
大青的眼睛有些湿了。
父亲叹口气,你这么高的学问,是不是觉得在家种地可惜了?
大青转头看了父亲一眼,可惜啥。谁让咱没考上呢!
哪儿跌倒了在哪儿爬起来,人都得争口气不是?父亲说,我觉得你还应该再比划比划。
还比划啥,我哪也不去,就在农村呆着了。大青说。
那你就是孬种。父亲瞪起了眼睛,你跟我说说,复读一年要多少钱?
孬种就孬种。大青懒洋洋地说,你看咱家这情况,说复读的事有意义吗?
让你说就说,父亲火了,钱不够我去张罗借。
大青想了想,支支吾吾地说,算上租房啥的,一年至少得一千五。
父亲点点头说,从明天开始,你在家好好看书,不用跟我下地了。
大青感激地看着父亲,爸,现在放假,我就帮家里多干点吧。
不用。父亲摆摆手,我就觉得做功课和种地一样,你耽误它它就耽误你。再说了,你的活就是好好学习,留下好苗,把心里的杂草薅出去,旁的别想。
大青家是外地户,除了几个朋友,远近没啥亲戚。父亲跑了好几个晚上,终于在大青复读前把钱借齐了。
母亲说,为借这钱,你爸说尽了好话,腿都跑细了。
大青说,妈,我知道。
父亲说,学习累,可也别苦着自己。想吃啥就买点啥,钱的事儿别担心。顿了顿又说,你该怎么做,我就不说了。
大青使劲点点头。
进城的客车缓缓启动,刚走了不远,大青看见送行的父亲突然蹲在地上,在阳光的映照下,眼角有东西在闪亮。他知道,那是父亲的眼泪。
虽然县城离家只有四十里,但复读的一年里,大青没有回过一次家。父亲因买农具,也只到过县城一次,只给他带了许多母亲做的咸菜。
第二年,当大青接到一所名牌大学的录取通知书,看到需要交纳的费用时,心中的喜悦和激动之情一下子荡然无存,又哭丧着脸进了家门。
父亲愣了一下,从大青手里接过通知书,看了又看,高兴地跳了起来。
母亲焦急地看着父亲,这是?
考上了呗,还是北京的学校哩!父亲把通知书递给母亲。
母亲翻过来掉过去看了一会儿,这是真的?
这还有假,白纸黑字写着呢,上面还有个大红官印。父亲拍了拍脑门,尴尬地笑了,这扯不扯,忘了你不识字了。
这可真是天大的好事啊!母亲的眼里笑出了泪,她冲父亲说,你赶紧去街上割肉打酒,二青今天正好回来,咱们得好好庆贺一下。
父亲把变得有些驼的腰挺了挺,乐颠颠地走了,大青噘起了嘴,妈,这有啥庆贺的,考上了也念不起。
傻孩子,你可是咱村的第一个大学生,能不庆贺?母亲笑眯眯地看着大青
反正我高兴不起来。大青的眼泪在眼眶里打着转。
你是担心费用吧。母亲回过神来,从箱子里掏出一本存折,你看看,这些够不?
大青迟疑着接过来,只看了一眼,便惊讶地张大了嘴,这么多钱啊?
母亲看了看四周,小声说,这钱你爸早就攒下了,都是他起早贪黑上山下河搞副业挣的,今年也挣了不少,还没存呢。要不是他硬拦着,我去年就跟你说了。
大滴大滴的眼泪从大青眼里流了出来,直到已经越发干瘦的父亲回来时才止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