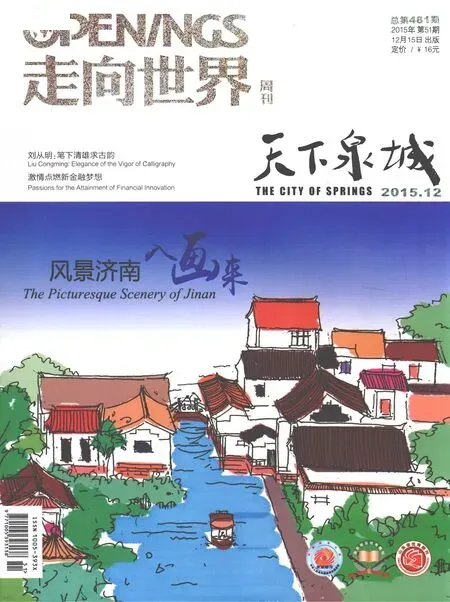父亲的烤火盆
父亲的烤火盆
FATHER'S BRAZIER

林毅
山东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副教授
父亲活着的时候,每到冬天都会用火盆取暖。那时农家贫苦的日子每点每滴都要精打细算,有了烤火盆就省了买煤买炉子。娘做完饭,从锅底挖几勺没有燃尽的木炭,盛入火盆里,烘烘屋里的凉气,一个冬天就熬过去了。
一个废弃的泥罐,经过父亲那双灵巧的双手,就变成了盆。再找两根独轮车上的辐条做火钳,烤火盆的用具就全了。父亲把平日里出工捡到的柞木、槐木等下脚料单独放置一个筐里,农闲时用锯截成约10厘米的小段,然后用砍刀劈成长条,留作冬季烤火用。他先在盆底铺上三指后的灰烬做底子,然后摆上劈好的小柴火,上面是从锅底掏出来的火炭,因了里面有这些柴火,能保存两三个时辰的温度。父亲在炕上还准备了一块比火盆稍大点的木板,防止盆底太热烫糊苇席。
在炕头墙上的高处,放着一个小酒壶。父亲伸手把酒壶和泡着东北人参的散酒取下来,倒入一指左右,把酒壶坐到火盆里,空气里都弥漫着酒水的香气,充溢着小屋。那时都是喝散酒,二斤半地瓜干换一斤,就这一斤酒也要喝好长时间,有时自己还往酒瓶里加一点水,就喝个酒味。逢年过节才买一元一瓶的串香五莲白干,就算高消费。 如果不小心撒到桌子上一点,恨不得趴到桌子上喝了它,嘴里直说“可惜了,可惜了,糟蹋粮食。”边说边从火盆里引燃抽烟纸,那时散酒都是65度,一碰就着。如果此时有人从房前屋后经过,闻到酒味就说:“好酒,看来这户人家来客了!”。看着父亲抿一口酒,咬一口萝卜咸菜,那种陶醉状,我也有想尝尝的冲动。父亲看出我的馋样,就用筷子粘一下酒,往我嘴里一抹,齁辣,我边吐舌头边找水漱口。长大后,读了臧克家先生“长辈贪杯我闻香”的诗句,觉着这句诗就是写的我。
那时农家孩子一个冬季没地方洗澡,身上的油灰都抹到棉袄棉裤里,油光发亮。最愁早上起床穿衣服,就像一块铁皮糊在身上,冰凉扎人。小孩子都赖被窝,不到上学的点不穿衣服。因有这个火盆,娘把棉袄、棉裤在火盆上一烘,顺手把裤腿、袖子都翻过来,里外都烤一烤,又快速翻回去。有时棉衣上招了虱子,娘就直接扔到火盆里,“啪”的一声响,“这得吃多少血!快起来吧,棉衣暖和了,虱子也拿了,快穿衣吃饭上学去。”我蹭地从被窝里钻出来,一天心里都暖乎乎的。
8岁那年的某一个晚上,下起大雪,落满了整个大地。父亲从工地冒雪回家,从怀里掏出一个纸包说:“今天雪大,工地没法开工,食堂改善伙食,每人三个肉包子,快把火盆端来,给小三烤烤吃。”父亲说着就用火钳把火炭拨拉了几下,又朝着火盆吹了几口气,炭火映红了我和父亲的脸。他把两根辐条担在火盆上,摆上包子。那年月除了过年能见点肉腥,平日里是闻不到肉味的。看着包子在火钳上来回翻烤,我的肚里就像装了两只小兔,直挠人心。偶尔从包子上滴出一滴油,火盆里就冒出一股烟,焦油的味道让人恨不能一口把这个包子吞下去。一会的功夫,包子就变成了金黄色。“好了,可以吃了!"我留着嘎啦子说,随手递给父亲一个,娘一个,他们四目对望了一下,两双锉刀一样的手,同时把包子塞给我。我上来就是猛咬一口,满嘴是油,肉馅在嘴里上下翻滚,烫的跳高。“慢点吃,没人跟你抢,别咬着舌头。”娘笑着说。
每当想起这个情景,就串起岁月的珍珠,它是那样的悠长而纯美,永远留在了我记忆的深处。今年的寒食节,我回家给父亲上五年坟。在父亲的坟头,我用烧纸叠了一个烤火盆,放到纸钱里一块将其烧掉。伴随着一缕清烟,纸灰飘上西南方向,感觉父亲坐在炕头,又在火盆前烫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