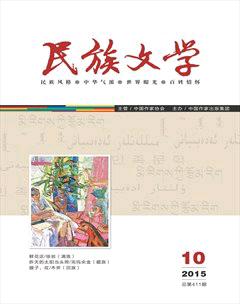我与民族文学的34年
尹汉胤
从1980年10月到中国作协,至2014年9月退休,我在中国作协从事少数民族文学工作整整34年。漫漫岁月,倏忽而过,可谓快矣。在整理办公室时,我翻检着多年来积存下的各种文件、书信、编辑的书刊、写下的文章、各时期的留影……逝去的岁月,历历在目地浮现于眼前,不禁感慨万千。记得1980年我到民族文学杂志社报到时,编辑部竟然在陶然亭公园深处古色古香的慈悲庵、云绘楼中办公,静谧的陶然亭公园中的《民族文学》正处在紧张的筹备创刊中。
这本全国性的少数民族文学刊物得以创刊,缘于蒙古族老作家玛拉沁夫于1980年初写给中宣部的一封信。此信很快转到了中国作协党组,中央有关领导在此信上作了批示:我们确应为少数民族文学办些实事,比如召开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比如举办全国少数民族文学评奖等。中国作协于1980年5月,在北京召开了少数民族文学座谈会,来自全国几十位少数民族作家出席了这个历史性会议。经会议讨论中国作协批准,决定1980年7月在北京召开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1981年与国家民委共同举办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评奖;立即创办《民族文学》期刊;在鲁迅文学院开设少数民族作家班;组织少数民族作家参观团赴内地参观学习。
为创办《民族文学》,中国作协从各民族省区调来了多位少数民族编辑、作家。各民族同仁怀着共同的目标聚首在北京,其乐融融地相处在这个民族大家庭中。创刊时的主编陈企霞是延安时期《解放日报》副刊的老编辑,副主编玛拉沁夫是蒙古族著名作家,两位编辑部主任,王谷林从新疆文联调来、达木林从内蒙古文联调来。娜仁高娃、曲凤苞、许国荣、伍略、韩昌熙、王文平、查干、特·赛音巴雅尔、那家伦、陈凤楼正值盛年,艾克拜尔·吾拉木、艾克拜尔·米吉提、李克坚、岑献青、李霄明、王山、郑继平、陈冲、邹晶晶……只有二十多岁,组成了一个不同地域、多民族文化背景、充满朝气的特殊文学群体。
上世纪80年代初的中国,正处在百废待兴、振兴中华的大时代。寂静的陶然亭慈悲庵、云绘楼中,激情满怀的各民族同仁,心里都憋着一股劲,在各自岗位上为《民族文学》的早日创刊共同努力工作着。经过几个月的紧张筹备,1981年1月,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全国性少数民族文学刊物《民族文学》创刊了。1980年7月在北京(西苑宾馆)召开“全国少数民族创作会议”。1982年1月在北京总参招待所(禄米仓)举行第一届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优秀奖的颁奖大会。由此开启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历史新纪元。
来到这样一个多民族的文学集体,使我心中既充满着新奇兴奋,又因对未来的工作感到陌生而忐忑不安。当时我在编辑部负责美术编辑,在此之前,我从未接触过刊物编辑工作。筹备创刊期间,编辑部特聘请内蒙古的画家思沁协助创刊号的美编工作。但主编要求我尽快熟悉工作,从第二期接手刊物的美术编辑工作。这对我压力很大,面对即将担负的工作,我连一点头绪都没有。但我没有退缩,最捷径的办法,就是找来各种文学刊物,从中参考学习,将各刊物中有创意的版式、插图样式记录下来,短时间内我便积累了一大批各具特色的设计图样。达木林曾担任过《草原》主编,他对我很关心,认真地给我讲解了文学刊物的版式规范、编辑流程,使我对文学刊物的编辑工作有了初步的认识。那时的刊物印刷,还处在铅字时代,我便到印刷厂认真了解了铅字的排版和印刷程序,到制版厂熟悉了各种图案制作成铅锌版的工艺,图案的印刷效果,通过一段如饥似渴的学习,使我对未来的工作拥有了自信。
拿到第二期稿件,我便开始封面、版面的设计,根据文稿要求配画各种插图、题图和标题字。为提高刊物美术作品的质量,我与北京画院、中央美院、中央民族学院(现中央民族大学)多位画家建立了联系,邀请一大批著名画家为刊物画插图,他们风格各异、优美传神的插图出现在刊物上,为刚刚创刊的《民族文学》增色不少,成为年轻的《民族文学》一道亮丽的风景。
父亲对我到《民族文学》工作非常高兴。在我到《民族文学》不久,他便到编辑部来看我。他走进云绘楼清音阁,环顾着对我说,你知道这座建筑的历史吗?它原建在中南海的东岸,是光绪皇帝写字画画的地方。中南海成为中央办公地要将其拆除,梁思成得知后,向周总理建议保留,两人便一同到陶然亭踏勘选址,然后决定整体搬迁到这里。这处独特的建筑搬迁到这里后,便成为了文人雅集的好去处,我与朋友们也曾在这楼上小聚过。想不到你们编辑部会在这里办公,在这座古建中办公可以触摸历史,感受到皇家气息,你们刊物可真会找地方。
同时他又感慨地对我说,我们家与少数民族工作有缘。1946年内战爆发,我便随内蒙古文工团进入了内蒙古草原,在那里工作了11年。你妈妈中央美术学院毕业后,到中央民族学院任教至今,如今你又从事了少数民族文学工作,这很有意思。你在编辑部一定要尊重其他少数民族同志,多向他们学习,多读书、勤动笔,少数民族文学是大有作为的事业。
当我亲身参与了一系列少数民族文学活动,平生第一次接触到众多的各民族作家,阅读了大量少数民族文学作品后,在我眼前开启了一个全新的生活视野。到这时我才深有体会地明白了父亲所说的“少数民族文学是大有作为”的内涵,从而使我对这项工作生出强烈的兴趣和向往之情。
那时我与各地来的少数民族同仁住在陶然亭编辑部里,每天清晨,当第一缕阳光照在窗子上时,整个屋子便立刻充满了灿烂的阳光。阳光召唤着万物苏醒,也使我浑身充溢力量。敞开房门,沐浴在温暖的阳光中,目下是一片静静的湖水倒映着蓝天,波光潋滟地环绕在四围,清新的空气中,不时传来晨练人们的呼喊声,使人从心底生出一种强烈的奔跑欲望。从那一天开始,我便每天投身在清晨的阳光中,沿着陶然亭蜿蜒的湖岸,伴随着《民族文学》的发展繁荣,不停歇地奔跑起来。
1984年,编辑部离开了陶然亭公园,在北京辗转了多处办公地点,最终落定在后海的大翔凤胡同3号丁玲当年的故居,又一处别具特色充满温馨记忆的北京四合院。
1986年我改做文字编辑,负责编辑散文、报告文学,与少数民族作家的接触更加密切了。在编辑过程中,我与各地少数民族作家频繁地书信往来,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其中许多人,虽然至今也未曾谋面,但从他们的稿件中,我熟悉了他们的民族历史、山川地域、民族风俗、情感生活……漫漫几十年与他们始终保持着联系。前年,我到湘西出席苗族作家侯自佳“文学创作50年”活动,他送我一本书,打开一看,书中影印着我们30多年来的所有通信,感慨时光匆匆的同时,更珍惜凝结着友谊的岁月文字,依然停留在那里默默守望着彼此的情感。
1995年,我离开《民族文学》,调到中国作协创联部民族文学处,负责少数民族文学的组织工作,在这一岗位上一干又是19年。记得时任书记处书记的吉狄马加,找到我谈起调我去民族处工作时,我不想放弃热爱的编辑工作,还有些犹豫。先我10年到民族文学处任处长的艾克拜尔·米吉提,力促我来接替他的这一岗位,说在这一岗位上可以更大地发挥你的作用。当我来到这个岗位上后,才知道了这一岗位的重要性。中国作协少数民族文学处的设立,是中国作协党组为适应迅猛发展的少数民族文学形势,于1985年具有前瞻性地作出的组织机构安排。在这一岗位上,使我拥有了更大的平台服务于少数民族作家。对我来说这次工作调动,是一种历史机遇,更是赋予了我一种历史责任。在这一岗位上我无怨无悔工作的19年中,负责组织了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第5至第10届的评奖工作,3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3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翻译会议,策划组织实施了多项少数民族文学活动。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我向作协党组建议,在鲁迅文学院举办囊括我国55个少数民族的作家班,党组接受了我的建议。这个55个民族的少数民族作家班的成功举办,为新中国成立60周年大庆的首都北京,增添了一道绚丽多彩的民族文学风景线,历史性地载入了共和国的文学史册。
回顾34年我与少数民族文学结下的不解之缘,无疑构成了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生经历。它使我有幸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时代,参与到我国少数民族文学繁荣发展的伟大进程中。在这一过程中,我不仅亲身经历参与了新时期以来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重大活动事件,而且伴随着民族文学的发展繁荣共同成长。这一历史机遇和人生经历,是无比珍贵的生命财富。在漫漫岁月中,我曾融入到维吾尔族兄弟中,与他们在依萨姆诙谐幽默的说唱中放声大笑举杯共饮;在青藏高原与经历了地震灾难的藏族同胞们默默行进在转经路上;置身在美丽的傣族村寨,在漫天飞舞的清水中与傣族同胞共享吉祥;在彝族火把节照彻天宇的篝火中,高擎火把欢歌起舞;坐在充满阳光的草原上,与蒙古骑手唱着苍凉的蒙古长调同悲共喜……这些难忘的生命经历,将成为永不磨灭的记忆,永远铭刻在我的心中,时时温暖、激励、净化着我的心灵。在这些积累的记忆中,流淌着我的青春,印痕着我坚实的生命足迹,使我身临其境、铭心刻骨地感受到了我们伟大祖国独具魅力的多元民族文化,深刻理解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发展脉络。尤为珍贵的是我曾有幸深入到人迹罕至的民族地区,亲身体验了大自然的独特地貌中人类生存的不同形态。这些特殊的经历、生命感受是常人难以企及的,而这一切都是民族文学给予我的。我要感谢与民族文学相伴而行的34年,无疑这是我一生中最成功的人生选择。
一个秋日的午后,我带着深深的怀念再次来到了陶然亭公园,沿着蜿蜒的湖岸曲径,内心充满着回忆向云绘楼走去。秋天明净阳光中的陶然亭公园里,游人如织,早已没有了当年的那种宁静。走近云绘楼,见当年那片幼小的银杏,如今已金灿灿地挺拔成了硕壮的大树,踏着落满黄叶的路径,我来到了云绘楼。
悠悠岁月,这座历经沧桑的建筑,依然默默地矗立在那里。梁柱的油漆已开始剥落,显得更加苍老了。是啊,她的一生目睹了中国太多的历史风云、时代变迁。这其中,也包括着34年前在这里见证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大事记——《民族文学》的诞生。正是当年,在这里工作过的一班人,创造了中国新时期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繁荣的一个重要原点。
感慨万千中我缓缓走过“印月”,面对“韵磬”二字时,耳畔似鸣响起来自久远时空的袅袅回音,那声音时断时续,却动人心扉、发人深省。静静聆听,啊,那声音就发自这回廊,这梁柱,这墙壁中。原来是34年前《民族文学》同仁们留在这里的脚步、欢笑、话语,依然潜伏萦绕在楼阁中。岁月无情,故楼有情。我忽然惊喜地觉得,34年前《民族文学》诞生在云绘楼清音阁,蕴含着某种寓意的,当年创刊号封面上飘动的那片祥云图案,如今已然飞霞漫天,由当初的一本刊物,已扩充为汉、蒙、藏、维、哈、朝6种文版;中国作协少数民族作家会员已由当年的100多人,增加到了囊括我国55个少数民族的近千名会员,34年间,置身于浮躁社会中的《民族文学》,却始终保持着独特纯美的清音。
34年前,我从云绘楼起步奔跑,岁月中奔跑的足迹已遍及高原、大漠、草原、江河、村寨……从未停歇地奔跑到了今天。屈指一算,不停奔跑的脚步,已累积出了一个“大数字”,已经围绕地球赤道有两圈多——80000多公里。
这一生与民族文学的不解之缘,使我有幸跻身在少数民族文学这一伟大事业中经历、成长、进步,成为了新时期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繁荣的一个参与者、见证者、讲述者。在这一人生旅程中有痛苦、有失误、有欢乐、有成功……可谓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灿烂的风景还在前方,我会毕生追随着她继续奔跑下去……
责任编辑 孙 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