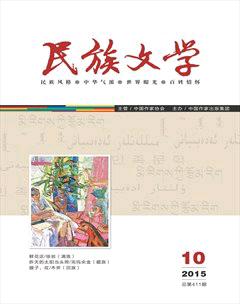楼房里的老人
伊力哈木·赛都拉+伊力哈木·赛都拉
阿不都热合曼老人早已没有心思坐在沙发上看电视了。老人不时地朝紧闭着的门望去。可是,从吃完晚饭到现在,外面的门一次也没有打开过。既没有任何人进来,也没有任何人出去。
儿子艾力上了自己的书房,做着在单位没有做完的事情。儿媳妇古丽海赛丽正在帮助上中学的女儿复习功课。他们没有工夫与老人坐在一起,叽哩咕噜地闲聊。其实,即便是有时间,他们所能聊的话也不会很多,有关亲戚的话题聊上一两句后,便无话可谈了。老人不仅对儿子、儿媳所做的事情,就是对整个城市以及城市生活,一点儿都弄不明白。唯有当孙子甜甜的撒娇时,他们才会有共同的语言。
他又朝外面的门看了看,门仍然紧闭。还是没有人从外面进来的样子。他甚至想,哪怕是某个邻居进屋子来,向自己问候一下也行,但这也只能是奢望。因为,这里的邻居们不怎么知道他。凡是来这个家的人,差不多都是为找儿子或媳妇而来的,要么就是一些娃娃们来找孙子的。
他觉得自己很孤独,好像已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了似的。一连几个星期,也不会有任何人来找自己。除了仅有的一年两次过年的时候,会有人前来给自己拜年,或者几个月有亲戚来慰问一下外,谁都不会到家里来找他,关心自己的情况。孩子们两三个星期来看望他一下。阿不都热合曼老人就是这样,常常在家里一呆就是几个星期,除了儿子、儿媳和孙子之外,大部分时间是见不到其他任何人的。
嗨,如果不是那个坎儿井的话,他每天会坐在那儿边喝水边做事,也绝对不会丢下自己生活了几十年的那个家,来到这里住在孩子的家。能有什么办法呢?水是生命之源嘛,有水才有生命,一旦没有了水就不得不搬迁。
那么,搬迁到哪里去呢?如果自己年轻力壮,就会搬到安装了自来水的新的居民区去。
阿不都热合曼是年已70多岁的老人了,身边没有一个可以依靠得上的孩子。四个孩子全都住在城里。孩子们都说,一旦搬迁,你们干脆就搬到城里来。老人这几年身体健康状况大不如从前,承包的责任田里的活儿也干不动了。老伴孜维迪罕也患有关节炎病,对她来说,承担家务活也开始成了严重的负担。
就这样,阿不都热合曼老人和孜维迪罕老太太于两年前丢下村里的位于干枯的坎儿井旁的家,将自己的责任田和少量的自留地,很便宜的承包给别人,搬到大儿子的家,就这样住下了。他们另一个儿子和两个女儿,每次前来看望他们时,好像没有别的话似的,总是不止一次地反复说着“你们到我家里住上几天”的话。
可是,老人根本没有到孩子们家里轮换着住的意愿。到他们家去住,又能怎么样呢?还不是像客人一样,住上几天后照样得返回呀。
依照习俗,老人应该住在小儿子家。然而,嘴巧手拙的小儿媳所做的饭菜,他一点儿也不习惯。小儿媳脾气很好、为人随和,一点儿也不把老人当外人看。虽然已是近40岁的人了,也仍然改不了娇生惯养的性格,在老人面前就像在自己的父亲面前般热情地撒着娇。然而,就是稍微有点儿懒惰,对操持家务、烧菜做饭不得要领。大儿媳是一位老成持重、自我动手能力强的女人,屋子收拾得洁净漂亮,还做得一手好菜,其他方面也让人称心,还善解人意,对老人体贴入微。而且,大儿子的经济条件也相对好些,住在这里对他们也不致于造成多重的负担。所以,在老人看来,自己住在大儿子家里更合适些。
可是,好像是成心与他作对似的,老伴孜维迪罕在大多数情况下,却会住在小儿子家。老伴说,大儿媳说话少、性情沉稳、看上去显得非常完美,在她面前我感觉有些拘束。而小儿媳人很随和、无傲气、嘴儿甜,像自己的女儿一样,我与她住在一起,就像住在自己家里一样。儿子们知道他们各自的心思,为了使他们的心得到平静,总是不断地安慰他们说,我们的家就是你们自己的家,你们不要拘束,想住谁家就住谁家,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吃什么就给我们说,不要难为情。但是,老人总觉着长期住在儿子家里就像客人一样。
当初,孩子们买这些房子时,虽然自己不惜拿出所有积蓄给予了资助,但不管怎么样,这房子毕竟是这些年来孩子们一手创下的呀。他们虽然说这就是你们的家,但说归说,毕竟与老人和老伴自己的家不一样啊。
孜维迪罕是位性格急躁而又固执的女人。虽说手脚患有关节炎,却不会安安稳稳地住在一处。常住小儿子家,也会去大女儿家住上一天,再到小女儿家住上一天。有时,老太太还喜欢从孩子们那里要点钱,或者去市场上买点东西,或者带上孙子们上街吃顿饭。而且,老太太的时间也从不固定。平时,她会在两三天、一星期或者十天左右来看一次老人。
这次,老太太去小儿子家已四天了,随时都可能回到老人这里来。正是这个原因,老人坐在那里,才不时地注意着门的动静。老人虽然眼睛看着电视,可是注意力却在门上。他好像是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似的,不停地朝门那里看看。隐隐约约地感到老伴孜维迪罕会来似的。老人虽然强迫自己看了很长时间的电视,但外面的门始终未被打开。于是,他失望了,决定还是先做宵礼(注:伊斯兰教徒每日最后一次礼拜,约在日落后两小时进行)。
做完宵礼,老人好像感觉有些疲惫,便往坐垫上放了个枕头,斜靠在上面。这个属于他的卧室,面积有15平方米左右。室内装饰时尚并有漂亮点缀。老人来了之后,对这个卧室做了改造。除了室内的西面墙壁上挂着伊朗式地毯外,北面墙壁上挂着一幅耶路撒冷圣地的画,东面墙壁上挂着的镜框里装着的是精美的阿拉伯文本的殉道者,镜框的上方悬挂着用阿拉伯文字书写的“以至仁至慈的安拉的名义”(注:穆斯林在行为之前首先恭颂安拉的专用语)挂钟。这种现代装修结合上述附加物,体现着浓厚的宗教色彩,从中可以看出,儿子为了给两位老人创造一个良好的居住环境,很是绞尽了脑汁。南面是个大窗户,采光极好,白天室内亮晶晶的,甚至晚上熄灯后,附近亮着的灯光,使夜晚的室内也处在良好的光亮中。与他们所在的农村的房子相比,这卧室虽然稍微小了点,但通风透光,整洁漂亮。
老人望着天花板,躺着深思良久,他头枕枕头,闭上眼睛,但似乎并无睡意。以前,他与老伴也来过儿女们的家里住一段时间。然而,那时是因为孙子们都还小,他们是为照看孙子们而来的,而且当时还有力气。在家里烦闷了,就带上孙子们到市场上去转一转。如果自己愿意,还轮换着回家住上一段时间再回来。而现在的情况不同了,没有需要照看的孙子们,也没有力气随心所欲地外出了。心烦时回的家也没了。住在这个房子,想伸着脖子看一看儿子、孙子的卧室,也觉着不好意思,甚至没有勇气。只好在儿子和儿媳上班、孙子上学,家里没有其他人的时候,他才走进孙子的卧室,用手摸一摸孙子所使用的写字台和睡床。
老人的日常活动仅限于此。在家里,朝哪个方向看都是墙。出了门,楼梯里上上下下的全是陌生人。老人向往位于湖边的那座自己的大房子、大庭院。从大房子出来便是大院子,从大院子出来便是广阔的原野。尽管湖水已经干枯,而在尚未干枯的大柳树和大桑树下面,坐着一群与自己同龄的老人,看到自己看着长大的年轻人,还有街坊邻居家那些叽叽喳喳、欢蹦乱跳的孩子们……是多么的可亲可爱啊,老人心里思念着那些美好情景,心急如焚。
有时,老人实在忍不住了就从窗户往外看,还是自己不认识的世界。打开电视机,所看到的也是自己不认识、难以理解的。如果有老伴在身边,那情况就不同了。老太太在跟前,他会觉得这房子是自己的似的,会忘掉那种像个长住的客人的感觉。这样想着想着,好像老伴就在眼前似的,只要眼睛一睁,老伴就会出现。就这样总是猛地把眼睛一睁,又闭上。刚闭上,又睁开。但次次看到的不是自己的老伴,而是室内摆放着的拥挤的东西、狭窄的墙壁,这使他憋闷得十分难受。
老太太的脾气的确不好,经常撇开他不知道去哪里转悠。有一段时间,阿不都热合曼也曾信马由缰,常常把孜维迪罕一个人丢在家里,想到哪里就往哪里跑。那还是他年轻的时候,老太太也不是老太太,还很年轻,就像一朵盛开的红花似的。而当时,年轻的孜维迪罕的脾气就不好,年轻轻的怎么想就怎么干。阿不都热合曼每次把孜维迪罕扔在家里几天不归时,只要一回到家,孜维迪罕肯定要与他大吵大闹,不把家里弄得昏天昏地绝不罢休。
那是他们婚后不久,正值盛夏酷暑,有一天,阿不都热合曼与居民区的几个朋友上山避了4天暑。刚回到家,孜维迪罕就堵住卧室的门,审问了起来:
“您说,我是嫁给了您,还是嫁给了这个房子?”
“我只是与哥儿们上山去了呀。”阿不都热合曼说着,也不理睬她那张已经变了色的脸。
“那您去上的山,我也一起上不行吗?”
“上山的全都是男人们,唯独让我把您带上,怎么能行?”阿不都热合曼生气地骂着,对她爱理不理的。
“那让别的人也把老婆带上,不就成了吗?”
“哎呀,您还有没有完,”阿不都热合曼来了个干脆不理她,准备到卧室去。
没想到,孜维迪罕气势汹汹地横到他的面前,阿不都热合曼好说歹说,她就是不肯让路。阿不都热合曼刚要举起拳头吓唬她,谁知孜维迪罕却主动把头塞到他的怀里,一边说:“打吧,您把我打死算了,我也不想活了。”一边撕扯着她自己的衬衣。阿不都热合曼本来想用力把她推倒在地,但是,这时孜维迪罕急火攻心。只见她突然牙关紧咬,脸色苍白,全无血色。浑身抽筋,蜷曲着紧贴在地上。
那次,孜维迪罕对阿不都热合曼两天也没说一句话。
第二年,就在她第一次怀孕的时候,阿不都热合曼沾染上了每天熬夜玩扑克牌的恶习。
一天,一群喜欢玩扑克牌的朋友正在他们家玩牌,孜维迪罕从婆婆身边出来,一见到这些玩牌者就气不打一处来。她像出了膛的子弹般地冲过来,将炕桌高高地举起,使出全身的力气砸到地上,炕桌立即成了一片片的。
玩牌者一个个张大嘴巴,呆呆地站在那里,望着阿不都热合曼,好像在说这叫什么事似的。他们原以为这下可有热闹看了,并期待着看热闹。阿不都热合曼的火气也上来了,真想把妻子酣畅地痛打一顿,以便在哥儿们面前将失去的面子找回来。但是,当他看到孜维迪罕那鼓起的肚子时,举起的拳头并未落在妻子身上,而是把炉子打翻了。
阿不都热合曼这次离家出走,两天后才回来。这次,孜维迪罕一个星期也没有让阿不都热合曼踏进卧室一步。
孜维迪罕的这些事,很快就在社区中传播开了。阿不都热合曼的哥儿们给孜维迪罕取绰号为“撒旦”。从那以后,谁都不找阿不都热合曼玩牌了。他们普遍认为,女人无论怎样厉害,也不能独占卧室不让自己的男人进屋,像孜维迪罕这样的女人实属罕见。对此,就连公公婆婆也深感失望。
然而,这时阿不都热合曼不知何故,对妻子这样的行为不仅可以忍受,反而感到滑稽。事情发生时,不但对自己很生气,而且每次事情过后,还向她开着玩笑。或许是因为那时他年轻力壮,意气风发,正是青春的热血迸发的年龄。妻子的泼辣行为让他有一种很诙谐、有趣,奇妙的感觉。在与妻子欢聚时,从她的这种坐地炮似的行为中,心里会产生一种莫名的快感。如果妻子一段时间变温顺,他们俩长久不发生争吵,在阿不都热合曼的生活中,反而会觉着像短缺了什么似的,变得烦躁不安起来,于是便会找茬子故意惹她生气。他把这种感觉深藏在自己的心底,不敢向任何一个人讲过。
随后,那样的事情就没有了。父母亲都上了年纪,孩子也多了,家庭的负担加重了,阿不都热合曼感到自己也不像以前那样身强力壮了。早先的劳累,使他体会到自己也需要有人来安慰、扶助了。
但是,孜维迪罕似乎对他并不体谅,脾气还是那样的差劲。
对于妻子的无赖行为,他现在不仅不感兴趣,而且让他难以忍受,给他带来了精神压力。
随着年龄的增大,孜维迪罕似乎更变本加厉了。尤其是两个孩子因病死亡后,她的脾气更加糟糕。成天哭哭啼啼,打砸东西,把家里搞得鸡犬不宁。有的时候,谁也搞不清她在生哪门子的气,无缘无故地就发起火来了。
阿不都热合曼曾对父母和伙伴们说,真后悔当初没有把这个妻子给休掉,但现在已经来不及了。他们接二连三地生孩子,前两个没能留住,剩下四个孩子都还小,孩子们需要母亲精心养育。阿不都热合曼心疼妻子和孩子们。
好像是老天故意捉弄、还嫌这些孩子拖累不够似的,就在十几年前、也就是孜维迪罕50多岁的时候,她又怀孕了。这让她感到在大庭广众之前非常丢人。当时,孜维迪罕对阿不都热合曼讨厌极了。然而,作为母亲的天性,她从内心深处又不同意打掉母体内这个小小的、无辜的、鲜活的生命。为此,她痛哭流涕,说什么也要把这个孩子生下来,但又不能生。在计划生育部门和廉耻的双重压力下,她最终同意不生这个孩子了,国家的政策不能违背呀。但是,这事对她来说是非常残酷的,此后,她对阿不都热合曼几个月也没有给过好脸。她说,生其他六个孩子所受的痛苦加在一起,也比不过这一次。当时,阿不都热合曼理解她此时的心情,知道她非常非常地痛苦。
从此以后,他容忍着妻子的坏脾气。每次妻子生气的时候,他都尽量躲开,避免站在一起僵持。就那样,阿不都热合曼咬紧牙关,日复一日地将就着过着。然而,孜维迪罕的脾气越来越坏了。从结婚到现在,这几十年也不知是怎么过来的。可是不管怎么说,他们如今都不再是年轻的时候了,过度的心病谁也扛不动了。现在,这老太太差劲到如此地步,老人都到这把年纪了,健康状况也不佳,这些好像与她都没有什么干系似的,丝毫没有觉着自己是上了年纪的人了,成天逍遥自在的,想往哪跑就往哪跑。嗨,奇怪,去小儿子家已好些天了,按说也该回来了。
老太太自离开坎儿井湖边那个家后,好像心里就不难过似的。但是,在培养孩子们成人,尤其是把孩子们都培养成中用的干部的过程中,老太太付出了不少心血。所幸的是,老太太这种急躁、好闹腾、差劲的性格,并没有给孩子们带来一点儿不良后果。尽管她自己没有文化,却能把孩子们聚集在大桌子上学习,让孩子们以大带小结成对子,互相帮助复习功课。孜维迪罕还把孩子们每学期的课本翻开,根据课本页数制定每天、每星期、每个月的学习计划。如果谁完不成计划,谁就别想离开桌子。有时,阿不都热合曼实在心疼孩子了,就前来说情,可孜维迪罕不但不给他一点面子,还像好斗的公鸡似地瞪着眼睛说:
“您是不是想让孩子们都像您一样,成为什么用也不顶的造粪机器?”尽管说孜维迪罕的脾气不好,但在对孩子的培养上,她所做的全都没错。您看,孩子们能有今天,都是她严格要求和精心培育的结果。当然,这四个孩子能够加入到读书人的行列,阿不都热合曼也付出了很多艰辛。一辈子拚命挣的那些钱,如果不是孩子们的念书,那会有什么用?
老人就这样在胡思乱想中,上下眼皮粘连在一起了。他好像看到老太太在身边,又忽地睁开眼睛。老太太还是不在身边。阿不都热合曼搞不清刚才这些是想象,还是做梦。在这四面都是水泥墙的狭小空间,他感到窒息,心里憋得难受。“我这老婆怎么这样差劲啊,既然我住在这里,您就也该住在这里呀。大儿媳虽然平时说话是少了点,但她不论在任何事上都顺着我们的心。哎,差劲的老婆啊,差劲啊,她向来就把我的话当成是耳旁风,根本就不把我这个男人放在眼里。”
门“咯噔”响了,他急忙抬起头,朝门那儿看去。像是有人闪过似的。他又泄气了,头枕在枕头上。刚才分明听到了轻轻的敲门声呀。敲门者一定不是老伴。老伴如果想进这个家,从来不敲门就进来了。儿子、媳妇或者孙子哪个想进来,总是很有礼貌地先敲门后才进来,老人对这种做法相当满意。不管怎么样,这间15平方米的卧室,被老人看成是自己的私人世界。在其他孩子家的话,就做不到这点。本来是给父母安排的卧室,孩子们却随随便便地进进出出,老人感到这是对自己的不够敬重。自己的房子就是咱们自己的,其他人随随便便进进出出的,老人会感到像受审似的委屈。而小儿子或其他孩子却说,这是给你们做伴,既可从与小孙子亲昵中得到愉快,又能摆脱独处的烦恼,还能从老态龙钟的心境中走出。连一间小小的箱子般的卧室,自己也成不了完全的主人。正因为这样,他才不轻易到其他孩子家里。老人从敲门的声音中判断,进来的人不是老伴,而是家里睡觉的人,就又把眼睛合上了。他感到卧室里这时来了一个人,像是在找着什么似的。“唉,等老太太这次来了,我非骂她个狗血喷头不可,以便好解解窝在心里的闷气。都失踪好几天了,好像我已不在这儿似的,这差劲的媳妇啊。”但是,常言道“江山易改,秉性难移”,脾气不好也是没有法子的事。这阵儿除了脾气如此糟糕的老太太之外,能与他倾诉衷情、牵肠挂肚的,还会有谁呢?
老人合上眼,开始进入梦乡。不知从哪里传来水的当啷声。老人以为这是在开启的坎儿井的大坝声。好像眼睛被外面的某一只灯照射,灯光直刺眼目。他用手遮住刺来的光线,极目远眺。眼前出现了一片绿色,它的那边则是一望无际的河滩。老人以为那大片的绿色就是自己的葡萄园,自己正在浇灌着葡萄园。啊,看到的真是自己的葡萄园。葡萄已经熟透,老人卖葡萄了,他现在正数着钱。这时,孜维迪罕不知从哪里冒了出来,一把夺过所有的钱。
“把钱拿来,孩子们上学用。”她说。阿不都热合曼生气的瞪圆双眼。眼睛又忽地睁开了。也许是发出着的剧烈的鼾声,使他感到有些口渴,鼻子火辣辣的。屋子里还是很寂静,老人伸手摸索着,手什么东西也未触到。老太太没有出现,四面还是令人窒息的墙壁,还是他孤独一人,气憋胸闷。“孜维迪罕哎孜维迪罕,您什么时候想过我。”老人伤感地哀叹着,眼睛又闭上,再次进入了梦乡。
梦见孜维迪罕头也不回、大模大样地走着。阿不都热合曼力图快快地追上。但是,他的脚像是被戴上镣铐般的沉重,使出了全身的力气,也没有挪动半步。于是,他对她非常气愤地喊叫:
“哎,您给我站住,您的脚怎么像个浪子,把我一个人扔下,要到哪儿去?”
“您不是跟我离婚吗?现在可好了,分住在两个地方,再不要为离婚感到难看了。”
“这话是谁说的?”
“您说的呀,难道您忘了?”
“我想不起来了,即使那样,那也只是说说而已。”
“您就是那样想的。”
“但我没有那样做。回来,这些天没有您在身边,我每天都像只是在等待阿兹拉伊勒(注:古兰经中记载的天使之一,专司死亡)似的。”
老人的腿像是被什么拉扯了一下,脚上戴着镣铐也解脱了。于是,便一下子追上了孜维迪罕。
阿不都热合曼忽地睁开眼睛,看到老太太就坐在自己脚头,正把他的脚拉在怀里,为他按摩着腿,从脚底传入一股细细的暖流,闪电般的迅速向全身扩散,血液好似青春岁月般的汹涌澎湃,睡意片刻间跑到九天云外了,整个知觉神志清醒。刚才还为强迫自己睡觉而焦躁不安,现在一下子精神舒畅了。然而,他怎么也得做出像睡得很香的状态中醒来的样子,假装很困难地睁开眼睛。
“回来了?”
“是的。”
“啥时回来的?”
“刚来。”
“都这样晚了。”
“是孩子们送我来的。”
“怎么能麻烦孩子们呢?你明天来不就行了吗?”
“您拿‘你如果不来,阿兹拉依勒就来的话相威胁,我要不回来怎么办?”
老人有点不好意思地抬起头,半躺半坐着。
“我刚才说梦话了吗?”
“那是梦话,我还以为您是在真给我说的呢。”
“您也70岁的人了,不要像浪子游逛了。在家里安安静静地坐着不行吗?”老人变换了语调,用责怪的口气说。
“我浪子什么了,我所去的是自己孩子们的家,这也不行吗?”老太太不甘愿示弱的说。
“您为什么要把所有的家都搞得不安宁?”
“我给他们添麻烦了吗?在小儿子家住了两天,然后去了大女儿的家,她丈夫不在家,我陪了她两个晚上,这也不可以吗?”
“即使您不去陪她,她还有两个孩子嘛,真是多此一举。”
“怎么,我自己孩子的家,来去自由。实在受不了,您也去嘛,他们不也是您的孩子嘛。”
“也不知道您啥时才学会懂得规矩。”
“什么?我不懂规矩?”老太太像好斗的公鸡似的瞪圆眼睛说。
那边卧室,刚刚进入爱人身边,上床准备睡觉的古丽海赛丽,感觉到从对面卧室传出的声音越来越大,躺不下了。
“您去看看嘛,不要让他们吵开架了。”
“都那么大年纪了,可能吗?”
“您听,您听他们的声音。”
丈夫连动也没有动。没有办法,古丽海赛丽只好自己从被窝里出来,站起来了,当她正要穿衣服的时候,从里屋传出的声音节奏变了。
“怎么,是不是想我了?刚才,像得了黑腿病似的,两条腿缠绕在一起,好像跑着追赶妖精似的,嘴里喊着‘回来,阿兹拉伊正要来。”听得出来,这是老太太粗声粗气的笑声。古丽海赛丽听到笑声后,站着不动了。
“过来,也许您的背痒痒了,我给您挠挠痒。”老太太继续将声音减弱后说。古丽海赛丽听到这里,放心地回到了被窝。
经孜维迪罕老太太长时间的挠背与按摩,老人感到相当的安逸。在挠背的同时,老太太还滔滔不绝地给老人讲了这四天来,她在其他几个孩子家里的所见所闻,老人津津有味地听着。听说儿孙们过得非常好,他心里十分高兴。老太太还与小女儿一起去了非常大的超市,超市里面很大,货物琳琅满目,让人眼花缭乱。那货物真是应有尽有,很多连名字都叫不出来,更不知道怎么使用了。即使是在超市里转悠上一整天,也不可能把货物看上一遍。还讲了进大酒店吃饭等诸如此类的事。
“不要老是麻烦孩子嘛,现在也已经够拖累他们的了。”
“当时为培养他们我吃了多少苦,花费了多少心血。正因为如此,至高无上的真主现在才把安逸舒适的机会降到了我们的头上了。您看,无论是儿子、女儿,还有媳妇、女婿,个个都体贴孝顺。我们真的很走运。是伟大的真主让我们在年老的时候,过上了如此舒心的生活。”老太太愉快地说。
“既然如此,您怎么能经常麻烦他们,让他们花好多钱了吧?”
“我经历生离死别地生了他们,为他们险些搭上自己的命。我付出全部心血抚养他们,从来没有什么舍不得的。现在,他们长大成人了,我也这把年纪了,多多少少花他们一点儿钱,又有什么呢?”
“哎,您这是什么话,孩子是您生的,您不吃苦怎么行。”
“不是这样吗?我是他们的母亲,让他们为我吃点苦就不行了?”
“真是牛头不对马嘴,差劲儿的媳妇啊。”老人早就料到自己所说的话,她根本听不进去。也不知是因为白天什么时候睡过觉了,还是因为老伴的按摩致使他过度兴奋,或是因为好几天未看见老伴了,这时候他不但不想睡觉,而且精神愈来愈好了。
“喂,你洗个澡吧,我来给您盛水去。”老太太说。
“如果孩子们知道了,会不好看吧?”
“有什么不好看的,他们又不是不懂事的小孩子。”
“好吧,那您也一块儿洗吧!”
“怎么能搞到热水?”
“厨房的暖水瓶里可能有开水。”老人非常精神地说。
老太太起身去了厨房。暖水瓶里果然有少量的开水,但不够两个人洗澡用。她不敢自己点燃煤灶的火。老太太心里打起了退堂鼓。刚准备返回卧室,眼前就闪现出刚才说到洗澡时,老伴那欢喜的神色,炯炯有神的目光。她不愿让老伴为此失望。想来想去,她最后决定还是把儿子叫醒。
“艾拉洪,艾拉洪,孩子,你醒着吗?”老太太敲着门说。
先是古丽海赛丽,接着艾力从睡意蒙胧中乏困地抬起头,面朝门的方向。
“妈妈,什么事呀?”艾力问。
“我想洗个头,没有热水。”
“浴室里不是有吗,您把龙头旋转一下就可以用了。”
“那个,我不会用它。”
“暖水瓶里有开水。”
“没有呀。”
“有呀。如果没有的话,那么您明天洗也可以呀。”
古丽海赛丽用手捂住艾力的嘴,起床了。
“好啦,您继续睡您的觉,还是让我出去。”她轻轻地对艾力说。然后面对着外面,用大一点的声音说:
“妈妈,您先回卧室里休息一下,我把水准备好后,会叫您的。”
古丽海赛丽出来的时候,老太太已经回到了卧室。古丽海赛丽先从浴室的电热器中,为公公专用的水桶装满兑好温度的洗澡水,又给壶里灌满开水后,来到公公婆婆的门前,轻轻地敲着:
“妈妈,我给水桶里装满了洗澡水。如果水桶里的水不够用,壶里还有开水。”古丽海赛丽说完,便轻步跑着似地进了自己的卧室。
老太太和老人进了浴室。他们洗完澡从浴室出来的时候,因为受了凉,老人浑身打着哆嗦。他才看到浴室的窗户是开着的,他想关闭窗户的时候,嗖嗖的凉风钻进了浴室。身上没有完全干,湿着身子出来,凉风直入骨头,不禁咳嗽起来了。但这时的他,精力仍非常旺盛。
“老伴,让你受苦了。我们不会用那个墙上挂着、水龙头只轻轻地一转就出热水的那个东西,会用的话,那可真是个好东西啊。”老人望着老太太,龇牙咧嘴地笑着说。
“喂,不然的话,我们也买上一个电壶吧?刚才我在敲孩子们的门时,感到很难为情。”老太太望着老人说。
“嗨,那个您会用吗?”
“我在超市里见过,既方便,又安全,只要一插上电就可以用了。”
“那需要多少钱?”
“好像说是200多元。”
“怎么那样贵?”
“怎么,吓着了吧?那就算了吧!我就知道您是个小气鬼。”老太太对老伴讥笑着说。
“这是为我们的后事专门存的钱,这您也是知道的。”
“那责任田承包出去的钱呢?是不是还想再娶一个老婆?”老太太望着老伴开玩笑地说。这下可把老人的情绪撩拨开了。老人不理会她的玩笑。
“哎哟,又不是很多钱。毕竟是孩子们养着我们的呢,所以我想那些钱孩子们用吧!”
“艾拉洪是这样说的,但是,那样的话……”
“算了,我这是开玩笑的话。这让女儿给买。今天她带我去了超市,想给我买那电壶,说是她嫂子不在家里的时候,您不会使用煤气炉。用电壶烧水,您也安全了许多。我明天就说让她买。”
“行了,别麻烦她了,我给您200元,不就行了嘛,拿上它明天去买吧。”
“真的吗?该死的。”老太太说着,向他付之一笑,面朝对方倒在床上睡下了。
“当然是真的了,明天我把存折给您,您给孩子说,从那里面取出200元。”
之后,老太太好像安静了下来。不一会儿,就喘着粗气地睡着了。这时,老人的睡意也不知跑到哪里去了,他的心情久久平静不下来。这时的他,就如同住在坎儿井湖边那座大房子一样,开始觉得这间屋子变宽敞、变舒服多了,心里一下子由憋闷变得舒展了。他的思绪穿越记忆的隧道,一会儿飞翔到自己的青年时代,在地下几十米的深处,人只能哈着腰才能勉强容得下的,又矮又窄的暗渠中,拖着短把子爬犁,半跪半坐着挖掘坎儿井的时光;一会儿又飞翔到在坎儿井湖边那片生长着茂密的树林里,满怀渴望的神情等着孜维迪罕的那被爱情燃烧的、热血沸腾的青春年华……如同正在放映着的电影一样,在他的眼前一幕幕地闪现。
不知何故,老人开始出现鼻子发痒、一连串打喷嚏、眼睛发胀、头又闷又热的症状。
古丽海赛丽回到卧室,躺了一会儿后,忽然想起了没有关窗户。因为现在天气已经相当热了,晚上的时候,他们习惯将窗户敞开。然而,今天婆婆要洗头。她在想,他们也许还可能会洗澡。如果是这样……她起了床,准备去关闭窗户。但刚走到门口,就听到老人已经从卧室出来了。于是,她改变了想法,又回到自己的床上并一下子睡过去了。
第二天天刚拂晓,就听到了不平静的敲门声。
“艾拉洪,孩子,艾拉洪,你们起床,快一点,你们的爸爸他……他发烧了。”这是母亲孜维迪罕颤抖的声音。
阿不都热合曼老人被送进了医院。孩子们都来了。他们得知老人没有别的事,只是着凉后得了感冒,只要住院治疗三天就可以好的情况后,孩子们都说中午来,便都上班走了。当病房只剩下两位老人后,孜维迪罕语带讽刺,笑着对阿不都热合曼老人说:
“电壶还买不买?”
“真是个差劲的媳妇啊。”老人翻着白眼珠子说。
“您嘛,就是这样的。当您身体好好的时候,我惦念着您健康;当您病了的时候,我因您的疼痛而伤脑筋。可是,到头来,我却成了差劲的媳妇。”老太太说这话的时候,眉头锁着个大疙瘩,嘴赌气似的噘着,也不正着看老人。
老人什么也没说,也懒得理老伴,只是一笑置之。
第二天病稍微好了点,老人将存折递给儿子:“孩子,你们从这里面取出钱来,把医疗费付了。取钱的时候多取出200元,给你们的妈妈买东西用。”
“算了,爸爸,这是您专门存下来的钱啊,别动您存折上的钱。”
“这哪能行呢,医疗费不付不行吧。”
“我早已经交过钱了。”
“这样的话,你也得从这里把钱取出来,用它填上。”
“爸爸,您对我就不要客气了,儿子也不是外人。”
“你们的负担也不轻呀。”
“那样的话,这账目就当着孩子们的面写在本子上,等你们承包出去的责任田的收入拿到手后,再从账目上分清,您看这样总可以了吧!”
“那样的话,也可以,但……”
“怎么又‘但是了?”
“就是,就是我说的那个烧水的电壶……你从这里面给我取出200元可以吗?孩子!”
“这个,您就不要发愁了。爸爸,古丽海赛丽昨天已经给咱家买了一个,说是给您用的。”
出院两天后,孜维迪罕老太太又去小儿子家了。老太太没有个固定的期限。阿不都热合曼老人想,自己才刚刚出了医院,老太太可能很快就会回来的。因此,只要外面的门的方向有一点儿响动,老人就会急忙回头,伸长脖子去看。然后,或者无望地、心不在焉地面向电视,或者朝卧室里走去。心里不停地嘟哝着:“真是个差劲的老婆呀,我的健康状况都成这个样子了,您回来得了吗?应该能回来呀!”
责任编辑 郭金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