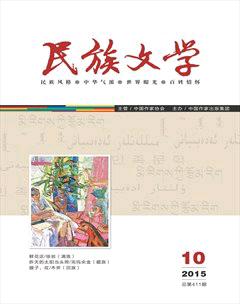昨天的太阳当头照
完玛央金
一
黄土的绕山梁的路,拓宽了许多。原先,路的两旁,菜园、纵横的小巷、一个挨着一个的院落,都被黄土的墙隔开。墙上,尺余宽木板印痕层层落落,那是筑墙的时候农人们在固定好的木板当中填上土,唱着号子,扯起夯,一下一下砸出来的。墙头茅草随风东摇西摆,落着些麻雀和百灵,常常一只对着一只鸣叫,并飞快地扇动翅膀,跳舞,献殷勤。放眼望去,即使不见一个人影,但有那敦厚的墙抚慰视线,便感觉格外踏实。那是些有故事,会讲话的土墙。
墙上方,常见一些树伸出枝来,春天,挑着白色、粉色和黄色的花朵,秋天,缀满金黄或鲜红的果实。那些树下,通常都拴着一只狗,没等路人靠近,警告的狂吠就会由墙的里面传出来。自由的是蝴蝶和蜜蜂们,它们起飞、降落在任何一堵墙的这边或是那边,采花粉,酿花蜜,特别是蜜蜂,频频举行阵容庞大的飞婚仪式,黑压压一片,嗡嗡飞过头顶,狗无奈地在树下望着它们。
巷道里的墙往往被顽皮的小孩用利器划出一道道深浅不一的沟槽。他们拿木棍或者碎瓷片对准墙面飞快地跑过,纷纷掉落的土粒让他们快活得咯咯大笑。这时,有年长的人呵斥一声,他们放慢脚步,贴立在墙根,低下头抬眼偷偷观察面前人的脸。看到他或她语气稍稍缓和下来,立马扭身一溜烟跑开。村里,几乎没有墙是完好的。一户外墙有些低矮,常见一些孩子骑在墙头一手拿块青稞面贴饼子,一手举棵葱,晃着腿大嚼大咽。
黄土的墙,熟视无睹,关乎它,却隐藏着一些秘密。
北山山脚有一家盖新房,在崖上取土筑墙的时候挖出了一个青花瓷碗。女主人不识字,用它舀粮食。一次,家里来了个教书先生,她拿出碗给教书先生看。教书先生拿到碗先是一愣,转来转去一看,接着告诉她这只碗是个宝贝,是五百年前的古董。女主人嘴里哦哦着,拿围裙一遍又一遍擦碗。次日之后,巨大的粮食储柜里换了只缺了口的黑粗瓷碗,家里再没有谁见到过那青花瓷碗的影儿了。
养了五个儿女的贾老四家改建老房,邻人听到整夜传来嘭嘭的挖掘声。一夜,听到轰隆一声巨响,自己的房屋被震得抖了几抖,猜想大约是隔壁的后墙倒塌了,早上赶过来看热闹,却不见星点土坷垃,地面收拾得光光堂堂。不多时日,村子里疯传贾老四拆后墙的时候挖到了砌在墙里的一坛银元,足足有七八百个。贾老四的大哥贾老大住隔壁院子,贾老大刚一听说就跑过院来探虚实。虽然贾老大认为是祖上遗产,贾家弟兄四人,贾老二早年病逝,贾老三远在三百公里外的省城,眼下无人知晓,他们两个偷偷分掉再合适不过。无奈贾老四矢口否认,说没挖到什么银元,捶着胸口仰首赌誓:真是天大的冤枉,我连坛子的毛都没有见到!贾老大狠狠盯了盯已经消失了的后墙,冲那里空荡荡的一地阳光吐了口唾沫,反剪双臂走了。贾老大再也不搭理每到饭口不是借醋就是借盐的贾老四或他的老婆,摸准时辰,一家子早早吃过饭刷净锅碗,大开院门,与老婆子坐在炕上,老婆子纳鞋底,自己咕噜咕噜抽水烟,冷眼等待他们进来,再看他们灰溜溜地出去。
每家家里的墙都被长年累月的烟火熏得黑乎乎,油亮亮的。黄泥掺和麦草的朴素形象早已被改观,火盆里红红的火苗和油灯的光焰在墙面舞蹈,活脱脱是阿婆故事里的鬼怪精灵,小孩子是不敢多看一眼的。遗腹女戎弟和表姐躺在炕上,做各种手影,在墙面上让兔子摇动长耳朵,狼狗张合大嘴巴,老头颤巍巍走路,老鹰振翅飞翔。再往后,过了三十多年,家家的墙面装饰奢侈了一些,报纸糊满了整个房间,戎弟和表姐的孩子像她们当年一般大,躺在当年那盘大炕上,一个人念报纸上的一条标题,一个人来寻找,夜夜重复,百玩不厌。
小孩子们完全不知道身边时时有各种事情发生。村头东智妈这年秋天在外院靠近崖边的空场地簸粮食的时候,突然间左半边身子疼痛难忍,接着全身不能动弹,村里人都说着了风了。东智妈躺了两个月,终于能下炕到檐下晒晒太阳。一日,坐着的她慌慌站起来,急切地朝屋里的东智喊:快!墙倒了!墙倒了!东智十八岁,高中毕业,趴在炕桌上看书,准备参加刚刚恢复的高考。东智三脚两步蹦出来,顺着母亲手指的卧房山墙看去,并没有什么动静,一切都是原来的模样。他对母亲说:没倒,墙好好的啊!母亲说:是我不成了!我不成了!说着,东智妈倒在了地上。东智妈再也没能站起来,躺了一个多月,去世了。墙竟还有这般严峻冷酷的神性,兆演未来,实在不敢怠慢,老人小孩每每走过,感到一种无形的恐惧,不由加快脚步避开。
二
黄土碾就的平坦屋顶,看得见木梯的顶端由房檐边伸上来。屋顶摊开晾晒着刚刚收割的麦子,浓郁的香味里面,头顶白手帕的妇人拿木叉子翻搅麦草。有些人家已开始脱粒,挥舞连枷拍打粮食。这边房顶和那边房顶上啪啪的响声交相呼应,组成美妙的和声奏唱。浮上每个人心壁的歌词都是不一样的。木梯常靠在厨房一边,下了木梯见一溜上房,上房两边坐着厢房。
殷实人家盖着小楼,底层圈牲口,上层居人。房间隔墙均使用木板,装有壁柜,铜制锁扣。铜锁的钥匙常常挂在一家之长的爷爷或是奶奶的腰间,孙子们眼巴巴望着他们能跪上炕沿,两只脚交叉蹭掉鞋上炕,然后撩起衣襟摸钥匙。那多半是要分发给他们糖果或是葡萄干、核桃之类的稀罕物了。楼房楼梯逼仄,仅一人可通过,楼道无灯,早晚间光线昏暗时上下,必以一手扶着旁边的墙壁,一手按腿保持平衡。有极淘气的年少男子,往往在全家熄了油灯准备睡觉时躲在楼梯上等待晚归的人。听见大门声响,他立即站起来,口衔燃烧的木炭,双手撑住两边的墙,一呼一吸。一呼一吸间木炭一明一灭,明时红光耀在裂开的大嘴里,脸上高高低低阴影毕现,进来的人见此情状大叫一声急忙转身,往往提防不住,从楼梯上翻滚下来。随后,就听见家长的破口大骂了:把你妈 × 的,不睡干啥着呢!
二楼有一块二十多平米的黄土平台,太阳红火的时候老人搬个小木凳,坐在那里晒太阳。脸被晒得赤红赤红。农历八月十五,新麦打碾出来,新麦面磨好了,小二楼女主人联络几家邻居或亲戚,烧好鏊子,烙饼子。那些饼子不是通常的饼子,它们被梳子和小铁夹压上或夹出各种图案,沿边被主妇们的巧手捏出各种造型,焦黄的皮里包裹着翠绿的葱花或艳红的玫瑰,它们是八月十五专有的美食。平台上烟火缭绕,小孩子们跑来跑去,断不肯离开锅边,为的是第一时间得到饼子,咬一口讨到满口的香脆。而他们得到的多半不是最好的,那些火候把握不准,烤焦了的被大人们放进手中,还被叮嘱:走路往地下看,吃了能捡到钱!真真有一天捡到钱,是每个孩子执著牵念的美好梦想。
平常百姓家盖不起楼,一院房还是要立起的。三间或五间、七间上房,宽宽的房檐下种几棵李子苹果树,牡丹和芍药花,左右各有厢房,一边住人,一边是牛羊圈、猪圈。住人的几乎间间盘一铺大炕,睡觉时老老小小一字排开。母亲或奶奶睡在靠窗台的地方,为晚上起夜的人一遍遍划火柴点油灯。
灶间连接灶台也是一盘大炕,中间用木板隔开,叫做洒栏子。人人抢着挨洒栏子睡,那里刚刚熄了做饭的火,躺在竹席上还是热乎乎的。孩子们躺在炕上不能马上入睡,你捅我,我捅你,有哭的,有叫的,烦劳了一天的母亲得不到清静,拿起烧火的竹条挨个抽打过去。
房屋的窗户都是纸糊的,分上下两扇,以木条隔成大小方格,中间的大方格镶玻璃,其余地方用白纸或是红纸、绿纸糊上。纸每年换一次,那是腊月里的事情。巧手的村里乡亲被请过来,好茶好烟招待,他或她盘腿坐在炕上,喝一口茶,拿起剪刀在各色纸上剪出花草果实、牛羊猪狗、鱼虫鸟兽,一夜之隔,它们就活生生地欢腾在洁白的窗户上了。
阳光初照,早饭的炊烟在家家屋顶升起,柴草的香气弥漫整个村落,狗也叫起来了,使劲刨地,它们听见了锅碗瓢盆的碰撞声,认定到了吃饭时间,冲厨房里的人撒娇、乞求,还带些小心翼翼的威吓。讨食。
吃过早饭,老弱的妇女收拾碗筷,年壮的劳力们扛起锄头走出院子,下地。三三两两在狭长弯曲的土巷道里遇上,相互问:喝啦?对方说喝了。尔后笑笑,各自向自家的庄稼地走去。只有这里的人听得明白,那“喝”就是“吃”的意思。祖祖辈辈汤面条是这里餐桌上的主打,吃饭时必然连吃带喝,喝的意义还要大于吃,久而久之,“吃”便等同于“喝”了。
腊月一过开始忙碌,话题自然也就多了起来。
一天早饭后某家的婆婆扛着锄头上到了半山上,老不见儿媳妇跟来,回望山下村庄里的家,见厨房上空炊烟重又冒起,料定是媳妇背着家人多放油,多放面,偷做好的吃了。回去抓现行又怕来不及,气的一屁股坐在楞坎上。晚饭过后,婆婆破天荒要给全家人讲古今(故事),看着身旁围坐的老少三代,她讲了个偷嘴媳妇的古今(故事)。儿媳妇红着脸低头不语,最后一把抱起婆婆怀里的儿子回自己屋了。偷嘴媳妇的古今流传开了,而且成了每家婆婆伺机要讲给新进门的儿媳妇听的一个古今(故事)。
三
晚上进巷道,不由人头皮一紧一麻。巷道弯曲再弯曲,向里边伸延,好像没有尽头。家家大门紧闭,门洞黑乎乎的,每走一步,都感到有人跟随。那人默不作声,忽而出现在身后,忽而好像又现在眼前,甩不掉。其实,是风在掀动那些伸出墙外树枝。树枝上叶子密密匝匝,落在地上的影子就是黑乎乎的一个滚动的球团。冬天,特别是冬至一过,巷道里祭过家祖神佛的烧纸,被流窜的风裹挟,绕脚边走,更是冷汗冒出脊背,心也咚咚直跳。
巷道口堆一草堆,每家门口也堆一草堆,旁边站着人。不多时,从里面一家院子传出哭声,随即,听见一声瓦盆摔碎的声响,哭声更大了,哭声中还加有号子,一人呼:起灵!就见七八个人抬一棺木从那家院子里出来,后面跟随着披麻戴孝的孝子们。棺木路过的人家,大门上堆起的草堆早被点燃,青烟阵阵,袅袅娜娜缠绕每个路过人的裤脚。
巷子中间是水路,家家院子和房顶上雨水雪水滴落下来,流出自己挖出的小渠,在院外汇集一起,便成了涓涓细流,路人须得贴墙而行。阳光灿烂的时候,常见老年男人披件外衣,嘴里衔着羊腿骨做的烟锅,蹲在墙根晒太阳。头发斑白的女人们已经老眼昏花,做不得针线,坐在小木凳上,任凭小孙子在膝边绕来绕去,把自己拉扯得东倒西歪。老奶奶们头顶白手帕,手里拿一块看不出颜色的布,擦那笑出来的泪滴。她们满口没有几颗完整的牙齿,凹陷的嘴角口水不时淌下来。狗也来凑热闹,热了躺在老人们腿下,伸出红红的舌头喘气。狗没有忘记自己的职责,眼睛四处巡视,见有陌生人进巷口,立时箭一般射出,汪汪狂叫。它是有十足底气的,它的老少主人都在身后。
小孩子用木棍掏出墙洞里的蜗牛,摆在石板上比大小。他们不理会身后走过去的邻家那个长辫子姐姐,她有意挺着胸脯,站直腰身,让乌油油的一对麻花辫在脊背上甩来甩去,还扭一下圆圆的屁股。巷道里的人停止说笑,都把眼光投向她,待她走过去,一句憋不住的骂声先蹦出来:妖精!那是紧挨着住在姑娘家南面的闹哥曼她妈。闹哥曼二十七了,个矮相貌丑陋,往媒婆那里送过三回鞋了,还没能被说定一家,把她嫁出去。接下来老汉们中间有一个人发言:要给她阿大说一下,管管!像啥话!大辫子姑娘不理会,屁股又多扭了两下,走出巷道。
夕阳一抹金色涂上墙头,老人们起身拍拍屁股腿上的土,拉上孙子各回各的家了。
四
太阳直射,黄土地热气腾腾,最先是青葱的味道窜出来,仔细嗅,可以分辨出韭菜、芫荽、蒜苗,还有白菜、菠菜、芹菜的清香。那是每家房前或是房后欣欣向荣的菜园。向日葵守在地垄,它不加入这一番热闹的场景,慢慢地发芽,慢慢地抽干,慢慢地开花,最后,在秋天肃杀的冷霜中美美地鼓起一腔饱满的子实,幸福地摇晃。
孩童的顽劣中,多次遭殃的是青葱,它们刚刚探出水嫩的叶子便被他们揪下来,填塞馋透的嘴巴。常见一名妇女追在后面,手指其背大声斥骂:再揪我的葱,把手指剁下来!吃葱的孩子跑得远远的,挤眉弄眼。
雨下了一天又一天,菜园里的菜叶舒展开身体,绿得没法说清。已经十多天没见水分了,泥土干得裂开了口,这时候只听见甜蜜又贪婪的吞咽声。雨中夹杂着菜蔬们哗哗的欢笑。
一日,叫康珠妈的女人在菜园间菜,听到一墙之隔邻家菜园有人说话,仔细听听是刘老汉儿媳妇在跟自己的妹妹说话,她吩咐道:酥油在韭菜底下,韭菜我拔的多,盖的严,看不见。一路把背篼背好。邻家刘老汉早年丧妻,患严重的哮喘病,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在百里外的牧区做事,常带来酥油、牛羊肉,让四邻羡慕。小儿子才十一二岁,不去上学,在家当羊倌。大儿子三个月前由老汉托媒成亲,新媳妇矮小伶俐,口甜如蜜,很讨公公喜欢。公公不管事,每天有吃有喝就行,家道交儿媳妇掌管。康珠妈故意咳嗽一声,墙那边顿时静悄悄的了。后来传说那媳妇的妹妹回家,途中,在一座山坡上休息,她解下背篼往地上放时没放稳,背篼翻倒了,里面的菜一下泼出来,一坨酥油也顺坡翻滚而下。一同还有伴,事情很快就传到村子里,人人皆晓,可能只有那媳妇的公公不知道,他常年出不了门,盘腿坐在炕上,靠着被垛喝浓酽的砖茶。康珠妈倚在院门上,看着邻家大门叹口气说:男人是耙耙,女人是匣匣,匣匣漏了,耙的再多也要漏掉。
菜园子不仅仅种菜,各种果树、鲜花也置身其中。李子、杏子、苹果,春季便性急地开出了繁盛的花朵,菜苗还在安静地等待身体一分一分长高,地边上牡丹芍药到了春末夏初才不慌不忙地一朵接一朵绽开,豆角,不知何时起,一条条挂在了它们的上方。
果子熟了,摘下来,按大小、成熟度分等次堆放。有疤痕、青涩小一点的自然是自家人首先要吃掉的,好的送亲邻或是摆上街卖掉,一同上街卖的还有时令蔬菜。卖水果蔬菜的活通常由妇女干,她们一大早起来摘果子、拔菜,在园子边精心“打扮”那些李子杏子苹果和萝卜青菜,一个个擦得干净透亮,梳理得整齐有序,像打扮自己的儿孙那样,不留一丝缺憾,然后放进背篼、提在竹笼里,拿到街上去卖。有果树多几棵的一户人家,老两口,果子堆放了半间房,外地工作的孙子刚娶了媳妇带回老家认亲,奶奶端出半盆子长把梨招待他们。新媳妇看到梨子几乎个个腐烂掉半边,很感动,她心里说奶奶爷爷真是可怜,梨子烂成这样了还舍不得扔掉,她忍着喉头涌上的酸涩,仔细削好梨子,认真地吃了两个。下午,她拉着丈夫要上街给爷爷奶奶买新鲜的水果,丈夫支支吾吾说不用买,说他们吃不了。新媳妇说不动丈夫,独自走出屋子到院子里转悠,她转到屋后,看到有个柴草房,好奇地进去一看,发现一大堆摘下来的果子,苹果、梨都有,一个个全是鲜亮完好无损的。她又气又恼,觉得奶奶心里没自己,回去便闹着丈夫要走。丈夫无奈地笑着对她说:你看看,都是果子惹的祸!丈夫解释不清在老家,老人们习惯于存放任何一种食物,哪怕那种食物再多再好。常常是腐了好的吃霉的,他们在对各种物品的存放中满足并快乐着。
快到冬天的时候,最后一茬菠菜一寸来高,被挨地皮铲下,在有些凉意的阳光里抓紧晒干,放到硕大的簸箕和笸箩里保存下来,进入冬季,抓几把放在三餐汤面里,绿茵茵的,享受在四季中轮转的踏实。
五
爬上山坡看,一个个院子组成了一方小小的棋盘。好多人家分里院外院两个,外院由半截土墙,半截木栅栏围起,有厕所、粪堆什么的,里院住人。手腕粗的树干扎成外院简易大门,门的旁边拴一条狗,狗汪汪大叫的时候,里院就出来人了。家家大门柱子跟前有两块大石头,上面常坐些老人和小孩。
漫长的冬季,堂屋高深的大躺柜里麦粒丰足得就要顶起盖子,满满一菜窖的洋芋、胡萝卜,还有白菜,压实了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的心,男人们没日没夜喝酒、摇色子赌钱,女人们做针线,为一家老小赶制过年的新衣。
那年,城里风行蜂窝围巾,一个十三四岁的小女孩围着粉红的蜂窝围巾跟哥哥回老家探亲戚。兄妹俩手拉手走进凸凹不平的村道,哥哥把沉沉的旅行包扛在肩上,腾出一只手拉着妹妹。先是有一两个闲人看见了两兄妹,很快,有不少人出来了,他们站在自家大门口,还有更多的人爬上房顶,一些腿快的甚至登到了更高处的崖边上,静无声息地观看。小女孩也看着他们,两只眼睛先是好奇,后来显得慌乱不自在,最终有些气恼了,低头不看他们,快步跟哥哥往前赶。小女孩也感觉到了哥哥心情的紧张,哥哥握着自己的手,越来越紧,拉扯自己越来越用力了,脚步也快得自己几乎要小跑步才能跟得上。过一家大门小女孩听见站在柱子旁的一个大妈说:这个新媳妇这么尕的!长得心疼得很!小女孩抬头看了看哥哥,哥哥正好也在看自己,他们相视一笑,心坦然了。兄妹俩到了亲戚家,舅妈才急匆匆从外面小跑进来,嘴里嚷道:说是外面来了一对新人,戴红头巾的新媳妇尕得很,我跑出去看了,人家说进你家了,我又赶上回来了,原来是你们俩啊!
舅妈性急了些,村子里第二天果然是有婚事。
一户人家迎娶在县上坐办公室的儿媳妇。凌晨三四点,巷子里就有咚咚咚的脚步声和妇女的说笑声。哥哥还睡着,小姑娘起了床,舅妈不在家,灶头上用碗扣着四只荷包蛋。小姑娘吃了两只,留给哥哥两只,扎好小辫出了门。
村子东头一扇院门里人出人进好不热闹,抬眼望进去,院子里摆上了方圆不一,高矮不同的十几张木桌,厨房门里腾腾白色蒸汽一团团涌出,只闻女人银铃般笑声不见其人。一伙男人围着其中一张桌子猜拳喝酒。日头照满整个院子的时候,有人喊叫:新媳妇来了!屋里屋外的男男女女往外奔,几个被算着是属相犯冲的人躲进厨房一角。新媳妇被人搀扶着进院门了,小脚碎步,一方大红绸巾遮盖住面庞,新郎对襟黑袄,身披交叉大红绸带,脸露疲惫而幸福的笑容。婚宴席是流水席,现来现吃,直到黄昏。
这一天,家家院门大开,空无一人,老半天有女人进来烫一盆豆衣和舀一碗剩饭端给猪和狗,又忙着出去,老人小孩都在办喜事的那家院里。有陌生人进村也不贸然走进谁家院子,站在大门口喊上两嗓子,引来狗叫,才会有这家主人匆匆赶来看究竟。静悄悄的院子静悄悄的房间,流浪的狗和猫窜出窜进,大肆偷情。
那个办了喜事的院子几十年后由一堵土墙从当中隔开。家里两位老人先后离世,两个儿子分家单过。小儿子两口子虽在县上,男的经营茶馆,女的拿公家薪水,却是毫不退让,生生把老家分了一半出去。分出去的那一半院子没有人照管,几年后房屋倒塌,
院子里荒草齐膝高,积水成潭,成了地鼠、青蛙们的乐园。
荒掉的院落相继多了起来,黄土将村子涂抹得一片混沌,菜园及耸立的树,褪尽了颜色。仅留存的几个院子,散发着畜粪合着柴草烟火的味道,偶尔听得见老人唱“什巴”(当地节庆或婚丧嫁娶时的歌舞)的苍哑的声音,孩子的欢笑声也飘出来,四巷空无一人。
伸向村外的土路多年后被柏油覆盖,一个个院落也消失在森林般竖起的高楼之下,你来我往的人少了,防盗门隔离了烟火的味道,封锁住了村里乡亲一日三餐客套却是从不曾缺少的问候。单元房要装载许多新的内容了,脚踏水泥地仰头看天,还是昨天的太阳,昨天的云彩。
责任编辑 陈 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