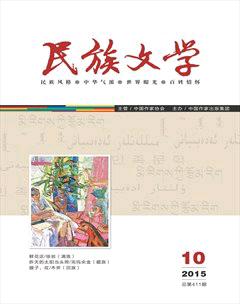月光梳过的地方(外一篇)
钟而赞
月梳洋!这真是一个美到极致的名称。况且,她还是先人,甚至是宗族从那时开始一直延续到今天的居住地。
翻开《福鼎畲族志》,最初的目的,是为了查寻宗族的由来。志上的记载却十分简单:“钟舍子自永乐二十一年(公元1404年),由福建建宁卫入迁福鼎店下夏家楼屯种定居,后转徙西岐月梳洋发派。”目光触摸到这个名词,心中不禁为之一动,而后便沉醉于一幅绝妙的图画:幽蓝的夜空,如梳的弯月,素洁的月光仿佛飞出千枝万枝玉色的梳齿,轻洒在一片不张扬阔大也绝不狭小逼仄的平野。村庄卧在平野与群山牵手的位置,承受着月光的抚爱,宁静而安祥。
我是把现在叫西岐的这个村庄当作梦中的月梳洋了。不然,月梳洋又在什么地方呢?志书上的记载至“月梳洋”戛然而止,她与西岐之间,是一片朦胧的月光,是一段无法抵达的距离。最初以为,她应该就在附近,于是向父辈询问,居然都不甚明了,只是依稀听过有这样一个地方,却是与己无关的一个缥缈之处,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与宗族的身世有怎样的联系。倒是一位被认定为神智有点不清楚的外姓人指出了具体的方位,说是村庄东向某处山谷就是曾经的月梳洋。他原先住在距离山谷百步有余的一个叫墓湾的山坳里,父母在世时曾有一座面阔三间的茅草房,现在已是孑然一身,因为造福工程,也已搬到我们的村里来居住。
墓湾似乎是借来的名称,它最早应该是指称山坳背后的那一片松树林,那里是我们的先人安息的地方,我仅在奶奶去世时去过一次。而也叫墓湾的山坳,却是童年常去的,当时还有另一座简陋的草寮,住着另一户人家,女人是哑巴,养着三个女儿,她们相继出嫁后,两位老人好像不久就过世了。我们的常去,一是因为与两户人家的子女年龄相仿,能玩得来,二是因为那一片柑橘林。山坳位于两座山的北面,两山之间有条小溪,溪两侧的山坡和上游的山谷中密实地生长着许多柑树和一些橘子树。这是生产大队的果园,也是我们童年时的乐园。未结果时我们在果树林里捉迷藏、捕蟋蟀、挖坑做灶搭上瓦片当锅烧烤食物。果树上开始挂上青涩的果实时我们便会做一些与年龄相称的坏事。园里有人看守,不过要躲过他们的目光却不是一件难事,而且,看园的人往往也不当一回事,也就吆喝几声,最多不过拿着一根细小的竹条追一追。
我却不愿意相信。
在我的印象里,“洋”是一个广阔的概念。面积不大的小山谷,而且并不平坦,怎么能称之为“洋”呢?翻《辞海》,却又怀疑“月梳洋”应该是“月梳垟”的讹变。辞典中“洋”字的四条义项与作为地名的洋毫无关系,倒是“垟”字只有一条解释:用于地名,如浙江乐清县有翁垟。家乡地处闽东,与乐清所在的浙南地区相邻,这一片区域,被称之为“洋”的村落很多。或许是因为生僻,原先的“垟”就被后来的“洋”取代了。我的关于“洋”的认识,一是海洋的概念先入为主,二是因为在我的家乡,只要是成片的农田,也都拥有一个后缀为“洋”的名称,而与山里人相分别的一个名词却又是“洋下人”。但是在我们村庄背靠的群山中,那些散落山旮旯里的村落,山坡山谷开几块狭促的山丘田,却也有个以“洋”为后缀的村名。这样的事实仿佛就是为了确认:满栽着果树的山谷,就是我的月梳洋。
然而终究不能确认。我更倾向于相信,温和地卧在村庄眼前的这一方良田才是我的月梳洋。她被三面的山围着,山与山之间,草木和岩石覆盖着几道山谷,山谷中潺潺而来的几条小溪,各自经过一段低调暗伏的行进后,在村前汇合成一条宽约两米的小河,蜿蜒着流向前方,汇入不远处的大海。这溪这河,怀着盈盈的爱意,滋养着这片村庄、田园,即使遭遇连续多月不下雨的干旱,也不肯完全枯涸,固执地、而又心力交瘁地延续着地表之下隐秘的哺乳。肥沃的粮田,数百年前还是一片浅海、一处滩涂,横亘在左右两山嘴之间的是一道塘沽,把潮起潮落挡在身外,围住一片生存的希望。塘沽已经成为车来人往的路,连接着村庄和外面的世界,却不叫路,还叫塘沽。我无法想象先人当年以肩挑手提的方式取土筑堤、拦海造田的场景,潮水是日日夜夜要来的,一定一次次冲走过那些石头、沙袋,直到有一天,终于有一块石头站稳了,有一个沙袋顶住了,而后是第二块、第十块、第一百一千一万块的石头、沙袋紧紧相依相偎,拦住了不死心的、更加肆虐的潮水,箍住这方圆数百亩散发着咸涩滋味的土地,平整、淡化,一年一年地尝试着播种,一年一年地失败,不怨不悔不离不弃。第一颗种子萌芽了,第一株庄稼成长了,第一条稻穗金黄了,这时才看到人们的脸上有了眼泪,在六月酷烈的阳光下,闪烁着光泽。
志书里记载的夏家楼,是宗族最初的落脚之地。作为领兵屯种的一名军官,不知道出于什么样的缘由,始祖选择了永久留下来,在这里开荒垦殖,繁衍子孙。叫夏家楼的这个小山村,落在村庄背倚大山里的一处山坳,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只剩下一排土墙黑瓦的破旧矮房。当最后一拨宗亲离开了那里搬到现在的村子来,那一排低矮的老房很快就破败、坍塌,成为一堆废墟。今年因祭扫祖墓,近距离寻找过它,却早已踪迹全无。我倒不为夏家楼的消失而伤感,从三百多年前第一批宗人下山寻觅新的家园开始,似乎就注定了它最终的命运,我在意的是从祖先定居夏家楼到今天的月梳洋这六百多年时光,仿佛有一种强大的力量支撑着一个宗族筚路蓝缕,为梦想中的另一种生活砥砺前行,自强不息。就像横筑在月梳洋之上的那道塘沽,拦住一片沧海,拦出一片肥沃的良田和丰足的生活,成为路,引领着一代一代乡亲走向更远的前方。
我已经不在乎她是叫月梳洋还是西岐了,对于我来说,她是带着体温的,就像母亲,不用说出来叫出来,一想起她,心里便油然而生一种温热甜蜜的感觉。这个数十户百来人口的小小山村,坐落在一年四季绿意葱茏的群山脚下,与十里八村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倚赖着、护佑着面前这一片宽广而丰厚的粮田。她是我的家乡,拥抱着我的童年和绝大部分少年时光的摇篮。我记忆着她的每一寸肌肤和附生在肌肤上的每一根毛发,记住在她温暖的体温中行走、飞翔、休憩和沉淀下来的动和静。每次回到村庄,脚步在她的肌肤上移动,目光在她涵养的人事与物象中游走,总是情思纷扬,甚至于不能自禁地让眼眶含着温热的泪水。
月亮从东向的山头徐徐升起,朦胧的清辉盈盈漫开,轻裹着山坡、果树林、村庄、田野,轻裹着小虫的浅唱、夜鸟的低吟、溪水的细语和三两声含混的犬吠、小儿的梦啼。独自静静地站在老家的院子里,沉醉于月光的温柔抚摸,沉醉于那些微渺的声音,关于村庄的所有记忆突然间变得清晰,可触可摸,可闻可感。那些纷芜的人物故事,不再拥挤争吵,它们自成一个又一个独立的单元,在各自的位置上轻轻地变换着各自的形容、各自的情节,又在月光的梳理下,互相牵连、交合。农家生活的紧凑与辛劳,困苦与伤痛,随着纤柔的月光飘散。
这就够了!对于乡亲们,以及先人,还有什么必要去寻找恍然如梦幻的月梳洋?
清明的鞭炮
天还没亮透,两只耳朵就已经竖立起来。粗陋单薄的砖墙木窗阻隔不了乍然鸣响的一串鞭炮声,我们可以准确地判断它的方位、地点,而后猴急猴急地掀被、穿衣,拉开门奔出去。也只有这样的时候,对于我们不管不顾又冒冒失失的匆忙,父母亲才不会斥骂。
村子的左边是山,右边是山,背靠的还是山。山脚山腰山坳坐着至少十来孔坟墓,后一层再后一层山里,还有不少。鞭炮声就来自其中的一处或几处墓埕。对于我们这些山村毛孩而言,这鞭炮声的意味是:每个人都将无偿获赠三五个饼。
大多是光饼,稍好的是软饼,有时还难得遇到油饼、芝麻饼,与代销店里搁在玻璃罐子里的没有任何区别,比起上街时经过作坊看到摊在笸箩里的,因为凉了受潮了,更少了香气和酥脆的口感。但它有个特别的名称,叫墓饼。代销店里的,作坊里的,我们必须用钱买或者用米和谷子换,在温饱是头等大事的年代,得来并不容易。这墓饼,来自赐予,我们所要做的,就是追着鞭炮声赶到现场,然后把两只小手向前高高地伸出去,叫着:我这儿,还有我这儿。
这是整场祭墓活动行将结束的一道程序。燃香,上供品,烧纸钱,拜过先人,走过这几道,接着燃放一挂鞭炮,既是宣告祭祀的圆满结束,也是通知远近人家来受墓饼的赏赐,像是代替先人,把他们的福乐赐予更多人。
先前已经放过一挂鞭炮了,在祭祀开始时。起始和结束,都要有个表示,或者就是发布声明、宣告。在我看来,认为燃放鞭炮是为了表达喜庆、渲染喜庆大概是一种误解,它的作用应该是广而告之,可能还不仅是向人民大众,更主要的是向皇天厚土、山川鬼神。婚嫁寿诞如此,丧葬禳灾亦如此。朴素的人民相信生活的安宁幸福来自天地鬼神的赐予和佑护,所以他们总是向神明告知喜事丧事,表达自己的虔敬、感恩和祈求。
无论是哪种仪式,最后的一项内容,通常与吃喝有关。事大,要宴请,少则一两席,多则十来席甚至数十席;事小,比如清明祭祖,分发光饼、软饼、芝麻饼,都是表示分享的意思,当晚,也是要略备几样小菜几杯淡酒邀来三五亲友聚一聚的。一些时候,鞭炮宣告过了就可以了;另一些时候,除了宣告,还要先敬供神明以酒食,然后才轮到人的大快朵颐,似乎表明,神明已接受了敬奉,开始赐福,且希望或者就是指示要福泽更多人。
不能理解我们的作为为什么被称为讨墓饼。讨,就是索要;而且据说,来讨饼的人越多,将给墓主人带来更多的好运。既然是赐予,既然能带来好运,又怎能说接受的人是索要呢?那时的我自然不会有这样的疑惑,然而生气的时候是有的。有时听到鞭炮声赶到某处墓地,却见祭祀人已经离开了,墓埕上是一小摊还发热的鞭炮皮,角落里的纸钱也还未完全烧成灰烬;有时赶得辛苦,分到手的是每人两个或才一个饼,甚至没分到却还要被斥责是耍赖要了一次又一次。当场不敢表达愤怒,过后是一定要对墓主人的吝啬来一顿狠狠的抨击。现在回想起来,不免为那些墓主人感到辛酸,如果不是因为穷,又何至于为了少几个讨墓饼的孩子而摸黑,匆匆忙忙来拜见祭奠先人,要计较多给别人一个两个不值几文钱的光饼?一边希望获得先人的福佑,一边又以促狭让自己也让先人蒙羞,他们一定也很无奈和难过吧。
记忆中的清明,总是雨水淋淋,雾岚缥缈,仿佛伤感无所不在。是因为这是祭奠追思先人的节日吗?如果是,可知天地有心,特意为人间布设了这样一个有别于平常日子的时空了。
人们的脸上却看不到太多的悲戚。清明祭祖,对于他们来说,与晨炊暮霭并无本质的区别。时光和人生的本来形态,实在与山间流淌而来的那条溪流无异,无知无觉一路走去,该跳跃就跳跃,该拐弯就拐弯,过程和结果已经摆明,所以也就无需揣测、质疑,付以悲伤或欣喜。死亡并没有带走什么,就像溪水顺手扯去岸边的一株水草一朵野花,很快就有新的水草和野花填充了短暂的空白。小小的异样感,不是因为天气,也不是因为清明和祖先,是生的患得患失和对死的不确定不自信的索求。一切仪式都是如此,它们成为一种习惯和传统,隐喻的意义早已模糊,若有似无,又叫人有所忌惮有所期待。
我们自然不会去关心那一张张脸是不是欢喜和悲伤,也不会在意一阵又一阵的清明雨,甚至对于被打湿的头发、衣裳和身子无知无觉。清明并非只有祭墓的鞭炮吸引住我们,那些蜷缩在岭下林间的一丘丘,裸露在山头山坡的一片片,是绿得青翠绿得可人的茶园。鹅黄的新芽密密匝匝又秩序井然,像是一群群刚脱壳的小鸡小鸭,齐刷刷向上张着嫩黄的喙,吵吵嚷嚷地叫唤。戴着竹笠披着无色薄膜的女人三三两两落在这宽广的绿幕上,透明薄膜遮掩不住的红黄蓝绿是信手点缀的色彩,在氤氲的雨雾中洇染成一团团一簇簇。站在某处岭头,我们争抢着指点叫喊自己的母亲姐妹姑娘嫂子,为谁今天采多采少争执不下。突然便觉得有些无聊,于是散了伙,各自跑到母亲身边,讨好卖乖帮忙采摘,享受母亲的一声夸奖,眼睛却不安分,东张西望寻找先前还闹在一起的伙伴,期待谁呼唤一声,或是哪儿响起一挂祭墓的鞭炮。
这样的欢乐从清明一直延续到立夏。这一个月里,除了清明,人们还可以另挑一个合适的吉日祭扫祖墓。习俗也照顾人情世故,想到这段时间恰是春茶采摘和田间农忙之季,便不固执限定单一的活动日子。春茶值钱,一阵暖风一场酥雨拂过,前些天刚采过一茬的茶园又是肥芽密布,追着你鸡叫五更就开始一天的匆忙。联产承包制刚实行不久,新的山地还没开挖,分到名下的茶园,这家两分那家半亩,还不至于让人忙不过来。赶,是为了挤出时间去大队的茶园多挣几块工钱。那大片大片连峰带谷的茶园,是当年城里来的知青和父辈们并肩作战的成果,也还未以承包经营的方式贱卖给村里几位所谓的能人,山坳里那一座规规矩矩的青石黑瓦房,还遗留着知青的痕迹,散发着那个时代的气息。恍惚记得大队给予的出工价是每斤几分,一天下来一个采茶女工的收入大约不超过七八角。而这沾着春雨和茶香的小小几张皱巴巴的纸币,足以让她们用爽朗的牢骚和笑声推开一天的疲劳。
即使读到杜牧,读到他笔下那场叫人断肠的清明雨,还有如泪的雨中饮着愁绪的杏花村,我的心空也还是一片晴朗。童年成为过去,但不意味着永别,甚至还不曾远离。祭墓的鞭炮声不再吸引我们,但漫山遍野的绿,繁忙的田间山野溅起几朵淘气的水花,都还美好地活泛在记忆里。
一个画面被淹没在纷杂的快乐中:父亲扶着犁铧吆喝那头黑水牛踩着清新的泥土和舒缓的节奏行进。跟在身后的我,忙不迭地又揪又捧,把那被犁铧翻出来、断了冬眠美梦的一尾尾滑溜溜的肥硕泥鳅,收进一只破旧的搪瓷杯里。
仿佛只是转了一个身,便落入了中年。一年一年的清明,忽然就有了不同。那雨还淅淅沥沥,有时却阳光明媚,然而心灵间藏着挥不去的似浓又淡的雨气。清明成为牵挂与期盼,是在父亲去世以后。八年了,三千个日子,时光一直迷迷蒙蒙,等待着清明这一天拨开阴霾还自己一个清醒。似乎是,与父亲有过一个约定,一年中的一次相会,就在清明。
已步入暮春时节。草木葳蕤中卧着父亲安息的家园。鞭炮声响起,燃香、上供品、烧纸钱,哥哥和几位堂兄弟在忙活着这些事。我只静静地贴近属于父亲的那间卧室,蹲下身子,默默地告诉他什么,默默地听他说什么。墓旁的万年青,枝叶已经很繁茂了,双眼一般大小的叶片,在三月轻盈的细雨、明媚的阳光中,绿得湿润柔和。我知道那是父亲的目光,目光里有话,像曾经那样。
没几个孩子还会关注清明的鞭炮声。饼是越来越精美了,应该也更可口,甚至有人想到了发钱,但都没能引来更多讨墓饼的人。山野平时是寂寥荒凉的,这一天倒是这儿一群那儿一伙。漫山遍野的茶园,零零散散地布着几个黑点白点红点,是留守在家的妇女和老人在各自的茶园里赶着季节采摘茶叶。祖先们似乎也已吃饱喝足,又回到漫长的睡眠里。接下来的热闹在家家户户的厅堂庭院、街上的酒店里。当亲人相聚推杯换盏成为清明的新主题,落在心里的最后一幕雨帘,大概要云收雨霁了。
责任编辑 石彦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