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教书匠
刘照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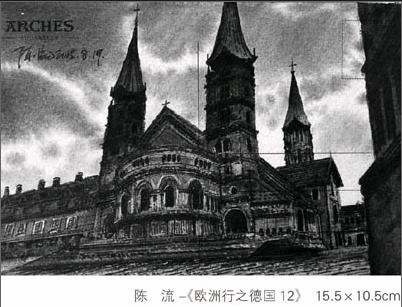

1
康庄镇西头住着一个名叫苏良的50岁男人,是一个私塾先生,在家里招收了十几个孩子,教他们念书。但是日本人来了几年之后,这十几个孩子,或者跟着家里大人外出逃难,或者被家人藏在屋里躲避灾祸,渐渐地都离开了学堂。苏良家的院子显得空荡荡的。
没了学生,苏良也就没了经济上的来源。苏良自幼念书,长大后一直做塾师,不会种地,也不会做生意,学生都离开了,他只能靠以前的节余过活。好在家里只有老两口,一个女儿已经出嫁,一个儿子在济南商埠当学徒,都不用苏良接济。闲来无事,苏良写写字,读读书,窝在家里不出门。
这天清晨,苏良拉开堂屋屋门,一股冷风让他打了一个寒噤。夜里悄无声息地下了一场大雪,地上的积雪已有一尺多厚。现在雪已经停了,苏良打算到东厢房里拿一把铁锨,铲一铲院子里的积雪。东厢房原来是学堂,学生离开之后,屋子里的书桌都已经码起来,另外放了一些柴草和杂物。就是在这个时候,苏良发现了雪地上那道宽宽的印子。
那道印子大约有三尺宽,从大门口一直延伸到东厢房门口。很明显的,夜里雪下了很久之后,有什么活物匍匐着爬进了苏良家的东厢房,弄出了这道印子,后来的落雪没能把这道印子完全盖住。苏良的心紧了一下,想到了自家的大门。苏良家的大门,有一扇门板下端朽掉了一块盆盖大的木头,平时经常会有狗啊猪啊甚至小孩子爬进来。苏良家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不怕偷,他很长时间并没有在意大门上的门洞。现在终于出现了这样的情况。
苏良踅回屋里,拿了一根顶门棍出来,踩着积雪猫向东厢房门口。他在门口停下来,侧耳听屋里的动静。东厢房里很安静,什么声音也没有。苏良在门口又停了一会儿,眼睛盯着门缝,心里默默地数着数,好像是在用这样的办法给自己壮胆。然后他再次哈下腰,把耳朵贴近门板,听屋里的动静。但这次苏良仍然觉得东厢房里很安静。苏良用顶门棍朝门板上捅了一下,门扇吱吜一声打开了。
苏良在他家东厢房里发现了一个男人。那人蜷着身子躺在屋角的一堆稻草上面,穿的衣服比较单薄,是薄棉袄和薄棉裤,但身上裹着一床认不出颜色的棉被,棉被很破旧,有几处露着瓦灰色的棉絮。那人身边的稻草上,还放着一个有豁口的饭碗和一根三尺长的棍子。很明显,躺在这里的人,是一个讨饭的乞丐。苏良用顶门棍捅了捅那个人的屁股,那个人没有动;他又捅了捅那个人的肩膀,那个人还是没有动。苏良扔下顶门棍,蹲下身子推了推那个人,发现那个人的身子像一截树桩,这才知道那乞丐怕是已经冻僵了。
冻僵的乞丐胡子和头发都很长,脸上也很脏,但仔细看一看,却是一个年轻人,年龄不超过30岁,他的脸上和手上都长着冻疮,那些冻疮已经溃破了,疮口流着黄水。苏良把手放在年轻人鼻子下面试了试,觉得这人还有微弱的气息。那就是说乞丐还有救。苏良想要搭救这个年轻人。
苏良把年轻人的身子搬动了几下,让他的身下铺上更多的稻草,又到堂屋把老伴叫起来。苏良告诉老伴说,“老婆子,你不要害怕,夜里下大雪,家里爬进来一个乞丐,现在躺在东厢房里,人已经冻僵了。”苏良让老伴找了几床被褥,两人抱着被褥到东厢房。苏良的老伴看到躺在稻草上的乞丐,连声说,“可怜死个人,真是可怜死个人呢。”
他们把两床褥子铺在年轻人身下,两床被子盖在年轻人身上,把年轻人裹起来了。做完这些,苏良又嘱咐老伴到灶房里去烧水。苏良说,“老婆子,你去烧水,用大锅烧,多烧几锅,不用烧开,烧热就行了。”苏良的老伴一边答应着烧水的事,一边说,“水缸里面有一根井绳,你把它拿出来放在窗台上;下面的地窨子盖,那块盖木已经朽了,你当心别把地窨子踩塌喽。”苏良的老伴知道苏良接下来要做什么,两个人在一起生活了30年,如今老了,心思很是默契。
苏良来到院子里,眼睛盯着放在东厢房南山墙旁边的一口大水缸。以前学生都在的时候,人多,喝水也多,苏良就添置了这么一口盛15桶水的大水缸,现在学生都不在了,水缸搁在院子里。水缸压在地窨子的木盖上面。苏良用脚扒拉了一下积雪,然后蹬了蹬缸底的木盖,发现那块盖木确实已经朽了。把水缸里面的积雪也清了清,果然看见有一根井绳躺在里面,苏良把井绳取出来,放在了东厢房的窗台上。
地窨子是前些年乡下的亲戚帮苏良挖出来的,主要是冬季的时候在里面贮藏一些红薯。红薯也是乡下的亲戚用地排车拉来,送给苏良,让苏良老公母俩调剂一下冬天的吃食口味。原来学堂正常开课的时候,家里孩子多,苏良怕孩子掉进窨井,就把大水缸压在了地窨子的木盖上面。
苏良把水缸放倒,在雪地上慢慢地往东厢房门口滚动。苏良的老伴从灶房里探出头来,说,“也不知道你这个办法能不能把那个人救活呢。”苏良说,“试试吧,不试咋能知道呢,总不能看着他在东厢房里挺过去吧。”
苏良除了当塾师教书以外,还是个半拉子大夫,有时候他也能给牛马猪狗看病,又是个半拉子兽医。镇上还有一个有名望的大夫,但那大夫看病收费太高,一般人请他不起。平时苏良家里人或者学生有点头疼脑热的,都是苏良自己来诊治。
这天早晨苏良想要救活冻僵的乞丐,打算使用这么一个办法:烧几锅热水,倒进一口大水缸里;水不能烧得太热,温度要和人的体温差不多;然后把乞丐放进水缸,泡两个时辰,这两个时辰里面,还要不停地往缸里加热水,保持水的温度始终和人的体温差不多;两个时辰之后,乞丐就会苏醒过来。去年冬天的大雪天里,苏良曾经用这个办法,为镇上的铁匠家救活过一只冻僵的看家狗。
大水缸被苏良摆放在东厢房的屋当门,他的老伴陆续把几锅热水倒进水缸里。苏良隔一会儿就把手伸进水缸,试一试水温。热水烧得差不多了,等到该把乞丐脱掉衣服放进水缸的时候,苏良遇到了问题。苏良的老伴表示乞丐是一个大男人,把他脱得光腚拉碴的,她不能在场,她要苏良一个人去弄。苏良一听这话就急了,他吼老伴说,“这个讨饭的还是一个孩子,你是一个老太婆,你怕什么?”苏良的老伴望着苏良的脸,迟疑了片刻,只好扭着脸帮苏良,一起脱那乞丐的衣服。
乞丐的身子很僵硬,腿和胳膊都不打弯儿,他们费了好大劲儿才把乞丐的衣服一件一件脱下来。苏良发现乞丐除了手上、脸上和耳朵上有几处溃破的冻疮以外,上身还有几处青淤的伤痕和很多细小的针刺印痕。把乞丐的衣服全部脱光时,又发现那乞丐没有穿内裤,裤裆里却缠着一块兜裆布。兜裆布是白色的棉布,在裤裆里乱七八糟的缠了好几层。苏良的老伴瞥了一眼乞丐的裤裆,说,“多大的人了,咋还缠着尿戒子!”
苏良的老伴说完这话,红着脸望了望苏良,却见苏良脸色煞白,嘴唇发紫,像是突然得了虐疾一样身上发抖。苏良的老伴问,“老头子,你咋着了?”苏良抖着,不说话。又过了片刻,苏良的两只手也像树枝一样僵直,不听使唤了。苏良举着两只手,哆哆嗦嗦地说,“老婆子,我的手,你看看我的手。”苏良的老伴赶紧把苏良的两只手搂在怀里,撸他的手指头。苏良的手指头像铁勾子一样又凉又硬。
太阳已经升起来老高了,雪后的晴天天光白亮。东厢房里亮堂起来,被脱光的乞丐的身子也花花的显得白亮。苏良老公母俩忙乱了半晌,但还仅仅是把那乞丐脱了个精光,他们并没有把他弄到水缸里去。苏良举着两只不听使唤的手,顾自说话,他的老伴一会儿看看苏良,一会儿看看乞丐,不知道如何是好。
苏良举着两手说,“老婆子,你看看这太阳也出来了,我说实话吧,我的手这个样子是遭报应了。”苏良的老伴诧异说,“你没有作恶,能遭啥报应?”苏良说,“刚才我想弄死这个人,我想掐死他,结果我的手就成这个样子了。”苏良的老伴说,“你为啥要弄死他?你不是要救他吗?”苏良看了看自己的两只手,又看了看屋外的天色,接着说,“老婆子,你看看这太阳也出来了,我说实话吧,他是一个日本兵。”苏良的老伴不信苏良的话,她差点笑出声来,“你咋知道他是日本兵呢,他脸上又没有写着日本字。”苏良的老伴又说,“日本兵咋会成这个样子呢?”苏良说,“老婆子,太阳出来老高了,我不骗你,他就是一个日本兵呢,日本兵裤裆里都缠着一块兜裆布。”
苏良的老伴听信是日本兵,脸一下子变得发黄,她一屁股坐在地上,身上也开始哆嗦起来。
许久之后,苏良的老伴说,“你还救他不?他的光身子躺在这里快一个时辰了,水缸里的热水也都凉了。”苏良说,“我的手还没有好,我咋救他?我这会儿脑子里想的不是救他的事,我想的是,他要是死在我家里,我把他的尸首弄到哪里去?”
2
苏良托人往城里捎信,让瘸子程德彬到家里来一趟,说是有急事找他帮忙。苏良还特意嘱咐捎信的人告诉程德彬,要程德彬偷偷地回康庄镇,不要让外人知道,尤其不能让日本人知道。
康庄镇离城里并不远,只有六七里路。这天半下午的时候,程德彬一步一拐地走进了苏良的家门,站在了这个过去曾经是私塾的院子里。前几天下的一场大雪已经化了,路不好走,程德彬的靴子和棉裤的裤角上沾满了稀泥,他的脸和耳朵也冻得通红。
很久互不联系的程德彬和苏良两人,其实是结拜兄弟。苏良年长两个月,为兄,程德彬为弟。小的时候,两人一起读过私塾,玩得投机。程德彬17岁那年去了济南,在一家日本人开的丝绸店里当小工。不过四年之后,程德彬又回到了康庄镇。他是在回到康庄镇的第二年与苏良结拜的。
结为义兄弟之后,程德彬和苏良两人相约,开始做私塾先生。那时苏良家境稍好,盖了东厢房,在东厢房里招收学生,开私塾学堂;而程德彬家境差,开不起私塾,就到城里富贵人家的家塾里“坐馆”。这样一路做下来,两个人竟然一口气做了20多年的塾师。
日本人打过来那一年,程德彬因为会说日本话,被日军的一个小队长看上了,抓去做了翻译。做了日本人的翻译,程德彬的名声很不好,康庄镇的人都说程德彬为日本人做事,是个汉奸。程德彬的老婆孩子在康庄镇也不好混日子,镇子上没有人理他们,还经常有人往他们家的大门上抹屎。
做了日本人翻译的第二年,在万福河的河堤上,程德彬被游击队的人摁在一个土坑里,用白腊棍打断了一条腿。程德彬以为自己断了一条腿,走路不方便了,从此就可以摆脱日本人的纠缠。可是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程德彬在床上躺了四个月,刚刚能下床走路,又被驻扎在城里的另一个日军小队长看上了,再次把他抓去做了翻译。这个日军小队长还专门为程德彬配了一辆东京牌的洋车子,出门有洋车子代步,不必劳累腿脚。就是这样,程德彬给日本人当翻译,前前后后竟然过去了五六年。
程德彬给日本人当翻译这几年,断了与苏良的联系。苏良知道程德彬胆小,在日本人那边受气,在中国人这边也受气,这几年日子过得很不舒心。
这天下午,程德彬一瘸一拐地进了苏良的家门之后,停在院子里,看到苏良和他老伴站在堂屋门口迎他,轻声地叫了两声,“哥!嫂子!”苏良用眼神招呼程德彬进屋。堂屋当门放着一小堆烧材,烧材旁边放着两只麻扎。二人进得屋来,苏良让程德彬坐在麻扎上。苏良的老伴用洋火把烧材点燃了,让程德彬烤火暖暖身子。看着苏良的老伴弓着身子弄火,程德彬忽然用双手捂着脸说,“嫂子,好几年了,德彬都没来看看你,德彬不是人呢。”苏良的老伴说,“德彬,看看你说的这是啥话。”苏良也说,“啥也别说了,你哥我心里啥都明白,在日本人手底下熬日子,也难为你了。”看到程德彬靴子和棉裤裤角上的稀泥,苏良问,“六七里路走来的?咋没骑洋车子?”程德彬说,“我咋能骑那个东西回来?太扎眼了。”苏良叹了一口气。
苏良把一个冻僵的日本兵爬进东厢房以及他如何用一大缸热水救活这个日本兵的事,一五一十地讲给程德彬听。苏良讲到他把日本兵泡到大水缸里,那个日本兵很像一只穿着兜裆布的大蛤蟆。他把日本兵救活之后,还给他剃了胡子,剪了头发。这话听得程德彬直瞪眼。一会儿,程德彬脑门上的汗就下来了。程德彬两手捂着在二人中间燃烧着的火苗,眯起眼看着苏良说,“哥,你摊上事儿了,这个日本人八成是一个逃兵。”苏良说,“我咋知道呢,一开始我只知道他是一个乞丐,看到他裤裆里的兜裆布,才知道他是一个日本兵。”程德彬说,“哥,前些日子,他们的人正在追捕一个逃兵,八成就是他。你不该救下他,你救下他你就摊上事儿了。”苏良说,“要是我不救下他,他就会死在我家里,那我把他的尸首弄到哪里去呢?”苏良用一根柴棍拨了拨火堆,又说,“德彬,你懂日本话,今天我叫你来家里,一个呢,就是想让你问问那个日本兵,他黑夜里爬到我家东厢房里来到底是咋回事;二一个呢,我想和你商量商量,这事接下来该咋弄。”
程德彬跟着苏良来到东厢房。那个日本兵躺在稻草上,好像已经睡着了。稻草已经被整理过,整理成了地铺的样子。日本兵身上盖着两床被子,只把头露在外面。他的脸上和耳朵上,有几处涂着铜钱大小的暗红色的药膏。程德彬问苏良,“他脸上是怎么回事?”苏良说,“他的脸上、耳朵上和手上有很多冻疮,我给他用了一个偏方。是炒焦研成末的柿子皮,用香油调的。”
在地铺一边,放着一只夜壶,夜壶散发着一股臊味儿。程德彬抬起那条不好使的腿,一只脚轻轻踢了踢夜壶,问苏良,“他还不能动弹?”苏良说,“他的一条腿冻坏了,没有知觉,这几天一直用生姜擦他的腿。”程德彬说,“也就是说,他现在还是不能走路?”苏良点了点头。程德彬收了收他的瘸腿,很费力地坐在日本兵身边的稻草上,望着日本兵的脸,轻轻地叹了一口气。
他们说话间,那个日本兵醒过来。日本兵看到身边坐着一个陌生人,一下子从地铺上折起了身子。他的眼睛惊恐地看着程德彬,一只手在身边胡乱地抓了几下,似乎是想找到什么硬物自卫。苏良说,“你不要怕,他不害你。”日本兵眨了几下眼睛,好像听懂了苏良的话,安静下来。他还坐在地铺上正了正身子,低下下巴,嘟嚷了一句日本话。
苏良拨拉了一下程德彬的胳膊,问,“他说啥?”程德彬说,“他说初次见面,请多关照。”苏良说,“你问问他,他遇见啥事了,为啥半夜里爬进我家东厢房里?”
程德彬就用日本话问日本兵。但日本兵低着头,像做了错事的孩子一样不说话。程德彬又对着日本兵的脸说了几句日本话。日本兵低着头,说了一句“狗米那啥一”。程德彬再用日本话问日本兵,那日本兵还是说一句“狗米那啥一”。程德彬连着问了好几句,日本兵连着说了好几句“狗米那啥一”。
苏良忍不住了,也蹲下身子,问程德彬,“他为啥一直说‘狗米那啥一?啥意思?”程德彬说,“他说的是‘对不起。问他的话他不说,光说对不起。”这时日本兵眼睛望着苏良,正了正身子,低下下巴,嘟嚷了一句日本话。苏良问程德彬,“他又说啥?”程德彬说,“他说谢谢你,你是他的救命恩人,他一辈子都忘不了救命恩人。”苏良说,“他净说些没用的,你让他挑有用的说。”停了片刻,苏良又说,“他谢我我知道,他每天都给我磕头。”
程德彬对着日本兵说了两句日本话,接着又对苏良说,“哥,我告诉他,他的救命恩人要他说实话。”苏良就拿眼睛盯着日本兵。但日本兵却不敢与苏良对视,他低下头,只是偶尔瞄一眼苏良。
过了一袋烟工夫,那个日本兵开始说话了。他说的第一句话,就让程德彬瞪圆了眼睛,张大了嘴。然后程德彬又瞪着眼睛看苏良,“哥,你猜他是干啥的?他说,他在日本的时候是一个私塾先生,在自己家里开私塾学堂。”听了这话,苏良也瞪圆了眼睛,“他是私塾先生?日本兵里面也有私塾先生?”那个日本兵还在说着话。程德彬就对苏良翻译说,“哥,他说你也是教书先生,你是他的前辈。”苏良皱了皱眉头,说,“他咋知道我是个教书先生呢?他们这些日本鬼子来了之后,我都好几年没有教过书了。”程德彬说,“他说,他看到这个房子里码着一些书桌,知道这里曾经是私塾。他对这些书桌非常熟悉。”
程德彬说着话的时候,屋里的三个人都去看码在屋子一角的书桌。这间房子里的其它东西都放得零乱,只有码在一起的书桌很整齐;别的杂物上面都落满了灰尘,只有书桌干净油亮。日本兵看着那些书桌,目光贪婪,鼻翼翕动,似乎想要闻出书桌散发出来的木香。
这样看了一阵子,程德彬眼睛里也有了泪光,他突然用一只手去拍日本兵的脸,一边啪啪响地拍着,一边对日本兵说了一句话。日本兵的神情有些惊异,眯着眼睛看程德彬。程德彬换了一只手,拍日本兵另一边的脸,拍得啪啪响,他对日本兵又重复了刚才说的那句话。此后程德彬就停不下来了,他手上的力道也在加重,实际是在扇日本兵的耳光,噼里啪啦,声音脆响。程德彬的嘴里一直在重复着那句话,而那个日本兵呢,伸着脖子让程德彬扇他的耳光,两个人好像在玩一个游戏。
苏良扯了一下程德彬,问,“你在对他说啥?”程德彬停下了动作,但并没有回答苏良的话。苏良搬过程德彬的肩,望着他的脸又问,“你在说啥?”程德彬咽了一口唾沫,噎着说,“我告诉他,我也是一个私塾先生。”
三个人很长时间没有说话。
后来,日本兵开始用右手挠左半边脸,停一停又用左手挠右半边脸。日本兵的脸上有几个冻疮,那上面糊着苏良研磨成的柿子皮药膏,结果有一块药膏被日本兵抓掉下来。苏良眼疾手快,双手接住了从日本兵脸皮上掉下来的药膏,捧在手心里。苏良看了看,药膏已经结成块,成了暗红色的,像是一块栗子皮。他又看了看日本兵的脸,发现日本兵脸上的冻疮开始结痂了。苏良说,“他的冻疮快要好了。”
日本兵又说话了,程德彬翻译给苏良听。程德彬说,“他说他叫麻生温良,日本山梨县人。他除了教书以外,还懂得一些医术,算是个半拉子医生。”苏良插话说,“这是在说他,还是在说我?”程德彬说,“在说他自己,他是个教书匠,还是个半拉子医生。”程德彬望了望苏良的脸说,“哥,他和你很像,教书,还给人看病,名字里面也有一个‘良字。”
麻生说话慢悠悠的,有时候上一句话和下一句话停顿很长时间,一点也不连贯,他的大部分话好像都需要想一想才能说得出来。程德彬不得不撮着嘴等待,等麻生说出完整的话,再翻译给苏良听。
程德彬说,“他说他今年28岁,祖上三代都作塾师。他的父母早逝,他是在哥哥姐姐的抚养下长大的。今天春天,日本政府征兵,要求每家都出壮丁,有逃跑的人拉出去就被枪毙了。”程德彬话音未落,麻生把两只手举起来,做出端枪瞄准的姿势,嘴里“叭勾”一声脆响。他这一声响吓了苏良一哆嗦。
麻生自己也哆嗦了一下,好像有枪口正在瞄准他似的。随后,麻生的话变得小心翼翼。
程德彬继续翻译麻生的话,“他说,他的父母生了他和哥哥两个儿子,按照政府的规定,必须送一个儿子去参军。因为他的哥哥已经结婚生子,需要照顾家庭,所以他应召入伍,成了一名随军军医。”
程德彬说,“他们家的私塾学堂,就在自家院子里,也是一间东屋。他教的学生一共有12个。政府的人上门去抓壮丁那天,他正在教学生念书。那天他央求政府的人,能不能让他把课讲完,把学生安置好,再跟他们走。可是政府的人不同意,他们硬生生地把他押走了。现在,不知道他的学生们怎么样了。”
麻生说完这些,就不再说话了。苏良望了望程德彬,说,“你再问他。”程德彬说,“不用问了,他是日本军队的一个逃兵。”程德彬望了一眼麻生,把手掌横在脖子上做了一个杀戮的动作,又补了一句,“逃兵是要杀头的。”
程德彬低下头,搓了搓手,又和麻生说话。程德彬和麻生说上几句,接着就把这几句翻译给苏良听。程德彬说,“我问他,你哪来的中国人的衣服?他说,一开始的时候他穿着日军军装,他穿军装在中国人的人堆里太扎眼了,没有人给他饭吃,还有人打他。在好几个地方,有好多中国人都打过他。有一次,几个老年男人还把他的衣服扒光,把他摁到一堆蒺藜棵上,用蒺藜搓他,一边搓,一边大声地叫他,‘鬼子!鬼子!”
程德彬的一根指头点了点麻生,说,“他懂得‘鬼子的意思,知道是在叫他。”这时麻生用中国话连着喊了好几声,他说,“鬼子,鬼子,鬼子!”接着,他又用日本话叽哩咕噜地说起来。
程德彬说,“他说,他只好白天躲藏起来,躲在破庙里、猪圈里或者是柴禾垛里,到了夜里再赶路。但还是没有吃的,他穿着一身军装,没有人肯给他吃的。有一天,他饿昏在村头的柴禾垛里。一对老年夫妻把他从柴禾垛里拉出来,给了他吃的,还给了他一身衣服,他们说,穿上这身衣服,就会有人给他饭吃,也不会有人再打他了。”
程德彬刚刚停下来,苏良就说,“你再问他。”程德彬又用日本话问麻生,然后说,“我问他,你从哪里跑到这里来的?他说,他从一个叫天津塘沽的地方跑过来。他是步兵第10联队的。”程德彬和麻生又说了几句,然后对苏良说,“我问他,你为啥跑到山东来?他说,他从地图上看到山东半岛有一个尖尖儿,那个尖尖儿离日本很近,他想跑到那个尖尖儿那里,坐船回日本。”
程德彬说完这几句,叹了一口气。停了一会儿,程德彬扯了一下苏良的衣袖,向苏良使了一个眼色,示意苏良借一步说话。苏良跟着程德彬到了东厢房的门口,两个人背对着麻生。程德彬说话之前,身子晃了晃,似乎觉得他们二人这样避开一个日本人说中国话,没有多大必要。他们又同时回过头去看麻生,看到麻生眯着眼,撮着嘴,像等待宰杀的羔羊。
二人回转头,重新背对着麻生。程德彬说,“哥,你得让他走;要是让日本人知道了他在你这里,你就遭殃了。我也会遭殃。”苏良说,“我知道,让他走。”苏良又回头看了一眼麻生,说,“可是,他的一条腿废了,这几天他解大便都得我架着他去茅厕。”程德彬低头想了一会儿,说,“你给他一根拐棍,再给他一点盘缠,让他走,明天就走。”苏良说,“嗯,明天让他走。”程德彬回头看了一眼麻生,说,“这都啥时候了,你可不能心软啊。”苏良说,“嗯,不软。”
3
这天傍晚,有一个陌生人叩响了苏良家的大门。这是一个瘦瘦的年轻人,他压低声音问苏良,“你是苏先生吗?”苏良犹疑说,“苏良。”年轻人说,“你在城里的结拜兄弟捎来一句话。”年轻人这话让苏良心里惊了一下。自从程德彬当了日本人的翻译,康庄镇的人都说程德彬是汉奸,没有人愿意把自己的名字和程德彬的名字联系在一起。苏良不知道这个年轻人站在自己的家门口是不是祸端,但他还是小心翼翼地问了一句,“捎来啥话呢?”年轻人说,“今天夜里刮大风,小心东厢房屋顶。”
年轻人走后,苏良皱着眉头在院子里转了几个圈子,才推开了东厢房的门。麻生看到苏良进来,费力地在地铺上扭动身子,扭了一阵子,趴在了地铺上,接着就捣蒜似的给苏良磕头。麻生自从进了苏良的家门,磕头成了家常便饭,只要苏良走进东厢房,十有八九麻生就会在地铺上费力地扭动身子,扭一阵子趴在地铺上,然后给苏良磕头。有时候苏良的老伴过来送饭,麻生也会这样磕头。以往苏良看到麻生磕头,总会弯下腰,把双手摊开在膝盖前,那样子既像是阻止麻生磕头,又像是把麻生磕的头拾在怀里。但是这一次看到麻生磕头,苏良却无动于衷。苏良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往东厢房的门口走,到了门口,他又回过头来看着麻生,说,“磕啥头呢?不是磕头的时候了。”
来到院子里,苏良叫老伴从灶房里出来。苏良的老伴正在灶房里做晚饭。那时天已经擦黑了,苏良的老伴影影绰绰地从灶房里走出来。苏良沉着脸对老伴说,“不好了,今天夜里要刮大风。”苏良的老伴居然听懂了这句话,她说,“老头子,你别着急,天塌不下来,让他走还是让他留,你拿个主意。”苏良说,“他往哪里走啊,他的一条腿已经废掉了。”
苏良又皱着眉头在院子里转圈子,转到东厢房南山墙旁边的大水缸那儿,停下来。他踢了踢水缸,对老伴说,“老婆子,你过来帮忙。”
苏良老公母俩把水缸移开,打开了地窨子盖。然后苏良让老伴守住地窨子口,他自己去了东厢房。那时天已经黑了,苏良进了东厢房,先点了油灯,端着油灯照麻生的脸。他对麻生说,“你们的人要来抓你了,你先躲一躲。”他示意麻生从地铺上起来,又说,“我们没有人想弄死你,可是你们自己的人想弄死你,你去躲一躲,躲过去就好了,那里面比这里还要暖和。”
麻生似乎能够听懂苏良的话,他很配合地起了床,又给苏良磕了几个头。苏良把油灯放在地上,架着麻生往外走。麻生整个身体的重量都压在苏良身上,他的那条废掉的腿,像棍子一样在身后拖着。苏良小声报怨麻生说,“你看看你,你死沉死沉的,我这辈子也没有扛过你这么沉的东西。”麻生小声说,“狗米那啥一。”
苏良老公母俩把井绳拴在麻生腰上,两个人拽着绳子,往地窨子里放麻生。麻生似乎不太愿意到地窨子里去,还有半个身子露在外面的时候,他忽然叽哩咕噜地大声说话,两条胳膊撑住窨井口的边沿。苏良害怕麻生大声说话被别人听见,丢了井绳,蹲下身子去捂麻生的嘴。他又去摁麻生的头和肩膀,结果麻生就被他摁下去了。苏良的老伴没有拽住井绳,只听地窨子里扑通一声,绳子跟着麻生的身子一块下去了。苏良的老伴惊了一下,说,“他不会摔坏吧?”苏良说,“这个地窨子总共一人多深,下面都是塇土,没有大碍。”
一袋烟工夫,苏良用另外一根绳子吊了一个竹篮子,竹篮子里放着一个花卷、两个窝头、一碗面汤、一截胡萝卜腌制的咸菜,他蹲在地窨子口,压低声音“嗨嗨”地叫了两声,下面就有了动静。待地窨子里的麻生把竹篮子清空了,苏良把空篮子提上来。过了一会儿,苏良又到东厢房里找出夜壶,用破布包一下,放在篮子里,吊进地窨子。做完这些之后,苏良老公母俩重新用木盖把地窨子口盖上,又把大水缸压在木盖上面。
天黑透了,苏良老公母俩这才想起去吃晚饭。饭吃到一半,苏良忽然又想起了什么,他吩咐老伴再点一盏油灯,把东厢房地铺上的被褥收起来,还要把地铺复原成草堆。苏良自己则再次来到东厢房南山墙外,摸着黑蹲在地窨子口旁边,用手指寻找木盖上的一条缝隙。确信那条缝隙的确存在,苏良又抠了抠缝隙两边的朽木,似乎想让那条缝隙变得更宽一些。然后,苏良把窨井口周围的潮土用手抹一抹,尽量不让人看出来水缸和木盖有刚刚被人动过的痕迹。
这天夜里苏良老公母俩一夜没有睡觉,他们只是和衣躺在床上,在黑暗中睁着眼睛看屋顶,支着耳朵听外面的动静。但是那一夜外面只有风声和一两声狗叫,日本人并没有来。
天蒙蒙亮的时候,苏良家的大门突然被踢得咚咚响。苏良从床上折起身子,拉开堂屋门,就看见日本人已经踹开大门进来了。先进来四个日本兵,他们在东厢房门口站下一个,灶房门口站下一个,堂屋门口一边一个站下两个。随后进来的是一个日本军官,军官后面跟着一瘸一拐的程德彬。程德彬一看见苏良,就低下了头,显得很害怕,他甚至往日本军官的身后躲了半步。这时苏良的老伴也从堂屋出来了,站在苏良的身后。
日本军官向几个日本兵使了一个眼色,站在堂屋门口、东厢房门口和灶房门口的日本兵分别进了屋子。一阵叮当乱响之后,几个日本兵陆续从屋子里跑出来,向日本军官摇着头。日本军官走近苏良,盯着苏良的脸,吼了一句话。程德彬缩在军官身后,向苏良翻译。这次程德彬没有叫苏良“哥”,也没有别的称呼,而是直接问,“你把他藏在哪里了?”苏良看了一眼身边的老伴,说,“这话我听不懂,我家里只有两口人,都在这里了。”
程德彬把苏良的话翻译给日本军官听的时候,脸上就开始冒汗,同时,他还朝着东厢房南山墙那儿瞄了一眼。苏良知道程德彬是在瞄那口大水缸。程德彬对苏良的家太熟悉了,前几年乡下亲戚在苏良家院子里挖地窨子那天,程德彬就在苏良家里喝酒。现在麻生的去处,瞒不过程德彬。但同时苏良也知道,程德彬不会把麻生的去处说出来的。
苏良害怕日本军官从程德彬的眼神中看出端倪,自己脑门上的汗也下来了。他这么一慌乱,不知不觉的也朝着东厢房南山墙那儿的大水缸瞄了一眼。只那么一瞬间,苏良赶紧把目光收了回来。这之后,苏良就感觉日本军官的眼神像火一样烤着他的脸,烤得他的脸皮肤发紧,热辣辣地疼。
然后,日本军官冷冷地笑了两声,向站在堂屋门口的两个日本兵叽咕了两句话。那两个日本兵朝大水缸走过去,日本军官也朝大水缸走过去。程德彬脸色腊黄,望着苏良,两条腿哆嗦得像是打摆子。苏良目光发直,脸也僵住了。
两个日本兵搬开了大水缸,又掀开了地窨子的木盖。此后,苏良和程德彬都把目光躲开了。苏良转过脸,面对着堂屋门,一只手扶着门框,弓着身子,低着头。苏良的老伴揪着苏良的衣角,也不敢往地窨子那边看。程德彬两腿哆嗦得不行,只好蹲下来,抱着头,望着自己的脚尖。
过了一阵子,日本军官喊程德彬和苏良过去,两个人才慢慢往东厢房南山墙那里走。他们看见麻生已经被两个日本兵从地窨子里弄出来了。麻生躺在地上,腰里还拴着井绳,敞着怀,胸脯上有很多抓痕,渗出的血已经凝固在皮肤上。他的脸有些肿胀,嘴唇和手指都是青紫色的。苏良蹲下身子,摸了一下麻生的脸。苏良的手指抖得厉害,他摸麻生的脸时像是在弹琵琶。但尽管这样,苏良还是发现麻生的身体已经凉透了。
日本军官抓住苏良的衣领子,把他提了起来,对着他的脸冷冷地笑了两声,然后说了一句话。说完这句话,日本军官松开了苏良,让程德彬把他的话翻译给苏良听。程德彬嘴唇哆嗦了几下,对苏良说,“你的好心没有得到好结果,你把他闷死在里面了。”
4
那几天又下了一场雪。化雪的时候,天气清冷。很快到了这一年的腊八节。
自从家里出了麻生的事以后,苏良一直提心吊胆地过日子。日本人没有和苏良过不去,这反而让苏良更加忧虑。苏良知道日本人歪心眼儿很多,也许他们是故意这样吊着他,让他食不知味,夜不能寐。苏良想,等过完了年,要是日本人仍然不找他麻烦的话,麻生的事才能算过去了。
腊八这天中午,有人叩响了苏良家的大门。来人还是上次捎话“今天夜里刮大风”的那个瘦瘦的年轻人,这次他递给苏良一个布袋子,说,“苏先生,这是你在城里的结拜兄弟捎来的。”苏良接过布袋子掂了掂,没有猜出是什么东西,就问,“有没有捎话来呢?”年轻人想了想,说,“没有。他只说这东西吃了好消化。”
年轻人离开后,苏良在院子里就迫不及待地打开了布袋子,却见是几个苹果。苏良忍不住又看了一眼布袋子里的苹果,笑了笑说,“好消化,确实好消化。”看见老伴眯着眼站在堂屋门口,苏良把布袋子朝老伴举了举,说,“老婆子,德彬从城里捎来几个苹果,你猜是啥意思?”苏良的老伴说,“我哪里猜得出呢。”苏良凑近老伴,低声说,“德彬是在报平安呢,平安无事。”
但腊八这天夜里,还是有事。晚饭的时候,苏良老公母俩一人喝了一碗中午剩下的腊八粥,饭后苏良还特意吃了一个苹果,早早地就睡下了。到了半夜子时,苏良又突然醒来。苏良觉得他是被一种声音吵醒的,是扑腾扑腾的闷响声,像是有人在隔壁挖墙。苏良怕是有贼,摸黑起了床,裹着大衣,在院子里转了一圈,却也没有发现异常。他又开了大门,来到院子外面,到堂屋的后山墙和东厢房的后山墙也看了看,仍然没有发现异常,这才惴惴不安地重新躺回了被窝里。
半个时辰之后,那个扑腾扑腾的闷声又响起来,这一次好像还伴随着低沉的、呜拉呜拉的抽咽声。苏良在床上折起身子,侧耳细听,渐渐地听辨出声音来自于东厢房的南山墙那里。苏良一下子明白了,是有人在地窨子里折腾,弄出的这声音。这么一想,苏良浑身的汗毛奓起来,他赶紧把老伴叫醒,让她也听听那个声音。可是苏良老公母俩再去听那个声音的时候,那个声音却消失了,外面连风声也没有。过了一阵子,苏良的老伴说,“赶明儿把乡下的亲戚叫来,把地窨子填平了吧。”
第二天中午,苏良开始发烧,浑身害冷。苏良的老伴到灶房里为苏良熬了两碗姜汤红糖水,喝下去好了一些,可是到了晚上,苏良又烧起来。苏良的老伴往苏良身上盖了三床被子,苏良还是喊冷。苏良的老伴把书桌上的一块墨磐石也拿了来,压在苏良的枕头下面辟邪,又到灶房里为苏良熬姜汤红糖水。
不知道苏良是在做梦,还是发烧把他烧糊涂了,感觉里东厢房的课桌被重新摆放开来,十几个学生都回来了。苏良站在一旁清点人数,回来的学生一共是12个,他们端端地坐着,准备上课。在讲台上教书的先生却是麻生。麻生一手拿着书本,一手拿着教鞭,样子很像苏良自己。
两个日本便衣就是在这个时候闯进苏良家的。他们从外面别开了大门,径直走进堂屋,把苏良从被窝里揪了出来。等到苏良的老伴觉察到动静,从灶房里跑回堂屋,苏良已经穿好了衣服。两个日本便衣在旁边不停地说着“哈牙哭、哈牙哭”,其中的一个日本便衣还往苏良脸上扇了一巴掌。苏良的老伴张着嘴,呆呆地站在一旁。两个日本便衣用绳子捆了苏良的双手,又往他的嘴里塞了一块破布,押着苏良走了出去。
苏良本来就害冷,被外面的冷风一吹,浑身直打哆嗦。两个日本便衣在苏良的身后,一会儿你推一把,一会儿他推一把,推得苏良踉踉跄跄。这样离开镇子,走了大约三四里路,来到了万福河的河堤上。
河堤上站着另外几个穿军装的日本人,其中的一个日本人手里拿着手电筒。苏良走近了,手电筒的光直接打在他脸上,让他睁不开眼睛。手电筒又往地上照了一下,苏良发现地上有一个刚刚挖好的土坑,他正站在这个土坑的边沿。一个日本人往苏良的腰上踹了一脚,苏良一头栽了进去。
苏良窝在土坑里,脖子有点疼,但他感觉土坑里的温度比外面要高一些,身上暖和了很多,鼻孔里吸进了冬天里难得一闻的新鲜的泥土气息。这个时候,又有一个男人被推下了土坑,栽进苏良的怀里。这个人也被捆着双手,嘴里塞着破布,浑身哆嗦着,嘴里发出浑浊不清的呜拉呜拉的声音。过了一会儿,手电筒的光又打过来了,苏良看清躺在他怀里的人是程德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