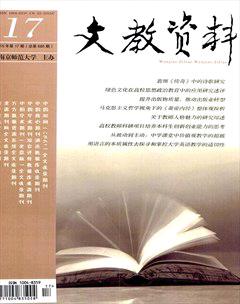“十七年”和“文革”传统诗歌“死亡”解读
李家富 陈俐
摘 要: 受时代大语境“革命化”、“英雄化”的渗透及影响,“讲故事”、“塑造典型”成了“十七年”和“文革”时期传统诗阵营中“诗歌戏剧化”最集中的价值体现。但事实上,当代传统诗歌在如何诗化现实生活的问题上,走进了极“左”文艺路线的死胡同,最终把诗的文体模糊了,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诗歌戏剧化。由于当代传统诗歌创作的历史性走偏,中国当代诗歌体验了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死亡。
关键词: 传统诗潮 叙述化 意识形态 诗歌死亡
中国当代诗歌一般以1976年“天安门诗歌运动”为界,分为传统诗潮与新诗潮两大阵营。传统诗主要包括“十七年”和“文革”两个时期的诗歌创作,新诗主要包括朦胧诗的“过渡时期”、“朦胧诗潮”和后“朦胧诗潮”三个时期的诗歌创作。以李季、闻捷为代表的“生活抒情诗”是传统诗阵营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他们的诗歌创作明显地受到了“十七年”和“文革”大语境“革命化”、“英雄化”思想的渗透与影响,“讲故事”、“塑造典型人物形象”成了他们诗歌“戏剧化”最集中的价值体现。但事实上,当代传统诗歌在如何诗化现实生活的问题上,走进了极“左”文艺路线的死胡同,最终只是把诗的文体模糊了,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诗歌戏剧化。
当然,要客观地弄清楚这股传统诗潮在当代文学发展史中的价值和意义,我们还要追根溯源,了解20世纪40年代解放区诗歌创作的历史背景。1942年毛泽东的“讲话”将左联的文艺方针变成了“金科玉律”。1944年周扬进一步阐释、明确了“讲话”的“大众化”文艺创作思想,并指出要实现“大众化”的目标,文学艺术的创作必须采用写实的手法。这样,诗歌的叙述倾向就变得十分明显,以致20世纪40年代叙事成了一种新时尚,叙事诗也变成了一种被时代所追捧的文体。李季、闻捷等在20世纪50年代立足于诗坛的诗人,基本上都是经过了抗日战争或解放战争的洗礼,在20世纪40年代便开始创作“写实”的叙事诗。新中国成立后,他们基本上还是继承了20世纪40年代的创作诗风,即突出诗歌创作的戏剧化。关于诗歌戏剧化的理论探讨,一直是当代学界最具争议性的一个文体问题。其实,立足于当下,要很好地解构传统诗潮中的“戏剧化”,我们认为还是要回到“历史”中去,回到闻一多、袁可嘉的理论阐释中。闻一多从人类文化学的向度提出了诗歌应该“不像诗而像小说戏剧”的观点后,质疑之声就此起彼伏。其实,只要我们把其观点置于时代语境中就会清楚地看到,诗歌应该“不像诗而像小说戏剧”就是要让诗歌“背叛自我”,偏离诗歌的艺术规律和技巧,让“讲故事”的诗歌达到大众化的戏剧效果,服务于更广泛的民众。闻一多的本意更多强调的是诗人要成为“时代的鼓手”,诗歌必须是战斗性的、鼓动性和宣传性的,而就当时的“抗日民主运动”来讲,闻一多的“诗歌”转向是可以理解的。在闻一多之后,袁可嘉针对当时诗歌走上直接发泄感情和一味说教的道路提出了“新诗戏剧化”和“戏剧主义”的概念。在袁可嘉看来,“人生经验的本身是戏剧的,诗动力的想象也有综合矛盾因素的能力,而诗的语言又有象征性、行动性,那么所谓诗岂不是彻头彻尾的戏剧行为吗?”[1]P34简言之,袁可嘉对于诗歌的观点是诗所用的材料、诗的动力及诗的媒介都是戏剧的,当然,诗歌建构的模式自然也是戏剧的模式。
“诗歌戏剧化”理论观照中的当代传统诗歌创作,就其内容来看,数量最多,影响最大的当数“生活抒情诗”。就生活抒情诗的代表诗人李季和闻捷相比,同样的题材,李季更倾向于叙述故事,他的叙事欲望比抒情欲望更强烈。在具体的诗歌创作过程中,有时为了突出叙事性,他无论是采用人物塑造方式(如《厂长》、《社会主义老头》),还是对话方式(如《客店答问》、《师徒夜话》),都会用直接的甚至是原生形态的生活言语再现细节;有时为了达到叙事的目的,他甚至直接采用戏剧、小说的创作技巧,哪怕是一些抒情性较强烈的诗歌,比如《至北京》,他也会想方设法地插入一些叙述语言,或一个个场景,打断诗歌的感情脉络。显然,这种诗歌创作的“戏剧化”,使得诗人要表达的感情就只能是讲出来的,而不是从诗歌形象的建构过程中自然流露出来的。当然,这种讲出来的情感就不可能达到艺术表层的戏剧效果,更不会达到袁可嘉所谓深层的喜剧效果;相比较而言,同样的题材,闻捷则能在以叙述为主导的诗歌创作过程中,较融情于景,多少还保留了一点诗的“味道”,让读者在诗歌消费的过程中能够“见仁见智”,满足不同的审美诉求。比如,他的诗歌《天山牧歌》,由于新疆独特的文化语境已经在诗人的情感世界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因此在创作过程中,感情的表达相对自然、朴素一些,诗歌的叙述在故事中不同程度地蕴蓄诗人一定的情感体验。
“十七年”的诗歌,诗人除了用叙述表达生活与情感之间的矛盾关系外,也常常通过构建生活中的人物形象寄托理想化的人生情怀。袁水拍的“《诗选》序言”在当时是被奉为抒情诗歌建构立场的“正统”。“序言”认为:“在诗歌领域中不重视典型形象的创造问题,可能是由于对抒情诗的不正确理解,以为‘抒情就是抒情,这和人物形象不相干。这是一种误会。”[2]P98为了进一步阐明自己的理论主张,袁水拍在“序言”中还进一步明确指出,抒情的主人公就是诗人自己。在诗歌建构中,诗人必须通体透亮、大红大紫地成为诗歌中的正面人物,用形象说话,即用诗人整个意识形态的正能量吸引读者、感染读者、震撼读者,让诗人与读者在诗歌文本中产生最直接的思想交流与情感共鸣。由于袁水拍强调诗人的直接文本介入性,因此,在诗歌创作中,“诗人只能是一个革命者,一个共产主义的战士……一个崇高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低级气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3]192。然而袁水拍的这种理想化的“完美”诗人,在现实生活中实属凤毛麟角。假如所有诗人都能具有如此道德品格,并要求他们把现实生活中极富生命个性的人都建构成为一种“高大全”的正面形象的话,“假大空”没有文学性的文学形象自然就产生了。
李季和闻捷等生活抒情诗人的诗歌创作,客观上出现了人物形象“工厂化”的问题。本来生活在现实世界之中的人物,其性格可谓是多元化的,其审美体验、审美认知的表达方式也是不同的。但是,在时代“大一统”大语境诗歌理念的渗透影响之下,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与感情世界在诗歌建构过程中就变得越来越扁平,越来越没有生气,可谓“纸人一个”。闻捷的作品,《哈萨克牧人夜送“千里驹”》、《种瓜姑娘》等;李季的作品,《社会主义老头》、《红头巾》等。这些作品中的人物形象,都被贴上了时代的标签,成了“工厂化”的产品,而这些“工厂化”的形象产品,因其“自我”的完全缺失,最终让诗歌由“戏剧化”行为变成了一种颂歌行为。
受“十七年”诗歌的影响,“文革”时期的诗歌创作依旧延续了“戏剧化”的诗歌创作理念。但“文革”时期诗歌的戏剧化是与当时整个文学样板化交融。样板化的诗歌创作简单地说就是以矛盾的冲突带动情节的发展,故事情节更突出矛盾的对立面,典型人物形象的塑造更加革命化、英雄化。在具体的诗歌创作实践中,吴欢章主张:“风雷激荡的革命时代,要求在诗歌中得到强而有力的回响。革命诗歌要充分地发挥时代号角的作用,必须向无产阶级革命文艺的光辉典范——革命样板戏学习。”[3]P194这在“文革”时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以致“文革”时期公开发表的诗歌和公开出版的诗集,都没有改变诗歌通过建构工农兵英雄形象抒发一种大众化、公式化的最美的无产阶级的革命情感。例如北京大学工农兵学员集体创作的《理想之歌》、王主玉创作的《雁回岭》等作品都是通过直接的无产阶级英雄人物形象的塑造达到表现和讴歌时代英雄人物的目的。
当然,“文革”诗歌戏剧化的另外一种表现方式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即在诗歌的抒情功能上通过舞台功能突出正面核心人物在集体中的感染力与号召力。袁可嘉曾经在《新诗戏剧化》中一再强调,诗朗诵和秧歌舞是很好的诗歌戏剧化的开始,因为二者都很接近戏剧和舞蹈,并且都突出强调动态的戏剧效果。“文革”诗歌不但缺乏动态性,而且存在感情放滥的问题,《手握钢钎叙深情》就是最有代表性的文本。除此之外,有诗歌的押韵特色的民间曲艺形式,例如京韵大鼓、快板书、北京琴书、山东快书……是接近民歌体的艺术形式,而这些艺术样式更需要舞台和演员精湛的表演才能达到更好的艺术效果。这些艺术样式在“文革”时期大部分都是被用来为塑造英雄形象服务的。生动的艺术样式却在极“左”的文艺路线的指导下偏离了艺术的轨道,成了政治的工具。结果,抹杀真情实感成了“文革”诗歌最突出的特征。
总的来说,诗歌戏剧化就其本质来讲是一个诗歌如何观照生活,达到戏剧效果的问题。不过,诗歌要实现真正的戏剧化,我们认为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内容形式化,形式内容化”的问题。文学实践的历史经验已证明,诗歌的戏剧化,诗歌的观念问题是最重要的。中国“十七年”和“文革”时期的生活抒情诗歌的创作,之所以没有产生如同艾略特所谓源于生命本能的审美快感,问题就出在极“左”意识形态的渗透与影响上。处于政治热情极度亢奋的李季、闻捷等生活诗人,以乐观的情调书写生活,这无可厚非,但令人遗憾的是他们并没有对这些生活素材进行独有的审美体验与审美认知,也没有发挥应有的意象、意境的建构能力。在受制于叙述和塑造“英雄”人物的潮流驱动下,他们的诗歌大多缺乏真情实感,以致在诗歌建构中往往失去了自我;再者,“十七年”和“文革”时期的诗歌过于直露而缺乏不确定性的“召唤结构”,以致读者与诗人因缺乏“对话”的空间而让诗歌变得淡乎寡味,其结果是诗人与读者双方都没有获得艾略特所谓的精神快感。虽然说,新中国成立以后的诗歌创作在形式上靠近戏剧,但事实上,“十七年”的生活抒情诗在戏剧化的道路上因过多的叙述语言、细节的刻画等使诗歌迷失了方向;而“文革”的生活抒情诗则是在革命浪漫激情极度膨胀的狂热政治语境中失去了自我。借用艾略特的观点,“对诗的感觉以及作为诗的材料的感情从各处消失的话,就是诗的死亡,也是人类的死亡”,[3]P199“十七年”和“文革”时期的诗歌创作无疑是体验了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死亡。
参考文献:
[1]袁可嘉.论新诗现代化[M].北京:三联书店,1988.
[2]袁可嘉.诗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
[3]陈顺馨.中国当代文学的叙事与性别[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