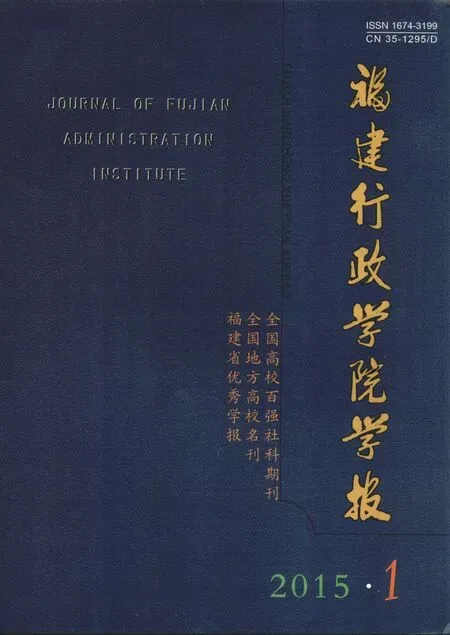论刑法的反向歧视
马荣春,谷 超
(扬州大学 法学院,江苏 扬州225000)
一、刑法反向歧视问题的提出
所谓反向歧视,是指形式上表现为对特定群体给予特别保护或照顾,但实际上却构成了对该特定群体的歧视。反向歧视在我国的刑法里并未明目张胆地表露,而是被深藏在法条背后。我国刑法第236条第1款规定:“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强奸妇女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刑法第237条第1款规定:“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强制猥亵妇女或者侮辱妇女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前述规定似乎蕴含着一种深意:女性的性权利容易被侵犯,故将女性的性权利列为刑法特殊保护的对象。
在现阶段国人的道德观念中,女性在一定程度上仍是男性的附属品,且需承担更多的性义务。可以认为,男权文化仍是中国社会发展方向的主导文化,而女性则被视为男权文化的附庸。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在性义务上,女性便承担更多。那么,一旦某个女性遭到性侵犯,该女性在男权文化中便不再属于“贞洁烈女”而属于“不干净的异类”。于是,道德观念之中的歧视便被隐藏到“保护弱者”的外衣之下而形成反向歧视。这便造成了名义上被给予特殊保护的群体即女性群体在面对占领了“男性文化制高点”的道德体系时,却事实地在性侵个案中成为公众所嫌弃的对象,而这里的公众包括被嫌弃的对象所对应的那个群体即女性群体的其他成员。那么,我们能够进一步看到的问题是,在畸形的道德体系中,刑法的反向歧视产生了对名为被特殊保护而实为被反向歧视的群体的“二次伤害”。于是,刑法变成了“恶法”。可见,刑法的反向歧视问题足够严重。
二、刑法反向歧视的成因
由前文论述已经可见,刑法的反向歧视牵扯着道德论。而道德论的立法理念是由道德观衍变出的立法理念,也即将道德观融入到法律规定之中的立法理念。在道德论的立法理念之下,只要是不符合道德观的行为,就应该被法律禁止;而符合道德观念的行为(如女性的坚守贞操的行为),就应该得到法律的褒扬和赞赏。于是,坚守贞操便在符合社会道德观念之中被纳入刑法的规制范围。当社会道德对女性提出了坚守贞操的特别义务要求,则迎合这一社会道德特别要求的刑法立法便在强奸罪和强制猥亵妇女罪问题上借保护之名而行性义务之苛求之实。那么,我们能够进一步看到的问题是:在道德论的立法理念之下,女性与男性的性义务是不对称的,进而性权利也是不对称的。而在这种不对称之中,遭到性侵的女性容易在道德观念与道德舆论中仍然扮演着“被强奸者”或“被强制猥亵者”的不干净的悲哀角色,而这一角色甚至影响其终身的社会交往乃至择偶等生活内容。于是,男性与女性在性权利的享有和性义务的承担上的对等性,被名为特殊保护的刑法规定予以撕裂了。
有学者指出:“任何法的适用,或执法、司法上的平等,都必须是以一定立法上的平等规定作为依据的”,而“只有法的适用,或者执法、司法上的平等,而无立法上的平等,也是不完整的法的平等。”[1]可是,当深究强奸罪和强制猥亵妇女罪立法背后的问题,我们可发现:尽管这两罪的立法出于特殊保护,却反映出立法者对于女性的贞操义务投入了更多的关注。而这背后是“性道德论”在作祟。当通过道德论额外强加的性义务没有被担当或有瑕疵时,反向歧视便在类似于“恨铁不成钢”的道德心理中得以形成。
刑法的反向歧视意味着刑法过多地重视道德乃至于形成一种“偏爱”。在刑法的反向歧视中,女性的性义务首先是道德领域的内容,即对女性性义务的评价首先属于道德评价。可是,“当某一群体统治另一群体时,两者之间的关系就是一种政治关系。如果这种政治关系长久地存在着,它就会变成某种意识形态。所有人类文明都处于父权制之下,这些文明的意识形态即大男子主义。”[2]显然,在这种统治关系下,男性主导之社会道德对于作为附属物的女性的性义务必然会提出较多的要求,但这较多的要求本该仅存于道德体系之内,即其本属于道德调整的领域。但是,刑法的反向歧视则在“响应”社会道德之中背离了刑法对人特别是女性的平等关怀。由此,刑法的反向歧视的片面性及其局限性显而易见。同时,由于刑法对道德观念的过分肯定,女性的性义务则由原来道德层面的“模糊义务”和“软义务”演变成法律层面的“明确义务”和“硬义务”。
女性作为社会的组成部分,其在社会中的价值定位特别是在道德中的价值定位,是基于女性自身的价值。但是,刑法的反向歧视是将女性在社会道德中的价值纳入到刑法体系之中,这种异化的体系是刑法对女性私人领域的过度干预,也是对女性人格价值的否定。刑法的反向歧视,是将女性的性义务对立于男性的性义务,是将女性的价值归于男性主导的麾下,是刑法对自身价值体系和评判体系的偏离。刑法的反向歧视意味着刑法对于女性私人领域与个人价值的过度侵犯,也意味着“导致发生在传统意义上的私人领域中的‘公事’不能获得法律的保护,也可能使得传统意义上的公共领域中的‘私事’反而受制于国家权力。”[3]46刑法的反向歧视意味着女性在刑法中永远都附属于男性及男性主导的社会道德而存在,而社会道德也会因为刑法对之“偏爱”而成为有“无声强制力”的评判标准。于是,实现刑法的平等原则特别是性别平等,只能是美好的憧憬;而实现刑法对女性权益有力保护的目标,只会是美好的期待。简而言之,在刑法的反向歧视中,女性的自身价值难以得到真正或彻底的实现。
三、刑法反向歧视的掩盖
德国法理学家伯恩·魏德士将歧视分为“原本的歧视”与“派生的歧视”。那么,性别歧视是基于两性价值分工而形成的原本歧视。基于性别原本歧视的道德观将男权主义渗透到社会的各个方面,其中包括刑事领域的刑法立法。而当刑法立法将性别歧视披上了刑法基本原则的外衣,性别歧视便越发地隐蔽,以致于难以被发现和批评。而这里所说的刑法基本原则包括罪刑法定原则、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和适用刑法人人平等原则,特别是适用刑法人人平等原则。
学者指出:“平等是指任何人依法享有的相同权利都应该受到同样的保护,任何人违反自己所承担的法律义务都应该受到制裁。”[4]由此可见,刑法中的平等原则即适用刑法人人平等原则不仅仅是形式上的平等,更应该是实质上的平等。但是,隐藏在刑法中的反向歧视有悖于平等原则,而这可以视为在男权文化中性别歧视的制度化和现实化。刑法的反向歧视与法学理论不无关联,甚至法学理论构成了“帮凶”,即如学者指出:“男性统治的法律理论也不断地极尽其‘科学’想象之能事,掩盖社会性别,为法律披上了性别公正与性别中立的外衣,从而使性别歧视的社会性别模式不断得以强化。”[3]21可见,在男性主导的法律文化中,性别歧视的掩盖是法学理论是有所假借的,而这其中包括平等原则理论。
平等原则的理论渊源是社会契约,而社会契约“通过把我们的社会说成是起源于契约,国家和公民法的权威以及现代公民政府的合法性就找到了一种解释。”[5]于是,平等原则逐步成了法律的应有之义。在平等原则演化的过程中,我们忽视了一个重要的前提:这些理论建立在男权社会的文化上,而男权文化中的平等只限于摒除女性的男性的平等。在这样的前提下,平等原则暗含并且强化了性别歧视,或曰这些理论使得性别歧视披上了看似平等的外衣。正如女权主义的学者所批判:“传统契约理论家们是如何起步于以下前提——使任何诉诸自然的政治权利的主张变为非法,进而将男女之间的差异构筑为天赋自由与天赋屈从之间的差异。”[6]这种前提有缺陷的平等原则,在法律被制定之时就被明确地规定了。
对于这种有缺陷的平等原则,我国法律有详细的体现。我国宪法第三十三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这意味着任何人不论性别在法律面前是平等的。我国刑法第4条规定:“对任何人犯罪,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有超越法律的特权。”该条确立了刑法的平等原则即适用刑法人人平等原则。对于刑法的平等原则,有学者指出:“刑法上的平等,理应包括定罪、量刑以及行刑等方面的平等。”[7]因此,“刑法平等仅仅而且只能是司法平等。”[8]正如学者在论述刑法平等原则时指出:“平等是指人们相互间权利获得与义务履行的相同性,它应是一种相对平等、地位平等。”[9]由于在法律面前平等和适用法律平等意味着司法平等,故法律平等原则遮盖了一个问题,即立法包括刑法立法中是否应先予实现平等。而当此问题涉及性别时,便牵扯出立法包括刑法立法中的类别平等问题。然而,实现在立法包括刑法立法中的平等正是司法平等的前提。学者们对于法律以及刑法中平等原则的理解仅局限于司法层面的个体间的平等,而未关注立法层面的类别间的平等。任何时代的刑法都是本时代的社会道德影响下的产物。刑法以社会生活为基础,故社会生活中的评判标准包括道德标准会影响刑法的价值取向。那么,当刑法的制定脱离了本时代的社会道德,则其会显得与时代格格不入。于是,为了契合道德的要求,刑法会吸纳道德观念中的相关内容。可是,当道德观念无法契合刑法明文宣示的原则时,则其便被隐藏在刑法条文背后,即被掩饰起来。我国刑法的反向歧视大致就是这样形成的。
我国刑法的反向歧视的掩盖,尚须联系女性的性义务予以揭示。在男性占据着社会主导地位的前提下,立法者便将本社会的反映男性主导的道德标准融入法律包括刑法之中。于是,性义务的额外强加便被带到刑法中并被掩饰起来,而掩饰的手段便是刑法的基本原则。在强奸罪和强制猥亵妇女罪中,之所以没有将男性纳入被害者的范围,从表面上,似乎是因为男性不可能被强奸,也极少有可能被强制猥亵,或曰即使男性被强奸或被强制猥亵,其所受害也小得无需刑法规制,但在实质上,却是因为在社会道德观中,男性所需承担的性义务比女性少。而在性义务承担的过程中,女性只是一个被安排者,其一直处于“安静地”接受的状态,即对于道德观念中女性承担的性义务,她们没有权利进行全面地甄别,因为她们虽然是社会的组成部分,但其道德观念必须和男性主导的道德观保持一致。那么,当性义务被女性“安静地”接受和承担并经刑法条文掩饰起来,性别歧视便在静止的状态下被刑法的条文掩盖了。而此掩盖似乎收到了“此时无声胜有声”的效果。
对于我国刑法的反向歧视的掩盖,我们尚可作出这样的领会,即男权主义主导的社会文化中,女性处于从属地位,而在这种从属性的状态之下,女性对于被道德观念额外强加性义务这一既定事实只能被动地接受,从而为法律即刑法的反向歧视埋下“祸根”。那么,在性别歧视被立法者接受之后,立法者会将其隐入法律规定,从而将本应由道德评价的内容纳入法律评价的体系之中。于是,性别歧视被确定为法律规制的内容,从而以法律规定维护道德性别歧视,从而强化道德目标。
四、刑法反向歧视的克除
刑法的反向歧视是将女性在道德中的性义务通过法条加以规制并予以掩盖,这使得女性的自身价值遭到否定。那么,如何克制乃至消除刑法的反向歧视呢?
这里涉及刑法立法对女性价值的社会评价归位问题。所谓刑法立法实现对女性价值的社会评价归位,意味着刑法在性的问题上要归位女性的性义务的社会评价,其目的在于避免刑法的功能在社会的各个方面被滥用,从而避免刑法的功能泛化。如果刑法的功能泛化,那么本该由道德评价的内容及本该在社会生活中实现的评价目标,都将交由刑法来完成,其结果是很可怕的。于是,当性义务被纳入到刑法规制范围,则社会道德便利用刑法来进行对女性的“二次伤害”。如何理解这里的“二次伤害”呢?在道德观念中,“强奸文化的信徒视女性性征为一种财产,只有男人才能真正有用,妇女常常是存储者,因此,男人理所当然地从我们身上夺去,而女人只能把自身托付给一个合法的主人。所以强奸变成了一个男人对另一个男人财产权的偷窃和侵犯。”[10]于是,刑法的反向歧视就变成了对女性没有“托付”好对男性的“性保洁”的一种谴责。这里所说的谴责是一次伤害,而社会道德的负面评价则是另一次伤害。“二次伤害”的结果在和道德评价的伤害叠加之后,形成对女性更加不利的局面。因此,刑法退出道德领域是对女性实现保护的需要,同时也是立法者对自身立法思维的一次净化和升华。如前所述,受社会道德的影响,刑法的反向歧视可谓事出有因。因此,去除性道德的影响和“牌坊文化”进行立法活动,实现平等地看待性别的差异,是刑法立法的重要目标。出于保护女性这一“社会弱势群体”的目的进行刑法立法,需要立法者能够坚守属于刑法的“领地”,需要立法者基于刑法对女性保护的本意,避免将社会评价纳入刑法立法之中。在立法过程中做到对女性价值的社会评价的归位,是坚持刑法的独立性的体现。唯有如此,才能实现性别的实质平等。
在立法过程中将道德评价剥离出刑法体系,还原道德评价本有的社会地位,是刑法立法需要实现的重要目标。在刑法立法过程中,需要将性问题所对应的道德评价放置在合适的位置,以处理好刑法与道德对待性的观念之间的关系。只有将道德中的性观念还原到本来的地位,即将性的道德评价功能归位,才能实现刑法在立法的过程中的自我规制。在刑法立法过程中,我们需要将道德中含有反向歧视的内容从刑法的规定中予以剥离,还原道德评价的本来面目和本来地位,这样才能避免刑法对道德评价的过度“揽事”,同时使得女性能够自由呼吸法律的空气,以助益女性价值在法律空间中的实现。但是,刑法的性反向歧视意味着刑法和道德的关系没有理清,导致刑法和道德交融,这便让道德逐步侵蚀了刑法的基本理念。而当社会道德对刑法立法作出了性观念传递,则刑法立法对社会道德必然有所继受或确认。于是,刑法立法很容易发生价值偏离,即由保护性权利而异变为苛求性义务,亦即将女性的自身价值置换为道德义务,以致于形成了刑法立法对女性的性反向歧视,从而将女性完全变成“性的受压迫者”。因此,刑法立法只有做到道德评价的归位,才能免除不平等的性义务苛求,从而实现其条文构建的“性别平等”。
归位道德评价意味着刑法不可过多地介入性的道德领域。虽然立法的过程中经常会出现道德需要立法确认的情形,但正如有学者所说:“法律不曾亦不能涉及道德的所有领域,若将一切道德的责任,尽行化为法律的责任,那便等于毁灭道德。”[11]那么,如果仅仅是道德需要,刑法立法过多介入性领域,其所导致的结果是刑法会将某种特定的模式强加于私人生活,进而产生难以被普遍和长久接受的强迫性秩序。波斯纳指出:“性规制将根据规则的实际后果来评判,而不是以是否符合一些道德的、政治的或宗教的观点来评判。”[12]因此,道德的需要并不是刑法立法过多介入性领域的理由。同时如果仅基于道德的需要而介入到性领域,则刑法立法就容易成为道德的“推手”,进而产生刑法过分干预个人私生活的后果。同时,刑法也将道德领域的歧视通过法律并且是最为严厉的法律予以确认。那么,为了避免刑法反向歧视,刑法须从性的道德领域中抽身,将属于道德的领域归还给道德。
在某种意义上,当涉及到性的问题时,刑法立法所面临的最大考验便是道德。而如果刑法立法在面临道德的考验时退缩,那么女性的个人价值会失去最后的屏障。如果刑法立法缺少对女性自身价值的确认和保护,那么隐藏在法条之后的反向歧视,便会进一步强化社会道德对女性已有的歧视。
在立法的过程中,如果刑法过多地介入道德领域特别是性领域,那么刑法立法就会被道德同质化。在男权文化占据着主导地位的社会中,道德的标准和内容往往会被偷换成男权道德的标准和内容。因此,在立法过程中,刑法如果过多介入涉性的道德领域,则会为男权文化巩固性别歧视提供充足的理由,致使女性成为“道德刑法”的牺牲品,其所导致的结果只会是刑法进一步肯定性别歧视的合法性,而平等原则在刑法中的真正实现会变得遥遥无期,最终女性永远成为道德枷锁下的“私人财产”。
归位对女性自身价值的社会评价,即将对女性的性苛求从刑法立法中剥离,意味着在刑法立法的过程中还原女性的自身价值。刑法对强奸罪等规定,其本意是对女性性权利的特殊保护,却形成了刑法的反向歧视,变相地强加或放大女性的性义务,这又构成了对女性自身价值的过多否定。这种强加或放大使得女性承担更多的道德义务,最终是不正义的。因此,在刑法立法过程中,想要还原女性的自身价值,须确立性别平等观念,以实现刑法构建的性别平等。但是,“迄今为止,所有现存的有关女性性行为的定义(至少在有关记载的历史上是这样)均为男性定义,因此,性行为本身的分类基本上被男权和‘男子气概’的实际活动败坏了。”[13]因此,刑法在立法的过程中对女性价值的还原,意味着刑法立法本身应将现有道德观念中的性秩序放置一边,并去除女性被强加的性义务。而这需要扭转男权主义,并使得刑法立法负有了这样的义务:对女性的性权利提供保护的法律依据;对于不该被过度评价的内容(如性义务)应“视而不见”。唯有如此,女性的自身价值才可能基于刑法的规定而获得稳当的保护。性秩序的构建离不开刑法立法的规定,但刑法立法应在克服男权主义之下,通过免除女性的“过剩的”性义务而确保女性的独立的自身价值。
《刑法修正案(九)》草案拟将强制猥亵罪的受害对象由“妇女”拓宽为“他人”,可以视为在平衡男性与女性人权保护之中,是立法者克除刑法反向歧视的一个努力。那么,我们同样期待的是,刑法立法不久也能将强奸罪的受害对象由“妇女”拓宽为“他人”,而这拓宽本应一并实现在《刑法修正案(九)》草案之中。
五、结语
刑法的反向歧视,可以视为在一种道德歧视或价值歧视之中违背了“性秩序”的社会发展规律,从而有违“刑法之真”[14]105。而如果将“刑法之真”归结为刑法文化[14]109-110,则刑法的反向歧视便是刑法不文明的一种体现。那么,刑法反向歧视的克除,便是健康刑法文化和推进刑法文明之举。
[1]卓泽渊.法的价值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
[2][美]约瑟芬·多诺万.女权主义的知识分子系统[M].赵育春,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
[3]周安平.性别平等的法律构建[D].苏州:苏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4.
[4]高铭暄.中国刑法解释:上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5][美]卡罗尔·帕特曼.性契约[M].李朝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6][加]丽贝卡·J·库克.妇女的人权——国家和国际的视角[M].黄列,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7]李永升.刑法与平等简论[J].河南社会科学,2010(4):125-126.
[8]何秉松.试论新刑法中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J].法律科学,1997(6):49.
[9]李邦友.论刑法平等原则的理论基础[J].现代法学,2002(3):104.
[10]王逢振.性别政治[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11]马长山.法治的社会根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12][美]理查德·A·波斯纳.性与理性[M].苏力,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
[13][美]杰佛瑞·威克斯.20世纪的性理论和性观念[M].宋文伟,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
[14]胡祥福,马荣春.论刑法之真——刑法文化的第一个勾连[J].南昌大学学报,201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