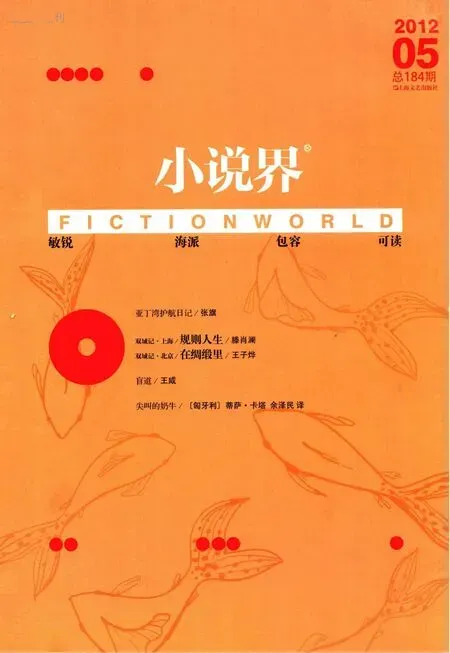人生是一座医院
文/蒋一谈
人在日月山川里,心思会慢慢接近澄明,眼前的西湖虽没有河川的无际,却也是城市里的开阔和湿润。我想到2010年的秋天,我坐在岸边,闭眼倾听木船上两位年轻女子的轻谈浅笑,想象她们是古代的琵琶女,安然等待暮色四合。船夫挑来灯笼,挂在船头,看谁第一个登上船来。
那个黄昏,我没有想到苏东坡,也没有闻见西湖醋鱼,我想到短篇小说《刀宴》里的沈家轮和那把明代老刀,老刀最终被沈家轮沉入西湖的淤泥里,这或许是合适的小说结局,只因从此以后,今人与旧物再无缠缚,即使是不得已,也总算落了个清净洒然。
花开花落,岁月不惊。人世的恩怨与炎凉,在西湖的耳朵里是充耳不闻的闲言碎语,大文豪的骚笔也只是一支竹竿笔,与农夫的锄头、船夫的楫桨无异,因为西湖可以自怜自惊,也可以独处守身,而我只是惊叹湖面和湖面下不透明的水,积攒了数也数不清的离愁别恨;我同时在想,如果波德莱尔来到西湖,会想到什么?
“人生是一座医院,每个病人都渴望着调换床位。”记不清是哪一年,我记住了这两句话。波德莱尔话里话外的意思很显白、很冷峻,每一个人都是现世的病人(地狱也许是一个可能的治愈场所),而他想离生活远一点,在一个不在的地方,一个离开世界的地方,他真正的渴望之地。
我在西湖岸边回味良久,看见了一幅画面:我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医生递过来出院通知单,我接过去,在心里笑了,觉得自己又完成了一件老天爷交给我的任务。我在想,人生即是理解和承受。我也想到弘一法师的临终遗言:悲欣交集。人的生死一场,被他道尽。
写完《庐山隐士》,我依照习惯为这本小说集选择扉页题词。我最初写下的是这两句话:命运是一个哑巴,命运喜欢沉默寡言的人。这个题词暗合了小说集的书名,那位庐山隐士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中年男人。四十五岁之前是青年,而我今年四十六岁,已是中年男人身,越来越觉得自己离半隐半出不远了。
但在某个深夜,我梦见了西湖,是冬天的景象,天空飘下雪片,伸手去接,握在手里的是春天的柳絮,一团一团的,想握握不住,想赶赶不走,缠绕着路边树和路边人。西湖是冰雪世界,湖面上排列着很多床铺,男男女女躺在上面,有的打情骂俏,有的在做爱,有的沉默不语,有的对我做鬼脸,而我想找到自己的床位。我找啊找啊,好像找到了,我走过去,躺在床上,没有女人陪伴,我闭上眼睛等待着,却和床一起掉进冰冷的湖水。我醒过来,想到了波德莱尔,想到了他的这句话。
与三位好朋友谈起小说集的题词,本来轻松的茶室氛围静寂了十几秒钟。一个朋友摇了摇头,说:“我敬佩那些明知自己有病却隐瞒病情的人,他不想打败病魔,只是想看看病魔到底怎样折磨自己。”
另一位朋友喝了一口茶,说:“谁都会得病,身体上的,精神上的,但我很在意自己的死亡方式。我不想被病痛折磨,我去医院看见痛苦的病人,想到自己晚年也可能这样,心里很难过。”说完这些,他抬眼看着我。
我也想说自己的感受,可是最先说话的那位朋友插话道:“我觉得,意外的死亡是最好的死亡方式。我在路上走,想着自己的心事,一辆大货车忽然侧翻,把我轧死了,痛苦的时间很短,我都不知道是怎么死的,这多好啊!对了,掉进街边的热力井也挺好的,一下子掉进滚烫的下水道里,瞬间被熏晕,失去意识,也没什么大的痛苦,身体被煮烂了也不知道。如果非得选一种病,我选择心脏病,从发病到死亡,挣扎个几分钟就嘎嘣完事了。”
第三位朋友一直沉默着,这时叹了口气,意味深长地说:“维摩诘说过,以众生病,是故我病。”说完,他站起身走向洗手间。
我本来也想说几句,可是我的电话响了。我走出茶馆。挂断电话之后,我站在茶馆外面的树荫下点了一根烟,顺手打开微信朋友圈,观赏一个讲述生命诞生的视频:一群精子在阴道里争先恐后地奔跑,强壮的精子杀死体弱的,最强壮的精子也是杀死同类最多的勇者。视频画面血红,好像是魔界里血流成河的杀戮现场。最强壮的精子最终强奸了卵子。万事大吉。
我揉碎大半截香烟,好像从刚才的画面里获取了某种即将失缺的勇气。举目远望,眼前黄昏的天空是现实的,也是远古的,如此平静,如此宜人,看上去像是假的。但我知道,我有实实在在的近忧,而生活的远意暂且是我的慰藉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