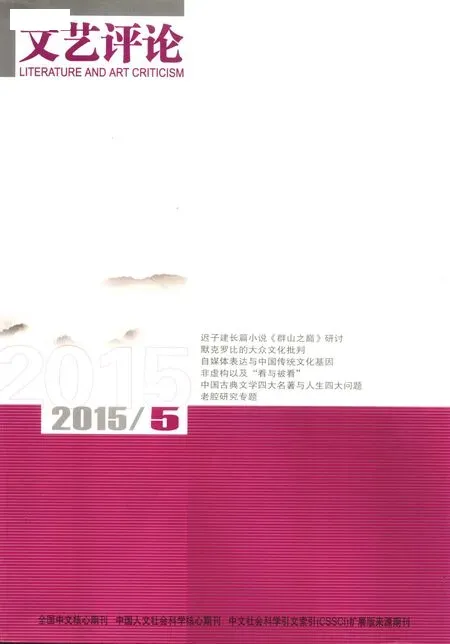方言与“五四”时期新诗的文体建构
○王佳琴
方言与“五四”时期新诗的文体建构
○王佳琴
“五四”文学语言变革倡导白话代替文言,“活”语代替“死”语,而在国语尚处于建设过程中的当时,白话的成分其实是相当复杂的。除了胡适所说应该多读的“模范的白话文学”如《水浒传》、《西游记》、《儒林外史》、《红楼梦》等之外,对来自不同区域的作家来说,他们的“活”语与其各自秉持的方言因子难分难解。正如研究者所说的:“活的语言与方言有不少曲径通幽之处,因此,不难发现现代白话新诗因语言整体结构上的白话化、口语化倾向,而与大地上千百年来的原生态方言保持着难以背离的血缘性。”①需要说明的是,从主观上来说方言入诗对有的作家来说是早年生活环境导致的自然而然的表现,如胡适早期的打油诗、郭沫若诗歌中的乐山方言;②而对有的作家和群体来说则是有意的试验,前者体现了地域文化对作家的潜在影响,属于“无意为之”,而后者则是文学领域内的有意的实践,为探讨方言入诗及其背后关涉的文学观念、文学评价及其得失,本文更加着重于对后者的考察。
语言变革不仅是新文学革命的重要内容,而且对新文学的构建起着重要的制约和影响作用。方言作为白话文学语言的重要资源之一,探讨其对新诗的文体建构、文学形态所发生的作用正是本文所要解决的问题。
一、方言入诗与诗剧
“五四”文学革命提倡白话代替文言成为正宗的文学语言,白话写诗打破了旧有诗词曲的格律平仄范式,虽然一度带来了俞平伯所说的失范状态,但是胡适所提出的“不拘格律,不拘平仄,不拘长短”的“诗体大解放”毕竟激活了诗歌文体的创生,白话写诗必将昭示着一个全新的情感表达方式不断生成和凝定的诗歌时代。
当代学者就注意到了口语入诗和诗剧之间的关系:“口语成了诗歌与戏剧进行嫁接的最佳切入口,也就成了诗剧的最重要特征。”③诗剧主要突出和侧重的是诗歌的戏剧化倾向,简单地说,就是设置一定的戏剧性场景,运用人物自己的语言来表现人物。众所周知,中国古代诗歌以抒情为主导,叙事诗因种种原因不够发达,戏剧性的场景因素在诗歌中较少体现,白话写诗无疑会催生这种戏剧化的诗歌体式。事实上,早在20世纪30年代叶公超就提出“新诗应当多在诗剧方面努力”,并且认识到诗剧与语言之间的关系:“旧诗的情调那样单纯,当然有许多历史的原因,但是它之不接近语言无疑地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限制。”④而新诗使用的是建立在自然语言节奏上的白话,可以通过“诗剧”打破这一格局,“诗剧……应当以能入语调为原则。惟有在诗剧里我们才可以逐步探索活人说话的节奏,也惟有在诗剧里语言意态的转变最显明,最复杂”⑤。诗剧可以最大限度地保持对日常语言的接近。
而在“五四”时期统一的民族共同语尚未形成,白话口语写诗会带来的一种结果就是,当戏剧性情境中的表现对象为某种特定地域中的特定群体时,其各自的方言因素必然被凸显出来。因此,当方言在“五四”时期随着诗歌语言总体的“口语化”潜入诗歌时,诗歌的戏剧化探索也被彰显出来,这种独特的语言因素使得新诗呈现出不同于古典诗歌的特征,在这一点上新诗与古代叙事诗完全拉开了距离。我们可以通过具体诗歌作品的对比来进一步认识方言给新诗带来的文体新质。
唐代诗人杜甫的《石壕吏》是现实主义创作的名篇,其中就有戏剧性的场景,诗人目睹了“有吏夜捉人”的情景,倾听了可怜的老妪凄苦的“致词”(“听妇前致词”):
三男邺城戍。一男附书至,二男新战死。存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室中更无人,惟有乳下孙。有孙母未去,出入无完裙。老妪力虽衰,请从吏夜归。急应河阳役,犹得备晨炊。
这里老妇的语言显然不像小说中的人物语言那样可以用直接引语的方式呈现,而是诗人出于古典诗歌写作的规范经过了特殊的加工,因此即使是戏剧性场景,诗歌的“情调”仍然较为单纯,叶公超所说的那种“诗剧是保持这种接近语言的方式之一”的情况在古典诗歌中不可能实现,经过诗人加工的语言呈现的是诗人对民生疾苦的了解,对下层民众的同情。而方言入诗,方言参与到新诗的戏剧性场景中时,表现的就不是诗人,而是诗歌中的人物在特定情境中表现自身。如徐志摩的《一条金色的光痕》也是一位老太太的语言,但是与《石壕吏》完全有别,试录如下:
“太太,为点事体要来求求太太呀!
太太,我拉埭上,东横头,有个老阿太”
这是一位乡下老太太进城求城里有钱的太太施舍,以安顿已死却没钱下葬的邻居老太的情境。在得到了帮助之后,她又说:
“喔唷,太太认真好来,真体恤我拉穷人……
格套衣裳正好……喔唷,害太太还要难为洋钿……喔唷,喔唷……我只得朝太太磕一个响头,代故世欧谢谢!
喔唷,那末真真多谢,真欧,太太……”
这里的语言完全是老太太在那个场景中自己的语言,非常微妙地传达了一个老太太的善良和求人帮忙时的世故,这正是引入方言——人物自己的语言后所表现的复杂的“语言意态的转变”和丰富的“情调”。
由上可见,方言作为白话文学语言建设的资源之一,用方言写诗或者方言入诗影响着诗歌文学体裁的建构。托马舍夫斯基说:“体裁的本质在于,每种体裁的程序都有该体裁特有的程序聚合。”⑥不妨认为,“特有的程序聚合”就是“体裁”的本质内涵。不同的文学语言经过某类文学体裁即某种“特有的程序聚合”时,会形成不同的建构形态。具体而言,文言和方言作为不同的文学语言,在经过诗歌体裁的程序聚合后,会呈现不同的诗歌形态。正如语言学家萨丕尔所说:“每一种语言都有它鲜明的特点,所以一种文学的内在的形式限制——和可能性——从来不会和另一种文学完全一样。用一种语言的形式和质料形成的文学,总带着它的模子的色彩和线条。”⑦方言写诗可以将某种特定的场景和其中的人物一并呈现,场景为人物表现自己提供了开放的情境,用人物自身的“语调”可以充分地展示“意态”的复杂性。用人物的活的方言写诗使得新诗呈现了异于同样情境中的古典诗歌,也因此突破了古诗“单纯”的情调,在这样的戏剧性场景中诗歌的内涵无疑得到了拓展,而方言入诗直接支持和催生了诗剧文体,丰富了新诗的文体建设。
二、方言入诗与民歌
方言不仅仅是特定诗歌情境中人物的语言,而且成为“五四”时期许多作家争相效仿和借鉴的诗语。方言入诗自然是白话代替文言的语言变革背景支持的结果,但是与方言和小说、散文其它诸种体裁相比,方言和诗歌的结合有一种现成的文体资源——民歌备受关注。
“五四”时期《歌谣》杂志的同人已经意识到民间歌谣对新文学建设的作用,刘半农则明确提出“破坏旧韵重造新韵、增多诗体”⑧的主张,他后来回忆自己作为新诗筚路蓝缕的探索者在文体方面做出了诸多尝试,其中就有“方言拟民歌”⑨。由此可见,“五四”新文学建设过程中出于反抗传统文学非常倚重民间资源,更需要注意的是方言歌谣同时还满足了诗歌草创期文体建设的需要,使得用方言写诗的尝试成为引人关注的领域。如刘半农《瓦釜集·第十九歌》中:
河边浪阿姐你洗格啥衣裳?
你一泊一泊泊出清波万丈长。
我隔仔绿沉沉格杨柳听你一记一记捣,
一记一记一齐捣勒笃我心浪!这种方言民谣的尝试受到沈从文的激赏,他认为刘半农的山歌“比他的其余诗歌美丽多了”⑩。1925年,沈从文自己也写作发表了一些完全用家乡凤凰方言“镇筸土话”写作的诗歌,其中一首《乡间的夏》写道:
(倘若是)一个生得乖生乖生了的
代帕,阿玡过道,(代帕为苗姑娘,阿玡为苗妇人)
你也我也就油皮滑脸的起来撏毛。(撏毛即开玩笑)
轻轻地唱个山歌给她听,
(歌儿不轻也不行!)
——太姐走路笑笑底,
一对奶子俏俏底;
我想用手摸一摸,
心里总是跳跳底。——
只看到那个代帕脸红怕丑,
只看到那个代帕匆脚忙手。
……
六月不吃观音斋,
打个火把就可跑到河边去照螃蟹:
“耶叻耶叻——孥孥唉!
今天螃蟹才叫多,
怎么忘记拿箩箩?”沈从文这样解释自己的此类创作:“若因袭而又因袭,文字的生命一天薄弱一天,又哪能找出一点起色?因此,我想来做一种新尝试。若是这尝试还有一条小道可走,大家都来开拓一下,也许寂寞无味的文坛要热闹一点呢。”⑪这种方言民歌是带着新文学建设期的胡适般的尝试精神进行的,方言有益于破除因袭,给诗歌注入新鲜的血液,但是弊端也同时显露。苏雪林后来针对刘半农的创作曾说:“民歌虽具有原始的浑朴自然之美,但粗俗幼稚,简单浅陋,达不出细腻曲折的思想,表不出高尚优美的感情,不能叫做文学。”⑫事实上,早在“五四”时期,周作人已经指出了民歌的缺陷:“民间的歌谣自有其特殊的价值,但这缺点也仍是显著……‘久被蔑视的俗语,未经文艺上的运用,便缺乏细腻的表现力,以致变成那种幼稚的文体,而且将意思也连累了。’”⑬跟戏剧性场景和小说中的方言使用不同,方言民歌体写作更易显出粗疏幼稚,这是由诗歌文体的特殊性决定的。诗人阿垅曾说:“诗是诗人以情绪底突击由他自己直接向读者呈出的。”⑭如果说小说中的语言和作者的关系是“直接”的,那么诗歌中的语言和诗人则较为“间接”。巴赫金也曾比较过小说和诗歌中的语言,他认为在诗歌中诗人“把整部作品的语言全作为自己的语言而对之全面地直接地负责,与这语言的每一个因素、语调、情味完全地一致……诗歌风格满足于一种语言和一个语言意识”⑮。由此可见,方言入诗过程中借鉴的民歌连同其词汇、韵律、诗体作为一个整体被新诗人仿效,民间的情味成为诗歌唯一的情味,而这种模仿即使再像,对新诗的未来发展也谈不上真正贡献。
民间歌谣的借鉴和仿写热潮一方面有利于诗歌的解放和创新,另一方面可能也存在隐形的束缚,有研究者指出:“现代新诗歌谣化倾向看起来好像是一个民间文化资源的利用问题,其实它暗示着中国现代新诗运动正在逐渐背离它的初衷,引导新诗重新走向诗歌合流的倒退之路。”⑯方言入诗与现成的民歌资源应当保持怎样的张力关系更应当成为思考的命题。
三、方言入诗的路径
如果还要利用方言来写诗歌的话,可以有哪些路径呢?在新诗发展的初期,有意识的方言入诗实践中主要有两种途径。
一种是提取方言中一些独特的表达方式。如朱湘在新月派诗人土白入诗的实践中就曾提出“拿土白来作诗”时“某一种土白中有些说话的方法特别有趣,有些词语极为美丽,极为精警,极为新颖,是别种土白或官话中所无的,这些文法的结构同词语便是文人极好的材料,可以拿来建造起佳妙的作品……所以我们不想作土白诗则已,要是想作土白诗,我们也必得走这条路上去发展。”⑰其实这种做法就是借用、淘洗一些方言、土白中特有的词语和文法,在此基础上,诗人的语言不会拘于方言而粗俗浅显,反而会因为丰富了白话语言而更加“佳妙”。这里方言入诗的限度是借鉴方言中的一些文法和词语,方言仅仅是作为一种“材料”进入诗人的诗歌语言系统的。通过这样的分析,也许可以使我们更好的理解郭沫若诗歌中的方言因子。如研究者所示,他的诗歌语言有很多乐山方言的词汇和表达法,⑱但是这并不妨碍他将“五四”的现代精神淋漓尽致的表现出来。方言及其思维方式在他的诗思中不占主导地位,方言没有成为诗歌全部的语言并进而成为诗人自己的语言,因此,没有牵掣其想象力的伸展和发挥。
另外一种路径就是前文所提到的诗歌的戏剧化。既然方言成为诗歌的语言很容易使诗人与方言紧紧扭缠,导致诗歌仅呈现模仿民歌、不能表达细腻曲折的情思之后果,那么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将诗人与方言进行“间离”,使得方言成为戏剧性情境中人物的语言,诗人抽离了方言的语境就使更深的意旨从情境中流露出来成为可能。刘半农《面包与盐》就是模仿北京下层两个穷人的谈话写成,此外还有徐志摩的《一条金色的光痕》、闻一多的《天安门》《飞毛腿》都是此类作品。不妨以朱自清1920年代的一首《小舱中的现代》为例,诗的开头非常口语化的、逼真的描摹了船舱中各类人物的语言,“洋糖百合稀饭”、“饺面”、“潮糕”、“梨子”等称谓语都带有浓厚的地方性,“行好的大先生,你可怜可怜我们娘儿俩啵———/肚子饿了好两天罗!”中的语气词也是方言独有的,但是这只是人物的语言,诗人却“从小舱的一切里,/这样,这样,/悄然认识了那窒息着似的现代了。”——这才是这首诗歌的意旨所在。由此不难看出,戏剧性情境的创设为诗歌表达复杂内涵提供了可能。小舱中活动着形形色色的人物,这样一个场景可以从不同的眼光和视角去解读,诗人所取的是其中之一,但绝对不是人物自身的语言所能呈现的。朱自清此诗运用方言又超越了方言,通过戏剧化情境表达了现代性的意旨。但是总体而言,20年代的方言入诗在诗歌的戏剧性实践方面,情境中的人物与诗歌最终的主题意旨基本一致。“五四”作家更多地以人道主义情怀观照下层民众,通过人物自身的语言(往往是方言)反映他们贫苦悲惨的生活,戏剧性的“张力”基本没有。
而在另外一类诗如徐志摩的《盖上几张油纸》中,题记中明确说明是在故乡硖石所作,并且“有事实的背景”⑲,一个乡下妇人肯定是用方言说话,但是在徐诗中已经舍弃了对方言的直录,诗句如下:
虎虎的,虎虎的,风响在树林间;
有一个妇人,有一个妇人独自在哽咽。
为什么伤心,妇人,
这大冷的雪天?
为什么啼哭,莫非是失掉了钗钿?
不是的,先生,不是的,不是为钗钿;
也是的,也是的,我不见了我的心恋。
这里的诗歌语言将妇人告白的语言进行了某种“纯化”,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与诗歌其余叙述部分节奏感很强的、伤感的、诗化的优美语言进行对接,如此一来基本上又回到了《石壕吏》的路数,方言已经消泯。
由此可见,诗歌的戏剧化作为一种尝试,一定程度上化解了方言和诗歌之间的“间性”,但是也可以看出方言与诗歌的“亲密接触”与方言入小说相比存在着相当的限度和难度。诗歌再怎么戏剧化,毕竟不可能像小说那样毫不设防地容纳人物语言的众声喧哗,这是由诗歌体裁的独特性所决定的,方言入诗的限度和可能在曲折、艰辛的实践中彰显无疑。
尽管如此,20世纪20年代的方言入诗及其与此有关的诗歌戏剧化仍然成为了一个可供拓展的平台。与新月派关系密切,坦言“受到写了《死水》以后的师辈闻一多本人的熏陶”⑳的卞之琳就进一步发展了诗歌的戏剧化,卞之琳利用诗歌的戏剧化将抽象与具体、一般和个别等对立的两极进行平衡,从而表现现代人细密而深刻的诗思,只不过此时方言已经不是唯一突出的因素了:“始终是以口语为主,适当吸收了欧化句法和文言遣词(这是为了字少意多,为了求精炼)。”㉑这是后话。
结语
综上所述,方言作为白话文学语言建设的重要资源,在新诗初期的文体建构中留下了重要的线索。作为一种活语,方言写诗可以保持活的语言方式和丰富的语言意态,从而扩大了新诗的表达内涵。同时,在反对文言雕琢陈腐、激赏民间语言朴实自然的历史时期,仍有论者和诗人注意到了方言这一资源所存在的问题,这正是“五四”新文学在利用方言时不同于古典诗人那种类似于鲁迅所说的“运用‘僻典’”的陶醉,而秉持的一份在现代意识烛照之下可贵的清醒。由于方言与诗歌体裁之间关系的特殊性,在方言入诗的实践中,事实上主要促成了诗歌的戏剧化,这对此后诗歌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研究方言与新诗的文体建构正是为了更好地认识新诗的艺术传统,为20世纪发展曲折的新诗提供些许启示。当下,流行语、网络语、口语、方言等活语是否可以入诗?在什么意义上、通过什么途径入诗,历史似乎已经为我们提供了一些答案。
(作者单位:盐城师范学院文学院)
①颜同林《困惑与诱惑:方言入诗的两难选择》[N],《湖南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
②⑱参见颜同林《方言入诗与中国新诗的发生》[J],《文学评论》,2009年第1期。
③吕周聚《杂糅复合,别创诗体——中国现代诗歌文体衍生模式初探》[N],《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6期。
④⑤叶公超《论新诗》[J],《文学杂志》,1937年第1期。
⑥[苏联]鲍·托马舍夫斯基《主题》[C],胡经之、张首映《西方二十世纪文论选》,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13页。
⑦[美]爱德华·萨丕尔《语言论》[M],陆卓元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199页。
⑧刘半农《我之文学改良观》[J],《新青年》1917年第3卷第3号。
⑨刘半农《〈扬鞭集〉自序》[A],鲍晶《刘半农研究资料》,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14页。
⑩沈从文《论刘半农的〈扬鞭集〉》,鲍晶《刘半农研究资料》[A],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87页。
⑪沈从文《话后之话》[N],《京报·国语周刊》,1925年第5期。
⑫苏雪林《〈扬鞭集〉读后感》,鲍晶《刘半农研究资料》,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01页。
⑬周作人《国语改造的意见》[J],《东方杂志》,1922年第17期。
⑭阿垅《形象再论》[C],王锺陵《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文论精华》(新诗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57-258页。
⑮巴赫金《小说理论》[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66页。
⑯谭桂林《论中国现代新诗韵律的诗学探索》[J],《福建论坛》,2006年第8期。
⑰朱湘《评徐君志摩的诗》[M],《朱湘散文经典》,北京:印刷工业出版社,2001年版,第133-134页。
⑲徐志摩《盖上几张油纸》[M],韩石山《徐志摩全集》,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31页。
⑳㉑卞之琳《雕虫纪历·自序》[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4页,第3-4页。
2014年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中国现代文学与国语的建构研究”(编号:14CZW077);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文学语言变革与中国文学文体的现代转型”(编号:13YJC751054)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