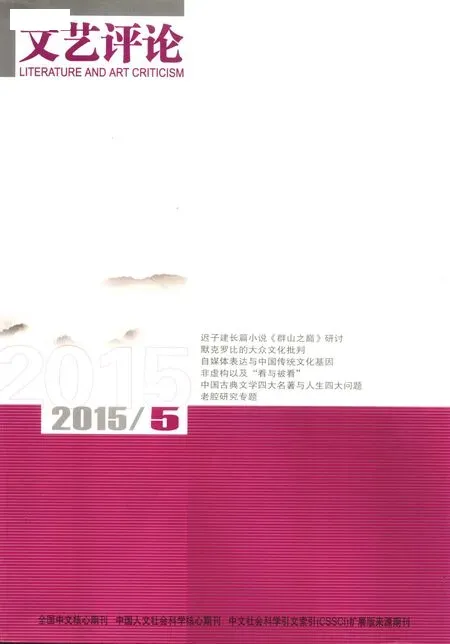悲欣交集的中国北疆世界
——评迟子建《群山之巅》
○金钢
悲欣交集的中国北疆世界
——评迟子建《群山之巅》
○金钢
熟悉迟子建作品的读者,面对她的这部长篇新作《群山之巅》,应会有亲切感,如见久别的朋友。这里有与《白银那》《逆行精灵》《越过云层的晴朗》等作相似的人和大自然,走进《群山之巅》,我们便知道是来到了迟子建的文学世界。在这个崇尚创新的时代,迟子建并没有急于寻求改变,她仍然执著于书写这块她生于斯长于斯的中国北疆世界,将这片天地构筑得更为扎实、动人心魄。
一、身世浮沉
《群山之巅》是一部包蕴浓厚历史感的长篇小说,只不过这种历史感不是呈现为重大的事变,而是深藏于普通人的身世里。迟子建所构建的中国北疆世界从地理位置上来看,即是她的故乡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区。这块东北边陲之地林木茂盛,土地肥沃,是不折不扣的“神奇的土地”。或许是因为其特定的地理位置、历史状况和丰富的自然资源,使得这块肥沃的黑土地承受了更多的血与火、开发与建设:军阀割据、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伪满政权、国共两党之争、开发北大荒以及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百余年风起云涌的历史进程给这里人民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冲击。过去的一百年,对于这里的人民来说,是一个埋藏了巨大悲欣的世纪。
辛氏与安氏祖孙三代的身世浮沉,勾连起了这块北疆世界的百年风云。“辛”“安”或许便是兴安的谐音。两家的老人辛永库与安玉顺都曾参加过抗联,打过鬼子,可如今的际遇却是天壤之别。战争给二人带来的创伤都是巨大的,家人离散、肢体伤残成为一生的伤痛。然而,他们承受的远不止这些。辛永库因偶然的原因脱离了队伍,变成了人们眼中的逃兵“辛开溜”,他在东北光复时,娶了一个日本女人,这种面对民族矛盾的“糊涂”立场,使他和他的妻子、“儿子”都成为民众欺凌与嘲笑的对象。安玉顺因肢体残疾被定为战斗英雄,后半生成了演讲机器,甚至在他未死之时,烈士陵园就给他留出了位置。沉醉于荣誉的安玉顺在生命的最后几年患上了老年痴呆,让人感叹这个战斗英雄“没倒在枪炮下,却倒在了疾病的隘口”。
因父母的奇特身份,屠夫辛七杂从小就饱受嘲讽,以至于他成年后不愿生养子女,不想让“不洁不义的血脉”流传下去。后在夫人的坚持下,抱养了一个孩子,却没想到在一次争吵中,夫人死在了养子的刀下。而他没想到的还有他其实和父亲“辛开溜”并没有血缘关系;他竟然还有一个俄罗斯兄弟。作为一个战败国的女人,他的母亲秋山爱子所承受的战争苦难比辛氏父子更重。安玉顺的儿子安平当上了法警,执行枪决是他的本职工作之一,但民众却视其为怪物,妻子离他而去,留下一个长不高的女儿。安平的孤独终于被殡仪馆理容师李素贞所融化,本以为两双频繁接触死亡的手可以互相取暖,但他俩的一次雪夜幽会,意外地导致了李素贞的残疾丈夫被煤烟熏死,这使她背负上了沉重的精神十字架。
辛安两家在第三代产生了交集,交集于一次强奸事件。辛欣来在将养母斩首之后,又强奸了被乡人视为神明的安雪儿。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罪大恶极的人,也有着悲伤的身世。他是当地权力“一哥”陈金谷与一个上海知青所生。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里,北大荒给予知青们的,不仅仅是“豪迈和诗意”,“还有艰辛和困苦,还有付诸东流的青春和理想,还有一条充满挫折的生活道路”①。应该说,辛欣来的悲剧源于生母的抛弃,而当他的亲兄弟陈庆北知道了他的身份后,毫无认他、救他之意,却要让他尽快定罪伏法,以取死刑犯的器官,这不仅让人感叹权力、金钱面前亲情和人性的丧失!从一定程度上说,安雪儿与辛欣来一样也是弃儿,从小被至亲抛弃造成了他们的畸形生长,只不过一人是生理上,另一人是心理上。
辛安两家的故事远不是《群山之巅》的全部,再加上陈金谷一家,以及老魏、单尔冬、烟婆、葛喜宝等人的故事,这本二十万字的小说头绪之多、线索之复杂、人物命运之奇诡,令人咋舌,真让人有身世浮沉,雨打浮萍之感。芸芸众生在百余年来历史、时代、命运的风雨击打之下,原本的血脉联系、人生路途变得支离破碎,而重组起来的生活都充溢着疼痛、悲伤、勉强和无奈。《群山之巅》用纷繁的人生故事编织出来一种悲凉的情绪,这种悲凉情绪的内涵便是:我们所期望的平稳、安逸只不过是梦想,凌乱、无序、身不由己才是人生的真相。
二、世事变幻
尽管时间的长河已流淌到了21世纪,百年间经历了重大的社会变革,但由于偏远和封闭,《群山之巅》所构筑的北疆世界还是保留了许多过往时代的风土民俗。迟子建所倾心的正是这古老的乡土,它意味着与自然的亲近,意味着野性的活力,意味着宁静和谐、纯净朴素、远离尘世的喧嚣。不过,随着现代文明的飞速发展,这片古老乡土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宁静和缓慢正无可奈何的离我们越来越远,田园牧歌的时代生活已经一去不复返”②。迟子建在中篇小说《原始风景》的结尾曾写道:“我的笔所追踪过的那架四轮马车,它终于走到故乡了。我写过了,我释然,可那遥遥的灰色房屋和古香古色的小镇果真为此而存在了么?我感到迷茫。”③作家对古老的乡土世界充满了憧憬,但同时她也发现那个世界正在缓慢地崩塌。
在《群山之巅》描绘的那个看似封闭落后的北疆世界里,现代化进程推动的各种潮流也在暗中涌动,其中对乡民们冲击最大的应是面对死亡方式的变革。关于死亡,美国学者拉蒙特曾指出:“死亡本身通常被认为是最大的灾难,是人类的最凶恶的敌人。”不过,“死亡为包括我们自己的后代在内的无数的人开辟了道路,使他们也得以经历生活的欢乐,从这个意义上说,死亡是尚未出生的未来一代的同盟者”④。一直以来,迟子建在写到死亡时都持有一种从容的态度,自《北极村童话》始,她便不断地倾心于对死亡的描述,死死生生本就是人间寻常事。甚至可以说,迟子建所描述的死亡是浪漫的、戏剧化的。在迟子建的文学世界中,存在并不单指有形的肉身,无形的思想、精魂也是,甚至更是。有形的肉身只能存在几年、几十年,最长也只有一百多年,这样的长度在历史的长河中只不过是弹指一挥间,而无形的思想、精魂却可能打破时间的界限,在历史的长河中喧嚣不息。《东窗》中有这样的话,“一个死了的人留下的就是一具躯体。活着时人是没有灵魂的,而死了之后灵魂就诞生了。不然怎么与死的人对话呢”⑤。《重温草莓》中,是父亲的灵魂带“我”神游了幽冥之界,让“我”重温了渴望已久的久违了的父爱温暖。
然而,在《群山之巅》中,死亡由充满了诗意浪漫的神性仪式演化为简单冰冷的现代流程。死亡在这里被称为“白事”,是与婚嫁这样的“红事”同等重要的人生节目。老人们都准备了上好的寿材,鄂伦春族的绣娘选的则是与自然沟通的风葬。在旧式葬礼上,“有灵棚,有棺材,有长明灯,有供品,有庄严的入殓仪式”;“病弱的小孩子可以钻棺祈福,儿女们可以在长明灯前守灵”。可是这些古老的风俗大多随着火葬的推广被破坏了,而且火葬的费用也给百姓们带来了不必要的负担。另外,死刑执行方式的改变也减少了乡民们接触死亡的环节,死刑由枪决改为注射后,“就只剩下一张布告,没有了游街,也没有山间的法场,而那些发生在山间法场的故事也就逐渐消亡了,死刑犯被带到执行车上,打一针,一瞬间就毙命了。现在很多老百姓都说,死刑犯死得太舒服了,以后是不是罪犯会越来越多?这个问题让人深思”⑥。
在《群山之巅》中缓慢崩塌的不仅有乡民们的古老风俗,还有这里的绿水青山。曾有论者指出:“相对于红尘滚滚一往无前的时代,迟子建的小说里始终活跃着那一个顽固而无可救药、可亲可敬的‘逆行精灵’。”⑦在《群山之巅》里,这个顽固的“精灵”依然活跃,她抗拒着现代文明的开发和建设,似乎任何变革都会让她不悦,引起反击。镇政府修了一条水泥路,并在山顶建了个八角亭,这样小小的变化就引发了毒虫伤人,江水泛滥等灾难,吓得唐镇长连忙派人掘掉水泥路,烧毁八角亭,让一切恢复原状。唐镇长可说是这个“逆行精灵”的代言人,他尽其所能地维护着故土小镇的自然生态,他放弃了去县城发展的机会,固守在小镇里。虽然他的一些做法——派遣斗羊去攻击地质工程师、不许辛开溜说山里有无烟煤、在山上修建土地庙等——显得荒唐可笑,但却蕴含着对故土人与自然的深切爱恋,而正是这深深的爱恋使寒冷、荒凉的北疆世界变幻为温暖、葱郁的家园。
三、白茫茫一片大地
在已往迟子建的乡土世界里,她所要努力表现的是源自土地及人类初始的古朴、善良、坚韧等等一切美好的事物,对她来说,人世的寒凉辛酸有跃动的炉火去温暖,而人心的罪恶是小的,乡民们都是有着小毛病的普通人。人们往往会在饱尝辛酸后终获温情,历尽艰难后终得爱意,这一点点温情与爱意浸透了忧伤,珍贵的温情与爱意冲淡了迟子建乡土世界中的悲剧氛围,使其淡化为一种古典的伤怀之美。如果用颜色来作比喻,那么以往迟子建的乡土世界显现为蕴涵生机的浅绿和怀有忧伤的淡蓝,而在《群山之巅》里,所有的色彩都一点一点被白茫茫的大雪所掩盖了,这是一个下着大雪的、混沌迷茫的北疆世界。
在《群山之巅》中,虽然有着身世浮沉、世事变幻的复杂,但种种复杂终归会聚为一种简单,那便是“悲欣交集”的生存状态。这样的会聚就像北疆世界的群山,在山脚、山腰是黄绿斑驳的,而到了山巅,呈现的却是常年积雪、旷远苍凉。“悲欣交集”四字原为弘一法师临终前写下的,这四字对于不同角度、层面的读者来说,会出现不同的理解。如叶圣陶先生解释“欣”字,一辈子“好好地活”了,到如今“好好地死”了,欢喜满足,了无缺憾。钱仁康教授认为“‘悲’是悲悯众生的苦恼,‘欣’是欣幸自身得到解脱”。《弘一大师传》的作者陈剑慧教授说“‘悲欣交集’是弘公当时临终的情境。是一种念佛见佛,一悲一喜的境界,不见佛的人,便不知道念佛也会起悲心”。此说托出弘一法师当时之心境,而此境是无法用语言文字所能表达的,只有过来人才能知晓,有同等感受之人才能道出。迟子建在小说的尾部将这四字用在安雪儿身上,“她悲欣交集”,这样一个简单的句子,却道出了安雪儿这个神奇人物的一生。
在迟子建的文学世界里,不乏精灵一般的形象,如《草地上的云朵》中的丑妞、《疯人院里的小磨盘》中的小磨盘、《热鸟》里的侏儒女孩等。而在《群山之巅》中,安雪儿这一形象从能够勘破生死、沟通自然的精灵,堕落到滚滚红尘中;从具有看出命运的能力的“小仙儿”,变成生养孩子的普通女人。这样的转变难以用好坏来形容,虽然“她安慰自己,一个毛边,抵得上自然界的万事万物,有他就是大千世界了,可她还是为现在的自己伤感”。在安雪儿的人生里,既有洞察宇宙微妙变化的神性喜悦,又有被生母离弃、被强暴的凡俗痛楚。可是,神性的世界虽美妙,却孤寂;凡俗的世界虽疼痛,但熙熙攘攘、可爱热闹。所以,安雪儿这一形象与迟子建已往塑造的“精灵”们大不相同,这是一个神性与人性复杂交融的角色,唯有“悲欣交集”四字才能形容其人生。
在《群山之巅》的结尾,迟子建以又一次强暴事件呼应了小说的开头。这次事件会让凡俗中的安雪儿重获神性,还是让混沌中的单夏回归凡俗?其结局无从得知,掩卷之后,留在心里的唯有那句“一世界的鹅毛大雪,谁又能听见谁的呼唤”。小说中的种种世事人生,如过眼云烟,神奇的安雪儿蜕变为普通妇女;美丽纯洁的唐眉一次犯错后便自甘堕落;孤独的法警安平找到了一双温暖的手又迅疾失去;单四嫂放下怨恨却再度被抛弃……在迟子建的随立随扫中,这块北疆世界终归变成了“白茫茫一片大地”,世界以我们无法把握的方式在前行,而一次次被搅动的心澜,最终化成了空寂。这空寂或许正是迟子建创作三十年的心境,三十年岁月匆匆而过,迟子建自己也从一个讲着故乡童话的青涩少女迈入知命之年,她这时的述说与故乡的黑土白雪水乳交融,我们知道,白茫茫的大雪下覆盖着肥沃的黑土,当大雪消融的时候,便会有生机萌发。总之,《群山之巅》将我们带入中国北疆一片半封闭、半神秘的传奇世界里,这里发生的故事是如此丰富多彩,有着各种各样的来历,而其终极的悲凉、欢欣却与别的世界并无不同。
(作者单位: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①陆星儿《生是真实的》[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77页。
②迟子建、阿成、张英《温情的力量——迟子建访谈录》[J],《作家》,1999第3期,第49页。
③迟子建《逝川·原始风景》[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235页。
④[美]科里斯·拉蒙特《人道主义哲学》[M],贾高建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0年版,第96页。
⑤迟子建《秧歌·东窗》[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13页。
⑥迟子建《50岁,开启一个作家的黄金时代》,《新京报》[N],2015年01月24日。
⑦施战军《独特而宽厚的人文伤怀》[J],《当代作家评论》2006年第4期,第52页。
国家社科规划青年项目“俄罗斯文化对近现代东北文学的影响研究”(批准号12CZW074)、黑龙江省社科研究专项项目“俄罗斯文化与现代东北文学”(批准号:11D017)]
——军旅写生作品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