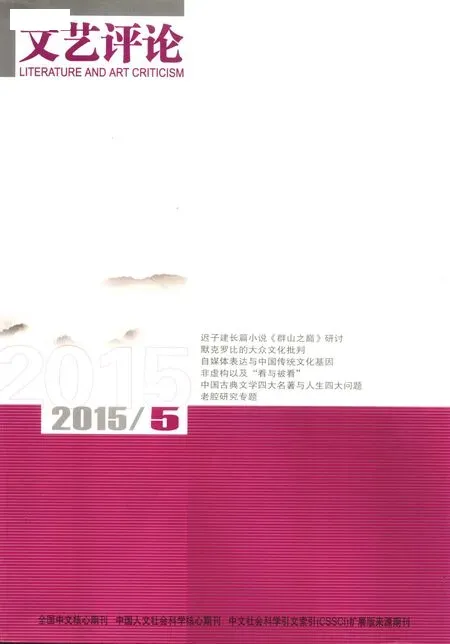古典美学的现代镀亮
——从《群山之巅》看迟子建长篇小说新的艺术追求
○欧阳澜 汪树东
古典美学的现代镀亮
——从《群山之巅》看迟子建长篇小说新的艺术追求
○欧阳澜 汪树东
《群山之巅》是迟子建推出的第八部长篇小说,出版后,反响甚巨;有人称其为呕心沥血、大气磅礴之作,认为它比《额尔古纳河右岸》更苍茫雄浑,比《白雪乌鸦》更跌宕精彩。在接受《新京报》记者专访时,迟子建曾说:“很多人对我说《群山之巅》是我最好的长篇,我没说什么。在我心里,《群山之巅》只是我50岁的一部沉甸甸的作品,蕴涵着我对社会和人生的一个阶段的思考。《群山之巅》不是对以往作品的总结,而是对未来作品的开启。50岁不是年龄上的黄金年华了,但它恰是写作的黄金年华,我希望自己刚刚开始这样的黄金时代。”①迟子建说得很好,《群山之巅》不是对她以往小说的总结而是对未来小说的开启。《群山之巅》聚焦大兴安岭边地小镇(在小说中化名为松山地区青山县龙盏镇),书写了时代大潮冲击下的乡土世界的凋零和蜕变,弥漫着中年人特有的沧桑和哀愁。如果从主题探索看,《群山之巅》无论是对边地民间小人物人性亮色的耐心打捞,还是对当前社会现实的锋锐批判,抑或是对乡村传统文化的哀婉回望,都依然延续着迟子建长篇小说的一贯主旨;但如果从艺术追求来看,《群山之巅》开启的屏风式结构、块茎式人物群像以及强化的意象叙事等,显示了迟子建长篇小说的艺术新质,而且是古典美学的现代镀亮。也许正是这些艺术新质预示了迟子建小说的可能向度。
一、屏风式结构的古典意趣
阅读《群山之巅》,笔者首先被其散发着独特的古典韵味的结构所吸引。全书共分十七章,每章含纳了某个民间小人物的若干人生故事,彼此相对独立又互相勾连,顺叙和倒叙花色相间,别出心裁地营构出一部花团锦簇的长篇小说。当记者问及迟子建在构思时为何想用这种方式铺排时,她说:“这本书的结构我确实是花了心思。对于一部描写当下又关联历史的作品,倒叙是比较合适的。因为整个故事内容非常丰富,要做足铺垫的话,二十万字是远远不够的。而我用倒叙的方式,就能很自然地把每个人物的历史和过往叙述出来,让人物在进行式当中,每个章节都有回溯,互相勾连,历史也带了出来,却又发生在当下,每个故事看似独立,但其实一环扣一环,没有前面故事的勾连,最后一章《土地祠》的故事你是看不懂的。我用倒叙的方式展开这个故事,能让历史呈现出它的自然状态。”②迟子建仅仅强调倒叙手法的合理运用,其实,该小说结构的最大特点决不是倒叙,而是一种屏风式结构的优雅展布。
如所周知,中国古代居室和庭院讲究移步换景、曲径通幽,屏风能够让平铺直叙的空间顿添律动与韵味。不论空间大小,都可通过精妙的分割与设计,让居所内处处成美景。一扇精致的屏风,在起到遮挡和间隔作用之同时,还给层次分明、雕梁画栋的古典院落营造出了令人流连的情趣,因为在文人墨客的眼里,屏风是有诗意的,它营造了一种似隔非隔、似断非断的意境。而且,屏风上还可布设文化意蕴各不相同的图案,和现实的景致构成多姿多彩的映衬,造成艺术世界和现实世界互增光辉的美丽。屏风自身的设计也别有韵味,每页屏风都可独立,又彼此相连,也可自由活动,每一转折就开辟出一个新的诗意空间。迟子建《群山之巅》采用的即为此类屏风结构。全书十七章,每一章就像一页屏风,十七章十七页屏风,构筑出一个边地民间意蕴深远的艺术世界。
这种屏风式结构特点鲜明。首先,每个故事就像每页屏风一样各自独立,又彼此勾连。第一章《斩马刀》主要是辛七杂和王秀满及辛欣来杀死养母王秀满的故事,第二章《制碑人》由辛欣来强奸了安雪儿,引出安雪儿、安平的故事,第三章《龙山之翼》再引出龙盏镇镇长唐汉成家包括唐汉成、陈美珍、唐眉等人的故事,第四章《两双手》再引出安平和李素贞的故事,第五章《白马月光》倒叙出安玉顺和孟青枝的故事……从整体上看,每一章都有较为独立的人生故事,但又始终围绕着龙盏镇辛家、安家、唐家各色人等展开。至于辛欣来杀人强奸后逃入森林直至最终被捕、被处决、肾被移植给亲生父亲陈金谷,给安雪儿留下儿子的经历,构成所有故事的一个联结引线。其次,每章的故事就像每页屏风一样,都处于同一个水平面上,没有高低上下主次之分。无论是辛开溜、安玉顺、绣娘孟青枝的故事,还是安平、李素贞、单四嫂、老魏、陈金谷的故事,抑或是安雪儿、安大营、辛欣来、林大花、唐眉的故事,都是边地民间小人物的悲喜人生故事,每个故事都说明着自身,没有中心故事和非中心故事的区别,也没有一个故事要为另外一个故事服务、解说的必要,而只是彼此互相引发、互相映照。再次,每个故事就像每页屏风一样彼此构成区隔,造成似隔非隔、似断非断的艺术效果。以辛开溜的故事为例,第一章《斩马刀》中仅仅提及他的籍贯和生活概貌,随后被其他故事隔断,直到第十一章《旧货节》中再展开他较为完整的人生故事,随后又被陈金谷、安平和李素贞的故事隔断,再到第十四章《毛边纸船坞》中延续了他和秋山爱子的故事,随后又被安平抓捕辛欣来的故事隔断,到了第十五章《黑珍珠》再次写他被斗羊挑伤,意外成为青山县第一个火葬的人。辛开溜的故事就这样若断若续,被其他故事隔断出青山隐隐水迢迢式的历史诗意来。
《群山之巅》的屏风式结构无疑淡化了线性的时间模式,突出并强化了空间的平面区隔和艺术组合。小说在读者头脑中形成了一幅清晰的松山地区青山县龙盏镇的空间地图。在此,龙盏镇北翼的辛家、单家、老魏、烟婆、王庆山等呈现了生活底层人民的辛酸和欢乐,南翼的安家、唐家、葛喜宝等展现了小镇头脸人物的悲喜,独自生活在小镇西坡的唐眉因赎罪遗世独立;再稍稍向外扩展,则为龙盏镇三村、五村的金素袖、李来庆、许大发等人的民间自在生活;而当地驻军野狐团团长、松山地区林市陈金谷等人则扩展了龙盏镇的外围,把龙盏镇边地民间的生活纳入时代大潮的波动之中。如果说柳青《创业史》、梁斌《红旗谱》等红色经典依托的是线性时间结构模式,必须在时间维度上建立终极意义的话,那么迟子建的《群山之巅》依托的则是地域开阔的屏风式结构,终极意义就蕴藏于空间的区隔、折叠和组合之中。
杨义曾说:“一篇叙事作品的结构,由于它以复杂的形态组合着多种叙事部分或叙事单元,因而它往往是这篇作品的最大的隐义之所在。它超越了具体的文字,而在文字所表述的叙事单元之间或叙事单元之外,蕴藏着作者对于世界、人生以及艺术的理解。在这种意义上说,结构是极有哲学意味的构成,甚至可以说,极有创造性的结构是隐含着深刻的哲学的。”③的确,迟子建《群山之巅》的屏风式结构卓然独立,蕴涵着她的世界观、人生观。迟子建最关注的就是乡土世界的温情和诗意人生,始终憧憬着前现代的乡土人性的单纯和质朴,质疑着现代文明对乡土温情的腐蚀。而现代文明就是建立在线性时间观基础上的文明,那种线性发展、纵深发展的结构模式,和迟子建要追求的乡土世界较为静态的人生明显有点隔膜;至于像《金瓶梅》《红楼梦》等采用以家族为中心辐射社会形态的网状结构,也和迟子建所关注的大兴安岭那里的边地小镇生活扞格难入;至于像意识流式的心理结构、结构主义式的花瓣结构、象征结构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结构模式也和迟子建要反映的生活难以融合。因此,《群山之巅》采用的屏风式结构恰到好处地展示了迟子建关于乡土世界的古典美学。
回顾迟子建长篇小说创作历程,可以看出《群山之巅》在结构模式上真正的创造性。《树下》(又名《茫茫前程》)是长篇小说处女作,起步阶段的迟子建试图采用线性结构模式来展示七斗的成长史,但由于作者缺乏开拓人物精神纵向深度的足够意愿,这种结构相对传统。《热鸟》的童话式写作,《晨钟响彻黄昏》的语言式写作,当属于迟子建的尝试性写作。《越过云层的晴朗》通过大黄狗视角按照时间线索来透视边地人生。《伪满洲国》采用编年式结构,《额尔古纳河右岸》也以一天的时间为结构要素。《白雪乌鸦》是迟子建有意采用屏风式结构的开始,但由于所叙述的故事是哈尔滨百年前的瘟疫灾难,叙事节奏和艺术结构存在冲突,难以展现最好的艺术效果。而《群山之巅》聚焦于边地民间的人生风景时,屏风式结构适逢其会,内容和形式融合无间。
二、块茎式人物群像的蔓延
理解了《群山之巅》的屏风式结构后,我们还可以发现它的人物群像塑造也是别出心裁。《群山之巅》全书只有二十万字,篇幅不算大,但有名有姓的人物就多达六十余人。把那些因情节需要甫一登场就退场的人物除去,尚有二十余人贯穿小说始终。这二十余人没有中心人物和非中心人物之分,每一个人物都围绕着自己的轴心旋转;除了辛欣来犯了杀人强奸罪、陈金谷犯有贪污罪外,也没有所谓的正面人物、反面人物之分;他们各自独立,又彼此联系,就像法国哲学家德勒兹所说的块茎一样四处蔓延。
在德勒兹看来,西方传统的理性主义思维可以比喻为“树状”模式,它强调的是统一性、等级体系、线性秩序和系统的胜利。从苏格拉底、柏拉图到笛卡尔、康德与黑格尔两千多年间的西方知识界始终在追求着某个理念中心,试图建构囊括一切的“树状”知识体系;与之相应,这种“树状”模式建构出来的社会往往是中心主义的、排斥异己的、统一的、静态封闭的等级体系。相对于“树状”思维模式的中心论、规范化和等级制而言,“块茎”思维模式往往呈现出非中心、无规则、多元化的特点,这无疑和真实世界复杂、多元、丰富多彩的特点更相符。“树状”思维实质上是一种“国家式思维”,“块茎”思维却是“游牧思维”。如果把德勒兹的洞见移用于小说人物领域,我们可以看到,那种强调中心人物和非中心人物、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二元对立的人物结构模式可以称为“树状”人物模式,而倡导反中心的、非二元对立的、多元共生的人物结构模式则可以称为“块茎”式人物模式。迟子建《群山之巅》塑造的人物群像就是块茎式人物群像。它要表现的就是迟子建对人生、世界的独特理解。在她看来,世界本来就只有普遍联系而没有所谓的中心,边地小人物就像块茎一样生机勃勃,呈现出民间的多元混杂的本真面貌。
《群山之巅》中的块茎式人物群像特点鲜明。首先,块茎式人物就其自身而言都是边地民间的小人物,都是自由自在的小人物。他们的生命往往缺乏像哈姆雷特、浮士德式的不断探索的精神深度,也不像贾宝玉、林黛玉那样能够领悟到生命的超越层次。作为民间小人物,他们就像土豆这种块茎植物一样深埋在地下,被世俗生活牢牢覆盖着,体验着凡俗人生的生死悲欢。他们的生命向度像块茎一样是横向的,而不是像树一样呈纵向的超越态势。在超越型人物看来,这种块茎式人物缺乏立体的精神深度和阔大的公民意识。但在块茎式人物看来,超越型人物却缺乏凡俗人生的丰满血肉。
其次,块茎式人物具有块茎式植物般的强大生命力。这些块茎式人物扎根于世俗民间,前现代的乡土社会赋予了他们较为明确而安稳的价值观、世界观、人生观,使得他们能够脚踏实地地生活。像辛开溜从小就饱经忧患,后来又被人误认为抗联逃兵,因为曾经娶了日本女人为妻就饱受汉奸之讥,即使儿子辛七杂也对他冷眼相看。但他坦然地接受命运,最后居然一度帮助孙子辛欣来逃避警察追捕,与其说是他是非不分,不如说他借此来证明自己作为抗联老兵的真实性。而像安雪儿被辛欣来强奸后,默默地承担命运,不怨天不尤人,都是块茎式人物的生命韧性的绝好明证。
再次,块茎式人物与其他人物之间少有冲突,具有典型的非中心化趋向。相对而言,“树状”思维塑造出来的纵向超越式人物,倾向于和其他人物进行非此即彼、非白即黑的冲突、对抗,由之彰显自己生命的方向和价值;但块茎式人物更倾向于围绕着自己生命的中心自在地生活,少有借助冲突、对抗来强化生命价值感、方向感的,不会让他人成为自己生命的中心,也不会让自己成为他人生命的中心。像辛开溜、辛七杂、金素袖、安雪儿、安平、李素贞、绣娘、老魏、单四嫂等民间人物均是如此。
《群山之巅》的块茎式人物群像的塑造无疑是古典审美和后现代主义风格的奇妙嫁接。《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中国古典小说都倾向于塑造块茎式人物群像,不过,受制于中国传统文化中根深蒂固的实用理性倾向,中心化、等级化、二元对立思维依然难以破除;真正较好地塑造出块茎式人物结构模式的是《儒林外史》,该小说里的人物就像块茎一样不断蔓延,构造出丰富复杂、多元共生的儒林景观。随着现代性的扩展,中国现代作家往往更被“树状”思维所捕获,达到顶点的是像《创业史》《红旗谱》等红色经典,中心化、等级制、二元对立思维登峰造极。而像贾平凹的《秦腔》《古炉》《带灯》等长篇小说则明显地再次复兴古典审美中的块茎式人物群像结构模式,日常生活中的小人物就像块茎一样烘托出多元共生的复杂社会景观。迟子建在《群山之巅》中借助块茎式人物结构模式无意中打通的就是后现代和古典之间的幽暗通道。
由于迟子建返回到中国古典审美中,她的块茎式人物群像基本上不像西方小说戏剧那样通过人物间的对抗、冲突来建构自身。迟子建笔下的块茎式人物都是边地民间的小人物,也缺乏现代人复杂疑难的多重心思,因此她在塑造人物时几乎少有心理描写,更不要说繁杂的心理分析了。排除了冲突对抗、心理分析,迟子建塑造块茎式人物最常用的手法就是古典式的对照和映衬。
中国传统文化最喜欢对照映衬原则,就像阴阳对照、阳刚与阴柔的映衬等;这无疑是从大自然受到的最深刻启发,像白天黑夜、春夏秋冬的时序对照,上下左右、东西南北的空间对照,高峰平原、江河湖海的地理对照,正邪忠奸、善恶美丑的人性对照等。《群山之巅》中的诸多人物就是在对照中眉目鲜明起来的。例如唐眉、林大花、李素贞都是犯下罪错的女人,唐眉出于一时糊涂给同寝室的大学同学下毒,结果只能终生默默赎罪,林大花半是自愿半是被迫出卖了初夜给与师长,结果痛恨自己无脸见人,而李素贞因为和情人安平的暴风雪夜私会无意中导致瘫痪丈夫死亡,结果请求法院判处她有罪。三人对照,罪错轻重,反应大小,见证了不同的个性。而安平和李素贞的爱情,辛七杂和金素袖的爱情,都是饱经忧患的中年人之间的爱情,相对而言,前者亲密中夹杂着内疚,后者却诗意明媚。
此外,还需注意的是块茎式人物结构模式无限蔓延的特性。德勒兹曾说:“一个块茎无始无终;它总是在中间,在事物之间,是间存在者,间奏曲。树是亲缘关系,但块茎是联盟,独一无二的联盟。树强烈推行动词‘to be’,但块茎的构架是连接:‘and……and……and……’这种连接携带着足够的力动摇和根除动词‘to be’。你去哪里?你从哪儿来?你朝哪儿走?这些都是毫无意义的问题。”④的确,表现于《群山之巅》中,无论是其块茎式的人物,还是由人物引起的情节,都具有无限链接、无始无终的特性。整部小说不但没有中心人物和非中心人物之分,而且就情节而言,也根本没有所谓的开端、发展、高潮、结尾,而是呈现出一种无始无终、循环往复的态势。例如小说从辛七杂用凸透镜引太阳火点烟斗开篇,到安雪儿去土地祠给土地献祭时再次被傻子单夏强搂住结束,全是生活流永无已时的芊芊蔓蔓,根本没有那种“树状”思维模式里所构想的矛盾的开端和解决。
三、意象叙事的明丽雅致
如果说屏风式结构和块茎式人物群像展示了《群山之巅》的古典美流风遗韵的话,意象叙事更显示了迟子建对古典美的倾心。当然,前两者是在《群山之巅》中才得到最完美的展示,至于后者一直是迟子建小说的耀眼亮色。
在杨义看来,“叙事作品之有意象,犹如地脉之有矿藏,一种蕴藏着丰富的文化密码之矿藏”⑤。他认为意象叙事乃是中国叙事文学有别于他国文学的神采之所在,关键在于汉语语法的独特性、中国式“天人合一”的宇宙观、长期处于文学正宗地位的中国诗歌向叙事文体的渗透、中国历史源远流长等因素。意象作为叙事作品的“文眼”,往往也具有多重功能,例如凝聚意义、凝聚精神,疏通行文脉络、贯串叙事结构,保存审美、强化作品之耐读性,等等,不一而足。当然,在一部好的叙事作品中,意象叙事的诸种功能并不是单独呈现的,而是聚合一处的,迟子建的《群山之巅》中的意象叙事就是如此。
整体看来,《群山之巅》展示的就是前现代式的乡土世界。虽然曾经孕育过温情和诗意,孕育过鲜活生动的凡俗人生,但在现代化浪潮冲击下,它已经不可避免地摇摇晃晃,随时有崩溃之虞了,因此作者能够表达的乃是深情回望乡土世界时无端的沧桑情怀和美丽哀愁。为此,迟子建选择的许多意象就别有韵味、别有深意。例如开篇就是太阳火意象。乡村屠夫辛七杂居然常常用凸透镜引燃太阳火点烟斗,“他说用太阳火烧的烟斗,有股子不寻常的芳香,值得等待”⑥。如所周知,现代文明崇尚便利、效率,给烟斗点火自然是火柴或打火机方便实用,但辛七杂偏偏要舍近求远,用太阳火点烟,其中抗拒现代性、固守大自然和乡土文化传统的精神意向就颇为分明了,这也把整部小说的核心主旨以一个独特意象点染出来了。因此迟子建曾说:“辛七杂一出场,这部小说就活了,我笔下孕育的人物,自然而然地相继登场。”⑦其实,辛七杂出场之所以如此重要,关键就在于是他引出了太阳火意象,从而点燃了《群山之巅》的芳香。
白马月光的意象和太阳火意象一样,也具有非比寻常的凝聚意义、凝聚精神的功能。《群山之巅》中,迟子建极为关注前现代乡土世界中的民间手工艺人,例如屠夫辛七杂、王铁匠、李木匠、做豆腐的老魏、做烧饼的单四嫂、制碑人安雪儿、绣娘孟青枝等人,均为龙盏镇最为明媚鲜活的民间人物。以绣娘为例,她是鄂伦春人,年轻时在文工团跳舞,后来嫁给英雄模范安玉顺,生子后她就在家给人绣婚服,成为绣娘。迟子建写她骑白马,“绣娘如今骑乘的马,是匹银鬃银尾的白马。它奔跑起来,就像一道闪电划过大地。绣娘喜欢它,也是因为人到老年,苍凉四起,这世上的黑暗渐入心底,她希望白马那月光似的尾巴,能做笤帚,将黑暗一扫而空”⑧。白马月光意象无疑隐喻着乡土世界的诗意生存。不过,最后,白马死了,绣娘也死了,按照鄂伦春风俗被风葬在森林中,“他们在午夜时分找到了白马的骨架,它刚好在四棵两两相对的白桦树间,这正是绣娘喜欢的树,像蜡烛一样明亮的树。他们在天明前,在树间搭就一张床,铺上松枝,把绣娘抬上去。白马的骨架像一堆干柴,在绣娘身下,由月光点燃,寂静地燃烧着;绣娘在白马上,好像仍在驾驭着它,在森林河谷中穿行”⑨。就连死亡,也被迟子建用纯美的意象点染得如此富有诗意,看来乡土世界的崩溃厄运无法避免,它只能在诗意语言中重建象征的存在。
《群山之巅》中还有两个身体意象极为醒目,即“手”和“肾”,对于揭示全书的核心主旨也具有重要作用。第四章名为《两双手》,写的是法警安平和理容师李素贞的两双手,就相当别致。手艺人在乡土社会中占据着重要位置,像辛七杂、绣娘等人都是手艺人,其实安平和李素贞也是手艺人;但因为他们从事的职业和死亡相关,就受到乡土社会其他人的排斥,这无疑显示了乡土社会的狭隘和俗陋。不过,虽然如此,安平和李素贞的两双手依然承担着乡土社会相应的职责,编织出乡土社会的温情故事,并摩擦出爱情的美丽火花。手的意象后来在第十三章《暴风雪》中再度出现,那是唐眉的手,她因为背负着赎罪的十字架,难以忍受,想和安平生下一个安雪儿一样的精灵,却被安平拒绝了,“唐眉手臂修长,她从背后环抱安平,手刚好搭在他胸前。安平觉得呼吸困难,那双手像强加于他的冰凉的手铐,令他惊悚。他用力扳开她手的时候,感觉到那双手是那么的干枯冰冷,虽说她的面容还是青春的”⑩。唐眉因为给同寝室的大学同学投毒,展现了对乡土温情的彻底背离,即使她想赎罪,也难以得到他人的接受。至于“肾”的意象,对于揭示当今社会的真实状况更有巨大的震撼力。第十二章《肾源》写身为松山地区副书记、组织部长陈金谷患了肾衰竭,就想花高价从穷人那里买肾;买肾不成,就想夺取已经沦为杀人犯的亲生儿子辛欣来的肾。一个“肾”意象,把当今中国特权体制对穷人掠夺的触目惊心的画面揭示得淋漓尽致,也展示前现代乡土社会面临的根本威胁。
杨义曾说:“意象作为‘文眼’,它具有疏通行文脉络、贯串叙事结构的功能。叙事作品往往是以情节或非情节的跳跃性思路,作为行文的线索的。在情节与情节的转换之间,设置一个意象,可以使转换不流于生硬简陋,而在从容转换中蕴涵着审美意味。在情节与非情节的跳跃之间,如果也能设计一个意象,跳跃就会变得更加潇洒,甚至产生一点蒙太奇的效果。而且由于同一意象在纷纭复杂的情节或非情节之中,别具匠心地重复出现,就可能造成有若诗歌中同一语句、意象反复出现的回环复沓的旋律波动。意象的重复出现也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重复中的反重复,在物象的重现之中包含着意义的增添和递进,这就有助于形成行文脉络的层次感和节奏感。”⑪就《群山之巅》而言,“白蛇”、“毛边纸船坞”都是具有疏通行文脉络、贯串叙事结构功能的意象。开篇第一章《斩马刀》就提及辛七杂请王铁匠打造了斩马刀,他没有用来杀马,只是到森林里去试过它的锋刃;后来听说山中有白蛇,王秀满就说白蛇是得道成仙的,不让辛七杂拿斩马刀出去了,怕万一伤及它,神灵降罪,家里就会遭殃。但谁知辛欣来却用斩马刀杀死了养母王秀满。最后,在花老爷洞里被捕时,辛欣来居然把白蛇吃掉了。对于王秀满等人而言,白蛇是可以得道成仙的;但对于辛欣来而言,白蛇是可以吃的;“白蛇”意象就将两代人的天壤之别展示了出来,并写出了乡土世界的危机。至于“毛边纸船坞”意象对于疏通叙事脉络更有意义。“秋山爱子的每张画,都有船的影子。船有大有小,有多有少,但都是靠在岸边的,每条船上都挤满了人。男女老幼,无论背着包袱的,扛着锹镐的,手持稻穗的,举着灯盏的,还是牵着马的,领着狗的,都是满面焦灼,看得出她心底浓浓的归乡情。她用毛边纸打造的这座船坞,伴她度过了无数寂寞昏暗的日子。”⑫借助“毛边纸船坞”意象,作者写出了秋山爱子在异国他乡的飘零流离、凄苦感伤,也写出了辛开溜对秋山爱子的一往情深、身世坎坷。后来辛开溜把“毛边纸船坞”送给了辛欣来和安雪儿的儿子,更是写出乡土社会代际生命延续的情感归属意义。
对于《群山之巅》主旨的揭示更不可忽视“土地祠”意象。乡土中国向来崇拜土地公公土地婆婆,筑祠祭祀,天经地义。然而,面临着席卷宇内的现代化浪潮,乡土社会难以抵挡,土地公公土地婆婆自身都是泥菩萨过河,又怎能守护乡土大地呢。不过,作为龙盏镇镇长的唐汉成却寄希望于渺茫的土地,“唐汉成不怕失去权力,最怕失去青山绿水。他在龙山顶上,在那两块巨石间,建了一座土地祠,祈求土地老护佑龙盏镇,不要沦为矿区”⑬。这实在写出了前现代乡土社会的艰难境遇。更具有反讽意味的是,当安雪儿得知辛欣来还有一个肾活着就去拜祭土地时,她居然在土地祠里再次有可能遭遇傻子单夏的暴力侵犯。就连作者都不由得惊呼:“一世界的鹅毛大雪,谁又能听见谁的呼唤!”⑭乡土社会的精灵沦落人间,品尝着悲欢喜乐,但又怎能一再地遭受伤害呢?因此迟子建如此动情地写到她的感想:“写完《群山之巅》,我没有如释重负之感,而是愁肠百结,仍想倾诉。这种倾诉似乎不是针对作品中的某个人物,而是因着某种风景,比如滔天的大雪,不离不弃的日月,亘古的河流和山峦。但或许也不是因着风景,而是因着一种莫名的虚空和彻骨的悲凉!所以写到结尾那句:‘一世界的鹅毛大雪,谁又能听见谁的呼唤’,我的心是颤抖的。”⑮“莫名的虚空和彻骨的悲凉”,实在起因于乡土社会在现代化浪潮的悲剧性处境,前现代乡土社会的温情和诗意终究无法支撑起坚实牢靠的现代人生啊。
四、结语
当我们如此详尽地阐释了《群山之巅》的屏风式结构、块茎式人物群像、意象叙事的独特性之后,我们就可以清晰地看出《群山之巅》中显示出来的迟子建长篇小说新的艺术追求了。迟子建尽可能地规避了现代性的粗疏浮躁,复活了中国古典小说诗学的美学遗韵,接通了前现代和后现代的艺术电极,给她倾心的乡土世界的温情和诗意找到量体裁衣般的形式和结构,从而创造出不同凡响的美学效果。然而,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迟子建过于眷注的乡土社会的温情和诗意终究会在现代化浪潮的冲击下沦为神话般的存在,当现实社会的狰狞世相、现代人性的深渊处境头角峥嵘地展露出来时,所有古典美的雍容雅致都难以延续,那样一来,就必须吁请、谋划新的美学因素,就必须企望比乡土世界的温情和诗意更充实、更真实、更有力的精神因素了。
(作者单位:湖北第二师范学院教育学院武汉大学文学院)
①[美]莱昂内尔·特里林《知性乃道德职责》[M],严志军、张沫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
②方守金、迟子建《自然化育文学精灵——迟子建访谈录》[J],《文艺评论》,2001年第3期,第80页。
③④⑤迟子建《群山之巅》[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第30页,第22页,第14页。
⑥[意]吉奥乔·阿甘本《何为同时代?》[Z],王立秋译,见: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125063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