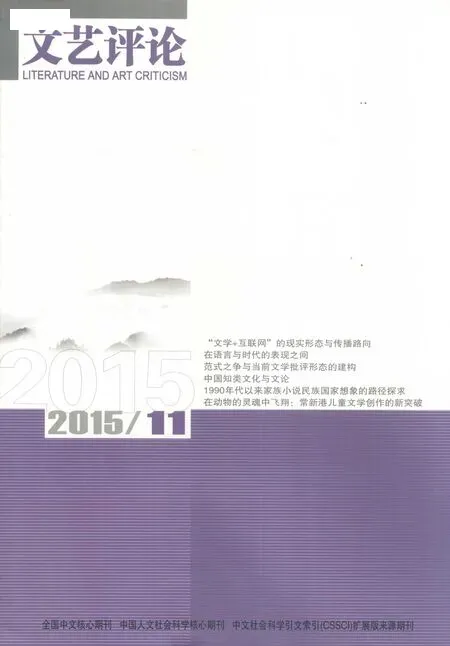现代性与西部现代性程度
○牛学智
在以前讨论西部文学批评的批评的许多文章中,我虽然未直接使用现代性这一词语,但都或多或少是以现代性为价值尺度的。一方面表明之所以是问题,是因为现代性使它们成为了问题;另一方面是为了强调,在西部,现代性实际上并未得到完全重视,致使到了城市化纵深阶段的今天,物质现代化虽然并不怎么落后了,但现代性这个价值结果却始终很不自觉。这样一个情况,无论人文社科知识分子的整体论述水平、文学叙述程度,还是大众文化、一般群众的集体无意识,实际上都处在与现代化错位的境地。这个意义来说,之于西部,现代性并不是过时了,而是展开得根本不够、不深入。这里,有一种颇为流行的观点必须有所清理,他们几乎在完全忽视具体背景和作者的批判针对性的情况下,仿佛是为着“前车之鉴”考虑,错误地转译英国哲学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或齐格蒙·鲍曼《现代性与大屠杀》等一类书中的“反意”,好像觉得中国正该“防微杜渐”,以免重蹈西方国家的“现代性后果”。一个常识告诉我们,中国现代化程度远没有西方国家完善,但中国的社会问题、经济问题乃至人文精神问题却为什么比西方国家更为严重?显而易见,本质上讲,无非是盲目的发展主义、科技主义,甚至把由此而形成的经济主义价值观当做唯一可行的实用的追求所致,这难道不是格外偏重物质现代化而漠视精神方向的现代性价值愿景造成的吗?这种普遍性情况,在中国任何地区都不同程度存在,然而在中国西部尤甚。正因为经济上的相对欠发达,企图来个大跃进式的补偿,这是其一;其二是怕产生投鼠忌器后果,反其道而行之,彻底退回到宗法文化的老路去,于是导致物质上疯狂攫取与价值观念完全主张关系学之间的严重错位,人本身的不完善,意味着现代社会机制的建构遥遥无期。这正是我们认为西部更有理由引进现代性价值机制的原因。当然,并不是说既有的西部文学研究中没有现代性视野,而是说20世纪90年代的那种研究突然中断了,转向了不很适应当前现实问题的路子。另外,20世纪90年代现代性的那种介入方式,不见得有效于经济社会发展纵深阶段的今天语境,故有必要重新梳理一下现代性在中国的实际状况。
赵一凡、张中载和李德恩三人主编的《西方文论关键词》,于2006年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南帆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批评99个词》,于2003年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这两本书大概是目前为较新较全的词条书籍。前者收集了“启蒙现代性”“现代性”和“现代主义”,后者仅收集了“现代主义”和“现代性”。
对照这两本书中的“现代性”词条,可能会得出这样一些初步的结论。
第一,现在学界比较通行的称谓,比如“社会现代性”“哲学现代性”和“文艺现代性”(或“审美代性”),均为西方哲学思想家或理论家所创造,它们产生于西方现代社会、西方现代文化和西方现代文学,是少数敏感的知识分子首先意识到了中世纪西方教会社会、政教合一文化和教会文学对人的漠视、对人的个体性与主体性的禁锢而首先发起的一种对抗权威、僵化和霸权的学说思潮,根本关怀在于平反人、解放人。即是说其共同的理论目的主要是反抗日益强大的资本主义及其话语霸权,之所以说是少数敏感知识分子的发现,是因为在整个思想运动过程中,一边是西方现代社会、西方现代文化和西方现代文学的推进和兴起,另一边仍然有多种学派或思想学说存在,也都有其基础支持。只不过现代性在慢慢获得多数人认可的时候,西方社会、哲学文化和文学艺术,也就开始摆脱现代性所反抗的那种局面,一步步走向完善和成熟。到了一定阶段,比如尼采的出现,阿多诺和霍克海默的出现,现代性可能又得遭遇“辩证”或“解构”,这一否定之否定过程,其实正是现代性本身的品质,它不是一个标准,而只是一种理想的设计或者是某种福柯所说的精神气质。有了这个总目标,三种现代性才会各司其职,分头并进,构成一个新的意识形态网络,人的问题才被提到了历史的新高度。具体说,文艺现代性通过语言革命,来走出叙事困境:1.颠覆传统叙事,现代派作家鼓吹杂语对话、含混多义,反对万能叙事者作统一明确的述说。2.题材上追求新奇、怪异、反常和私人化,以此来攻击资本主义生活秩序。3.结构上支离破碎,用以摆脱现实主义的有机整体观。哲学现代性,通过与传统的断裂,企图告别中世纪愚昧,主体性、理性、革命、解放、进步与发展等,便成了其关键词,正因哲学现代性话语中的“启蒙辩证法”的存在,到了尼采那里,竟然把后现代性作为了突破现代性的理性外壳的“反叛美学”,至此,哲学现代性又开始了它的形而上学循环——从神话学汲取养料。社会现代性则以吉登斯为最著名,他通过“时空分割重组”“金钱与专家合成变革新机制”和“知识反思与社会再造”①来应对现代社会的“断裂性与两重性”,从而达到引导社会走出危机并进行重新建构的目的。
第二,在西方现代性话语的推进下,中国的现代性研究时间也并不短,但创造性的确乏善可陈。这说明,中国学者虽然一直进行着力所能及的转化处理,只不过,这种转化和处理,从微观角度分析,的确很少独创性,也就几乎谈不上与西方现代性话语的平等对话。这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中国很少有哲学乃至社会学的现代性论述。中国现代社会一直到近三十多年改革开放所造成的社会剧变,除了“社会主义”这样的主导性话语,似乎还少有吻合其性质的哲学的和社会学的论述,那么,附丽其上的现代性也就不会彻底。南帆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批评99个词》一书,其“现代性”词条虽然重点以文学批评为中心展开,但从中也不难看出中国现代性不自主的特点。据刘小新梳理,在中国文献中,“现代性”一词最早见于1918年周作人的译文《陀思妥夫斯奇之小说》,但正式进入中国文学批评领域,则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从1992年所谓的“后新时期文学”到90年代末的“反现代性的现代性”或“文学现代性的悖论”止,中国学者对现代性的讨论,实际上一直是西方现代性迟到的转译。1.“现代性的终结论”,显然是对“西方后现代主义解构宏大叙事观点的搬用”。2.“现代性未完成说”中的“未完成论”与“终结论”之争,“酷似哈贝马斯与后现代主义之争的中国版”。3.刘小枫的“关于现代性事件的知识学”的观点,实际上是对齐美尔和舍勒现代性论述的借用。4.汪晖、周宪等人现代性的分裂与矛盾张力说,即资本主义政治经济过程的现代性概念与现代主义前卫的美学的现代性概念的尖锐对立、“文化的现代性与启蒙的现代性”之间的对抗或“审美现代性与启蒙现代性”的分裂与对抗,等等观点可能来自于“韦伯、卡林内斯库、鲍曼等人的现代性论述”②。
由此可见,要彻底弄清中国现代性的进度问题,一定程度等于对西方现代性的转化和澄清。而转化和澄清,不是被殖民和他者化,是身在中国语境的感受、理解、阐释乃至使用。用王富仁的话说,之所以恰在这个时候一部分中国人最先敏感到西方话语的有用,并且因为“被感受、被理解、被阐释和被使用”推而广之,乃至于被大多数人所接受,是因为被采纳的西方话语正好适合于反对已经成为了权威的霸权话语。他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例,令人信服地说明了这一点。话语霸权是一把双刃剑,它不但能够扼杀反对这种话语的话语,而且能够扼杀自己。“当宋明理学家把儒家文化的霸权地位在中国社会上牢固地树立起来,当不但孔子的话语成了人们不能质疑的权威话语,而且他们对儒学典籍的阐释也成了不能质疑的权威阐释的时候,儒家的文化就再也进入不到人与人思想和情感的交流活动之中去了,它的霸权化使发话者不能传达自己独立的思想和感情,只能成为儒家话语的传声筒,而受话者在儒家话语面前则只能表示赞佩、接受和顺从,也不能表达自己独立的见解或感受,它就失去了作为传达思想和感情的话语的本质职能”。正因为儒家文化是作为维护封建王朝的政治统治工具而获得话语霸权的,那么,那时候像“科学”“民主”“自由”“个性解放”一类西方话语,实际上是中国文化圈内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对禁锢着中国思想发展的传统霸权话语的反叛,是在中国这个本土的思想解放运动中被感受、被理解、被阐释和被使用的,在这个过程中,这些“‘西方话语’实际已经成为‘中国话语’”,当然,更是“中国话语”对中国传统霸权话语的批判。“它的结果是中国文化的革新和发展,而不是中国文化的衰弱和消亡”③。
任何出身并不高贵的话语,一旦成为霸权话语,即使是其生成过程无可置疑,但结果必然是被主流意识形态甚至统治者征用,定为一尊的话语。王富仁对儒家文化的论述既证明了这一点,同时也扫清了截至目前横亘在中国学人面前的一个学术障碍——总觉得一提西方文化,就意味着背叛;一提西方话语,就意味着自我他者化或者被殖民。五四新文化运动被一些人说成是对中国本土文化的毁坏,近年来国人又力倡中国传统文化并掀起“国学热”,其思维是一致的。久而久之,所谓中国现代性,其实不是现代性,是不动原有基础的现代化描述。按照现代性的理论期许,这种旨在物质结果的现代化描述,不可能触碰作为人的目的现代性,也就只不过是对现代性的敷衍罢了。为了强调问题,王富仁特别指出,“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是两个独立的概念,不存在谁化谁的问题,也不存在谁吞没谁的问题,能进入对方并且经过重新组合而生成新的话语、生成新的意义的,永远是“话语”而非“文化”。也就是说,“能够进入到‘中国文化’内部的永远是‘西方话语’而不是‘西方文化’。‘西方文化’吞不下‘中国文化’,‘中国文化’也吞不下‘西方文化’,但‘中国话语’(像‘忠’‘孝’‘节’‘义’,像‘文化大革命’)和‘西方话语’(像‘科学’‘民主’,像‘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是可以在不同的文化圈之间穿行的,是可以进入到其他民族的语言中并成为这种语言的一种外来的话语形式的”④。“西方话语”进入到中国文化内部必须与中国固有的各种话语实现重组,并在中国的话语系统中取得自己相对独立的意义。正是这个新的意义,才成为激活固有文化,生成新文化的精神核心。
另外,撇开现代性的术语与概念,还有至少两个流行观点需做进一步澄清。其一是“现代性”的时间观念问题。“现代”或“当代”作为一个时间观念,虽然是中国现代(或当代)社会、中国现代(或当代)文化、中国现代(或当代)文学的第一推动力,但却不是唯一推动力。在这里,还有一个人的现实需要问题。即是说,中国现代(或当代)社会、中国现代(或当代)文化、中国现代(或当代)文学是以“现代性”的生成与发展为标志的,但却不是中国现代(或当代)社会、中国现代(或当代)文化、中国现代(或当代)文学的普遍性质与特征,古典性、经典性、传统性仍然是中国现代(或当代)社会、中国现代(或当代)文化、中国现代(或当代)文学存在和发展的主要基础和土壤,其中已经加入了“现代性”的某些成分,但“现代性”的成分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仍将是次要的、非主流的。所以,“现代性”是一种价值,但却不是中国现代(或当代)所有事物、所有文化现象的价值,亦即它不是惟一的价值标准,这才是它需要我们“瞻望与追求”的充分理由。⑤以此观之,“反现代性”是以“现代性”追求的出现为前提的,是与某些具体的“现代性”追求不同的“现代性”追求,它因此也就比古典性、经典性和传统性更了解“现代性”。同为“批判”,它也就与那种只针对“人”的批判,与那种没有实际社会和历史内容,只是一种个人姿态的批判有了根本性区别,类似马克思和鲁迅都曾说过的,是没有任何私敌的批判。“反现代性”是如此,“现代性”也是如此。
其二是“现代性”的价值观问题。在“公平”“正义”基础上追求个体的“自由”与“平等”,是“现代性”价值中的一个由衷许诺,这里就产生了一个歧见。首要的分歧是对“危机”的理解上,高瑞泉引入美国哲学思想家亚历克斯·卡里尼克斯《平等》一书中的“机会平等”与“实质平等”指出,在当前中国,一些观点认为似乎平等注定是自由的敌人,甚至是民主的敌人,现代民主政治不再是平民政治而应该是精英政治,原因是“平等”意味着弱者将强者拉低到与他们同等的水平——具体的措施即主张农村的孩子既然上不起学,就应该像他们的父辈一样好好务农,不应该上学;城市“80后”男青年买不起房子、找不起城市对象,不如等到有了钱再买房子、再找对象也不迟。他们也当然谈平等,但却过分强调机会平等和结果平等的对立;换言之,他们只谈机会平等或形式平等,反对认真看待实质平等的要求。他们完全无视当前中国社会贫富差距所带来的危险,无视某些人在形式平等的口号下制造出严重的实质不平等,继续大批平均主义,凡是认真思考如何实现经济平等的思想都被冠之以平均主义的帽子。“实际上,这种视平等和自由为对立的两极的看法,正如亚历克斯·卡里尼克斯批评的那样,是‘范畴性错误’,因为‘自由属于平等之可能的运用领域而平等则属于自由之分配的可能的模式之一’。过分强调平等对于自由的消极意义与平均主义一样是不正确的。实质上,平等某种程度上是自由——即过我们所希望过的生活——之必要条件。而机会平等常常是含混不清的概念,在它的含混使用中很容易掩盖实质上的不平等。”⑥参照孙立平、黄宗智等社会学家最新的研究成果,所谓“断裂”“失衡”和“博弈”及其所产生的后果“利益集团”的形成、“阶层固化”,所谓“政、商、学铁三角”(地方官员、私营企业和自由主义经济学)⑦等等,一再表明,当前中国一些人的所谓“个人独立”和“自由”,基本上是企业家和市民文化所滋养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自由。
有了这个必要的心理准备,现代性西方话语本来就应该是发现我们的问题的当然参照。无论作为标准,还是作为方法论,抑或作为视野,都应该首先是基于中国当代西部社会、中国当代西部文化和中国当代西部文学的感受、理解、阐释和使用。它所发现的问题,理所当然是我们需要正视并解决的,通过它的折射并反过来再把它作为我们的镜子所映照出来的不足或弊端,也理应是我们力争矫正和避免的。这样的一种正常心态、正常感觉,才有利于提高自己,方可避免因过度自恋而走向文化自大,方可警惕因过于自卑而堕入地方主义或民粹主义的自我封闭。这么说,我意在强调,在观照中国西部文学的现代性程度时,西方思想理论家的相关研究与中国学者的跟进转化成果,都将是有力支持。只有在现有成果水平之上,对中国当代西部文学现代性体验的判断,才会尽可能免于个人好恶的狭隘估量。
大致说来,中国当代西部文学的现代性体验及其进展水平,至少有下列几种表现:
第一,“文化融合”或“大文化圈说”,冲淡了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这不是说一定要坚持文明必然冲突的论调,而是说文明冲突论首先是一种方法论。西部多民族的现实反映到西部当代文学中,其实是对文明冲突论中文化差异性的抹平。从欧亚大陆一直划到中国西部的几大文化圈,这意味着西部实际的文化表征被取消了,而不是被突出了。当“融合”“打通”等文化意识渗透到文学叙述中来的时候,西部文学不管讲述多长的历史,也不管讲述多新奇的底层故事,人物的活动时间轴一般不会超出主流政治经济学话语的范围。换言之,人物必须在规定的文化圈内进行意识活动和情感发展,如此,“去政治化”甚至“去身份”,把人物变成超社会、超阶层、超现实的一分子,唯求心性的安宁、人性的良善,构成了西部文学一般性文化属性。而这个属性,往往回旋在既有民间宗教信仰文化和民间民俗宗法文化的底部,人其实并不是目的,物质或者更进一步说人的文化符号占据了首要位置。这样一来,审美现代性所一直强调的用美学对抗权威霸权的终极目的,在西部文学及其批评中则蜕化成了西部现实支持如此审美的佐证,“对抗”变成了“和解”,“批判”变成了“打通”,“反讽”变成了“赞美”,一句话,貌似自然主义的叙述,实则变异成了新保守主义或审美无政府主义。这个意思正是哈贝马斯从哲学层面发现的“告别现代性”的企图。打着现代性的旗号,而试图再次反抗现代性。⑧即是说它们并不是在反抗传统的基础上的深一层努力,而是绕了一大圈,以文化的名义接通了悠久的传统,并形成了与悠久的传统之间的同谋关系。享有盛名的长篇小说《白鹿原》(陈忠实)中代表儒家文化的朱先生身上似乎具有着无限文化能量,就很能说明问题。问题还远不止这部小说本身,因为它的“茅奖”光环,再加上电影的推波助澜和无数文学批评家给予的过高赞誉,“能流传下去”“新时期以来最厚重的小说之一”等等,足以促成其价值观的更广泛流布,“蝴蝶效应”不难形成。本来人控制政制的时代,被视为现代性的开端,⑨但在这里,指定的文化——某种政制的形式,反过来控制了人的意志。也可以说,不是现代性的现代性,反而成了西部现代性的代表。
第二,西部快速城市化,产生了势力可观的准市民阶层,准市民文化趣味又导致了一批西部“城市文学”。在西部城市文学中,城市空间中的瑜伽馆、棋牌室、健身房、洗浴中心等,瞬间替代了现实主义文学时代凋敝的乡村、狭小阴暗的发廊、露天的工棚和城乡结合部条件恶劣的租住屋。紧接着,类似19世纪欧洲上流社会阔太太的沙龙文化出现了,她们关心的是身体美学、心态美学和人际厚黑学。在她们的生活天平上,微信点赞刷屏人数的某次骤减,可能导致大呼小叫乃至郁郁寡欢;某块赘肉的长期滞留,或许构成人生质量的威胁。然而,在这些有闲有钱人群的眼皮子底下,也许就是成堆的巨额房贷按揭者、昂贵医疗费用的筹集者和为了让孩子上个差不多的学校而奔走求人者。面对时空错置和命运错位,我们读到最多的西部文学,显然已是经过城市化及想象中的城市文化粗糙组装过的,它们乐意处理一桩桩个体心灵遭遇的细节,也更愿意观照一帧帧充满励志色彩的于连式人物(巴尔扎克《红与黑》)的奋斗史,或者宁愿续写中老年孙少安、孙少平(路遥《平凡的世界》)的幸福故事,并且在“人性”的平衡度上撰写中产阶级现代性。按照卡林内斯库的界定,这种现代性是导致先锋派产生的现代性,自其浪漫派的开端即倾向于激进的反资产阶级态度。“它厌恶中产阶级的价值标准,并通过极其多样的手段来表达这种厌恶,从反叛、无政府、天启主义直到自我流放。因此,较之它的那些积极抱负(它们往往各不相同),更能表明文化现代性的是它对资产阶级现代性的公开拒斥,以及它强烈的否定激情。”⑩具体到当前中国西部的文学叙述,与其说是批判激情的退却,毋宁说是自觉的中产阶级化,批判的现代性思想,转而成了为其城市赋形的“媚俗艺术”。《现代性的五副面孔》中,卡林内斯库之所以把媚俗艺术视为现代性面孔之一,就是因为现代性在反传统意义上的“现时性、实验、庞德‘使之新’”,与媚俗艺术对时尚的依赖和迅速过时使得它成为可消费“艺术”的主要形式,具有本质的一致性。所以他说,媚俗艺术和经济发展之间的联系实际上是如此之紧密,以至于可以把媚俗艺术在“‘第二’或‘第三’世界的出现看成‘现代化’的准确无误的标志”⑪。无独有偶,无论经济指数,还是文化趣味,中国当代西部社会和中国当代西部文化此时正在生产这样的现代性。
第三,第一世界学术圈之内的站在第三世界知识分子文化立场上的声音,构成了中国西部文学自我意识的强有力支持。比如出生于耶路撒冷的美国学者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甫一出版,首先在中国知识分子这里得到了广泛认同。该著提出的“后殖民”“他者化”等理论,尤其深受中国西部伊斯兰文化圈作家的青睐,其渗透结果是,西部文学抹掉了《东方学》的反西方中心主义思想背景,在政治经济边缘化的语境中,对“殖民”“他者化”产生了深度认同,以至于把固守前现代文化模式当做去殖民化、去他者化的有效途径,文学叙事于是被囿限于具体的地方知识、民族风俗和生活习惯的记录上、呈现上——这绝不是一般意义的自然主义文学,是经过现代性洗礼之后的“现代原始主义”⑫。张承志20世纪90年代的写作不但具有代表性,而且还带有一定的模范性。以此审视,后来以局外人的眼光写新疆的小说家红柯和诗人沈苇、被誉为20世纪“最后一个乡村哲学家”的散文家刘亮程和以伊斯兰宗教文化信仰者身份给人物以“隐忍”“安详”“内省”的小说家石舒清等等,更高一层面看,仿佛都很注重特殊的自我生活方式,并以此来对抗现代化带来的自我迷失和价值错乱,其实不然,他们的深层意识里脱不了萨义德理论的影响。就是说,在断裂性和双重性的现代社会,自我标榜反而不是在重新发现自己,也不利于“新的认同感”的形成。吉登斯把“时空分离”“抽离化机制”“制度反思”看作是干预普遍性“危机”的三个方法论,原因就在这里。在他看来,“时空分离”并不意味着从此以后它们成为人类社会组织的相互异己的方面,恰恰相反,“它为不同场合协调社会活动提供了时空重组的坚实基础”;“抽离化机制”包括符号标志(货币)和专家系统两方面,在普遍存在信任危机的现代社会,知识信任支撑着我们赖以对自我行动加以定向的一大堆日常决策,“更为通常地,它是作为这些决策基础的心智上的一般化态度,植根于信任和人格发展之间的纽带之中”。反过来说,如果格外标识自我特殊性,按照吉登斯关于前现代与现代性的阐释,那属于前现代特征。因为前现代的显著特点是行为处事的确定性,这一点正为自我内修建立了机制。为了避免前两者的绝对化,吉登斯提出了“制度反思”,旨在反复进行阶段性修正多数社会活动以及人与自然的现实关系依据新的知识信息可能产生的误导或偏离。⑬虽然不能说吉登斯的这个现代性应对措施多么周全,但相比个体内在性甚至把个体私密性经验和意志,当做获得现代社会信任感和认同感的唯一途径,并因此而消除危机感的态度来说,前者肯定更为熟知现代社会的内在真相一些。
以上三点可视为重要的西部文学的现代性体验进度,以目前关于现代性的前沿思想来衡估,人文惯性使然,西部文学现代性意识显然还很不自觉。当然这需要具体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