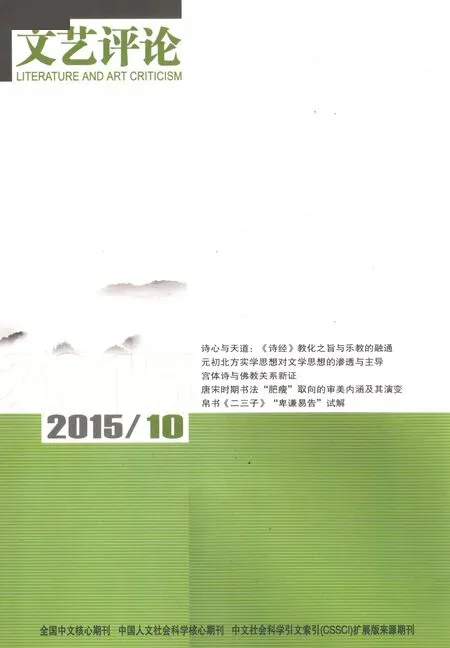论苏门文人画论及其诗画情怀
徐海容
论苏门文人画论及其诗画情怀
徐海容
据米芾《西园雅集图记》载,元祐二年(1087年),苏轼、苏辙、黄庭坚、秦观、张耒、晁补之等十六人雅集西园谈诗论道、挥毫泼墨,当时的名画家李公麟将这一艺苑盛会画成《西园雅集图》,以资纪念,这就为我们重温苏门文人的雅集诗会提供了直观感受。苏门文人是由苏轼、苏辙和被称为“苏门六君子”的黄庭坚、秦观、陈师道、张耒、晁补之、李腐等组成。其能诗善画,多才多艺,艺术素养深厚,本文即从此入手,研究苏门文人在绘画方面的审美趣味和主体追求,分析其诗画情怀的内涵与表现,并借此探讨中国古代文人画的形成过程,以求教于方家。
一、清新自然:苏门文人画论之旨趣所在
苏门文人不是职业画家,但多擅长绘画,比如三苏,苏辙《汝州龙兴寺修吴画记》云:“予先君宫师平生好画,家居甚贫,而购画常若不及。予兄子瞻少而知画,不学而得用笔之理。辙少闻其余,虽不能深造之,亦庶几焉。”①其余如黄庭坚、秦观、陈师道、张耒、晁补之等,或本身就是书画家,或多喜爱书画,对于绘画有着较深的造诣。这些人与苏轼亦师亦友,唱和往来,切磋交流,逐渐形成较统一的绘画思想,都强调清新脱俗的旨趣,追求画作的自然之美。如苏轼在《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二首·其一》中提出画作“天工与清新”的要求,把清新自然当作论画的准则,在《书晁补之所藏与可画竹三首》中,苏轼借赞扬好友文同的画作,重复了这一要求:“与可画竹时,见竹不见人。岂独不见人,嗒然遗其身。其身与竹化,无穷出清新。”在《跋蒲传正燕公山水》中,苏轼则对这一准则进行系统阐释:
画以人物为神,花竹禽鱼为妙,宫室器用为巧,山水为胜。而山水以清雄奇富变态无穷为难。燕公之笔,浑然天成,灿然日新,已离画工之度数而得诗人之清丽也。②
燕公,指北宋画家燕文贵,苏轼与之高度赞扬,认为其画妙处在于笔法“浑然天成,灿然日新”,这与评析文同的画作一致,都强调“清新”“自然”的审美旨趣。
清新自然是绘画的最高标准,如何达到清新?这就是要脱俗,对此,苏门文人有着统一的认识。黄庭坚便认为“子瞻论画语甚妙”③,其《书嵇叔夜诗与侄榎》推崇清新脱俗的画风:“余尝为诸子弟言,士生于世,可以百为,唯不可俗,俗便不可医也。或问不俗之状,余曰,难言也,视其平居,无以异于俗人,临大节而不可夺,此不俗人也。士之处世,或出或处,或刚或柔,未易以一节尽,其蕴然率以是观之。”④《论子瞻书体》“观其少年时字画已无尘埃气,那得老年不造微入妙也!”⑤其《姨母李夫人墨竹》:“深闺静几试笔墨,白头腕中百斛力。荣荣枯枯皆本色,悬之高堂风动壁。小竹扶疏大竹枯,笔端真有造化炉。人间俗气一点无,健妇果胜大丈夫。孤根偃蹇非傲世,劲节腥枝万壑风。闺中白发翰墨手,落笔乃与天同功。”都强调书画的“本色”,反对俗气之作,追求“自然”“脱俗”的清新之美。
在苏黄等人看来,清新脱俗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追求画作的神逸,即意境,这是一种高尚的人格追求和精神境界。如苏轼强调在“随物赋形”⑥基础上,追求更高层次的“神逸”,其《画水记》中称孙位“画奔湍巨浪,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尽水之变,号称神逸”⑦,《与米元章札》“但念吾元章迈往凌云之气,清雄绝俗之文,超妙入神之字”⑧,《书唐氏六家书后》“张长史草书,颓然天放,略有点画处,而意态自足,号称神逸”⑨,都倡导神逸的美学标准。苏轼的这一说法,得到其他文人的赞同,如苏辙《汝州龙兴寺修吴画记》:
凡今世自隋晋以上,画之存者无一二矣。自唐以来,乃时有见者。世之志于画者,不以此为师,则非画也。予昔游成都,唐人遗迹遍于老佛之居。先蜀之老有能评之者,曰:“画格有四,曰能、妙、神、逸。”盖能不及妙,妙不及神,神不及逸。”称神者二人,曰范琼、赵公佑;而称逸者一人,孙遇而已。范、赵之工,方圆不以规矩,雄杰伟丽,见者皆知爱之。而孙氏纵横放肆,出于法度之外,循法者不逮其精,有従心不逾矩之妙……其后东游至岐下,始见吴道子画,乃惊曰:“信矣,画必以此为极也!”盖道子之迹,比范、赵为奇,而比孙遇为正,其称“画圣”,抑以此耶?⑩
苏辙纵论画家诸作,提出“能、妙、神、逸”的审美要求,将其当作绘画的高标,并以此评判画家作品。黄庭坚《东坡居士墨戏赋》评价苏轼的画作:“东坡居士……作枯槎寿木、丛绦断山,笔力跌宕于风烟无人之境,盖道人之所易,而画工之所难……惟天才逸羣,心法无轨;笔与心机,释冰为水。”⑪《刘明仲墨竹赋》认为刘明仲的画作“用意风尘之表,如秋高月明,游戏翰墨,龙蛇起陆……凛凛犹有生气”⑫也体现出对“神逸”的推崇。晁补之在其题画诗《和苏翰林题李甲画雁》也认为“画写物外形,要物形不改。诗传画外意,贵有画中态。我今岂见画,观诗雁真在。尚想高邮间,湖寒沙璀璀。凌霜已凌厉,藻荇良琐碎。衡阳渺何处,中沚若烟海。”点明绘画具有表现物象客观之神和作者主观之意的双重效果,强调画家作画时个人思想感情、精神境界的表现,追求“神逸”的意境之美,即画外意、笔外情,在《赠文潜甥杨克一学文与客画竹求诗》中,晁补之又重复了这一观点,借赞扬文与可的竹子,强调作画“神会久已熟”的绘画要领。陈师道《晁无咎画山水画》云:“前生阮始平,今代王摩诘。偃屈盖代气,万里入方尺。朽老诗作妙,险绝天与力。君不见杜陵老翁语,湘娥增悲真宰泣。”借赞扬晁补之的绘画,也表明对画画“神逸”之美的追求,都体现出对苏轼绘画观点的继承和发挥。
苏门文人追求的清新脱俗、神逸之美,代表着宋代绘画的普遍倾向。北宋以后,封建政权加强统治,党争激烈,文祸连连,导致士吏多“忧谗畏讥”,正如苏辙《四十一岁岁莫日歌》所云士人“坐谈王霸了不疑”⑬的进取精神不断受挫,如苏轼在狱中已料定必死无疑,写下“是处青山可埋骨,他时夜雨独伤神”⑭的诗句,晚年《答李鳸书》也说自己“少年时,读书作文,专为应举而已,既及进士第,贪得不已,又举制策,其实何所有……人苦不自知,既以此得,因以为实能之,故譊譊至今,坐此得罪几死……自得罪后,不敢作文字。⑮”文人墨客难得在政治上施展才华,多处于失意境遇之中,人生追求便发生了潜移默化的变化。其逐渐追求以自我解脱为核心的人生哲学与自然淡泊、清净高雅的生活情趣,精神寄托的对象从名利事业转移到大自然,寄情于自然景物之中,与此同时,理学兴起,强调天道心性。这就导致文人士大夫们在对自然审美的观照中最终获得精神的解脱,其论画多追求自然天成之美,追求超群脱世、清新飘逸的神来之境。如范宽最初师从荆浩、李成等大画家,但最终如苏轼《滟滪堆赋》所论,感悟“与其师人,不若师诸造化”⑯,向自然学习,观摩写生,追求灵魂的释放,其画作清新刚健,在巨大的空间感与体积感中表现了一种沉思的、内省的精神境界,颇具神逸之美,被誉为“师心自然”“默然与神通”,“天下皆称宽善与山传神”⑰。米芇、米友仁父子更以“平淡天真”为绘画之旨所在,其画作多微茫山水,云山烟雨的神秀飘逸之笔,以此表达深沉内敛的人格精神。韩拙《山水纯全集》则提出新的绘画“三远”说:“愚又论三远者,有近岸广水,旷阔遥山者,谓之阔远。有烟雾溟漠,野水隔而仿佛不见者,谓之迷远。景物至绝而微茫飘渺者,谓之‘幽远’”⑱,这比郭熙所谓的高远、平远、深远又进了一步,实质就是强调以形写意,重在境外之韵的孕造,追求神逸的画外之境。和苏轼友善的画家王诜作画也讲究气韵生动,意境幽远,其《烟江叠嶂图》重峦叠嶂,云霞明灭,飞瀑流泉,充满笔有尽而意无穷神逸之境。苏轼作《书王定国所藏烟江叠嶂图烟江叠嶂图》为之感叹:
江山清空我尘土,虽有去路寻无缘。还君此画三叹息,山中故人招我归来篇。
赞扬王诜追求清新、神逸的画外之境,表现自我的弃俗出世、林泉隐逸之趣。这种将画作的审美表达与士人的精神追求关联,与当时文学发展中崇尚清旷的思想潮流密不可分。事实上,苏轼、黄庭坚、秦观等与王诜、米芾、李公麟等名画家关系亲密,经常群居雅集,谈诗论画,诗画酬唱,这最终促进苏门文人诗画一律论的形成。
二、诗画一律:苏门文人诗画之变革方向
苏轼等人的画论,其实和诗论是一脉相承相通的。其论诗也以清新自然为要,如《和犹子迟赠孙志举》:“清诗得可惊,信美词多夸”。《次韵致政张朝奉仍招晚饮》:“新诗如玉屑,出语便清警。”《游惠山》:“壁间余清诗,字势颇拔俗”、“皓月徘徊应许共,清诗妙绝不可言”。在苏轼看来,追求诗歌创作的清新自然、韵外之旨,其实和作画是一样的,两者彼此相通,在《次韵吴传正枯木歌》中,苏轼将诗、画两种艺术相提并论,认为“古来画师非俗士,妙想实与诗同出”,在此基础上,苏轼提出“诗画一律”的观点,其《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二首》云:
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赋诗必此诗,定非知诗人。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边鸾雀写生,赵昌花传神。何如此两幅,疏淡含精匀。谁言一点红,解寄无边春。
苏轼认为诗和画有着共同性,都不是简单描摹物象的“形似”,强调无论诗人还是画家,都要重视对“神”、“态”的追求,只有抓住客观物象的本质,追求以貌取神,达到“天工与清新”,便会升华至诗画合一的高度,创作出优秀作品。这种关于诗画同构,认为“诗画一律”的提法承前启后、充满着变革画坛的精神,最终促进了画坛和诗坛的互动,对北宋的诗画发展起着重要作用。
诗、画两种艺术相提并论在中国古代由来已久。晋代陆机云:“丹青之兴,比雅颂之述作,美大业之馨香,宣物莫大于言,存形莫善于画。⑲”唐代张彦远亦云:“记传所以叙其事,不能载其形;赋颂所以咏其美,不能备其像;图画之制,所以兼之也。”⑳但两人并没有说明诗画两种艺术之间的联系,此后王维《为画人谢赐表》云:“乃无声之箴颂,亦何贱于丹青”㉑,将丹青之作喻为“无声之箴颂”,注意到诗与画的共性,但王维的观点并没有引起唐人的普遍重视。宋代以降,伴随着绘画创作高潮的到来,对诗画的关系的重新认识成为艺术家关注的热点。作为杰出的诗人和画家,苏轼响应文化发展大潮,率先提出“诗画一律”的文艺观点,强调诗和画的同质性,指出其贵在传神达意,追求意韵之美,其《文与可画墨竹屏风赞》:“诗不能尽,溢而为书,变而为画。皆为诗余。”㉒《书摩诘蓝田烟雨图》云:“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㉓赞赏王维作品诗情画意的美学风格。在《韩干马》中又云:“少陵翰墨无形画,韩干丹青不语诗”,借评论画家作品,再次重复了“诗画一律”的观点。较之于前代论家,这在诗学、画学史上是一大进步,其将诗和画两种艺术的界限彻底打破,认为诗歌和绘画都是一种抒发个人情感的艺术,强调诗歌形象思维基础上的情意表达,同时也将绘画提到一个更高的层次来看待,认为绘画贵在体现创作主体的审美追求和精神气质,完全可以成为文人抒情达意的工具。这种关于诗画结合的论述,赋予中国画清新蕴藉的意味,也使得中国诗歌情景相生的写作传统得到加强,具有典范意义。
苏轼此论一开,得到广泛响应。黄庭坚《次韵子瞻子由题憩寂图》:“李侯有句不肯吐,淡墨写出无声诗。”以作诗形容作画,说明绘画也具有写意传情的功能,其《写真自赞五首》:“诗成无色之画,画出无声之诗”㉔,直接点面诗画两种艺术的同一性,其《题赵公佑画》又云:“诚妙用笔,非俗工所办也。余初未尝识画,然参禅而知无功之功,学道而知至道不烦。于是观图画悉知其巧拙工俗,造微入妙。然此岂可为单见寡闻者道哉!”㉕强调画者本身的创作动机和审美追求,即诗意之情调,在《题辋川图》中,赞赏王维作画“笔墨可谓造微入妙……可见其得意于林泉之仿佛”㉖。此外,晁补之《和苏翰林题李甲画雁二首》认为:“画写物外形,要物形不改;诗传画外意,贵有画中态。”陈与义《心老久许为作画未果以诗督之》也云:“秋入无声句。”钱鍪《次袁尚书巫山诗》言:“终朝诵公有声画,却来看此无声诗。”都强调诗画的互动交融,追求诗情画意,这实质都是对苏轼“诗画一律”的再发展。
尽管唐代就有意味着诗画融合的题画诗出现,也有王维那样的诗人兼画家,但对诗画精神的融合理解最为透彻的还是苏黄等人。这种“诗画一律”的提法,现实针对性明显,目的在于唤起宋代诗坛、画坛的改革。宋初以来,诗坛盛行西昆体,其“缀风月,弄花草”,重复着六朝诗文虚浮绮靡的俗套,虽屡经努力,但收效甚微,正如苏轼《谢欧阳内翰书》所云:“文教衰落,风俗靡靡,日以涂地。圣上慨然太息,思有以澄其源,疏其流,……罢去浮巧轻媚丛错采绣之文……士大夫不深明天子之心,用意过当,求深者或至于迂,务奇者怪僻而不可读,余风未殄,新弊复作。”㉗而画坛亦盛行院体画,其华美细腻,浓艳绮丽,追求强烈的装饰色彩,强调形似、写真,这就忽视了艺术品位,日渐落入精工繁富而意韵不足的俗套,“山水中,多以楼阁台榭,院宇桥径,务为人居处牕牖间景趣味耳。乏深山大谷烟霞之气,议者以此病之。㉘”以致“世之论画者,谓学人规矩多失之拘,或柔弱无骨鲠。”㉙
苏轼作为继欧阳修之后的文坛领袖,其倡导诗画一律,弘扬诗画两种艺术形式的互动和渗透,将清新自然作为诗画的最高准则,这就给予诗人和画家创作以新的审美规范和发展方向,对宋代诗文革新及绘画发展有着积极作用。以诗歌创作而言,庆历至元丰年间的北宋中期,是宋诗形成的关键阶段,也是宋人真正跳出中晚唐诗学窠臼而树立自己诗学形态的时期。欧、梅时代,主要是对唐代李、杜、韩、孟诸大家的模仿与学习,但欧、梅不同于宋初“三体”纯粹“形似”之仿,而是力求“神似”。苏轼等人继承了这一观点,通过绘画理论来指导诗文创作,追求诗歌创作中的画意,即清新雅丽的神逸之美,反对低俗肤浅之作,如其《题柳子厚诗二首》讲到作诗:“要有为而作,用事当以故为新,以俗为雅。好奇务新,乃诗之病”㉚,强调诗歌在景物描写之外的感情抒发,追求画面的韵外之旨,重视深层表达,这种追求诗情画意的创作思想,使得“清新”、“雅丽”的诗歌开始受到重视。熙宁以后,在文体改革风暴的影响下,在“复雅崇格”之路下的审美诉求中,苏轼、王安石等人的诗歌,在新的语境下普遍显示出了“清劲”的色彩。经过苏轼、王安石、黄庭坚等人的努力,宋诗形貌渐渐清晰,在元祐时代终于确立了其体格形态,体现出独立的审美追求和思想境界。
苏轼诗画一律的理论,也波及到绘画领域。苏门文人多画家,也和画家有着良好的交集,如李公麟《西园雅集图》所画主友十六人,包括王诜、李公麟、苏轼、苏辙、黄鲁直、秦观、李公麟、米芾、蔡肇、李之仪、郑靖老、张耒、王钦臣、刘泾、晃补之等,这其中李公麟、王诜、米芾、蔡肇、刘泾等都是职业画家,其中李公麟、王诜等都是著名的院体画家,而王诜更是贵为驸马。就其交游来看,苏黄等诗画一律的理论,不可能对其无所影响。如王诜“喜作诗,尝以诗进呈神考,一见而为之称赏”(31)“以至奕棊图画,无不造妙……写烟江远壑,柳溪渔浦,晴岚绝涧,寒林幽谷,桃溪笔村,皆词人墨卿难状之景。而诜落笔精致,遂将到古文超轶处”(32)而王谷“于儒学之外,又寓兴丹青,多取今昔人诗词中意趣写而为图绘。故铺张布置,率皆潇洒。”(33)特别是李公麟,被誉为“宋画第一人”,其画风左右着宋代画坛的发展方向。在此情况下,宋代绘画发生了变化,邓椿《画继杂说》云:“画院界作最工,专以新意相尚,尝见一轴,甚可爱玩,画一殿廊,金碧熀耀,朱门半开,一宫女露半身于户外,以箕贮果皮作弃掷状,如鸭脚、荔枝、胡桃、榧、粟、榛、芡之属,一一可辩,各不相因。笔墨精微有如此者。”(34)可见宋代院体画不仅注重写实,而且开始追求画面的新意,重视情致之美,反对为画而画。陈善《扪虱新话论画》载:
唐人诗有‘嫩绿枝头一点红,动人春色不须多’之句。闻旧时尝以此试画工,众工竞于花卉上妆点春色,皆不中选。唯一人于危亭飘缈、绿杨隐映之处,画一美妇人,凭拦而立,众工遂服。此可谓善体诗人之意矣(35)
由此可知,伴随时代发展,宋朝画院招画工,将能否理解诗意作为标尺,以资鉴考,旨在以诗入画,追求诗情画意的韵外之旨,不仅考察画家的绘画水平,更考察画家的诗学素养,《宣和画谱》评价画家胡擢“一遇难状之景,即寄之于画,乃作草木禽鸟,亦诗人感物之作也。”(36)评价画家赵仲佺“写难状之景,寄兴于丹青,故其画中有诗,至其作草木禽鸟,皆诗人之思致也。”(37)这就更体现了画坛对于“诗画一律”的认同与推崇。
三、写意传情:苏门文人诗画艺术的审美追求
在《跋宋汉杰画》中,苏轼首次提出“士人画”的概念:
观士人画,如阅天下马,取其意气所到。乃若画工,往往只取鞭策皮毛槽枥刍秣,无一点俊发,看数尺许便倦。汉杰真士人画也(38)。
在《凤翔八观·王维吴道子画》诗中,苏轼又将吴道子和王维比较:“吴生虽绝妙,犹以画工论。摩诘得之于象外,有如仙鬲谢龙樊。”(39)认为王维的画作更具士人之美。这就进一步对文人士大夫画家与画工在审美意境上加以区分,强调文人画应当具有更为高远的立意,有更为丰富的思想内容。苏轼本人并不以绘画为业,偶尔画一些枯木、丛竹、怪石等自娱。他的作品洒脱、奔放、无拘无束。其创作心态是超脱名利的,追求一种写意传情的精神享受,其《书朱象先画后》强调“能文而不求举,善画而不求售……文以达吾心,画以适吾意而已”(40)。邓椿《画继》这样记载苏轼作画:
高名大节,照映今古。据德依仁之余,游心兹艺。所作枯木枝干,虬屈无端倪,石皴亦奇怪,如其胸中蟠龙郁也。作墨竹,从地一直起至顶。或问何不逐节分?曰:竹生时何尝逐节生也?”虽文与可谓吾墨竹一派在徐州,而先生亦自谓吾为墨竹,尽得与可之法。然先生运思请拨,其英风劲气逼人,使人应接不暇,恐非与可所能拘束制也。又作寒林,尝以书告王定国曰:“予近画得寒林,已入神品。”(41)
唐代张彦远也曾说过:“骨气形似,皆本于立意,而归乎用笔。”但是张彦远所云“立意”在很大程度上还属于艺术构思的范围,而苏轼强调的“意”是指主观感受在笔墨上的流露,即在绘画“笔墨情趣”中表现自己的心境,把“意”的概念范畴扩展到精神境界。苏轼认为士人画之所以成功,在于“取其意气”,即画家学识、品德、修养在作品中的综合体现,这就突出了对画家主体人格和文学素养的积淀,将绘画当成一种综合性的艺术。在《晁补之所藏与可画竹》苏轼写道:“其身与竹化,无穷出清新。”直接道出画家主体人格与“清新”艺格的关系。在苏轼看来,文同画作之所以天工清新,原因正在于其作品寄托着自己高雅的人格追求与思想价值,传达出一种超然豁达、清雅逸兴的文人式意气情感,这就是“士人画”的最高艺术境界。在《次韵吴传正枯木歌》中又写道:“天公水墨自奇绝,瘦竹枯松写残月。梦回疏影在东窗,惊怪霜枝连夜发。”认为吴传正作画在墨色渲染、构图设置方面之所以别出心裁,原因就在于追求画作的写意传情,以“奇崛”之笔彰显“清新”之美,这种追求得到黄庭坚、晁补之等人的进一步阐释,如黄庭坚《题七才子画》云:“一丘一壑,自须其人胸次有之,但笔间哪可得”(43),强调画家的精神气质决定着绘画作品的艺术内涵。晁补之《自画山水留春堂题其上》也云:“胸中正可吞云梦,盏底何妨对圣贤。有意清秋入蘅藿,为君无尽写江天。”所谓“胸中云梦”,即画家的人品胸次、道德修养和人格气质,晁补之认为这些从根本上决定了绘画的生命和价值。
苏轼与黄庭坚曾唱和郭熙《秋山平远图》,东坡诗由画中景联想到江南送客,将“人”视作画面的灵魂,追寻人性关怀,其《郭熙画秋山平远》强调抒写其“立朝而意在东山”之思:“恰似江南送客时,中流回头望云巘。伊川佚老鬓如霜,卧看秋山思洛阳……我从公游如一日,不觉青山映黄发。”(44)黄庭坚则将画境与东坡贬谪黄州事联系起来,感慨岁月飘零,人生沧桑,其《次韵子瞻题郭熙画秋山》云:“黄州逐客未赐环,江南江北饱看山……坐思黄柑洞庭霜,恨身不如雁随阳。”(45)强调观画的情思抒发,此外,苏轼、苏辙、黄庭坚、张耒、晁补之等关于李伯时画御马的唱和诗也说明了这一点,可见强调人文关怀、注重情思意境的表达正是其品画的精髓。所以说,苏门文人论画,更多关注画面之外的人性的情意表达,追求韵外之旨,这种追求与其诗学精神是一致的,这在苏轼的《答谢民师书》、《江行唱和集序》、《书黄子思诗集后》中多有表达,不赘。
如何达到画作的写意传情,成为具有高雅品位的文人士大夫之画?这就要求创作主体的心灵的纯净自然,远离尘埃,出世脱俗,黄庭坚《道臻师画墨竹序》云:“夫心能不牵于外物,则其守全,万物森然出于一境,岂待含墨吮笔磅礴而后为之哉。”(46)如此才能达到苏轼《书吴道子画后》所论“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秒理于豪放之外”(47)。这种重视画家个人道德修养的画论主张体现了儒家“吾养吾浩然之气”的艺术观,影响着画坛的发展方向,对宋人艺术思维的转变有着重要意义。在苏黄等人的倡导下,文人士大夫以自己特有的诗书修养、文人心理而介人绘画,其笔下的花鸟山水已不仅仅是追求客观的自然之美,而是“借物以言志”,追求写意传情,这就使得文人画成为一股有相当影响的艺术潮流,开始从院体画与画工画中分化出来,在意韵情致行更胜一筹,正如郭若虚《图画见闻记》所云:
窃观自古奇迹,多是轩冤才贤,岩穴上士,依仁游艺,探蹟勾深,高雅之情,一寄于画,人品既已高矣,气韵不得不高。气韵既已高矣,生动不得不致,所谓神之又神,而能精焉。(48)
邓椿《画继》亦提出:“画者,文之极也。故古今之人,颇多著意。……本朝文忠欧公、三苏父子、两晁兄弟、山谷、后山、宛丘、淮海、月岩以至漫士、龙眠,或评品精高,或挥染超拔。然则画者,岂独艺之云乎?”(49)提出文化修养与绘画之间的关系问题,强调画法的气韵生动、写形传神。而李公麟、文同、米芾、杨补之等人更倡扬“笔法墨色”,在创作实践和理论批评上推动着文人画的发展。如黄庭坚《跋东坡论画》所载李公麟作画“以立意为先,布置缘饰为次。其成染精致,俗工或可学焉,至率略简易处,则终不近也。盖深得杜甫作诗体制而移于画……叹曰:‘吾为画如骚人赋诗,吟咏情性而已。’”(50)文同写墨竹,创浓墨为面,淡墨为背之法,“富潇洒之姿,逼擅弈之秀”、“托物寓兴,则见于水墨之戏”(51)。米芾、米友仁父子以书法入画,用大笔触水墨表现烟云风雨变幻中的江南山水,追求诗情画意。其余如马远、夏圭的山水,仲仁、杨无咎的墨梅,都将文人画由理论变为直接技法上的运用。宋徽宗《宣和画谱》更将文人画作为“逸品”,纳入官方典籍,强调“画中有诗”,画作的意境要“默合诗人句法”才称得上“高致”(52)。此后,文人画作为中国绘画的重要流派,从此步入中国绘画之殿堂。而判断文人画的重要标准便是看其有没有“笔墨趣味”,是否很好的写意传情。所以“写意”便成为文人画家的最高审美追求。这样一来,绘画艺术便成为一种表达个人情感的方式,与“诗言志”的传统结合在一起。诗书画三位一体,文人们与绘画的关系越来越密切,最终引领着整个传统美术的格调和意境,促进了中国绘画的繁荣发展。
李泽厚指出:“文人画主要指文学意味的突出,虽然以诗情入画并非由北宋开始,但作为一种高级审美思想和艺术趣味的自觉提倡,并日益成为占统治地位的美学标准,却要从此算起”(53)。苏黄等人本着“诗画一律”的原则,推崇诗画创作的情意表达,追求清新脱俗的神逸之趣,强调意境、格调及创作主体的学养积累,这就为宋代诗画的发展开拓了新的道路,使得宋代诗画创作,呈现出较高的艺术水准。深入研究苏门文人的诗画理论,有助于我们把握整个宋代文学的发展规律,对于中国古代文艺美学的整体研究也有着启迪意义。
【作者单位:东莞理工学院中文系(523808)】
①⑩⑬《苏辙集》,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106、1107、169页。
②⑥⑦⑧⑨⑮㉒㉓㉗㉚(38)(39)(40)(44)(47)《苏轼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2191、645、913、1907、2187、1661、2189、2189、1655、2189、2194、22、2191、348、2190页。
⑭《苏轼全集·予以事系御史台狱狱吏稍见侵自度不能堪死狱中不得一别子由故作二诗授狱卒梁成以遗子由二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234页。
③④⑤⑪⑫㉔㉕㉖㉗(45)《黄庭坚全集》,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731、1562、1433、299、1361、559、728、730、1562、81页。
⑯史梦兰《尔尔书屋文钞》,清光緖十七年止园刻本。
⑰㉘㉙(50)(51)(52)《宣和画谱》,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185、195、200、131、310、158页。
(31)(32)(33)(36)(37)《宣和画谱》,人民美术出版社1964年版,第204、203、199、248、262页。
⑱(41)(48)(42)(49)杨成寅《中国历代绘画理论评注》,湖北美术出版社2009年版,第193、271、145、33、274页。
⑲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人民美术出版社1964年版,第3页。
⑳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叙画之源流》,江苏美术出版社2007年版,第2页。
㉑《全唐文》,山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955页
(34)(35)俞剑华《中国古代画论类编》,人民美术出版社1957年版,第81、85页。
(46)《中国美学史资料选编》,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6页。
(53)李泽厚《美学三书》,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16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