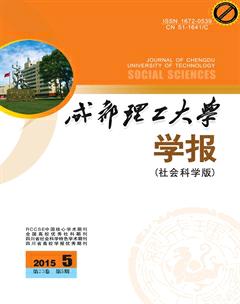社会符号学视阈下霍译《葬花吟》言内意义的再现
李菁++王烟朦
摘要:采用“意义相符,功能相似”的社会符号学翻译标准,以双关、典故和重复三种修辞的翻译为例,探讨了《葬花吟》霍译本中言内意义及相应功能的再现。分析表明,英汉两种语言符号的差异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言内意义及相应功能在翻译过程中的流失。因此,在诗歌翻译的过程中,要注重言内意义的转换,尤其是修辞的再现。
关键词:“意义相符,功能相似”;《葬花吟》;修辞;言内意义;社会符号学
中图分类号: H059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6720539(2015)05011205
一、引言
《红楼梦》中有形式多样的古诗词,它们是全书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无可比拟的艺术价值。风格上类属“初唐歌行体”[1]118的《葬花吟》就是书中众多诗篇中的一经典之作。该诗出现在《红楼梦》的第27回:“滴翠亭杨妃戏彩蝶,埋香冢飞燕泣残红”[2]2。在这首五十二行、三百六十一字的《葬花吟》里,作者曹雪芹用精炼的语言,采用借景抒情的方式,“勾画出林黛玉纷繁复杂的精神世界,奏响了她身世遭遇的全部哀音。”[3]91此诗也是《红楼梦》中黛玉众多诗作里的压卷之作,是她用全部心血谱写的生命之歌。
《葬花吟》现有多个英译本,其中戴维·霍克思(David Hawkes)的译文风格自成一体,独具特色,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基于此,很多学者已经从语篇视角的转换[4]、三美论[3]、认知心理学[5]及复调叙事理论[6]等视角对《葬花吟》霍译本进行了研究。但现有的研究多是停留在理论层面的探讨,即通过翻译理论来寻求支撑。翻译归根结底是一种语言符号之间的转换,而社会符号学研究人类社会中的一切符号系统,因而对翻译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因此,本文拟从社会符号学翻译法的角度出发,以修辞的翻译为例,探讨《葬花吟》霍译本中言内意义的再现,以期为诗歌的翻译提供参考与借鉴。
二、社会符号学翻译法
世界充满了各种符号,人类所使用的语言也是一重要的符号系统,是一种音和意不可分割的交际符号系统。曹明伦曾提出“翻译是把一套语言符号或非语言符号所承载的信息用另一套语言符号或非语言符号表达出来的创造性文化活动。”[7]114同时,翻译的“本质属性是语言符号转换。”[7]125而“符号学是系统地研究语言符号和非语言符号的一门科学。”[8]24社会符号学又是符号学的一个分支,研究有意义的实践,解释意义的生成。因此,“用社会符号学来研究翻译能够做到最有深度,它比其他任何翻译法来进行跨语符翻译都优越的关键就在于它研究人类社会的一切代码,而重点研究的是人类所使用的最综合、最复杂的符号系统,即语言。”[9]164
奈达首倡社会符号学翻译法,认为在社会符号学翻译法下翻译就是翻译意义,并提出了“功能对等”的理论。这种对等要求译者用目的语将原语忠实地表现出来,让目的语中的读者像原文读者一样感受到原文的意蕴和内涵。但奈达并未对该理论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在众多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陈宏薇提出了“意义相符,功能相似”的社会符号学翻译标准[10],并指出美国学者查尔斯·莫里斯(Charles Morris)的符号学三个意义观基本涵盖了语言交际中的一切关系,彼得·纽马克(Peter Newmark)对六大语言功能的界定则全面又简洁,较适用于指导翻译实践,并由此构成了“意义相符,功能相似”的内容。具体来说,意义包括:(1)指称意义;(2)言内意义;(3)语用意义。纽马克的功能观即:(1)信息功能,反映语言以外的思想感情;(2)表情功能:表达信息源的思想感情;(3)祈使功能:使读者去感受、去思索、去行动;(4)美感功能:使感官愉悦,诗歌的节奏与韵律、修辞等都是美感功能的体现;(5)酬应功能:使交际者之间保持接触,也可以反映交际者之间的社会关系;(6)元语言功能:指语言解释或命名自身特点的功能[11]39-44。其中,“功能反映的是文本的整体效果,该效果必须通过意义的表达来实现。”[10] 67
社会符号学翻译法强调分析和解释语言需要从文本和语言结构出发,还需要考虑到社会结构和社会过程、信息和意义。意义表达一定的功能,功能含有一定的意义。“意义和功能是判断译文质量优劣的两个重要方面……原语文本的意义在译语中是否得以充分再现是评判论文质量的首先标准,其次是功能。”[12]8因此,意义和功能是衡量译文质量不可或缺的因素,二者不可分割开来。
三、从社会符号学的角度浅析《葬花吟》霍译本中言内意义的再现“言内意义是词语成分之间、句子成分之间和篇章之间的关系所反映的意义。”[10]67因此,言内意义体现在语音、词汇、句法和语篇层面。语言韵律的平仄、双声和押韵等反映了语音关系;双关、拈连、飞白等修辞格是利用词素之间的语义关系形成;排比、对偶、层递、顶针等修辞格和句子的结构、长短都体现了句子成份之间的关系;篇章的层次、段落的排列、语义的连贯和衔接等都体现了篇章内符号的关系[10]。可以看出,词汇和句法层面主要是各种修辞手法的运用。通常,语音和语篇层面的意义较容易实现,而词汇和句法层面较为复杂,翻译难度也大。同时,语言的功能是通过语言的形式和意义来体现的,具体就言内意义而言,主要对应信息、表情和美感功能。
“言之无文,行之不远。”(《左传·襄公二十年》)也就是说,文章要讲求文采和修辞艺术。译文若不能正确地表现原文中的修辞手法,就不能准确再现原文的思想和风格,进而削弱原文的感染力,影响言内意义及相应功能的实现。《葬花吟》原诗词汇和句法层面运用了多种修辞手法,使得原文具有丰富的言内意义。其中,双关、典故和重复三种修辞的使用最为典型。因此,本文拟探讨《葬花吟》霍译本中这三种修辞手法的翻译对再现诗歌言内意义及相应功能的影响。
(一)双关
双关是“利用语音或语义条件,有意使某些词语或句子在特定的语言环境中构成双重意义的一种修辞方式,即表面上是一种意思,实际上又是一种意思。”[13]77双关语的翻译对言内意义的传达尤为重要。原诗中有时是在写花,有时又是花人一体。这也是为什么清人明义曾咏之:“伤心一首葬花词,似谶似真自不知”[1]117。原诗中双关表现为一语双意,共使用了三次。郭晶萍[14]认为,由于汉语词义的概括含蓄,容易造成诗意模糊,《葬花吟》中以花喻人、借花抒怀手法的运用对于英译而言,是难以攀越的高山。霍氏对原诗双关的转换总体上是瑕不掩瑜。请看下例:endprint
(1)原诗:明媚鲜妍能几时,一朝漂泊难寻觅。[2] 22 (1)
霍译:How can the lovely flowers long stay intact,
Or, once loosed, from their drifting fate draw back?[15]39 (2)
诗表面上是写恶劣的天气对花的摧残,感叹现实的残酷,但实际上花已经与黛玉娇怯病弱的身体和无法把握的命运结合起来了。自己的命运就像这花一样,一旦凋落,就再也不能享受这美好的春天了。霍氏采用的“the lovely flowers”翻译出了暗含的主语,字面意思有效地表达了出来。但是,原诗中既指花又指黛玉自己,读者不易把花的形象与黛玉的命运结合起来。因此,霍氏在此处的翻译只传达出了部分言内意义。同时,相应的信息、表情和美感功能也有所损失。
(2)原诗:质本洁来还洁去,强于污淖陷渠沟。
霍译:Pure substances the pure earth to enrich,
Than leave to soak and stink in some foul ditch.
在大观园里,黛玉窥见到热闹背后的世间百态与冷漠,感受到世态炎凉。而自己是像落花一样被人践踏,还是竭力用生命来维护自己的自由和幸福、贞洁呢?面对即将吞噬她的现实,黛玉始终坚持玉可碎而不可改其白,竹可裂而不可变其节。纵使自己殒落,也要保持崇高的气节。正如百花一样高洁地在世上走一遭,也要干干净净的离开。根据Oxford Advanced Leaners Dictionary(8th Edition),“substance”指“the most important or main part of something(构成某物最重要或主要的部分)”[16]1544。例(2)中,霍克思翻译的“pure substances”隐含了主语, 花人合一,物我两忘,生动传神。言内意义得以再现的同时,信息、表情和美感功能也跃然纸上。
(3)原诗: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
霍译:One day, when spring has gone and youth has fled.
The Maiden and the flowers will both be dead.
这两句是全诗的高潮,表现了黛玉的茫然无助和极度痛苦。春逝去,百花凋零,周围的人对此似乎是毫不在意,无怜悯之惜。“红颜”既指花的美艳,又指少女自己。多愁善感的黛玉觉得正如没人会记得这花曾经的鲜艳明媚,自己也难逃命运的安排。年华也终将老去,容颜不再。Oxford Advanced Leaners Dictionary(8th Edition)对“youth”的解释有“the quality or state of being young(年轻的状态或富有朝气的品质)”[16]1793。例(3)中霍氏译的“youth”一语双关,既可以指花的鲜艳,又指年轻少女黛玉的青春。读者很容易把两者结合起来,联想到黛玉红颜薄命、短暂凄美的人生。正如“成功的翻译就是要在译文中重塑与原文相同的文本功能,使目的语读者在阅读译文时获得与源语读者读原文时同等的感受。”[17]37霍克思将言内意义及其对应的信息、表情和美感功能也很好地传达了出来。
(二)典故
典故指“人们在日常谈话和写作中引用的出自神话、传说、寓言、文献、文学名著及历史等的故事和词语。”[18]29钱钟书曾谈到诗文中用典的艺术原因:“诗人要使语言有色泽、增添深度、富于暗示力,好去引得读者对诗的内容作更多的寻味,就用些古典成语,仿佛屋子里安放些曲屏几,陈设些古玩书画。”[19]14原诗中暗引了“湘妃泣竹”和“杜鹃啼血”两个典故,增添了悲凉的气氛。请看下例霍克思的翻译:
(4)原诗:独把花锄泪暗洒,洒上空枝见血痕。
霍译:The solitary Maid sheds many a tear,
Which on the boughs as bloody drops appear.
古代传说舜(上古三皇五帝之一)南巡死于苍梧。二妃(娥皇、女英)往寻,后跃入湘江殉情而死。途中泪染青竹,竹上生斑,因称“潇湘竹”或“湘妃竹”。《红楼梦》中探春也曾把黛玉称作“潇湘妃子”。原诗用潇湘竹的典故意,旨在表达黛玉对美好爱情的执着与追求。宝黛二人是“木石前盟”,互为知己,情投意合,无奈两人的爱情未能受到以贾母为代表的家长的肯定。唯有叹息“叹人间,美中不足今方信”。例(4)中,“bloody”一词给人以血淋漓的感觉,很好地传达了“泣血”之意。霍氏的翻译只是简单的传递了原诗的表面意思,“潇湘竹”的典故意义在译文中未能得到再现,深层的意义也没有挖掘出来。言内意义及相应的功能均有流失。
(5)原诗: 杜鹃无语正黄昏,荷锄归去掩重门;
霍译:At twilight, when the cuckoo sings no more,
The Maiden with her rake goes in at door
春夏季节,杜鹃彻夜不停啼鸣,啼声清脆而短促,唤起人们多种情思。众多研究,如郭晶萍[14]都是从“蜀王杜宇”来分析此处的用典:传说蜀国杜宇帝让位臣子,归隐山林,死后化为杜鹃悲鸣啼血。但杜鹃往往是有多重意向。唐代诗人元稹就曾在《思归乐》中有:“山中思归乐,尽作思归鸣。尔是此山鸟,安得失乡名”,借此来抒发思乡之情。这里“杜鹃”应该还有劝归者的形象,抒发的是思归离愁之感。原诗表达的是黛玉的伶仃之苦,父母已经不在世,也无姊妹兄弟,自己像飘泊的野草。胸中苦谁知,满腹心事向谁诉,大千世界哪里又可以让自己容身?“cuckoo”首先将杜鹃的意向正确地翻译了出来,霍氏译的“sing no more”,呈现了动态的过程,暗示了此时连彻夜不停啼鸣的杜鹃,声音都已经沙哑,不再歌唱了。这衬托了黛玉的孤苦无依,更是增添了凄凉之感。自然引起读者对黛玉的共鸣。但是,同例(4)一样,“杜鹃啼血”的典故在译文中未能得到再现,言内意义和功能也有丢失。总体上来说,部分言内意义及信息、表情和美感功能也有所产生。(三)重复endprint
重复往往是“出于表达的需要,说话人通过反复使用同一词语、词组或句子来突出话语重心,强调感情,增强节奏感,这是一种积极的修辞手段。”[20]91原诗中在第九和第十诗节两处使用重复。霍克思两处的翻译分别如下:
(6)原诗:昨宵庭外悲歌发,知是花魂与鸟魂?
花魂鸟魂总难留,鸟自无言花自羞;
霍译:Last night, outside, a mournful sound was heard:
The spirits of the flowers and of the bird.
But neither bird nor flowers would long delay,
Bird lacking speech, and flowers too shy to stay.
花儿要谢,鸟儿要飞。自己希望它们能够留下,亦或自己跟随它们一起。可这似乎是注定不能改变的。霍克思将“花魂鸟魂”两处分别翻译成“the spirits of the flowers and of the bird”和“bird nor flowers”。首先,霍氏未能准确把握原诗的内涵,其次也没有体现原文重复修辞手法的运用。因此,此处的翻译未能突出强烈的情感和语气。言内意义有所丢失,表情和美感功也能有所损失。
(7)原诗:愿侬胁下生双翼,随花飞到天尽头。
天尽头,何处有香丘?
霍译:And then I wished that I had wings to fly
After the drifting flowers across the sky:
Across the sky to the worlds farthest end,
The flowers last fragrant resting-place to find.
她热烈执着地追求理想,想脱离这令人厌恶的现实世界。“何处有香丘?”是她对自己命运的追问。她知道这样的一片净土是没有的,但是又至死不渝地追求人生理想,哪怕粉身碎骨。霍氏采用了“across the sky”,准确地把握了“天尽头”的意思,也勾勒出一幅风中落花图。两次连用“across the sky”,再现了原诗中的重复修辞手法,增强了气势,把黛玉的呐喊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言内意义和相应的功能得以再现。
四、结 语
总的来说,霍氏最大程度地再现了原诗的言内意义及对应的信息、表情和美感功能。正如他在《红楼梦》译本第一卷的前言中写到:“我遵循的原则就是翻译一切——甚至是双关。……我认为,书中的任何有目的的东西,都应表达出来。”[21]46但是,其译本中有的地方也未能实现“意义相符,功能相似”,值得进一步探讨。
翻译难,翻译诗歌难,翻译小说中的诗歌更是难上加难。英汉两种语言具有鲜明异质性特征,英语重形合,汉语重意合。诗歌又是汉语中极具特色的文学符号,两种语符之间的转换不可避免地会造成符号意义上的差异,《葬花吟》霍译本中修辞的翻译导致部分言内意义及相应功能的缺失就是最好的例证。因此,在诗歌翻译的过程中,译者在从原语向译语的转换过程中需要考虑到符号、事物或概念的关系,要注重言内意义尤其是修辞的翻译,从而再现诗歌的艺术魅力和博大精深的内涵。
注释:
(1)考虑到原诗的底本问题,文中中文例子皆选自曹雪芹,高鹗(汉英对照)《红楼梦》第二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2年,第22-24页。
(2)霍译本的例子皆选自 The Story of the Stone(VolumeⅡ),Penguin Books出版,1977年,第39页。
参考文献:
[1]蔡义江. 红楼梦诗词曲赋全解[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
[2]曹雪芹,高鹗. 红楼梦(汉英对照)[M].上海:上海外语出版社,2012.
[3]刘肖杉.《红楼梦》中《葬花吟》两译文比读与赏析[J].外语教学,2007,(9):91-94.
[4]张军平. 论翻译中语篇视角的转换——从《葬花吟》英译谈起[J].西安外国语学院学报,2005,(2):67-71.
[5]范敏. 诗歌翻译的诗美构建研究——以《葬花辞》英译为例[J].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07,(6):18-23.
[6]张岚岚. 《葬花吟》的复调叙事及其互文性生成[J].红楼梦学刊,2012,(3):196-208.
[7]曹明伦. 翻译之道:理论与实践(修订版)[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3.
[8]衡孝军. 从社会符号学翻译法看汉语成语英译过程中的功能对等[J].中国翻译,2003,(4):24.
[9]Nida, E.A. Language, Culture, and Translating[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1993.
[10]陈宏薇. 汉英翻译基础[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1.
[11]Newmark, P. A Textbook of Translation[M].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
[12]李明. 社会符号学的历史渊源及其翻译原则[J].上海科技翻译,1997,(4):8.
[13]牟丽. 论双关语的翻译[J].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3):77.
[14]郭晶萍.《葬花吟》七种英译本修辞转存[J].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10,(4):61-64.
[15]Hawkes, D. The Story of the Stone(VolumeⅡ) [M]. London: Penguin Books, 1977.
[16]Hornby, A S. Oxford Advanced Leaners Dictionary(8th Edition)[M].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17]谭震华. 论双关语的翻译[J].上海翻译,2006,(4):37.
[18]田传茂,许明武. 报刊科技英语的积极修辞及其翻译[J].中国科技翻译,2001,(1):29.
[19]江弱水. 互文性理论鉴照下的中国诗学用典问题[J].外国文学评论,2009,(1):14.
[20]徐莉娜. 重复译法的衔接功能探究[J].山东外语教学,2012,(6):91.
[21]Hawkes, D. The Story of the Stone(VolumeⅠ) [M]. London: Penguin Books, 1973.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