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孝贤的精神线索
温天一
侯孝贤之所以备受瞩目,不单单只是因为他的影像和语言,更多的还在于电影所反射出的精神内里。他的生存经验、阅读和体悟,以及特殊的岛屿叙事与世界语境的关系,共同铸就了侯孝贤的精神内核
翻开一部华语电影史,我们很有可能会在上面看到两个侯孝贤。
一个是来自南台湾的暴烈少年,于岛屿之上,抒写着快意恩仇的少年往事与恋恋风尘,那些暴露于阳光之下的忧郁与感伤,看起来也显得明媚动人。
而另一个侯孝贤,则是站在古老中国幽深昏暗的背景之上,背后点染着几千年历史的莽莽苍苍,他如同旧时代的吹笛人,音符逸出,无意识地流淌一阕关于家国、故土与乡愁的哀歌。
特立独行的存在
“某个大学时代独自在寝室的夜晚,我看完了《童年往事》,然后整个人被一种无法言喻的忧伤所笼罩,只想冲出门去,到燠热的操场上,放声大哭一场。”“这是电影第一次带给我如此巨大的感动与心灵冲击。”
电影学者、《无人是孤岛——侯孝贤的电影世界》一书的译者黄文杰这样形容自己 初次触碰侯孝贤电影的感受。
随后他开始慢慢走近并且研究起侯孝贤的作品,但随着研究的深入,黄文杰发现,某种程度上,侯孝贤是华语电影中的一个“异数”。
“他从没有受到过严格的理论训练,既不像与他同时代的台湾导演李安,从小受儒家文化教育,后来又到美国接受了戏剧与电影的系统学习;他也不像杨德昌,生长在知识分子家庭,从小就看了大量的西片与书籍,深受西方思潮和风尚的影响。”
而用朱天文的话来形容,侯孝贤的“电影导演养成记”更像是一种“土法炼钢”,有着迥异于学院派条理分明、循规蹈矩的特色。 对此,黄文杰说,“侯孝贤的身上带有一定天才的色彩,但我们也不能够说,他完全是靠着天才走到了今天。”
侯孝贤在年轻时代即投身到台湾本土蓬勃发展的电影工业中去,以助理的身份跟随以严格著称的李行导演进行实践学习,靠着大量的实践积累起对于电影的经验。“其实从他开始当助理导演,拍摄那些琼瑶式的爱情电影时,就已经在一点点地进行并且完成着侯孝贤对于自己的塑造。”黄文杰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北京电影学院电影文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陈山则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起他在上世纪80年代初时首度接触侯孝贤电影的情景。“那时候中国大陆电影界对于侯孝贤电影的宣传口径,还是在强调他的台湾乡土化特征,在电影美学上与李行导演的《原乡人》《汪洋中的一条船》等一脉相承。”
张爱玲曾在上世纪60年代初访台湾之后,写成一篇题为《A Return To The Frontier》的英文散文,二十年后,她又将此文重新用中文翻译,命名为:“重返边城”。张爱玲借用了沈从文那部著名的、以一座坐落在川湘交界处的蛮荒边界小城为故事背景的小说题目,来形容她眼中惊鸿一瞥的台湾。那座偏居一隅的南中国小岛,有着青葱翠绿的颜色,“像古画的青绿山水,不过纸张没有泛黄。”
张爱玲与沈从文都是侯孝贤所喜爱的作家,某种程度上说,在台南“边城”长大、并没有受到过系统教育的侯孝贤,他的人生就因为看了朱天文推荐的《从文自传》而改变。
“我们总是在探讨,侯孝贤为什么会成为今天的侯孝贤。他在当年台湾电影创作条件极其有限的情况之下,靠着大量的实践和自己摸索出来的经验,还有从小积累的庞杂阅读储备,最重要的是一点是,朱天文推荐的《从文自传》从视角上打开了他的眼界,可以说,侯孝贤从此豁然开朗。”黄文杰说。
陈山则认为,与朱天文以及朱天文背后所代表的文学创作理念的合作,是侯孝贤电影生涯的重要节点。“朱天文给侯孝贤带来的文学影响太大了,甚至直接教会了他怎样去拍摄台湾新电影。”陈山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早期侯孝贤的作品还带有一些李行式‘健康写实主义的风韵,而他与朱天文合作之后,尤其是《冬冬的假期》,侯孝贤自己的影像风格已经于此基本奠定形成,他电影中的内心视角,长镜头和画外音的运用,都开始具备了浓浓的个人风格。”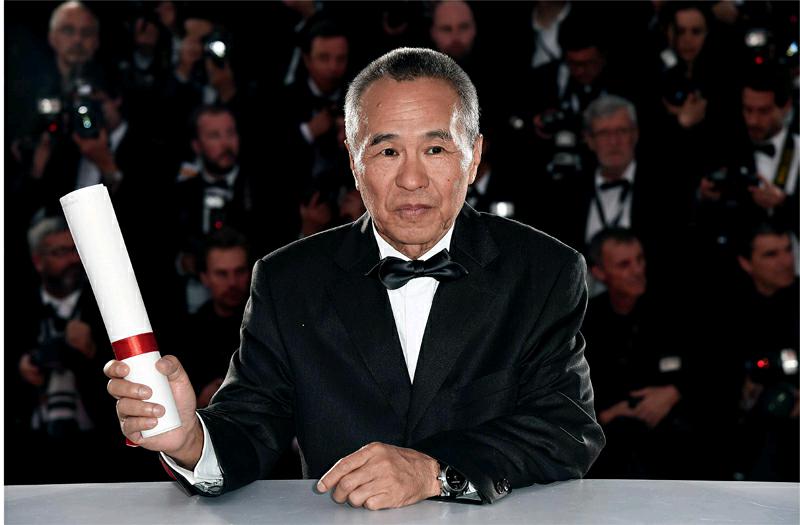
而用侯孝贤自己的话形容他初看沈从文的印象:“沈从文写自己的故乡,自己的家,再大再悲伤的事也都发生在阳光底下,没有波动,好像是在俯瞰着整个世界。”
事实上,不论沈从文抑或张爱玲的文学作品,还是作为胡兰成弟子、“张派”风格的传人朱天文,都在各自的程度上,向侯孝贤直接或间接地提供了一种创作的可能性:不仅仅依靠知识储备与逻辑推理,而是更多地以一种极为风韵天成又理直气壮的直觉来观察整个世界,敏锐、剔透,并且还带着一种年轻人特有的犀利质朴的气象,如水晶玻璃一般闪烁着硬硬的光芒。
“其实侯孝贤的人生经历也和沈从文有点类似,他们都来自天然乡野,靠着自发性的创作欲望与在社会中摸爬滚打的实践来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风格。”黄文杰说。
“早年的侯孝贤确实有点沈从文的意思,但后来由于时代的原因,沈从文走上了另外一条路,他的文人气更重一点,而侯孝贤的江湖气息则一直都存在。”陈山认为。“侯孝贤不是一个能够简单归类划分的导演,即便是处在某一个群体当中,他也是一个非常特立独行的存在。”
琐琐碎碎中的味道
曾经有一部描述台湾诗人的纪录片叫做《他们在岛屿写作》,从某个角度上说,这个强调着由地域特征而衍化出文化价值的名字,也很适合来形容侯孝贤某一阶段的电影创作。台湾作为岛屿的强烈的标性特质,和1949年后与中国大陆隔海相望的文化对应,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侯孝贤的创作。
按照美国文化评论学者詹明信所提出的“国族寓言”理论,第三世界的文本,即便那些看起来与民族无关、纯粹描述个人欲望与内心冲突的故事,也通常不能摆脱掉与民族以及国家命运息息相关的联系。换句话说,第三世界的文学永远不可能存在纯粹个人化的书写。
一直以来,有很多研究者都在套用詹明信的理论来解读侯孝贤所代表的台湾电影。而在中文的语境中,“国族寓言”似乎有着更加暧昧与复杂的味道,“家”意味着归属,而“国”则意味着一种更大意义上的认同,但台湾,似乎只有作为一个“岛”,在海天茫茫中被孤立出来的概念,在侯孝贤的大部分电影中,这座岛屿更像是一座孤独的城邦,在风雨飘摇中承载着历史与民族的重负。
电影学者戴锦华则认为,如果按照詹明信所谓第三世界“国族寓言”式的解读脉络,侯孝贤的电影代表作“台湾三部曲”《悲情城市》《戏梦人生》《好男好女》会成为看似极为恰当的切入点。“以此为解读者上溯或顺流而下的中转站,便揭示出侯孝贤电影序列的另一番面貌——以20世纪最后20年的台湾为主轴,上溯至日据时代、光复初年的台湾社会—— 一段被重写的历史,一份再度显露血痕和创楚的记忆,某种厚重丰盈又重重纠结的情感结构。”
但同时,戴锦华也认为,侯孝贤的作品有着极为深刻的“作者电影”烙印:“绵延着一条极为清晰的个人书写或曰风格的痕迹。”事实上,极度个人风格化的“作者电影”与台湾本土的“寓言”式解读,都存在于侯孝贤的作品中,“有着判若两然的历史语源与实践内涵。”
学者陈山则并不认同用西方理论套用中国电影的方法,他认为《悲情城市》《戏梦人生》与《好男好女》的伟大之处在于,“作为世界级导演的侯孝贤,借助这一系列影片,构造出了一部完整的台湾人精神史”。
而黄文杰则认为,与庞大的历史叙事相比,侯孝贤更倾向于关注琐屑与凡俗的日常生活。“他不关注大的东西,他喜欢那些幽微的细节,这就是为什么侯孝贤那么喜欢《海上花》,那里面写的都是些琐琐碎碎的东西,他偏偏就喜欢,觉得特别有味道。”而即便是《悲情城市》这样宏大的历史题材,“他也是选择从相当个体的角度切入,而且影像上几乎没有大场面出现。”黄文杰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据黄文杰介绍说,侯孝贤非常喜欢日本女作家林芙美子的作品,他不仅自己看,甚至还买了很多套书送人。林芙美子在中国文学界被誉为“日本的萧红”,她的一生充满了颠沛与破碎,甚至曾经随波逐流地参与过日本侵华战争的报道。但林芙美子文字中的苍凉以及关注“流动在被众人忽视的空间中的人的命运”,让侯孝贤有所触动。
从这一点看,侯孝贤绝不是一个有着政治考量的创作者,他最为关注的,还是剔除在政治与历史背景之外,每一个生命个体在苍茫时代中的经历与选择。
他拍大时代,却更是深深扎根在厚重与繁琐的日常生活之后,如同他形容自己阅读张爱玲《雷峰塔》的观后感:“里面最精彩的部分是一群老妈子之间的斗嘴,那才是真正的民间精髓。”
作为电影导演的侯孝贤,似乎并不关心电影理论的风潮,很多理论学者常常把他的影像风格与小津安二郎作对比,而侯孝贤本人在拍片之时根本未曾接触过小津的电影,后来是因为大家都说像,他才特意找来看一看。
而侯孝贤对于家国与历史的理解,也许更像是博尔赫斯在《交叉小径的花园》中对于“一个国家”概念的定义,“即萤火虫,语言,花园,流水,与西风。”换句话说,他从未试图充满野心地去书写历史,而是一直在精细地刻画着远山近水与稻田清溪。
老灵魂的前世今生
导演贾樟柯曾经在少年时代于报纸上阅读到一封廖承志写给蒋经国的信,其中一句“经国吾弟:咫尺之隔,竟成海天之遥”,让当时那个长在红旗下的12岁汾阳少年惊讶不已——古典雅驯的措辞,却句句惊心地道出了命运之苦。这样陌生又熟悉的语言,让他开始对海峡对岸产生了好奇。
七年之后的1989年,贾樟柯又一次在山西小城的报摊上阅读到一则关于侯孝贤导演的影片《悲情城市》获得了当年威尼斯国际电影节金狮奖的消息。他没有看过电影,但却因为这部片名而联想到了12岁那年读信时的心绪:“1949年,‘旧社会、‘旧语言、‘旧情义都随国民党政府从大陆退守到了台湾,出生在‘新社会的我,此刻为什么会被‘悲情这样一个陌生的词打动?……就像看到侯导的名字,‘孝贤二字总让我联想起县城那些衰败院落门匾上,诸如‘耕读之家、‘温良恭俭的古人题字。我隐约觉得在侯孝贤的身上,在他的电影里一定还保留着繁体字般的魅力。”多年后,贾樟柯在随笔《侯导,孝贤》中这样写到。
有评论认为,在台湾新电影导演的群体中,侯孝贤是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最深刻的一位。侯孝贤本人也曾经深入剖析过自己的文化谱系,他说:“中国对我而言,是台湾文化的源头。我们从小受教育读中国的经典、诗词歌赋,后来我又爱看武侠古典小说和戏曲,这些已根深蒂固成为我人生的背景、我所有创作的基础;这样的中国,和今天的中国内地,是两回事。”
陈山认为,研究侯孝贤的作品与风格,分析他所受到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滋养是极为重要的环节。“从《戏梦人生》开始,侯孝贤的作品就已经开始脱离其早期的台湾本土化限制。”据陈山介绍,《戏梦人生》的部分镜头是侯孝贤“跨过海峡”,在福建取景拍摄的,而“他的创作意识,也慢慢升华到了一个能够从中国传统文化大背景下出发的高度。”
而到了《海上花》时期,侯孝贤不仅仅跨越了海峡,甚至直接在银幕上打造出了一个“张爱玲心目中的上海”,重重深院掩映着的旧梦依稀,隐隐散发出鸦片的甜香,一个复杂、暧昧又充满了鬼魅般气息的古中国映像。在新片《聂隐娘》中,侯孝贤显然走得更远,他历经数年的筹备,借助浩如烟海的资料与典籍,一点一点地打造了一个他心目中对于唐朝的想象。“从晚清,民国,再到大唐,侯孝贤早已经走出了台湾,拍他自己独特的东西,描绘那些他没生活过的时代,表达中国人独特的民族精神与生存哲学。”陈山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侯孝贤绝对是中国文化上生长出来的导演,我们不能因为他拍了不少台湾本土题材,并且在作品中做了大量对于台湾历史与政治的反思,就把他局限在岛屿之上。看待侯孝贤,必须要站在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框架之中。”黄文杰说。
陈山甚至觉得,侯孝贤作品中的诗意,带有着浓厚的古典诗词况味。这一点与费穆导演的《小城之春》相类似,“侯孝贤的作品充满着凝视感,如诗般的意境,并且带有一定的中国传统田园式韵味。最重要的一点是,他和费穆都喜欢通过人物的内心视角来展开叙事。并且,侯孝贤从不会去拍摄纯写实的东西,而是留有很多想象的成分。”
但与费穆作品中流露出的旧式知识分子儒雅的诗情相比,侯孝贤的诗意明显带着更加浓烈生猛的草根特色,如果说《小城之春》时时流露出“花褪残红青杏小”的迷惘惆怅,那么侯孝贤的意境则更像是“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
朱天文与朱天心姐妹曾经出过两本散文集,分别叫做《花忆前身》与《江山入梦》,将这两个词汇连缀到一起,倒是很适合形容侯孝贤电影中对于故土、故国与故人的遐思与想象。在他的电影版图中,有一座绿水青山的边城岛屿,芒果树暗影婆娑,龙山寺前一缕烛火星星跳动,少年沿着铁轨奔跑而过,老伶人用沧桑的嗓音吟唱着古老的歌,而站在取景框后面的侯孝贤,则在时代汤汤的洪流之中,一手勾连起整个民族的前世今生,在时间、记忆与历史的反思中,蜿蜒着踽踽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