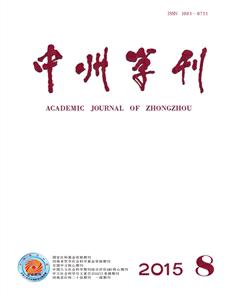《左传》与汉代文化精神
刘 梅
刘知几在《史通》中说,《左传》“传孔子教,故能成不刊之书,著将来之法”①。《左传》于两汉或隐或显,一直传承不绝,汉代文化精神就包含有《左传》的种种文化因子。
一、《左传》“争立学官”与汉代经学文化
两汉是经学的全盛时期,大师辈出,学者众多。《汉书·儒林传》曰:“自武帝立五经博士。”“百有余年,传业者寖盛,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②从西汉末到东汉,汉代经学围绕着《左传》进行了四次论争。
第一次是刘歆欲将《毛诗》《古文尚书》《逸礼》和《左氏春秋》列于学官,由于诸儒反对而无果。汉平帝时,王莽总揽朝政,刘歆得王莽政治上的帮助,使《左传》立于学官。
第二次是韩歆等与范升围绕《左传》进行的论辩。东汉光武帝建武年初,“时议欲立《左氏传》博士”,而范升“奏以为《左氏》浅末”。③争论遂起,此后今文学家范升与古文学家韩歆、许淑等人之间不断辩论。后范升又与古文家陈元论争。“诸儒以《左氏》之立,论议讙哗,自公卿以下,数廷争之。”④经过不断的论争,推崇古文学的人逐渐增多。
第三次是贾逵和李育围绕《左传》进行的争论。建初四年(79),章帝“诏与诸儒论《五经》于白虎观”。今文家李育与贾逵辩论,李育“以《公羊》义难贾逵,往返皆有理证,最为通儒”。⑤这次辩论,加速了今文学的衰微。建初八年,汉章帝“乃诏诸儒各选高才生,授《左氏》、《谷梁春秋》、《古文尚书》、《毛诗》,由是四经遂行于世”⑥。
第四次是郑玄和何休争论《公羊传》及《左传》的优劣。虽然东汉时期古文经学已经被很多人认可,但仍有不少争论,这种争论一直持续到东汉末年何休对《左传》的攻击,他作《左氏膏盲》《谷梁废疾》来攻击古文学。而郑玄则作《针膏盲》《起废疾》来回应。最终以郑玄“括囊大典,网罗众家,删裁繁诬,刊改漏失”使今古文经学得以综合,“自是学者略知所归”。⑦围绕《左传》进行的争论,虽然有一定的政治原因,但也说明,《左传》的内容和价值在汉代经学中占有重要地位。
二、《左传》“著将来之法”与汉代经世致用文化
《左传》以其丰富的史料记载了《春秋》二百多年的历史,在纷繁的历史事件叙述中表达政治主张,将春秋时期的历史经验为统治者提供借鉴。《史记》记载说:“上大夫壶遂曰:‘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雍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⑧《左传》成为汉代人们解决社会问题的文化工具,汉代经师们常常征引《左传》来为现实政治作解说。
如阻止太子领兵评定叛乱。黥布谋反,高祖刘邦病,“欲使太子将,往击之”。辅助太子的人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认为“太子将兵,有功则位不益太子,无功还,则从此受祸矣。且太子所与俱诸将,皆尝与上定天下枭将也,今使太子将之,此无异使羊将狼也,皆不肯为尽力,其无功必矣。”让吕后求高祖亲征,“于是上自将兵而东”。⑨太子将兵的故事也见于《左传·闵公二年》的记载,晋献公使太子申生伐东山皋落氏,里克劝献公“夫率师,专行谋,誓军旅,君与国政之所图也。非太子之事也。师在制命而已,禀命则不威,专命则不孝,故君之嗣嫡不可以帅师。君失其官,帅师不威,将焉用之?且臣闻皋落氏将战。君其舍之”⑩。或许太子的谋士们就从“君之嗣嫡不可以帅师”得到了以资借鉴的依据。
又如遵行“不伐丧”之礼。《汉书·萧望之传》记载“五凤中匈奴大乱,议者多曰匈奴为害日久,可因其坏乱举兵灭之”,以绝后患。而萧望之则认为:“《春秋》晋士匄帅师侵齐,闻齐侯卒,引师而还,君子大其不伐丧,以为恩足以服孝子,谊足以动诸侯。”[11]据《左传·襄公十九年》云“晋士匄侵齐,及谷,闻丧而还,礼也”[12]。还有类似的《左传·襄公四年》“三月,陈成公卒。楚人将伐陈,闻丧乃止”[13]。《左传》中比较注意军礼中的“不伐丧”之礼。汉人也继承了这一点,故而萧望之的建议被采纳,“上从其议,后竟遣兵护辅呼韩邪单于定其国”[14]。
另外,穿着甲冑不拜之礼也从先秦时期延续到了汉代。《左传·成公十六年》晋楚鄢陵之战中,郤至三遇楚子,“免胄而趋风”,并说“间蒙甲胄,不敢拜命”。[15]《史记·绛侯周勃世家》记载周亚夫面对文帝前来劳军,说:“介冑之士不拜,请以军礼见。”[16]当然,《礼记·曲礼上》也有“介者不拜”之语,但《左传》中详细而真实的描绘为礼仪的实际实施提供了较为确切的证据。
东汉初年,隗嚣与诸将议自立为王,郑兴乃以《春秋传》中“口不道忠信之言为嚣,耳不听五声之和为聋”[17]劝说隗嚣,从而使隗嚣打消了自立为王的念头。郑兴所言,就是《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富辰谏周襄王之辞。其后隗嚣又欲广置职位,郑兴又以“孔子曰:‘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相劝。这一句话见于《左传》成公二年:“仲尼闻之曰:‘惜也,不如多与之邑。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18]
西汉时期宗室诸王坐大以致谋乱,东汉时期外戚宦官专权,统治者无不希望能够找到维护封建礼教的良药,而寄寓着深刻的君臣父子之义的《左传》,正可担此重任。据刘师培《左氏学行于西汉考》考证,包括高祖与文帝的诏书、武帝制令、哀帝册封,《汉书》中张敞等本传所附奏书,《淮南子》《说苑》《列女传》等都引用过《左传》内容。当年贾逵向章帝进言:《左氏》“皆君臣之正义,父子之纪纲”,“《左氏》义深于君父,《公羊》多任于权变,其相殊绝,固以甚远”,“今《左氏》崇君父,卑臣子,强干弱枝,劝善戒恶,至明至切,至直至顺”。而且章帝自己也“特好《古文尚书》、《左氏传》”。[19]
汉代注重和强调“经世致用”的文化结果,使《左传》经常被汉代经师们用来资政并作为劝谏的准则,足见其“著将来之法”在汉代所起到的经世致用效应。
三、《左传》“崇礼宜乐和”与汉代礼乐文化
经学大师郑玄认为“《左氏》善于礼,《公羊》善于谶,《谷梁》善于经”[20]。礼是《左传》全书的思想核心。《左传》“包含了非常丰富的典章制度,礼乐文化,如实地记录了各种礼典,包括冠、昏、丧、祭、響、射、朝、聘,其中聘礼尤备,还有丰富的军礼”[21]。如《左传·文公六年》就记述了典籍和礼仪的创制:“古之王者知命之不长,是以并建圣哲,树之风声,分之采物,著之话言,为之律度,陈之艺极,引之表仪,予之法制,告之训典,教之防利,委之常秩,道之礼则,使毋失其土宜,众隶赖之,而后即命。”[22]而“礼”与“乐”是相互配合,相辅相成的,《乐记·乐论》曰:“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别。”[23]“《左传》崇“礼宜乐和”,重视礼乐的作用。《左传·襄公十一年》云:“夫乐以安德,义以处之,礼以行之,信以守之,仁以厉之,而后可以殿邦国、同福禄、来远人,所谓乐也。”[24]
《左传》以其自身的内容与价值影响着有汉一代的礼乐文化。汉人汲取了周人的统治经验,更汲取了暴秦的教训,他们充分认识到了礼乐文化的关键性作用。如汉初贾谊将《左传》的“重礼”思想发挥到其《新书》之中。章太炎《春秋左传读叙录》说“贾书中《道术》篇、《六术》篇、《道德》篇,正是训故之学,有得于正名为政之意者也。其作《左氏训故》,又何疑乎”。[25]徐复观先生说“《新书》引《左氏》,他的深通《左氏》自不待言”[26]。贾谊《新书》中的“礼”学思想不少是从《左传》而来。比如《新书·礼》说道:“礼者,所以固国家,定社稷,使君无失其民者也。”[27]而《左传·昭公五年》云:“礼,所以守其国,行其政令,无失其民者也。”[28]《左传·隐公十一年》云:“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29]由此看来,贾谊对“礼”的看法,与《左传》的记载不仅大意相同,句式也类似。又如贾谊把能否守“礼”作为能否取得民心,获得胜利的原因。贾谊说:“齐桓公之始伯也,翟人伐燕,桓公为燕北伐翟,乃至于孤竹,反,而使燕君复召公之职。桓公归,燕君送桓公入齐地百六十六里。桓公问于管仲曰:‘礼,诸侯相送,固出境乎?’管仲曰:‘非天子不出境。’桓公曰:‘然则燕君畏而失礼也,寡人恐后世之以寡人能存燕而朝之也。’乃下车,而令燕君还车,乃剖燕君所至而与之,遂沟以为境而后去。诸侯闻桓公之义,口不言而心皆服矣。”[30]贾谊认为,桓公能讲“礼”,以“礼”作为行为的标准,因而能九合诸侯,扶兴天子。这与《左传》的观点非常相似,如《左传·襄公十一年》云:“八年之中,九合诸侯,如乐之和,无所不谐。”[31]显然,精通《左传》的贾谊是受到了《左传》礼乐思想的影响。
司马迁《史记》中许多史料都是取自《左传》,而《左传》对“礼宜乐和”的追求必定对其产生影响。《史记·乐书》谓:“乐者,通于伦理者也。”“惟君子为能知乐。是故审声以知音,审音以知乐,审乐以知政。”“合情饰貌者,礼乐之事也。礼义立,则贵贱等矣;乐文同,则上下和矣。”[32]在司马迁看来,“乐”是与人伦相通的,它不仅可以和合人情,使相亲爱,而且可以整饬人的行为包括外貌,使尊卑有序,和谐美满。更重要的是,通过音乐,能够了解社会和政治,通过了解而使社会、政治贵贱有位,上下和合。这也与《左传》的礼乐思想相一致。
东汉末年社会混乱,礼法崩溃,郑玄认为“为政在人,政由礼也”[33],所以他致力于经学,目的即在于通过注经和著述,“序尊卑之制,崇敬让之节”[34],正“名分”,维护礼法制度和封建统治。郑玄遍注《三礼》,又认为“《左氏》善于礼”,因此始终强调推崇礼教的《左传》。他虽然没有为《左传》作注,但据《世说新语·文学》记载,郑玄欲注《春秋传》,因知服虔之注“多与我同,今当尽以所注与君”[35]。说明郑玄是注过《春秋传》的。而服虔注《左传》,多以“三礼”解说之,这恐怕也与郑玄的崇重礼教有密切的关系。
四、《左传》“蕴美学因子”与汉代审美文化
《左传》蕴含着丰富的美学因子,我们从《左传》的赋《诗》观乐就可看出端倪。《左传·昭公元年》记载:“赵孟为客,礼终乃宴。穆叔赋《鹊巢》,赵孟曰:‘武不堪也。’又赋《采蘩》,曰:‘小国为蘩,大国省穑而用之,其何实非命?’子皮赋《野有死麕》之卒章。赵孟赋《常棣》,且曰:‘吾兄弟比以安,尨也可使无吠。’穆叔、子皮及曹大夫兴,拜,举兕爵,曰:‘小国赖子,知免于戾矣。’饮酒乐,赵孟出,曰:‘吾不复此矣。’”[36]这是一则典型的赋《诗》场景:大国使臣到来,小国君臣设宴款待,赋《诗》助兴,其目的显然在于政治上的交好。不过,在觥筹交错,诗礼交融之中,政治的功利色彩减弱,审美感受加强,这也是赋《诗》活动的一个自然结果。从赵文子所发出的“吾不复此矣”的感叹中,我们不难发现赋《诗》活动所产生的巨大的情感力量。赋《诗》活动所产生的这种审美情感,也说明《诗》作为春秋时代礼乐政治文化的产物,其政治功用的实现与美的享受常常是协调一致的。钱穆说:“春秋时代实可说是中国古代贵族文化已发展到一种极优美、极高尚、极细腻雅致的时代。”[37]赋《诗》、观《诗》、用《诗》,体现着春秋时代贵族阶级的温文尔雅及其礼义教化,也体现着春秋时代士子文人独特的政治志向与审美嗜好,体现着他们对邦国政治、风俗民情熟稔了解的程度,而这些,均潜移默化地塑造着人们的审美心理,对后世诗学理论的形成与审美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汉代诗学理论和审美观念的形成自然也不在其外。
又如襄公二十九年,吴公子季札聘鲁,鲁人为之演奏《诗经》十五国风和雅颂以及《大武》《大夏》等六部乐舞,季札一一加以评论。季札用了十一个“美哉”,还有“大哉”“至矣哉”“观止矣”来表达自己的大美情怀。对《颂》的评价是:“直而不倨,曲而不屈,迩而不偪,远而不携,迁而不淫,复而不厌,哀而不愁,乐而不荒,用而不匮,广而不宣,施而不费,取而不贪,处而不底,行而不流。五声和,八风平,节有度,守有序。”[38]这些都是从审美角度出发,是对音乐美的描述。而当我们沉浸于“叹为观止”的“大哉之美”时,又总能体会到“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的中和之美。显然这种追求大美而又归于平和的审美思想无疑也对汉大赋的“以大为美”却又“归于讽谏”的写作方式是有着深远的影响的。汉大赋是有汉一代的代表文体,极尽铺陈夸张,但最后往往是曲终奏雅,归于讽谏,如司马迁在评论司马相如的赋时说它“虽多虚辞滥说,然其要归引之节俭,此与《诗》之风谏何异”[39]。其实从季札的评论我们不能不说汉大赋的审美文化是受到了《左传》美学思想的影响。
季札观《诗》观《乐》,其基本立场是把《诗》看成是政治状况的反映,认为《诗》可以使人们辨别政治的优劣与风俗的好坏,从而达到改进政治的目的。不过,从季札的观《诗》观《乐》活动中,我们也不难发现春秋时期的观《诗》活动所具有的审美意味。这不仅表现在季札使用了“勤而不怨”“忧而不困”“乐而不淫”“险而易行”“思而不贰,怨而不言”一类语言描述其观《诗》的体会,表现出对中庸平和的审美趣味的崇尚,而且还表现在季札通过这类观《诗》观《乐》活动的描述,展示出《诗》《乐》对人们情感心理的深刻影响,这对于汉代以《毛诗序》为代表的诗歌评论有直接的启示。
《毛诗序》强调“风刺”应“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和“发乎情,止乎礼义。发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礼义,先王之泽也”。从“主文而谲谏”看,“主文”或如《毛诗序》所谓“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以讲求诗的音声和美,悦耳动听,富有感染力;而“谲谏”是一种委婉含蓄的寓讽于志的方式,所以“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其目的是要达到“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的诗教感化的中和美效果。[40]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左传》所蕴含的美学因子对汉代审美文化的浸染。
注释
①刘知几:《史通》,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302页。②班固:《汉书·儒林传》卷八十八,中华书局,1962年,第3620页。③范晔:《后汉书》卷三十六,《郑范陈贾张列传》,中华书局,1965年,第1230页。④范晔:《后汉书》卷三十六,《郑范陈贾张列传》,中华书局,1965年,第1233页。⑤范晔:《后汉书》卷七十九下,《儒林列传第六十九下》,中华书局,1965年,第2582页。⑥范晔:《后汉书》卷三十六,《郑范陈贾张列传》,中华书局,1965年,第1239页。⑦范晔:《后汉书》卷三十五,《张曹郑列传》,中华书局,1965年,第1213页。⑧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卷一百三十,中华书局,1959年,第3297页。⑨司马迁:《史记·留侯世家》卷五十五,中华书局,1959年,第2045—2046页。⑩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81年,第268页。[11]班固:《汉书·萧望之传》卷七十八,中华书局,1962年,第3279页。[12]赵群生著:《春秋左传新注》上,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590页。[13]赵群生著:《春秋左传新注》上,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514页。[14]班固:《汉书·萧望之传》卷七十八,中华书局,1962年,第3280页。[15]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81年,第887页。[16]司马迁:《史记·绛侯周勃世家》卷五十七,中华书局,1959年,第2074页。[17]范晔:《《后汉书》卷三十六,《郑范陈贾张列传》,中华书局,1965年,第1218页。[18]赵群生著:《春秋左传新注》上,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413页。[19]范晔:《后汉书》卷三十六,《郑范陈贾张列传》,中华书局,1965年,第1236—1237页。[20]刘大钧主编:《郑学丛论》,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9页。[21]许子滨:《〈春秋〉〈左传〉礼制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页。[22]赵群生著:《春秋左传新注》上,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93页。[23]张新泰主编:《礼记新读》,新疆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91页。[24]赵群生著:《春秋左传新注》上,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554页。[25]黄觉弘:《左传学早期流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152页。[26]李维武编:《徐复观文集·两汉思想史》,湖北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05页。[27]贾谊撰,闫振益、钟夏校注:《新书校注》,中华书局,2000年,第214页。[28]赵群生著:《春秋左传新注》下,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759页。[29]赵群生著:《春秋左传新注》上,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8页。[30]贾谊撰,闫振益、钟夏校注:《新书校注》,中华书局,2000年,第249页。[31]赵群生著:《春秋左传新注》上,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554页。[32]司马迁:《史记·乐书》卷二十四,中华书局,1959年,第1184、1187页。[33]刘大钧主编:《郑学丛论》,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285页。[34]耿天勤主编;《山东省志·诸子名家志》编纂委员会编:《郑玄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12页。[35]刘大钧主编:《郑学丛论》,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271页。[36]赵群生著:《春秋左传新注》上,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716—717页。[37]钱穆:《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71页。[38]赵群生著:《春秋左传新注》上,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681页。[39]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一十七,中华书局,1959年,第3073页。[40]白雪,李倩编著:《古文鉴赏大全集》,中国华侨出版社,2012年,第178—1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