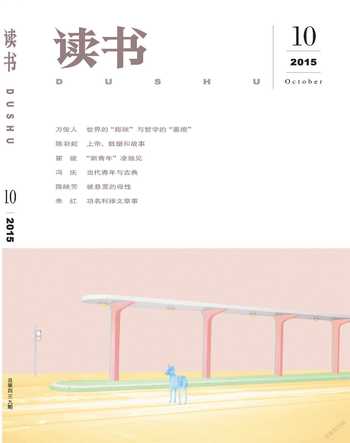松窗长昼忆平生
王振忠
去年五月,复旦大学博物馆曾展出一批明人书画,其一为松石图,画面上,枯松一株傲然挺立,左旁题句曰:“清标不受秦皇诏,劲节应嗤沈约腰。”此画作于“万历年新夏”,具体年份不详,但其言志咏怀,显然意在彰显松树之清标劲节。
一五九三年(明万历二十一年),画作者张瀚写道:
余自罢归,屏绝俗尘,独处小楼。楹外一松,移自天目,虬干纵横,翠羽茂密,郁郁苍苍,四时不改,有承露沐雨之姿,凌霜傲雪之节。日夕坐对,盼睇不离,或静思往昔,即四五年前事,恍惚如梦,忆记纷纭,百感皆为陈迹。谓既往为梦幻,而此时为暂寤矣。自今以后,安知他日之忆今,不犹今日之忆昔乎?梦喜则喜,梦忧则忧,既觉而遇忧喜,亦复忧喜。安知梦时非觉,觉时非梦乎?……
这段人生感悟冠诸《松窗梦语》一书卷首,读来令人神驰。著者张瀚时年八十三岁,写下此话不久,他就溘然长逝,因此,该段绝笔实可视作对个人一生的感喟。当时,张瀚致仕回乡已十数年,上揭文字是根据退隐蛰居后的周遭环境,回忆平生的经历见闻,夹杂着个人的今昔感悟,笔之于书。所谓梦语,是指现实与梦幻其实都只是相对而言。此类颇具哲学意味的人生思考,显然用的是庄周梦蝶的典故。据此看来,此时的张瀚一定想起了个人一生的宦海浮沉……
张瀚生于一五一○年,为嘉靖十四年(一五三五)进士,时年二十五岁。此后,他历任南京工部主事、庐州知府、潼关兵备副使、大名府知府、陕西左布政使、右副都御史、大理卿、刑部右侍郎、兵部左侍郎、两广督府、南京右都御史、南京工部尚书等职。一五七三年为张居正提携,出任吏部尚书。四年后,因不赞成张氏“夺情”而致仕家居,时年六十七岁。
在明代,官员在任如遇父母去世,一般情况下皆应弃官,家居守制,称为“丁忧”,待守丧期服满再行补职。而所谓夺情,亦称“夺情起复”,意指为国家而夺去孝亲之情。在这种情况下,当事人可不必去职,以素服办公,只是不参加吉礼而已。“夺情”是忠孝不能两全的权宜之计,但后来也成了一些官员恋栈的借口。在明代政治史上,张居正之“夺情”极为著名,对此,《松窗梦语》卷一有所记载:
江陵闻丧之越日,传谕令吏部往谕皇上眷留意。江陵亦自为牍咨部云:“某日闻讣,请查照行。”盖讽使留己也。
这是说张居正本应丁忧,但他却恋栈不去,想尽各种办法,甚至让吏部出面挽留他。对此,主政吏部的张瀚认为极不妥当,遂假装不明白他的真实意愿,主张—应当让礼部根据历年阁臣丁忧的恩典,从重加以优恤。这当然得罪了张居正,不久,在后者的指使下,便有数人相继对张瀚提出弹劾,让他奉旨退休。得知这个结局,张瀚先是朝北叩头,以示对皇恩浩荡的感激,接着前往张居正那儿道别—
张瀚道:“顷某滥竽重任,幸佐下风,见公闻讣哽咽,涕泗交横,谓公且不能旦夕留,区区之心,诚欲自效于公,以成公志,讵谓相矛盾哉!兹与公别,山林政府,不复通矣。”张瀚的微词婉讽,在在点中张居正之要害。在他笔下,袖原善舞的张氏听罢此言,似乎是愧悔交并,不胜凄惶。而随后拂袖而去的张瀚,则深得时人的叹赏,有人赠言道:“去国一身轻似叶,高名千古重如山。”
十多年后,决绝的张瀚对于此番人事沧桑仍耿耿于怀,他显然是以枯松自况,说楹外一松“有承露沐雨之姿,凌霜傲雪之节”,前句是比喻皇恩浩荡,后者则形容自己的为官操守。
对于为官节操,张瀚一向颇为看重。早在他刚中进士不久,就曾前往王廷相的私第拜谒。王廷相是河南仪封人,为人素性端方,言动威仪,历任翰林院庶吉士、兵科给事中,后因得罪权阉刘瑾,被贬到地方任都察院副都御史并巡抚四川,后又升为兵部左、右侍郎,最后升任南京兵部尚书。这位当世名臣曾对张瀚讲过一个意味深长的故事:雨后的大街上,有位轿夫穿着新鞋上路,从灰厂经长安街,走路都很小心,总是找一块干的地方走,战战兢兢,怕弄脏了鞋子。后来转入内城,地上渐多泥泞,一下子踩脏了,此后也就顾不上这双鞋子了。他说,做人的道理也是如此,失足一次,就无所顾忌,恣意而为了……
此一故事,被张瀚郑重其事地写在《松窗梦语》卷一《宦游纪》的开头,而他对于张居正“夺情”一事的抵制,则书于该卷的卷末。如此编排显然煞费苦心,可见张瀚认为自己当年的做法是正确的,而这与王廷相的教诲则密切相关。
揆势衡情,“夺情”事件对张瀚的影响一直是如影随形。在晚年,他曾追忆某次自杭州北游的经历:
渡扬子江,登金山寺,绕佛阁七层,高者临绝顶。……四顾青山,峰峦峭拔,如万笏朝拱。睹江上舟航,往来迅捷,其行如飞。旦暮视日月之出没,大如车轮,光焰万丈,目夺神竦。时江飙乍起,波涛汹涌,雪浪排空,已而风恬日朗,江波澄静,浑如素练。人生显晦升沉,亦犹是耳!安得砥柱中流,屹然如金、焦者?
涉历几多寒暑,文人的追忆间或亦杂夹着时空的错位。不过,从字面上看,是时,张瀚站在金山寺前俯瞰长江,但见江面帆樯不断,橹桨如织,面对着汹涌而至的波浪触绪萦怀,平生经历中的点点滴滴,一一浮现于脑际……或许,数十年宦海沉浮中最令人感慨的,便是湍流驰激,砥柱为难。
因“夺情”事件,张瀚被迫致仕家居,但在此前,他少年得志,“泛览群书,尤酷嗜左、国、庄、骚,至寝食俱废,遂烨然成名当世”,二十五岁就中了进士,一生从政长达四十余年,“宦辙所至,几遍海内”。在这部“随笔述事”的著述里,张瀚用了八卷的篇幅分三十三“纪”,对一生的经历见闻做了记述。其中的《宦游纪》、《南游纪》、《北游纪》、《东游纪》、《西游纪》和《商贾纪》等,多根据个人的亲身经历写成,颇为翔实可靠。
《宦游纪》主要是讲张瀚为官的经历,不过,个中也涉及各地的民情风俗。例如,他提到:
江北地广人稀,农业惰而收获薄,一遇水旱,易于流徙。
庐阳地本膏腴,但农惰不尽力耳。年丰粒米狼戾,斗米不及三分,人多浪费,家无储蓄。旱则担负子女就食他方,为缓急无所资也。
“庐阳”亦即庐州府(今安徽合肥一带),其北面就是凤阳府,上述记载实际上与传统时代的“凤阳花鼓”、“凤阳乞丐”密切相关。对此,张瀚在其后的《商贾纪》中也指出:“庐、凤以北,接三楚之旧,苞举淮阳,其民皆呰窳轻言少,多游手游食。”这段话其实源自《史记·货殖列传》:“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贾而足,地执饶食,无饥馑之患,以故呰窳偷生,无积聚而多贫。”在司马迁的时代,战国楚地被分作“三楚”,也就是西楚、东楚和南楚,“呰窳”亦即贪懒、不肯力作、委靡不振的意思。及至明代,庐州府、凤阳府一带是大批乞丐诞生的摇篮。据清人赵翼在《陔余丛考》中的记述,江苏各地,每到冬天必有凤阳人来,老幼男妇,成行逐队,散入村落乞食,至翌年春季方才离开。他们唱着“家住庐州并凤阳,凤阳原是个好地方,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的“凤阳歌”。本来以为这些人是因为灾荒而外出乞讨,但实际上即使是丰年,他们也照样外出乞食,形成了一种顽固的风俗。
为了防止“凤阳乞丐”的大批产生,张瀚在庐江当地开发水利,采取种种措施对逃荒者加以限制。据说,在他的努力下,庐江一带的灌溉条件有所改善,抛荒现象逐渐减少。不过,倘若我们从晚明时代庐江、凤阳一带的实际情况来看,这如果不是张瀚的夸大其词,那至少也说明此种状况不会持续太久。庐州和凤阳二府位于江淮之间,黄河全流夺淮入海以后,此处的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因频遭灾荒,当地民众遂养成一种不事产业、轻出其乡的习气,此种现象源远流长,有其深刻的自然地理背景。
《松窗梦语》卷二的《南游纪》、《北游纪》、《东游纪》和《西游纪》四篇,皆是游记,记录了他在全国各地的游历。此外,还有《北虏纪》、《南夷纪》、《东倭纪》和《西番纪》,涉及北方游牧民族及中国周边(琉球、日本)和西部(吐蕃、回回)等人群的生活习性及其风俗。以《西游纪》为例,篇中驰骛翰墨,远引旁搜,有不少地理方面的描述。如:
归州四里之城在高山之上,临大江之涯,居民半居水涯,谓之下河,四月水长,徙居崖上。
归州属湖北荆州府,山水萦回,源流澄澈,此处濒临长江,属三峡地区。上文描述了当地的聚落,人们随着水位之高低而居住于不同的位置。接着,文中还描写四川:
蜀城内外,平地仅四十里许,而四面皆高山,天色常阴翳,如晴明和煦、风朗气清之日绝少。至若白日杲杲、明月辉辉岁不数日,而月尤罕见,故云“蜀犬吠月”。气候较暖,初春梅花落、柳叶舒、杏花烂,暖如江南暮春时矣。地多二麦,春仲大麦黄,小麦穗,皆早于江南月余。民俗朴陋鄙俚,虽元旦、灯夕,寂然无鼓吹,灯火不异平时。惟妇女簪花满头,稍著鲜丽,丑嫫出汲,赤脚泥涂,而头上花不减也。
此段文字笔触细腻,饶有画意。这是杭州人眼中的四川,文中说蜀地有雾的日子很多,节候也较江南要早,风俗比江南更为俭朴,朱门娇媛,穷巷荆钗,其审美方式亦颇不相同。《西游纪》刻画陕西为:
气候寒于东南,惟西风而雨,独长安为然。……地产多黍麦,有稻一种名“线米”,粒长而大,胜于江南诸稻,每岁入贡天储。民俗质鲁少文,而风气刚劲,好斗轻生,自昔然已。
此处尽情摹写,对东南与西北的气候、物产、风俗皆加以比较。其中,还特别写到陕西的三原:“三原二城,中间一水,水深土厚,民物丰盛,甲于一省。”在稍后的《商贾纪》中,张瀚还指出:“至今西北贾多秦人,然皆聚于沂、雍以东至河、华沃野千里间,而三原为最。”可见,三原一带为陕商重镇,故而颇为富庶。张瀚又写到山西蒲州的情况:
渡黄河,即为山西之蒲州,州城甚整,民居极稠,富庶有礼,西北所绝无仅有者。俗尚多靡,中有山阴、襄垣二王,枝派繁衍,朱门邃宇,不下二百家,皆竞为奢华,士夫亦皆高大门庐,习为膏粱绮丽,渐染效法。
张瀚于山川佳处驻足流连,他描述了蒲州的富庶与奢靡,对当地明朝宗室(山阴、襄垣)之活动亦多所状摹。关于蒲州,在随后的《商贾纪》中,他还指出:山西“以太原为省会,而平阳为富饶。……独蒲坂一州富庶尤甚,商贾争趋”。可见,蒲州一带烟户繁盛,市廛辐辏,也是晋商重要的桑梓故里。平阳位于今山西省西南部临汾市一带,靠近陕西,黄河从其西面和南面流过,“平阳富庶甲于秦、晋,以秦、晋财货多出于途”,当地系山西、陕西最为富庶的地区,为秦晋商人商品流通的重要区域。
《松窗梦语》卷四的《百工纪》,谈的是百工技艺以及与此相关的奢靡风气,其中提到:北京是中国的政治中心,是个典型的消费性城市,全国各地大批的商品都汇聚于此。当时,商品主要的来源地是东南一带,所以从事百工技艺的人群也大多出自东南,其中,以江西、浙江、南直隶、福建、广东一带居多。接着,他又指出北京的奢靡风尚对全国的影响:
自古帝王都会易于侈靡,燕自胜国及我朝皆建都焉,沿习既深,渐染成俗,故今侈靡特甚。余尝数游燕中,睹百货充溢,宝藏丰盈,服御鲜华,器用精巧,宫室壮丽,此皆百工所呈能而献技,巨室所罗致而取盈。盖四方之货,不产于燕而毕聚于燕。其物值既贵,故东南之人不远数千里乐于趋赴者,为重糈也。……上有好者,下必甚焉。……今也散敦朴之风,成侈靡之俗,是以百姓就本寡而趋末众,皆百工之为也。
这一段文字是说,北京对于全国的奢靡风习颇有推波助澜之力,直接的后果便是人们纷纷弃本逐末,从而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
除北京之外,另一个对全国奢靡风习起引领作用的是苏州:“至于民间风俗,大都江南侈于江北,而江南之侈尤莫过于三吴。自昔吴俗习奢华、乐奇异,人情皆观赴焉。吴制服而华,以为非是弗文也;吴制器而美,以为非是弗珍也。四方重吴服而吴益工于服,四主贵吴器而吴益工于器。”这是从地域观照的角度,提到苏州对于明代社会风俗的重要影响。
从历史地理的角度来看,《松窗梦语》中最值得关注的是卷四《商贾纪》。该卷概括阐述了明代两京十三布政司的经济、文化及习俗,指出全国自然资源、经济地理的布局特点:
余尝总览市利,大都东南之利,莫大于罗、绮、绢、纻,而三吴为最。……西北之利,莫大于绒、褐、毡、裘,而关中为最。……夫贾人趋厚利者,不西入川,则南走粤,以珠玑金碧材木之利,或当五,或当十,或至倍蓰无算也。然茶、盐之利尤巨,非巨商贾不能任。……西北在茶,东南在盐。
在这里,作者以“东南”、“西北”将全国一分为二,分析了当时的经济地理布局,并举例加以说明。他说自己的祖先就是以丝织业致富,而在浙江,不少人皆以贩盐、卖茶发家致富。而在西北,畜牧业则占有重要的地位。作者还分省对明代两京十三布政使司的风俗做了颇为细致的分析。譬如,关于南直隶:
沿大江而下为金陵,乃圣祖开基之地。北跨中原,瓜连数省,五方辐辏,万国灌输。……自金陵而下,控故吴之墟,东引松、常,中为姑苏,其民利鱼稻之饶,极人工之巧。服饰器具,足以炫人心目,而志于富侈者争趋效之。庐、凤以北接三楚之旧,苞举淮阳,其民皆呰窳轻言少,多游手游食。煮海之贾操巨万资以奔走其间,其利甚钜。自安、太至宣、徽,其民多仰机利。舍本逐末,唱棹转毂,以游帝王之所都,而握其奇赢,休、歙尤夥,故贾人几遍天下。
根据张瀚的描述,南直隶风俗大致可分为三个部分,若以现代行政区划来看,即今江苏省的江南部分,安徽和江苏二省的江北部分,以及安徽省的江南部分。这里也提到苏州引领全国时尚,庐州、凤阳二府多游手游食之人,这些情况已见前述。至于“煮海之贾”,指的则是盐商。在明代,淮扬盐商相当著名,获利亦甚巨。根据差相同时的《广志绎》之记载:“维扬中盐商,其盐厂所积有三代遗下者。”而在淮扬从事盐业的,大多为徽州盐商。在明代,徽州的风俗颇为独特,“徽州多山少田,民逐末利,风俗日偷”。张瀚将以徽州为中心的皖南视作一个风俗区,有着相当的道理。特别是徽州的休宁和歙县,在明代中叶更以商贾众多闻名遐迩,以致官府在制定经济政策时,也注意到这种风俗。据明人吴子玉的《丁口略》一文指出:因休、歙之人多精于商贾榷算,故政府对当地的课税要高于徽州府的其他四个县。对此,虽然“休、歙二县民甚苦之”,一些地方人士也疾声力呼,要求取消此种不平等的重赋,但都没有什么结果。在此背景下,这种政策导向,无疑更刺激了徽州人计觅锱铢,纷纷外出经商。从《太函集》、《复初集》和《大鄣山人集》等明人文集来看,南直隶安庆府、池州府、太平府、广德州、宁国府等地,皆是徽商麇聚之区,这些地方,都不同程度上受到徽州风俗的影响。
除了南直隶外,张瀚对浙江风俗的描摹也相当精彩。他将浙江风俗分为三个部分,即杭嘉湖、宁绍温台和严衢金华。犀照之下,可谓无微不察。此种划分,与同时代其他人文地理著作(如《广志绎》)之描摹也大致吻合。
二十多年前,谭其骧先生曾撰文呼吁应积极开展历史人文地理的研究。他指出,中国人“对人文地理现象的记录和研究,至少可以追溯到成书于二千多年前的《禹贡》,而在司马迁的《史记·货殖列传》和班固的《汉书·地理志》卷末所载的‘域分’、‘风俗’中,对战国至西汉各地人民的生产、生活情况,农商工矿各业的盛衰和风尚习俗的差别,都有极其生动具体的叙述”。不过,汉以后的正史地理志忽视了人文地理的记述,有关人文地理现象的文献东鳞西爪,这种情况直到明代才有所改观。对此,谭先生特别指出,在明代,丘浚的《大学衍义补》、章潢的《图书编》、谢肇淛的《五杂组》以及王士性的《广志绎》,都是这方面颇为出色的论著。在他的倡议下,上述诸书都受到历史地理学界的重视,有的还出版了专门的研究论著。
从历史地理的角度来看,《松窗梦语》中最为系统、最有价值的是《商贾纪》。在我看来,《商贾纪》无论是谋篇布局还是行文措辞皆是在刻意模仿《史记·货殖列传》。事实上,在明代,《史记·货殖列传》受到不少人的追捧,张瀚并非绝无仅有的一位。在徽商的桑梓故里,成书于十七世纪初的万历《歙志》,卷十就是《货殖传》,其卷首提及:
太史公传《货殖》,班氏非之,谓其失受命之旨,乃亮之者,则曰太史公得罪,而汉庭诸公卿无有能为端木、子皮其人者,故发愤而为此,以为若皆白圭、乌倮耳,岂可与圣门高弟、霸国英臣等埒哉?其然是或然矣,凡史与志不必有此,而邑中不可无此。因尝反覆《货殖传》,而以当今之世,与邑中之人比之,盖亦有同与不同焉。
在编纂者谢陛看来,为商贾之乡歙县修志,不能没有“货殖”各传。为此,他仔细研读了《货殖列传》,并将歙县的现实与之相对照,从物产、城镇、人地关系、商人构成、社会观念和价值观变化等诸多侧面,详细分析了两者的不同。而在福建,何乔远所著的《名山藏》中也有《货殖记》,他指出:“余览传记,得富者数人,仿太史公作《货殖传》而为之……”从“货殖”一词的本义来看,此处的“货殖记”与“商贾纪”同义。
除了篇目之外,在写法上,《史记·货殖列传》较为系统地概述了“山西”、“山东”、“江南”和“龙门碣石以北”各区域的经济特点及其相互联系,深刻地指出了形成区域间差异的历史渊源和环境因素。而《商贾纪》也注重区域的划分、区域特征和人地关系等方面的观察与研究,将经济与文化、风俗诸因素综合起来加以考察。另外,从作者的生活年代以及作品的成书年代来看,张瀚的《松窗梦语》作于一五九三年(明万历二十一年),王士性的《广志绎》自序于万历丁酉,即一五九七年(万历二十五年),而谢肇淛的《五杂组》则出版于一六一六年(万历四十四年)。个中,无论是作者的生活时代还是著作的成书年代,皆以张瀚的《松窗梦语》为时最早,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商贾纪》对人文地理现象的系统描述,标志着《史记·货殖列传》、《汉书·地理志》相关传统在明代的全面复兴。
张瀚出生于工商业者之家,虽然他在《商贾纪》中也引用《周书》的说法:“农不出则乏食,工不出则乏用,商不出则三宝绝。”不过,他的总体思想落后于时代。在张瀚之前,江南一带早已出现“崇奢黜俭”的主张。此类主张认为,“俗奢而逐末者众”,奢侈可以提供诸多就业机会,令贩夫走卒易于为生,因此,当政者应“因俗以为治”,毋须强力禁奢。在这方面,张瀚的立场颇为保守。在《百工纪》中,他说自己在广东苍梧,某年灯夕,属下的封川县送来一盏纸灯,以竹篾为灯骨,又以花纸作为装饰,看上去似乎并不太值钱,但此类奇技淫巧,“束缚方圆,镂刻文理”,需要专精此业的工匠花费数十天的功夫方能制成。灯夕刚过,门隶就想将之毁掉,张瀚痛惜“积月之劳毁于一旦”,急忙制止。这让他想起自己家乡的风俗,浙江“灯市绮靡,甲于天下,人情习为固然。当官者不闻禁止,且有悦其侈丽,以炫耳目之观,纵宴游之乐者”。接着,他又发了一通感慨,说倘若贾谊再世,看到这种现象,不知要如何痛哭流涕而长太息:
今之世风,上下俱损矣,安得躬行节俭,严禁淫巧,祛侈靡之习,还朴茂之风。以抚循振肃于吴越间,挽回叔季末业之趋,奚仅释余桑榆之忧也!
《松窗梦语》卷七有《时序纪》和《风俗纪》,其中有不少都与张瀚的故乡杭州之风俗相关。在这一卷中,张瀚时常强调,“余遵祖训不敢违”、自己“世能守之”云云,以此凸显作为文人士大夫的守礼循规。在张氏生活的时代,世当承平,俗随世变,“金令司天,钱神卓地”,社会风尚极其奢华。残躯老迈的张瀚,疾声力呼反对其时的奢靡之风,但他生活在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十六世纪末期,安享着锦攒花簇轻裘肥马,却穷思极想,希望整个社会重返太祖高皇帝的时代,这岂非荒唐可笑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