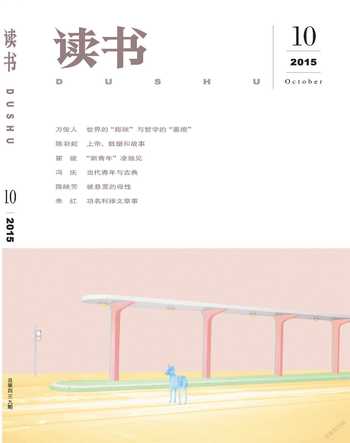民国汉译的价值
晚清以来,西力东渐,西方文化思想的著作也大量译成中文,最著名的如严复与林纾的译著,影响了整个二十世纪中国的知识界与文学界,使得中国文化的思维脉络为之丕变。除了西方思想经典、文学与实证科学著作的翻译,以实证方法系统化探讨中国文史的域外汉学,也对中国学术思想界产生了莫大冲击,改变了中国学术的著述方法与取向。
中国传统的知识结构,是按“经史子集”四库分类的,以儒家意识形态的经学为文化知识的砥柱,以史学为贯串历史经验的殷鉴,至于子部与集部,则是作为保存文献、扩大知识面的附带知识,可以耽情冥想,可以悠游玩赏,却都是边缘化的知识,无关圣教的弘扬,无关文化精髓的宏旨。西方文艺复兴之后的现代学术体系,在知识分类上,与中国传统大相径庭,讲究系统分科,不同知识领域各有其客观存在的价值,有其相对独立的目的与标准。日本知识界在明治维新以来,鉴于东方文明落后于西方的船坚炮利,率先效法西方,在追求“文明开化”、“脱亚入欧”的过程中,为日本学术发展循着现代西方的体例,建立了哲学、文学、历史学、经济学、法学、商学、物理学、化学、地质学、医学、农学、工程学、植物学、动物学等等新型学科,企图与西方学术齐头并进,从而影响了中国近代学术体系的发展。
“近代海外汉学经典丛刊”选印二十世纪上半叶出版的汉学译著百种,分为三大类:“历史文化与中国社会经济”、“语言文学与古典文献”、“中外交通及边疆史”,反映民国时期学术界重视西方及日本汉学研究的成果,借助他山之石,重新审视中国传统历史文化的意义,特别是开拓了传统学术忽略的领域。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学者如蔡元培、胡适都提倡“整理国故”,以理性实证的方法,对中国文化传统做出系统化的研究,是与这些汉学译著相辅相成的。这些译著除了介绍域外汉学的成果,还引进了崭新的学术研究方法与视角,有助于梳理中国文化传统的脉络,重新整合知识结构与学术体系。虽然这些学术著作不是中国学者的成就,无法纳入二十世纪中国文史学术的主脉,但是从中文译本的影响而言,起码也应当视为中国近代学术发展的支脉或潜流,不容忽视。可惜的是,到了二十世纪下半叶,因为两岸政治形势的变化,这些汉学译著,除了部分因王云五重新入主台湾商务印书馆,而得以在台湾做了少量的重印,在大陆的出版界,则完全受到遗忘,甚至在许多新成立的大学图书馆中也不见踪影。我们搜集了上百部尘封的汉学译著,呈现给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学术界,一方面是为了铭记前人为推展学术而做出的努力,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提醒新常态时期的学人,学术发展有其历史累积的脉络,可以从中汲取历史经验,温故而知新。
说到“温故知新”与这批早期汉学译著的关系,可以从两个方面来思考,以见翻译域外汉学如何反映了时代精神,为融汇东西方学术思维,重新阐释中国文化传承,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一是域外汉学的研究对象,以中国历史文化典籍为主,属于中西文化碰撞期间兴起的“国学”范畴,与五四新文化人物提倡的“整理国故”运动若合符节。研究中国历史文化,并赋予新的学术意义,是清末民初知识精英念兹在兹的心结。历史发展走到一个环节,时代的狂风扬起了批判传统的大旗,风中的英雄帮着推波助澜,却又无时或忘自己民族文化主体的未来,纠缠于“传统”能否“现代”的困境。域外汉学的出现,以西方实证方法研究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综合东西方各种语言文字材料,扩大了研究国学的眼界,即使无法打开中国文化传统是否走到尽头的心结,至少是提供了一个解惑的方向,在大雾弥漫的夜晚,看到了依稀渺茫的星光。
二是翻译域外汉学,有一种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吊诡作用,逐渐化解了中国文化思维中的自大心理与封闭心态,让唯我独尊的国粹基本教义派解除武装到牙齿的盔甲,转而吸收并接受西方实证研究的学风。民国期间新式教育制度的推行、学术体系的变化、大学学术专业的创建,具体到北京大学国学门的成立、中央研究院规划历史、语言、考古的研究领域,都与翻译域外汉学背后的旨意是息息相关的。因此,重新阅览这批民国期间的汉学译著,对二十一世纪的现代学人来说,温故而知新,不但可以窥知民国学人追求新知的心理状态,也会刺激吾人反思,认真思考学术研究方法与中国学术发展的前景,更进一步,探索文化传统的重新阐释与新知介入的关系。知识体系的变化当然与传统的重新阐释有关,是外因的影响大呢,还是内因变化的成分居多?
《论语·为政》记载孔子说:“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历代解经,对这个“为师”的道理,有两种相近似但又取向不同的解释。朱熹《四书集注》说:“故者,旧所闻。新者,今所得。言学能时习旧闻而每有新得,则所学在我而其应不穷,故可以为人师。若夫记问之学,则无得于心而所知有限,故《学记》讥其不足以为人师,正与此意互相发也。”虽然朱熹把知识分为“旧所闻”与“新所得”,强调的却是“学而时习之”,从中生发新的心得,也就是从诠释旧典中得到新知。这个说法与朱熹在鹅湖之会以后,作诗唱和,写给陆九渊的诗句,“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涵养转深沉”,异曲同工,是一个意思,万变不离其宗,旧学与新知是同一个脉络的知识学理。
然而,有些朱熹之前的经学家,解释“温故知新”,却有不同的取向。皇侃《论语义疏》就说:“故,谓所学已得之事也。所学已得者则温燖之不使忘失,此是月无忘其所能也。新,谓即时所学新得者也。知新,谓日知其所亡也。若学能日知所亡,月无忘所能,此乃可为人师也。”皇侃明确说到,“故”指的是过去所学的知识,而“新”则指的是新近学到的知识,新旧结合,相互发明,就可以“为人师”了。邢昺《论语注疏》循着皇侃的思路,也说:“言旧所学得者,温寻使不忘,是温故也。素所未知,学使知之,是知新也。既温寻故者,又知新者,则可以为人师也。”这里讲的“素所未知”,就不只是研读旧学,有了新的体会,从过去的传统中发展出的“新知”,而是从来没听过、没想过的新学问了。这种“素所未知”的新学问,结合“旧所闻”,对习以为常的知识框架,就会产生巨大的冲击,而出现飞跃性的结构变化。知识内容或许大体沿袭传统,知识结构却得以重新整合,出现崭新的认知系统,重新审视自己文化传统的意义,打开文化传承的新局面。二十世纪上半叶的汉学译作,就发挥了这样的作用,促使中国学者放弃自我中心的文化态度,从各种不同侧面,探知中国历史文化的光谱,以域外(或是全球)的角度观测中国传统,摇动了文化的万花筒,看到七彩缤纷的中国。
严复在甲午战争之后,改良变法思想风起云涌之时,开始大量翻译西方思想经典著作,是有感于国人(特别是传统文化孕育的知识精英)思维系统封闭,企图介绍实证新知,引进逻辑思维的方法,以破除儒学之道“一以贯之”与“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虚妄。他翻译《天演论》,在序文中提到,有人归纳东西方学术思想,认为中国文化重精神,是形而上之学,立意高超,而西方文化重物质,是形而下之学,只追求功利的回报。他认为,这种自以为是的蒙昧态度,陷入传统旧学的框囿而不自知,没有自我反思的能力,无法吸收“素所未知”的新知识,也就无法开展并弘扬自己的文化传统。严复非常清楚他翻译西方经典的目的,是为了介绍新知,打破中国传统思维的封闭性,但是,作为披荆斩棘的拓荒人,他深知思想封闭者的顽固心理,必须因势利导,以免遭到盲目卫道之士的攻讦。严复有其防身的策略,不会像许褚战马超那样赤膊上阵,而是以桐城文章译述赫胥黎、斯宾塞、穆勒、亚当·斯密、孟德斯鸠,博得晚清知识精英的赞许,由文章深闳而传入了新知义理。从文化变迁的角度而言,通过翻译,以迂回战术来介绍西方思想,得到巨大的成功,产生了改变传统思维体系的实效,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影响深远的大事。以此类推,民国时期大量翻译域外汉学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思想史课题。
关于清末民初西方学术思维冲击中国知识精英,颠覆传统文化的知识结构,钱穆在《现代中国学术论衡》的序言中,从中国文化本位的立场,发出深刻的感慨,做了笼统的批评:“文化异,斯学术亦异。中国重和合,西方重分别。民国以来,中国学术界分,务为专家,与中国传统通人通儒之学大相违异。循至通读古籍,格不相入。此其影响将来学术之发展实大,不可不加以讨论。”钱穆所指出的问题,是传统知识体系强调“通”,文史哲不分家,最崇尚通儒,而现代学术讲究专业分科,各司其职,以至于读不通古籍呈现的整体性知识思维。姚名达在撰写《中国目录学史》的时候,对西力东渐,西潮带来的翻译著作及新知新学,也有类似的感慨:“‘四部’分类法,不合时代也,不仅现代为然。自道光、咸丰允许西人入国通商传教以来,继以派生留学外国,于是东西洋洋籍逐年增多。学问翻新,迥出旧学之外。目录学界之思想不免为之震荡。”这种对学术体系发生重大变化的观察,反映了中国学人从晚清一直到民国,夹在东西方两种不同思维体系的冲突,身历其境的切身感受,因此感触良多。
二十世纪上半叶最能代表中国学术的通儒是王国维与陈寅恪,他们浸润了经史子集的四部知识传统,承继乾嘉笃实的考据学风,却都经过西洋逻辑思维与实证科学的洗礼,参与中国知识结构的转型。对西方现代知识结构如何在中国生根发芽,不但再三致意,并且以自己的学术实践来努力促成。王国维早在一九○二年就写信给张之洞,反对把经学列为大学分科之首,而主张效法西方与日本的大学,设立哲学科,明确指出知识结构的分类不可因循传统,而必须另起炉灶。陈寅恪在一九二五年就清华大学建制的问题,写了《吾国学术之现状及清华之职责》,指出大学的职责在于学术之独立,而中国学术界的情况令人十分不满,必须认真效法西方学术的体制及实践。他说:“盖今世治学以世界为范围,重在知彼,绝非闭门造车者比。”这两位国学大师,对西方与日本的汉学研究十分注意,都是以开放态度对待域外汉学研究,集思广益,以成其大家。
再回到“温故知新”的历代经解,说说文化传承的阐释学意义。刘宝楠在《论语正义》中指出,上古之时,文化知识是上层统治精英的家学,不再治理实际政事的长者可以传递德行的知识,可以为人师。“温故而知新”,就显示长者不忘旧时所学,且能吸收新知,继承并发扬这种学术与政治合一的传统。到了孔子之时,时代出现了变化,士大夫不见得能够谨守家法,弘扬德行,也不一定能够“为师”了。孔子之后,世变日亟,“道术为天下裂”,文化知识不再为少数统治精英所垄断,也不必然与治理政事有关,学术在民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但是,学术知识发展的脉络基本未变,仍然是要温故知新,进德修业。从刘宝楠不经意的阐释中,可以看到时代变迁影响了学术文化的内容,改变了知识结构的体系,但其内在发展的理路仍旧,还是需要旧学与新知的融合,才能有所发展。
刘宝楠还引述了刘逢禄的解释:“故,古也。六经皆述古昔、称先王者也。知新,谓通其大义,以斟酌后世之制作,汉初经师皆是也。”刘宝楠赞成这个说法,并指出,汉唐人解释“知新”,大多数都沿用此意。也就是说,旧学是传统的知识结构体系,新知是时代变化出现的新知识,必须相互斟酌,才能发挥得宜。至于如何对旧学“通其大义”,就见仁见智,各有说法了。从这个通达的诠释来讨论近代西学东渐的情况,我们可以看到,“温故而知新”在民国学人的心底,是产生“传统”与“现代”纠葛的心理陷阱,不易跨越。若依照朱熹的说法,“学能时习旧闻而每有新得,则所学在我而其应不穷”,虽然在哲理上可以模模糊糊说通,但在清末民初的具体历史时代环节,西学的新知属于完全不同的知识体系,在原有的旧学脉络中,根本无从立足,如何“其应不穷”?所以,真要放之四海而皆准,提升“温故而知新”的普世意义,以理解域外汉学译著与近代学术知识体系变迁的文化史意义,我们认为,皇侃、邢昺,一直到刘宝楠的阐释,是比较合适的,并与现代文化阐释学的说法相近的。
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在他的名著《真理与方法》中,说到认知理性与文化传统的关系,特别指出,人们通过理性,来判断历史文化中事实的真相,但是人的理性与生存环境息息相关,与传统所衍生的丰富文化底蕴有关,不可能完全超越文化传统的思维脉络。他认为,人生活在文化传统之中,就不可能“遗世独立”,以全能超越的抽象思辨来认识传统,甚至是批判或颠覆传统。传统是历史文化延续与传承的表征,不会一成不变,而我们的认知理性也会因时代变迁,而不断重新诠释传统。伽达默尔的阐释学以西方文化传统为例,说明新知如何纳入传统,而使文化传统生机不断,生生不息,与中国历代经学家的说法(朱熹除外),有异曲同工之效。以此观照民国时期的汉学译著,我们认为,这批学术新知传入中国,对中国文化传统的繁衍与发展,实有承先启后之功。
道术之存亡,全在人心之向背。这批民国汉学译著重新问世,对我们生长在承平之世的学人,应当有激励的作用,为学术研究多尽分力,让中国学术发展更上一层楼。
(“近代海外汉学经典丛刊”,郑培凯主编,山西人民出版社即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