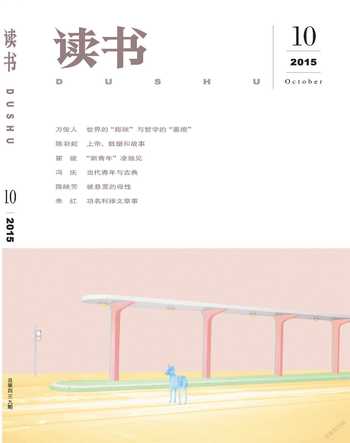外位性理论与个人主义的危机
罗卫平
方方的小说《涂自强的个人悲伤》二○一三年初发表之后,引起了颇大的社会反响,成为诸多青年文学研究者近年来讨论最多的小说之一。这部小说之所以特别触动青年研究者,是因为大家了解大学毕业后变成“蚁族”的同辈青年的境遇,也对“拼爹”现象日趋严重和贫困代际传递的现状感同身受。这部小说最后通过涂自强同学之口,说出了“蚁族”青年涂自强的悲剧包含的问题:“这果然只是你的个人悲伤吗?”有评论者指出,这一悲剧事实上呈现了个人主义意识形态在今天遭遇的危机,人们强烈意识到,社会关系和社会资本积累对于个人生活历程的高度重要性,开始从经验上发现,八十年代以来彰扬的“个人奋斗”意识其实只是一种错觉,个人总是处于一定的社会关系结构之中。这样看来,个体的自我需要直面自我如何建立与他人的社会关系的问题,包括个体之间通过何种形式组织起来的问题。
这也提示我们,个人主义应该成为理论反思的对象。而从这个角度切入,或可重新理解巴赫金对话理论的内涵和意义。巴赫金的对话理论揭示了一种值得探究的主体构建图景:人无法脱离他者而存在,自我与他者对话的过程,也就是主体构建的过程。他指出,“理解”的对话性特征,根源于“我生活在他人话语的世界里”这一基本事实。“我的全部生活”,都是在他人话语中定位,都是对他人话语的反应;“对每个人来说”,“用话语表现的一切”“都分解为二”,一个是自己的话语的狭小世界,另一个是他人话语的无边世界,“这是人类意识和人类生活中一个基本事实”(《巴赫金全集》第四卷,407页)。人无法脱离他者而存在的状况,就是所谓“外位性”。巴赫金所说的外位性(空间上的、时间上的、民族的)是“理解”的本质特征,所有理解都有外位性,并没有那种不需外位性的“理解”,“一般来讲,要摆脱外位因素的实体存在恐怕是个无法实现的任务”(同上,521页)。巴赫金毫不客气地指出,上述基本事实其实“至今很少研究(很少被人意识到),至少没有意识到它那重大的原则性意义”(同上,408页)。
由此看来,把握巴赫金关于自我与他者对话的论述,外位性理论是关键。邱运华在收入《静默的旋律—学术史与文化研究》的多篇论文中,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他指出,外位性理论贯穿了巴赫金的全部学术活动,进而成为一种有关人文学的理论。巴赫金在《论人文科学的哲学基础》和《人文科学方法论》等札记中明确指出,所有的人文学科都带有外位性和对话的特征,如果我们认为有的人文学科并不具有外位性和对话的特征,那只是我们并没有意识到而已。
巴赫金将精密科学与人文学科相对比,指出人文学科是主体对主体的认识,“只能是对话性的”。精密科学是“独白型的认识形态”,其中只有一个主体—认识(观照)和说话(表述)者,与他相对的“只是不具声音的物体”。但是,人文学科是一个主体对主体的理解,主体本身不可能作为物来感知和认识,因为他作为主体,“不能既是主体而又不具声音”。因此,认识另一主体的积极性,就是“认识者的对话积极性”(同上,379页)。在巴赫金这里,对话性是“理解”无法摆脱的特征。
巴赫金指出,在研究“语言”以及“意识形态创作的各个不同领域”时,人们避而不谈“所有话语都分为自己的和他人的两类”这一基本事实,而是认为存在着一个“抽象的第三者立场”,人们把这个第三者立场等同于一般的“客观立场”,等同于一切“科学认知”的立场。他认为,在“抽象的科学认知领域和抽象思维领域”中,才可能有所谓“第三者立场”和“客观立场”,但在人文学科(“关于精神的科学”)中不可能有这样的立场。人文学科的研究对象,不是一个“精神”,而是两个“精神”(一个是被研究的精神,另一个是从事研究的精神,两者不应合为一个精神),是不同“精神”间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对于巴赫金而言,那种认为人文学科有“第三者立场”和“客观立场”的看法,不过是对人文学科的一种假想和误解。
巴赫金对外位性和对话的思考,是在康德将人视为认识主体与认识对象的复合体的基础上的推进。福柯在论述人文学科的重要著作《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中分析了作为现代思想和人文学科基础的康德的“人类学”,那就是,“当自然史成为生物学,当财富分析成为经济学,尤其当语言反思成为语言学,以及存在和表象共同所处的那个古典话语消失时”,人与其模糊位置一起出现,“即作为知识对象和认识主体:被奴役的君主,被注视的观察者”(《词与物》,莫伟民译,406—407页)。在这样的关于人的“有限性分析”中,人是一个“经验—先验复合体”,人既是认识的主体又是认识的对象。在福柯看来,这一“经验—先验复合体”形成之日,才是现代性的开端,而不是“人们想要将客观的方法运用于人的研究的那个时刻”。福柯的这一分析,指出了康德的批判哲学带来的哥白尼式革命,将西方现代人文社会学科的基本问题设定为“我如何能知”,而不是古典时代的“我知道什么”。《发言与讲座》所收的“巴赫金的讲座”(一九二四年十至十一月)显示,当时巴赫金特别关注新康德主义马堡学派,并与《审美活动中的作者与主人公》的写作有密切关系。其中指出,“康德的了不起”就在于打破了人仅仅作为“自然主体的整体”这样一个“统一体”。参照福柯的分析,在古典时代,知识与普遍智力训练的恒常而基本的关系,证明了有关一个最终统一的认识体(un corpus)的设想,而在十九世纪初,智力训练的统一性被打破了,突破途径之一是区分先验主体性与客体的存在方式。
巴赫金承续和推进了康德有关人作为认识主体的有限性的思考。在康德那里,作为认识主体的人存在于各种经验事物构成的可能性条件之中,具有历史的厚度与纵深,同时也是有限的。同时恰恰基于这种有限性,人会不断努力去突破这些局限,从而使现代生物学、经济学和语文学得以诞生。在巴赫金这里,外位性与对话理论进一步凸显了“他人话语”对于人这一认识主体不可或缺的限制性意义,即“他人话语”是主体形成的条件。“我”只有在与其他的对话者互动的过程中,只有通过他人的话语,才能形成自我的主体意识,这是“我”的有限性所在。
巴赫金相对于康德最为重要的突破是,他认为主体认识活动的主要空间在于话语层面。无论是外位性,还是对话,都是就话语(自己话语与他人话语)而言的。巴赫金提供了一个在话语空间中构建主体性的特别场景,那就是,在多种“语调”对话构成的话语网络和话语场域中,自我总是在某个时刻获得某个暂时的位置。“外位性”意味着自我构建的一个必要条件是,自我内部要包含有异质性的他者存在。自我内部的他者与自我无法分离,但自我也无法将异己的他者完全吸纳。因此对于自我而言,“外位性”也有内在性的一面;“对话”是外在性与内在性的结合。总的来看,居于流动位置的自我,既不是意义的仲裁者,也没有真理在手,只是不断通过与他者的对话构建自身,这是自我的主体性构建的基本事实。
在认识“我生活在他人话语的世界里”(以及必须通过“他人话语”构建主体意识)的基本事实的基础上,人们可以自觉地运用外位性这一“最强大的推动力”,以尽可能地发挥创造性和充实自己。巴赫金批判“教条主义的惰性”,认为抱残守缺的教条主义“不可能自我丰富”。他指出,“理解者不应该排除改变或者甚至放弃自己原有观点和立场的可能性。理解行为中包含着斗争,而斗争的结果便是相互改变,相互丰富”(《巴赫金全集》第四卷,406页)。在文化对话和经由他人话语构建自身主体性的过程中,“‘我’和‘他人’永无休止地互相争论”要更为重要。并不是客气和谐的并存才是对话,反而是互相争论使得对话更有分量、更有意义,使得自我主体构建更为充实。对于自我与他人社会关系的建立、对于社会共同体营构而言,这无疑是真知灼见。
(《静默的旋律—学术史与文化研究》,邱运华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二○○三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