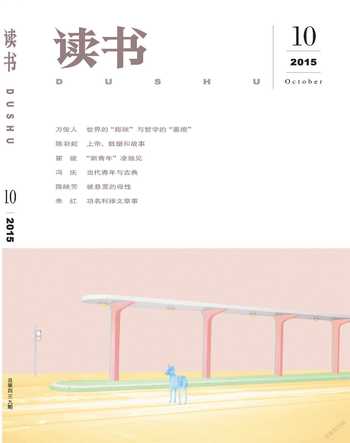“新青年”凌独见
瞿骏
新文化运动中的读书人之竞争当然不乏激烈而残酷的一面,但它与戊戌时的新旧之争最大的区别是当年读书人尚觉得有教可“翼”,且要杀人翼教。而到新文化运动时早已是“天下为学说裂”的时代,对绝大多数读书人来说不过是谁更加“趋新”的程度区别而已,名教的房子基本已被他们自己有意或无意地拆光了。而此时“主义”的时代又未真正来临,“人间正道是沧桑”之类的你死我活还要等上数年,因此,对当时的读书人之争应多从其社会上升的追寻、关系网络的分野与“思出其位”的冲动等方面来加以考察。
今年是新文化运动一百周年,“凌独见”这个名字对这场运动来说似既有些熟悉,又有些陌生。说他熟悉是因为这个名字出现在几乎每个关于浙江、关于杭州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叙述中,在这些叙述里,凌氏好像堂吉诃德,以一人之力执笔一本叫《独见》的周刊,一期又一期地写文章与施存统等人“作战”。说他陌生是因为在同样的历史叙述里,凌氏好像仅仅是作为五四新文化和施存统等人的对立面和背景墙而存在。谁又真的在意过这个曾活生生地与大历史相碰撞过的青年呢?就我有限的阅读来说好像极少。而在我看来此人的故事恰正可成为今日我们重新理解新文化运动的一把钥匙。
关于凌独见,现在的状况是几乎所有成果都既不知凌氏早年,也未读过《独见》周刊文本,但在缺乏史料的基础上对其人、其刊的大论却比比皆是,更不用说探究凌氏言行引发的反响和凌氏离开浙江第一师范学校后的生命轨迹。其中最典型的迷思为从即时的亲历者阮毅成开始,到今日不少研究者竟都认为《独见》周刊“全用文言文”!这是稍翻一翻书就能解决的问题,因此重构凌氏的生活史或相当必要。
凌氏名凌荣宝,浙江衢州江山县溪滩乡人。有说其眇一目,故又号独见;又有说其出过天花,相貌丑陋,满脸麻子。家中为小业主,在杭州官巷口开一家规模不大的柴炭店。据其自述,民国四年即《新青年》创刊那一年他已写了不少白话诗,其中一首《狂风》云:“半夜忽然起狂风,吹得门户叽咕吆。梦中糊涂未细辨,惊呼有贼撬墙洞。”另一首《城站酒家》云:“城站一带酒家多,生意盛衰竟若何。炉前如有年少妇,可断酒客必满座!”大概一九一九年中,凌氏进入浙江一师,成为一师“二部”的学生。这个“二部”指的是非一师本科,而是中学毕业或小学教师来一师培训一年者。凌氏在一师的“显山露水”当然开始于严厉批驳《非孝》的《独见》周刊。这份杂志据《五四时期期刊介绍》说现存第1—4号,仍待查。但《介绍》和《浙江省青年运动史研究参考资料》等书都引述了不少《独见》里的文章,从其内容看非但不用文言,凌氏的文字和文风委实“新”得可以。他不但能够直接用白话与白话争,且几乎将当时所有时髦的新文化概念都熟练运用到了其文章中去。
如他在“发刊词”中就说:“中国旧社会的黑暗,要变他为光明,我以为只有教育这条路。有了教育,什么真理啊,人道啊,一起涌现眼前了。至于平等、自由、博爱、互助等,也尽在其中了。不过我程度很浅,能力很薄,又在求学时代,还要请大家本了互助的精神来指教我才好,研究教育道德,是我的主要旨趣。”
正因为凌氏的文字压根不是“翼教”文字,但又不属于新文化中最激进的层次,因此除了一师那些与他有直接冲突的学生,不少人实欣赏或至少表面上认同《独见》与凌氏其人。时任《星期评论》主编的戴季陶就曾给他写信说:“我很欢喜你的勇气和精力。很希望你做一个自由的研究者、批判者。”白屋诗人吴芳吉亦曾邀凌氏为他主办的杂志《新群》作文。在吴芳吉看来,凌氏“一人自创一报,自当编辑,自当发行,自己去投送,自己去贩卖,其言论极平允”,因此“可与漳州之《闽星》、广州之《民风》为沿海言论界之领袖”,但世人“都以为(其)位卑言轻,皆忽之”。而据一九二一年浙江新塍小镇中几个新人物所办的《新塍半月刊》,其东栅的竺饮冰家设有借书处,新的杂志很多能在那里看到,其中既有《浙江新潮》,又有《独见》。
正因如此,凌独见在“非孝”之争中虽遭到学生自治会的“公审”,树敌不少,导致他有些黯然地离开了浙江一师,但亦较成功地建构起了自己的一个关系网络。夏衍曾回忆:“办这份报(《独见》周刊)的绝不是(凌独见)一个人,所谓‘独见’也绝不是一个人的见解,在他后面,显然还有一个有力的‘校长团’的背景。”
夏衍此话若是说独自办刊的可能性未免把人看小,当时一人独办一份杂志的大有人在。日后与胡适有过激烈交锋的温州瑞安才子林损就曾一个人办了《林损》杂志,而且办得还相当不错。但夏衍说凌氏后面不乏有力背景,实应有根据。但此事究竟是有意布局,还是顺水推舟,因史料关系不得而知,但凌氏因此而与当时的浙江省教育厅厅长夏敬观(剑丞)攀上了交情却是肯定的。一九二○年夏氏专门给张元济去信推荐凌独见,说他“浙江师范毕业,续往龙门师范,今年毕业,善白话文”。这里颇值得玩味的是与遗老过从甚密且作为保守势力代表的夏敬观以“善白话文”来推荐凌氏,此种推荐一方面反映了当时青年谋事的时趋所在,另一方面亦在相当程度上展示了夏氏实知道凌独见有多“趋新”。
不过对夏敬观的推荐,张元济似未特别上心,据他日记说是“久已忘记”。至一九二○年十月初突然想起朋友有托,才急匆匆地帮忙办了。由此不难推测尚名不见经传的凌独见需证明自己有能力在大城市立足,而其证明的利器或正是以“白话文”、“国语”等为标识的新文化。
一九二一年大约十一月凌氏赴北京参加教育部办的第三届国语讲习所。在讲习所内,凌独见做过不少新文化大家的学生。如由黎锦熙讲“国语文法”和“国语教学法”,钱玄同讲“声韵沿革”,胡适则正好讲“国语文学史”,这为日后两人的交锋埋下了伏笔。在北京的凌独见曾在“新文化”传播的重镇《晨报副刊》上发表过两篇文章,颇能见其当时的心态。在《一个杭州人眼光里的北京》中,凌氏强调自己是一个“生在杭州,长在杭州的杭州穷鬼”。在另一篇文章中凌氏则说自己去看了“嗜好的新戏”—北京实验剧社编的《英雄与美人》,见到了“久仰的陈大悲先生”,“花了不多的铜元,得到不少的快乐,着实值得了”。戏看完,回寓去,“在路上,狂呼跑跳,我的同学见了,都说独见发疯”。上述文字不难看出一个刚到北京的外省青年的自卑感和新鲜劲,以及为掩饰这种自卑感而故作的格格不入和寻找到新刺激的真情流露;同时也颇能见凌独见一直走在不断“趋新”的道路上,正如他在文章里所说:真正好戏是让“人们走做‘人’的路,到大同的世界去”!
到一九二二年最早不超过八月中旬,凌独见出版了一本《国语文学史纲》。此书出炉的背景是一九二二年三月浙江省教育会办国语传习所,要凌氏去讲国语文学史,他答应了,因此要编讲义。而省教育会特别请凌氏去讲国语文学史和他参加过教育部办国语讲习所,已是省内的“国语专家”密切相关。除了能在省国语传习所授课外,凌氏亦有资格在浙江省内各地巡回演说“国语”和“国音”,按照胡适给他们的寄语就是各位“回各省去,负的责任很大”。
不过凌氏上一年既已听过胡适的“国语文学史”课,且“(文学史讲义)胡适之先生已编到十四讲了,大可拿他来现成用一用”。那么凌氏为何不用,却执意要“另编”呢?据他说是因为在文学史上和胡先生意见有“不大同的两点”:
一、他只主张从汉朝说起,我却主张从唐虞说起。二、区分时期上,他只分两期:北宋以前为第一期,南宋以后为第二期。我却认为要分四期,自唐虞到周为第一期,自秦到唐为第二期,自宋到清为第三期,民国以后为第四期。
或正是得之于胡适,又力图区别于胡适的缘故,凌氏的《国语文学史纲》呈现出“新”的状态,但又露出些“旧”的马脚。说其新,是因为此书用“国语”写成,标题横排,并特地加上了标题的注音符号;内文竖排,用新式标点。而说其有些“旧”,则因其序言是夏敬观和马叙伦所作,其中马叙伦被新青年,尤其是鼎力支持胡适的顾颉刚、傅斯年等视为“旧派”,且他亦对胡适的观点经常有直接的反对。一九一九年顾颉刚即说:“马叙伦一辈人,做什么读书小记,什么校勘记,什么疏证,他自以为是一个大学者;他心里也不晓得学问是什么东西;不过是他晓得有了名,受人恭敬,是很快乐的。这辈人的结果,只是个绝物。”又说:“马叙伦在杭,痛骂胡先生以《水浒》、《红楼梦》教学生,又说他的《哲学史》误处甚多,修改不了。但没有举出理由来。马之为人,妄得可笑!”傅斯年更是在《新潮》上直指马叙伦的《庄子札记》是“自居创获之见,实则是攘自他人而不言”,如卷十八第五至八页中“所有胜义皆取自胡适之先生《中国哲学史大纲》第九篇第一章七、八两页”。
若继续细读,我们会发现夏、马二序中对《国语文学史纲》的荐语均有些大而化之,不着边际。夏敬观说:“凌君独见以近编国语文学史见示,并属为序,意其盛也!撷其内容,条理明晰,取材丰盛,甚足为后来编文史之参考。”马叙伦则说:“凌君有鉴乎此,抉择古今文辞之具有特性且能与时代相辉映者,凡千数百首,绎而条陈之,为《国语文学史纲》,书成属序,喜其方颇精审,足为文史之鉴也。”这都表现出二人实未必认真读过此书,夏敬观大概是碍于旧情,而马叙伦则或见其开篇即与胡适意见相左,而在一定程度上引凌氏为同道。
同时凌独见也未必与作序二公意见一致,反倒在不少看法上承袭胡适。这一年(一九二二)他在《杭县教育杂志》上就发表文章夸赞胡适解释文学的话说得好,并直接引胡适的话说:“《石头记》、《水浒传》等书,是禁不绝的,你们不许学生看,学生还是要偷看,与其偷看,不如当官看,不如有教员指导他们看。”
此语出自《中学国文的教授》,载于《新青年》第八卷第一号(一九二○年九月),这又一次证明了所谓的“卫道青年”凌氏不但读《新青年》,而且深受其影响。更有趣的是,据《国语文学史纲》的封底广告,凌独见同时还写了另一本书叫《新道德》,在“德目篇”中他列举了仁爱、劳动、自由、平等、互助、正义、中和、智慧、人道、创造等十个条目,亦可见凌氏对于“新文化”的把握和追随的程度。因此凌氏要夏、马二公作序,大概只是由于《国语文学史纲》初版,出版机构和作者都寂寂无名,想借助夏、马二公(马继夏之后做过四个月的浙江省教育厅长,后来在浙江教育界与黄人望有“马黄党”之称)在浙江省乃至全国的名气和势力罢了。
转过年去,凌氏的“国语文学史”开始引发新的波澜。一九二三年二月凌氏的《国语文学史纲》改名《新著国语文学史》再版(以下简称“凌著”)。此次再版在内容上基本无改动,但值得注意的变化有三:
一是这次凌著的身价大增,是由全国最强大的出版机构之一—商务印书馆来发行。
二是在夏、马二公的序之外,凌著加上了与作者有国语讲习所 “师谊”的黎锦熙之序言(有趣的是商务为求出书之速,到二版时竟连原书目录都忘了改动,仍是“自序”,而非“序三”)。黎氏序言颇“别出心裁”,用注音符号写成,再由章寿栋译成白话文,以一序两版的面貌出现在书中。此外黎氏不像夏、马二公说此书是“精审”、“明晰”、“足为文史之鉴” 云云,而是意味深长地指出自己不过是“大略地翻了一翻”,觉得“搜集材料很不少,足表示他读书的勤快”,因此很赞同凌氏说此书不过是一部“读书录”的话。黎氏的保留当然是有原因的,稍后详论。
三是商务印书馆为求销路,将凌著从国语传习所讲义摇身一变为“中学用书”,因此新版封面加上了“中等学校用”字样,《教育杂志》的广告中亦说凌著“材料丰富得未曾有,为中等学校最切用之教本”。
正是这些“变动”引发了胡适及其同人的注意,他们开始有所动作。
一九二四年八月七日《晨报副刊》发表了章衣萍的长文—《糟糕的国语文学史》。此文对凌著展开了凌厉的攻击。据章氏说,“一个整年多前”在胡适家中,“先生一手拿着纸烟,一手执着笔作文”,笑嘻嘻地对着桌上的凌著说:“糟糕,商务印书馆竟出版了这样的书!”胡适的话让章氏起了大好奇,过几日在书摊买了凌著来读,一读之下章氏对凌著的意见甚多,觉得这真是一部“糟糕的国语文学史”:
首先章氏觉得“楹联”没有资格入文学史,而凌氏竟把“我是一片婆心把个孩儿送汝,你做百般好事留些阴骘与他”这样的“育婴堂联”也写入其中。在章氏看来:“把孩儿丢在育婴堂里是不是一片婆心?试问是不是受经济压迫或者是旧礼教压迫(如私生子),才把孩儿丢在育婴堂里?凌先生,你老如是相信阴骘的,我劝你赶快把这本国语文学史的版毁掉,省的贻误人家子弟,流毒无穷!”
其次章氏嘲讽凌氏把前文提及的自家白话诗也写入文学史,讥讽道:“中国近代就是无诗人可入文学史,也何至于劳及凌先生!”
最后也是最严重的指责,在章氏读来,凌著可分两部分:“一部分是暗暗抄袭胡(适)著《国语文学小史》(按即胡适在国语讲习所的讲义)的,大体上还说得过去,一部分是凌先生自己做的,像汉以前的文学,宋以后的文学几章内,引证的错误,诗词句读的荒谬,论断的离奇,真可令人大笑三日。”
章文一出,八月十二日《晨报副刊》就有署“直陈”的文章回应章氏的意见说:“衣萍君所指出来的‘育婴妙联’,衣萍君说是‘糟糕’,说是凌君‘相信阴骘’,还不知道这是乡下人挂在送子娘娘面前通俗的对联呢?妙呵,妙呵,简直是‘糟糕’。”
之后,各种对凌著的批评意见层出不穷:一九二五年有署名“长弓”的在《现代评论》上发文说:“当国语文学史—凌独见底—产生以后,虽说有许多批评者指责牠,我总是想我们不当它是国语文学史,当它是国语文学读本去看;因为那里边引的诗词是很多的。我们看了至少要知道某朝代某作家的作品怎么样”,但是“前天没事,将它拿出来随便一翻,却给我了一个大问题”。这无疑是说凌著非但不能做“文学史”读,连作为“国语文学读本”的资格都没有。
到一九二九年章氏将《糟糕的国语文学史》一文又收在了他的自选文集《古庙集》里,由北新书局出版。同年谭正璧在《中国文学进化史》中说:“凌独见的《新著国语文学史》,差误百出!” 一九三二年,胡云翼在他的《新著中国文学史》自序中说:“这些著者对于中国文学多未深刻研究,编著时又多以草率成之,卒至谬误百出,如凌独见、周群玉之著,其错误可笑之处真触目皆是,文学史书堕落至此,实堪浩叹!”这本书又是北新书局出版的。
这些批评意见大致可证明凌著的水准确不甚高,甚至有剿袭之嫌,难怪黎锦熙对此书并不大加颂扬。但除了对凌著的质量有所判断之外,对我们而言,凌著和凌氏其人背后所反映的新文化运动曲折反复的各种面相可能才是更重要的话题。综合前文我们可以发现凌氏无论从其家庭出身,还是教育程度,甚至是形容样貌都属于“民初那些介于上层读书人和不识字者之间,但又想上升到精英层次的边缘知识分子”,因此新文化最符合他“社会上升”的需要,他也早早地接触并熟习了他所能获得的“新文化”。但这里的重点在于以往多认为启蒙本身就具有强大的魅力,似乎德先生、赛先生、穆姑娘等一出现,就会俘获人心,让人自动地去阅读和接受新文化。其实对于边缘知识青年来说,这些概念和其背后的知识与思想固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吸引他们,但更大的吸引力来自新文化和新思想在其人生中“形形色色的使用”,理解了这一点我们才能重新梳理“非孝”之争背后的凌独见们和施存统们。对于他们来说,比理念之争更重要的或是吸引新文化大家的注意,获取社会的关注,积累自身的声名。而从结果看,这批从浙东僻壤走出的青年—施存统、凌独见、曹聚仁等都获得了“出其位”的成功,远离了他们原来被规定的回山区家乡担任穷教书匠之路,从“五四”开始拥有了走向全国舞台的可能性。而之后凌氏的生命轨迹正是从属于这一逻辑的,即不断通过新文化运动拓展出来的各种时势来争取其赫赫之名与显著声光。在这一过程中上下之互动呼应异常明显。在上,北洋政府教育部往往出乎推动者意料地颁布让新文化运动大发展的部令章程。一九一九年底蔡元培不过是听说“教育部决定中学国文兼采白话文”,就觉得“将来白话文的发达很有希望了”。到民国九年(一九二○)教育部竟就颁布小学教材改语体文通令和公布《国音字典》。无怪乎黎锦熙会认为这意味着“中国政府竟重演了秦皇、汉武的故事”,是“四千年来历史上一个大转折的关键”。在下,知识青年则持续利用政府强力推行“新文化”的契机来改善其社会地位。正是从一九二○年起凌氏以“善白话”谋成了事,以“国语”、“国音”闻名省内,进而获得机会编写国语文学史讲义。又正逢商务、中华等巨鳄都欲抓住“国语”、“国音”之大商机赶着大量出书,凌著遂能应运而生。
不过时代的多变与善变给了凌独见这样的边缘知识分子相当多的机会,但也给他们带来了无穷的困惑。在商务印书馆出版著作既是凌氏一生辉煌的顶峰,但又因新文化大家的封杀而成为其再次转向寂寂无名的起点。一九二八年九月常熟的一个士绅因黎锦熙为胡适《国语文学史》写的代序而对凌著发生了兴趣,但却遍寻无着。而此时的凌独见或正在《申报》馆中奋笔疾书,撰写评论,继续着其已不大为人所注意的文字生涯。此后他又曾在浙江国民党省党部和省政府里任过职,后来回到家乡江山办了“独见书店”,成为“安分守己的书店老板”(曹聚仁语)。抗战期间,“非孝”之争中施存统的死党曹聚仁在江山偶遇凌独见,二人既谈往事,也谈起了早年入共产党,又脱离组织,已改名“复亮”,如今在金华乡间做闲人的施存统。谈及前尘往事,当年的对手相视而笑,这笑中正包含着两个五四青年对走过之路的无限感慨,也颇让今人费一些思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