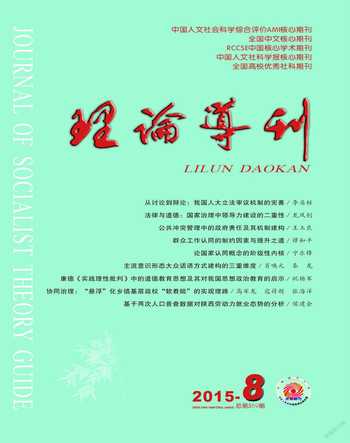从讨论到辩论:我国人大立法审议机制的完善
李店标
摘要:立法辩论和立法讨论作为法案审议的两种机制,有必要结合理论和实践对二者进行界分。受传统观念、苏联模式和对代议制认识不足等因素的影响,我国人大立法审议采用的是讨论机制,这种机制不利于立法质量的提高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创新。完善我国人大立法审议机制的途径之一在于实现由讨论到辩论的转换,推动立法辩论的法制化、常态化、充分化和有序化。
关键词:人大立法;立法辩论;立法讨论;审议机制;法制化
中图分类号:D920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5)08-0004-04
国外议会法案审议采用的是辩论机制,而我国人大立法审议采用的是讨论机制。立法辩论和立法讨论并非同一概念,二者在立法审议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也不相同。在辩论已成为当代国外议会法案审议基本模式的背景下,有必要对我国当前人大立法审议模式进行重新审视,推动立法审议由讨论机制向辩论机制的转换,以实现立法质量的提升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创新。
一、辩论与讨论的界分
一般认为,“辩论”的英文对应词语为“debate”,尽管“argue”“dispute” “argument” “controversy”“discourse”和“deliberative”也有辩论的意思。《牛津英语词典》对“debate”的解释为:“在公共会议或立法会议上就某一特殊事宜所做的一种正式的讨论。相反的意见在讨论的过程中会被提出,并通常由投票而结束。”[1]《布莱克法律词典》对“debate”的解释为:“辩论,议事规则的内容,是指以正式发言的形式针对动议的价值展开正式审议,或反对抑或以其他方式处理动议。”[2]《不列颠百科全书》对辩论的解释为:“两个人、组或集团之间正式的、口头的交锋,一般是按一定的方式或程序提出论据以支持一个问题相对立的一方。”[3]国外理论界关于“辩论”一词概念的探讨大多集中于政治学和逻辑学领域,而且一般都将辩论视为一种追求特定目的的活动。如“辩论是质问和论争的过程,是对某个辩题作出合理判断的方式”;[4]6辩论指意见交流,不仅仅意味着谈判,其目的是通过论证某事为真理或正确而说服对手,或被人说服而认为某事为正确或正当等。[5]
在我国古代汉语词典(如《辞源》《古汉语常用词源流词典》等)中并不存在“辩论”一词,而是以“辩”来指代辩论,意指争论、争辩。《现代汉语词典》对辩论的解释为:“辩论是指彼此用一定的理由来说明自己对事物或者问题的见解,揭露对方的矛盾,以便最后得到正确的认识或共同的意见。”[6]87我国理论界对辩论的界定也多存于政治学和逻辑学领域,如“辩论就是运用事实或道理作为根据,通过逻辑推理,论证自己所持观点的正确性,揭露对方所持观点的虚妄性”。[7]我国法学界对辩论问题的研究成果较少,虽然民事诉讼法学领域近年来有不少学者在研究“辩论主义”“辩论原则”等问题,但由于部门法学者研究方法和视角的独特性,他们往往并不重视也很少对辩论的概念加以界定。可以说,法学界对“辩论”一词的界定目前还没有形成比较权威的观点或主张。但通过上述中西方文献的梳理可以发现:首先,辩论在本质上应是一种言语活动;其次,辩论应是过程和结果的统一体;再次,辩论的主体应是同一问题上观点相反的两方,而且主体之间地位平等;最后,辩论活动的发生应是在同一时空范围内。基于此,笔者认为,辩论是指针对同一问题观点明确对立的平等双方主体,在特定时空范围内所展开的针锋相对的口头对话活动。
在国外法学领域,“讨论”这个词的使用频率较低,《牛津法律大辞典》《布莱克法律词典》《基础法律词典》《科林斯法律词典》中均没有将“讨论”作为独立的概念进行解释。从我国《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来看,讨论一般包含辩论的涵义,但辩论往往不解释为讨论,即“讨论是指就某一问题交换意见或进行辩论”。[6]1333我国多数学者认为,讨论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讨论可以包含辩论,但狭义的讨论却和辩论存在着区别,如讨论相比辩论而言辩驳现象少、讨论没有辩论正式、讨论没有辩论激烈等。美国学者弗里莱等的论述为本文区分辩论和讨论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思路:“几位参议员可以在委员会上讨论某一问题,但在参议院院会上却不可能。参议院太大,不宜进行讨论,只能进行辩论。当然,非正式辩论可以在讨论过程中进行,而讨论也可以作为辩论的前奏。如果通过讨论不能解决分歧,按照逻辑,就要运用辩论了。”[4]1112
笔者对相关资料整理后发现,现有的研究成果显示辩论和讨论区别在于:(1)辩论的主体是观点明确对立的两方,而讨论的主体则不一定是两方,观点也不一定对立。(2)辩论是参加者之间进行的口头较量,其目标在于获胜,而讨论的目标在于达成共识。(3)在辩论过程中往往参加者受到严格规则的限制,重视程度和正式性较为明显,而讨论的环境和氛围要相对轻松。(4)讨论并不强调观点不同的主体进行针锋相对的沟通,而辩论所强调的恰是相反观点之间的直接对话和反驳。
二、立法辩论与立法讨论的界分
立法辩论作为一个独立的概念在国外主要有两种表达方式:一是“legislative debate”,二是“debate on bill”,但按照汉语的使用和翻译习惯,前者似乎应是更为合适的选择。在国外,立法辩论是议会辩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对“议会辩论”的界定存在三种思路:一是以目的为出发点,如“议会辩论是在合乎议会程序的规则指导下进行的辩论,它的目的在于通过、修正或废弃那些提交给议会的动议和提议”;[4]2223二是以行为为出发点,如议会辩论是立法机关依据议事规则,围绕一项动议所举行的正式讨论、争辩和表决;[8]三是以形式为出发点,议会辩论是以立法会议形式进行的辩论,不包括民众讨论、舆论宣传、议会小组讨论等形式。[9]在国外,根据辩论的主题是否为法案,一般将议会辩论分为立法辩论和非立法辩论。如英国,立法辩论是针对法案审议进行的辩论,非立法辩论是针对监督政府、讨论时事等进行的辩论。[10]“美国国会辩论有两种类型,立法辩论和非立法辩论。立法辩论是指国会参众两院议员在一定时间内针对当前或未决的立法而展开的一般性辩论;非立法性辩论是国会议员讨论任何话题(可以是政策性和非政策性)的公共论坛。”[11]由于当代议会所承担的主要职能是立法,因此立法辩论构成了议会辩论的核心内容,尽管国外关于立法辩论的很多研究成果都是囊括在议会辩论之中,而且很少提及“立法辩论”这一概念。
在我国,对立法辩论问题提及最多的应数政治学领域的学者,他们在考察国外议会制度时往往都必不可少地对议会法案审议过程中的辩论机制进行介绍和评析,但他们并没有重视立法辩论概念的界定。在法学领域,诸多立法学著作中虽然也有提及立法辩论机制或制度,但同样也很少有人直接阐明立法辩论的概念。不过也有学者进行了有益的尝试,提出:立法辩论是指在法案审议过程中,代表之间或常委会组成人员之间对法案中的重大问题或个别有争议的条款进行辩论和分清是非。[12]
笔者认为,在我国理论界对立法辩论的概念界定尚未形成普遍性观点和主张的情况下,对立法辩论的界定需要以国外立法辩论的制度设计与实践操作为基本参照。首先,立法辩论应仅限于权力机关,而不包括行政机关,事实上国外的立法辩论无论是文本规定还是具体实施都是针对议会这一特定主体。其次,立法辩论仅指议会法案审议会议上议员之间的辩论,不包括立法听证会、立法论证会和立法讨论会上的辩论。国外议会立法辩论一般在议长的主持下,在议员之间展开,非议员只有旁听权,而无发言权。最后,从过程与程序的划分角度来看,立法辩论的程序应仅指动议提出到辩论终结这一阶段,但过程则包括辩论前的准备、正式辩论和辩论后的表决三个环节。基于此,笔者认为,立法辩论是指观点对立的议员(或人大代表)在立法机关的法案审议会议中,依据一定的议事规则围绕一项法案动议所进行的正式论证、争辩和表决活动。
和立法论辩一样,立法讨论一词在我国的使用频次和证成程度也较低。如吴大英等认为,“从立法程序来看,讨论法律草案是指立法机关对列入议事日程的法律草案正式进行的审查和展开的辩论。同时,讨论法案还包括立法机关有组织有领导地在公民中举行的对法律草案的讨论。”[13]崔卓兰等认为,立法辩论的着眼点在于立法沟通的动态过程,立法讨论着眼于静态的体制,立法辩论是立法讨论的一部分,二者可以是一致的用语。但讨论与辩论相比,略显立法中争论和反对的声音不够。[14]在我国台湾学者的立法学著作中,“辩论”和“讨论”的使用也比较混乱。如同样是针对法案审议程序,罗传贤在《立法程序与技术》一书中使用的是“讨论”,而朱志宏在《立法论》一书中使用的是“辩论”。[15]笔者认为,立法讨论的范围相比立法辩论更为广泛,其至少应包括立法机关内部的讨论和社会公众对法案的讨论两种形式。我国当前的各种关于立法程序的法律文件几乎都对审议法案进行讨论做出了规定,这即立法机关的内部讨论;而社会讨论或公共讨论主要是针对法案的公开征集意见而言的,如早在1954年制定宪法时全国就有15亿多人参加了这部国家根本大法草案的讨论。此外,立法辩论和立法讨论最主要区别在于前者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较高,国外议会议事规则中所规定的法案审议模式几乎都是辩论,而非讨论。
三、我国讨论式立法审议机制之检讨
在我国2000年生效的《立法法》文本中并不存在“辩论”一词的表述,而与之相近或相关的“讨论”一词却出现五次,分别在第19条(四次)和第27条(一次),针对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法案审议过程。2015年修改通过的《立法法》并没有改变这一状况,在人大立法审议程序问题上仍然是对“讨论”进行了重述。在1989年生效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议事规则》中也没有“辩论”的表述,而出现了五次“讨论”的表述,分别在第6条(一次)和第13条(四次)。在2009年修改通过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议事规则》文本中同样找不到“辩论”一词,但“讨论”一词出现了两次,分别在第6条(一次)和第17条(一次)。通过考察《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议事规则》的制定过程会发现,在1987年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审议该法律草案的过程中,胡绩伟和杨克冰等委员曾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讨论议案可以进行辩论,在议事规则中增加允许辩论一条,但上述建议后来并没有写入该议事规则。[16]可以看出,作为规范人大立法程序的基本法律,《立法法》和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议事规则并没有将辩论纳入其文本之中,人大立法审议所采用的是讨论机制。
虽然我国相关法律法规对人大立法审议讨论过程中的发言场合、次数、时间和程序等问题进行了专门规定,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议事规则》第七章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议事规则》第六章,但上述规定仅仅为讨论机制设计了一个简单框架,并没有将讨论的形式、次序、内容和限制等予以具体化。“我国现在立法审议,都是采用分组讨论、大会发言的方式进行。这种方式看起来很平和,没有大的分歧和争论,其实并不正常。”[17]更有学者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审议仅仅停留在一般的议论、表态上,甚至用‘衷心拥护’、‘完全赞同’之类的套话来敷衍塞责,那就失去了它的本来意义。”[18]立法审议讨论机制导致了我国早期全国人大法案审议会议中,讨论式发言往往是各说各的,没有观点之间的交锋和对抗。尽管目前我国人大法案审议会议上的讨论已经做到了有序性,随意打断别人发言和离题发言的现象已极少存在,但人大代表充当“和事佬”的现象却十分明显。可以说,我国当前人大立法审议的讨论机制弊端是显而易见的,尽管没有讨论的人大会议是寂寞的,但没有辩论的人大立法应是失真的。
比较而言,在国外议会,没有辩论就没有议会民主,也就没有立法审议程序。“由于议员能够利用诸如质询、辩论等正式的议会论坛,就政府法案有失偏颇之处各抒己见、提出建议、甚至加以批评,所以他们在立法过程中,仍然有一定的贡献和影响力。”[19]而我国重实体轻程序、重民主轻科学、重礼仪轻法仪、重数量轻质量的法律传统一直对立法审议程序的完善起着阻碍作用,影响了立法质量的提升,侵害了公民的民主权利。事实上,我国当前人大立法审议采用讨论机制而非辩论机制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1传统观念制约。综观我国古代立法历程,绝大部分朝代的法律都是出自君王,而且针对立法中的分歧和异议总是使用暴力的方式予以解决,缺乏民主和辩论观念已成为我国古代立法的特色。法案审议中辩论传统的缺乏与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是密不可分的,“和为贵”已成为中华民族几千年延续下来的最重要的传统文化,能言善辩往往不仅不被认为是一种才能,反而被视为一种狡猾的技巧。“讷于言而敏于行”、注重秩序和礼仪等在儒家观念影响下成为了君子的美德,并长期影响和制约着我国公民辩论个性的发展。这也间接推动了平和型的讨论机制的诞生,在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立法过程中当面“唱反调”对于很多人大代表而言是很难接受的,由此也使他们养成了不想辩、不能辩和不敢辩的习惯。
2苏联模式影响。建国初期,我国在政权建设问题上一直强调人民代表大会与苏联苏维埃政权的联系,而苏联模式的典型特点是不重视法案审议中的辩论。“原苏东国家代表大会的会期往往很短,一般是每年10天左右;代表大会受执政党的严密控制,执政党还利用代表大会来总结过去的成就,提出未来的目标。持续的热烈鼓掌是大会的组成部分,而自由辩论根本不存在。”[20]尽管我国当前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已经日益摆脱了苏联模式的影响,但在履行其内部职责和功能时行政化色彩较浓仍然是立法讨论机制的支撑。“我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讨论法案的制度,大多数情况下由代表或委员们发表一通赞成、支持法案的表态性意见,然后提一些很具体的修改意见。法律的一些重点、焦点问题并不是有很多人能提出来。有时虽有人提出切中法律要害的焦点问题,提出一点不同意见,但不可能、也不允许形成争论,这样一些很重要的和关键性的意见就被忽视了。”[21]
3对代议制认识不足。尽管资本主义代议制的种种弊端在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时代已充分暴露,但“资产阶级的共和制、议会和普选制,所有这一切,从全世界社会发展来看,是一大进步”。[22]我国当时对资产阶级议会的批判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建立,更多地不是来自对资本主义代议制的亲身体验,而是来自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加之,自中华民国成立之时就开始引入的国外代议制并没有使我国走向富强和摆脱压迫,其在中国失败的实践使人们对之产生了怀疑,使部分人抛弃了向西方学习的迷梦。对代议制缺乏全面的认识,决定了当时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建立很难对资产阶级议会的一些运作机制进行理性借鉴。虽然我国近年来一直强调积极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以加强制度建设,但长期存在的关于代议制民主的片面认识并非短时期内能够改变,尤其是在引入作为代议制民主运作形式之一的立法辩论问题上更是如此。
四、我国辩论式立法审议机制建构的基本思路
法案审议缺乏辩论一直是我国人大立法过程中的一个薄弱环节,“缺少辩论,使得人大对立法案的审议在事实上陷入了‘沉默的螺旋’,大多数代表通常的选择就是附议领导意见——代表权就在这样的会议规则之下被无形消减了。”[23]尽管我们对国外议会立法辩论的理论、制度和实践都有一定程度的认知和理解,但真正要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立法辩论机制,却是一个既存在动力,又存在压力的事情。因此,厘清我国辩论式立法审议机制建构的基本思路应成为首要问题。建立我国立法审议辩论机制并不能靠简单地移植国外各项辩论规则,实现立法辩论的法制化、常态化、充分化和有序化无疑更为重要。
1立法辩论的法制化。在我国,立法辩论法制化首先要解决的是,在当前法律文本中将“讨论”修改为“辩论”,还是实行“讨论”与“辩论”的同时表述问题。尽管在国外议会议事规则中很少见到“讨论”一词,但我国法案审议的讨论模式由来已久,变“讨论”为“辩论”虽然是必然趋势,但仍需要一个缓冲和试验期。因此,立法辩论的法制化可以分成两个步骤完成:第一步,在相关法律中的“讨论”表述之后增加“辩论”的原则性表述;第二步,将相关法律中的“讨论”修改为“辩论”。具体而言,立法辩论的法制化需要:一是在《立法法》(2015年修订版)中增设“辩论”的明确表述,将当前第21和29条的“讨论”修改为“讨论和辩论”,在专门委员会法案审议的条文中增加“讨论和辩论”的表述;待条件成熟后将“讨论”再修改为“辩论”。二是在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的议事规则里增加有关“辩论”的表述。如在我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议事规则》第24条中应增加辩论的相关词语表述;将《全国人大常委会议事规则》第17条中的“对会议议题进行讨论”变更为“对会议议题进行讨论和辩论”。三是在地方立法程序法规中增加立法辩论的具体规定或出台专门的立法辩论程序规则。可在“引文”或“总则”部分增加“辩论”的原则性表述,在正文中对辩论的组织、程序、原则和规则等相关内容进行具体规定;出台专门的立法辩论规则,可参照地方立法听证规则的框架体系对辩论的对象、主体、范围、程序、原则、规则和限制等内容进行规定。
2立法辩论的常态化。在国外立法辩论的实施遵循常态化思路,不管法案的类型如何、内容如何、重要程度如何,都必须经过辩论这道程序。立法辩论的常态化要求立法机关不能有选择地针对个别法案进行辩论,尽管对于事关民众利益的重大立法的辩论更能引起民众的关注,但这一制度只有在常态化的实施过程中才能不断发展完善。有学者断言,“随着利益多样化和市民民主经验的日益丰富,立法中的协商将会更加频繁和困难。协商的内容将会更加广泛,协商的形式也更趋于多样化和具有公开性,讨论的话题也会越来越深入,公开辩论将会司空见惯。”[24]而实现我国立法辩论的常态化,不仅需要立法机关树立科学的立法观念,而且需要努力提高人大代表的专业素质。为了使立法辩论制度在引入后能尽快适应我国的现实国情、政情,当下需要创设条件进行制度移植前的环境培育。
3立法辩论的充分化。“人民只是一个虚拟,他不能说话与思考,他是通过所有的个体来说话与思考的。在一个数千万甚至以亿计人口的国家里,要想大家实际上都参加立法辩论,大家都参加立法决定,这不仅成本太高,而且事实上也不可能。”[25]但国外议会立法的实践告诉我们,大量时间花费在议员之间的辩论上是有其价值的,这也是立法辩论得以展开的基本要求,尽管有辩论时间的限制和冗长发言的阻碍。展开充分的辩论可能会对立法进程和立法效率产生负面影响,但却对于辩论主体的权利保障、辩论过程的民主性和辩论结果的科学性起着决定性作用。没有经过充分辩论而制定出的法律,不仅在民主性方面有所欠缺,而且往往科学性和公正性方面也难以得到保证。反观我国目前人大立法现状,人大的开会时间尚不足以保证代表充分表达自己对法案的看法,更不用说对法案的辩论了。而且,如果立法辩论的充分性没有引起足够重视,或者没有予以解决,那么我国将来所建构和实施的立法辩论制度也将流于形式。“建立立法辩论机制,并不意味着持某种观点的人只表述其结论,还要求设立专门的制度,保证其充分、详尽地阐述自己的理由,并与不赞成自己观点的人就某些问题逐一进行辩驳。”[26]
4立法辩论的有序化。在国外为使立法辩论的进行能井然有序,议员发言的时间、态度、内容、甚至聆听他人发言时的行为,在议事辩论规则中都有明确的规定。只有坚持有序原则,立法辩论才能成为一种民主、理性、和平和宽容的意见交涉过程,立法辩论的价值才能真正显现。孙中山先生曾经就我国近代立法会议的无序性进行过批评:“尝见邦人之所谓会议者,不过聚众于一堂,每乏组织,职责缺如,遇事随便发言,彼此交谈接语,全无秩序。如此之会议,吾国社会殆成习惯。其于事体容或有可达到目的之时,然误会之端、冲突之事在所不免,此直谓之为不正式、不完备、不规则之会议可也。”[27]当前,我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法案审议过程中“温和”讨论或自由发言都较为有秩,但因缺乏辩论而常被称为“座谈会”式法案审议。如我国《立法法》规定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法案可采用分组、联组和全体会议三种形式,但实践中由于时间和人员等限制因素辩论很难展开,而且缺乏辩论程序和组织方面的可操作性规定。因此,我国立法审议辩论机制的建立需要反思我国现实和借鉴域外经验,在制度设计上既要进行引导和控制,又要进行激励和惩罚,以使我国人大立法审议会议上辩论做到有序性。
参考文献:
[1]Catherine Soanes and Angus Stevenson. Oxford Dictionary of English[K].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353.
[2]Bryan A. Gamer. Black′s Law Dictionary (Eighth edition)[K]. Minnesota:Thomson West, 2004∶1209.
[3]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不列颠百科全书》国际中文版编辑部.不列颠百科全书(第5册)[K].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190.
[4]Austin J. Freeley and David L. STEINBERG. Argumentation and Debate: Critical Thinking for Reasoned Decision Making[M]. Boston: Wadsworth Cengage Learning,2009.
[5][德]施米特.政治的浪漫派[M].冯克利,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162.
[6]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K].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7]高明光.论辩论[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1.
[8]P. SILK AND R.Walters. How Parliament Works[M].London:Longman Group Ltd.,1995∶198.
[9]D. EASTON.A System Analysis of Political Life[M].New York:Wiley Press,1965∶213.
[10]蒋劲松.议会之母[M].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1998∶631.
[11]Michael A. Genovese and Lori Cox Han. Encyclopedia of American Government and Civics[M].New York: Facts On File, Inc.,2009∶80.
[12]李龙.政治文明与依法治国[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4∶242.
[13]吴大英.比较立法制度[M].北京:群众出版社,1992∶514.
[14]崔卓兰.地方立法实证研究[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7∶381.
[15]罗传贤.立法程序与技术[M].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6∶552554; 朱志宏.立法论[M].台北:三民书局,1995∶148152.
[16]佚名.全国人大常委会《议事规则》产生前后[J].瞭望周刊,1987,(49).
[17]孙笑侠.浙江地方法治进程研究[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7879.
[18]苗连营.立法程序论[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1∶90.
[19]Butt Ronald. The Power of Parliament[M].London:Constable,1969∶22.
[20][英]黑格,哈罗普.比较政府与政治导论[M].张小劲,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374.
[21]蔡定剑.历史与变革——新中国法制建设的历程[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384.
[22]列宁全集(第3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7374.
[23]王琳.人大理应成为辩论的圣坛[N].东方早报, 2008-07-12(11).
[24]路江通.地方人大立法中的协商[G]//陈剩勇,何包钢.协商民主的发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326.
[25]周永坤.规范权力——权力的法理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124.
[26]周光权.有充分辩论, 才能立出良法[N].南方周末,2009-03-26(E31).
[27]孙中山.建国方略[M].牧之,选注.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274.
【责任编辑:张亚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