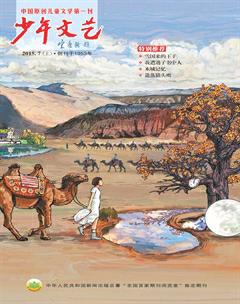创作感言
我的脑海中一直有一个沉默的盲人女生的形象。
为此,2014年秋天,在诸多尝试和努力之后,我来到上海盲童学校体验生活。
但身处盲校,我并没有发现想象中的所谓“沉默”的孩子,大家都在花一样的年纪,每一个人都快乐爱笑、多才多艺,凭借一双敏锐的耳朵便可足下生风,手指触摸盲文便可“一目十行”。他们为数学题而疑惑不解,为喜欢的歌手争得面红耳赤。有个16岁的女孩兰兰和我尤其亲密。她是低视力患者,平日里总是拿着很大倍数的放大镜看莎士比亚的书。她的男友S也是从盲校毕业,是一位白化症患者。两人因为家教而彼此结缘。S非常优秀,从特殊学校考入综合性大学,现在成为了一名特殊教育老师。和S接触的过程中,他的亲和与善良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2年前他的母亲病逝,他说那种打击令他难以承受,但如今从他年轻的脸上已经看不到失去亲人的阴霾。
后来我才知道,在快乐与开朗的背后并非没有无奈: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盲校里有不少孩子来自单亲家庭;特殊学校高考的门槛和过去相比大幅提高,这些学生中大部分人进入大学的希望渺茫;尽管好多学生信心满满地对我说可以自己坐地铁来学校,但他们不会告诉我的是,作为一个盲人,对于在社会上受到冷言冷语甚至侮辱嘲讽也早已习以为常。
他们和普通的孩子没有任何区别,因为明媚的阳光之外,那些忧愁和烦恼也仿佛与生俱来,早已被深埋在心底。学校的老师说,盲校的孩子通常会遇到两种人,那种充满恶意、言语攻击的人自不待言,而另一种是对他们充满同情的人。这种同情,往往来源于健全人自上而下的优越感,从而演变成一种小心翼翼的对待,这种刻意却会让盲人越发感到尴尬。我想,之所以会这样,也许还是因为缺乏对盲人生活的了解吧。无论是盲人,低视力者,或是罕见病患者,他们和每一个普通的人一样,都拥有才能,也怀有烦恼,会快乐,也会害怕。
那几个月间和兰兰他们的交往,带给我很多思考,许多原有的想象变得不堪一击。在刚进盲校的那天,我曾写下这样一句话:“人生有好多种可能。不要自以为是地定义和评价他人,就是对别人最大的温柔。”我把那些日子的所见所闻,糅合了自己的体会,全部写进了《雪国来的王子》。因为写的都是真实的事情,所以文章欠缺技巧和戏剧性,对于这些早熟孩子内心的强大和隐忍,没有很好地表达,姑且只能算是素材的记录吧。
作者档案

庞鸿,女,1990年生。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现就职于上海电影集团。上海作协会员。1999年起在各类报纸杂志发表作品。出版中篇小说集《刘大凡和她的同学们》、长篇小说《未来对我说》。作品曾获上海文化发展基金文学创作专项基金资助,入选2014年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向全国青少年推荐百种优秀图书目录,获2013中国上海国际童书展“金风车”最佳童书奖、“中国原创童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