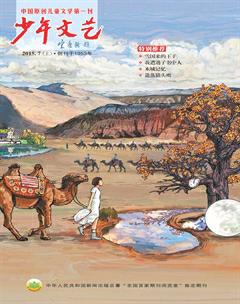我遭遇了书中人
常新港
还没入冬。草甸子里的草黄了,但没黄透,还有绿意在挣扎,在苦熬,在等着太阳迟一点落山。
那个季节,我们边境农场又提前挖防空洞。一旦邻国的飞机扔下炸弹时,我们就钻进防空洞藏身。训练的警报声比鸭子的叫声都频繁。每天几次地响,我真的拿警报当鸭子叫了。
我饿了,刚挖了一会儿防空洞就爬出来找吃的,没找到,就吃了一块喂鸡的豆饼,又急急地喝了一瓢凉水,肚子只响了几下,就开始拉肚子。我一直拉了一天半,走在路上,感到身体都飘了。我就近躺在人家的草垛上睡一会儿。等我醒来时,就觉得身下硌得慌,一摸,是本书。书的名字叫《城与年》。我觉得是某个人藏在这里的。因为中国的六十年代中后期,人们都在烧书,也有人偷偷地藏书。人都有捉谜藏的习惯,越不让看的东西,就越有人藏。大庭广众不能说的事情,都在背后没完没了地说。
我把书藏在家中的鸡下蛋的窝里。天一凉,鸡就不去下蛋了。没想到,妈妈经过下蛋窝时,习惯性地伸手摸了一下窝,倒把那本书掏了出来,一看,再一翻,妈的脸色就变了,冲我喊道:“你藏的吧?”
我点头。家里,弟妹都小,只有我对厚厚的书有兴趣。
“你爸还在牛棚里,你就别给他添乱了!这书是外国人写的,很危险!你看这种书,让人知道了,会要你爸爸的命!”
我说:“我马上还给人家!”
说着,拿着书在外面转了一个弯,把它藏在了邻居家猪圈的防雨棚上,找一块石头压着,秋天的风大,一吹,会把书吹没的。
我得到那本书的头一个月里,还不知道会跟里面的人物遭遇。一开始,我并不喜欢这本书,因为它里面的字是竖排版的繁体字,读时要猜字,很累。
在一个夜里,我悄然走进了一条街道。那是书中的一条街道。我瞪着眼睛,注视着街道上发生的一切。
我一转身吓了一跳,以为是身后有人跟着我。其实是电线杆的影子。有的灯坏了,留下一个巨大的黑洞。有的电线杆子歪了,像一个喝醉酒的人画的画。
街上就是一部电影的故事。我还记得有风,风把树上的叶子吹得哗啦啦地响。我恐惧地感觉到,在街上滚动的树叶的后面,会有更加恐怖的东西随之而来。
我清楚地记得自己的年龄,十二岁。
我记得书中的一棵树,记得书中窗前的一只麻雀,记得书中的一只受伤的蚂蚁。但是,我为什么总是走不出书中的那条街道呢。
书的作者是一个叫费定的俄国作家,他长着一张普通的瘦削的脸,他给我的第一印象,他永远不会轻易开口说话。他一直端坐在书的扉页的右上角,右手托着下巴,在等着一个真心倾听他讲故事的人。
他是一个讲故事的人,他是一个会讲故事的人,他给全世界的人讲故事。
在那个下午,我走进了一个完全不认识的城市,走进了一条陌生的街道,走进了完全陌生的世界,也遭遇了一群陌生的人。
那是一条圣彼得堡的街道。
但是,我要先说德国的柏林。那天早晨,他朝我走来,一个德国男青年舍脑。在我十二岁的时候,他在书中的最初的年龄是十六岁,还是十七岁?
舍脑比我大五岁,站在我面前,竟然比我高出两个头。难道德国的奶油面包会比中国北大荒的小麦和豆油有营养?
书中的舍脑显然不知道中国的北大荒。他听我解释北大荒概念的时候,面露难色。不是,我看错了他的苍白的脸色,他是面无表情。“你十七岁?为什么长这么高啊?你每天都在吃什么?”
德国柏林的准青年舍脑不明白,一个生活在北大荒的孩子,为什么会天天惦记着吃。
舍脑问我:“你没有理想吗?”
我反问他:“我吃不饱肚子,顾不到理想。”
他对我说:“一个饿肚子的孩子,也该有理想。”
我固执地对他说:“一个饿着肚子的孩子,只想吃饱肚子,没有理想。要是有理想,那就是每天都吃饱肚子!”
这个叫舍脑的德国准青年,觉得我是一根北大荒的草,一只在草丛中乱窜的兔子,一只没有思想的傻狍子。他把背朝着我,抬头看天上的星星,好像他是来自星星,他的故乡在天上。
我从他冷冷的背影上,看出他不屑跟我谈话了。
但是,我对他有兴趣,对他的穿戴有兴趣,我问他:“你在想什么呢?”
他的脸还是朝着多云的天空,他忧虑地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就要开始了!”
我不解,也像是没听懂:“你说什么?”
他转过头,脸孔朝向了我。他的脸色更加地苍白:“战争。这个世界上从未有过的战争!”
我继续问道:“你说的战争,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吧?跟你有关系吗?你的脸色为什么这么难看?”
德国准青年舍脑对我说:“我读的是军官学校。”
“哦?”我似懂非懂。
“战争一旦打起来,一个上军官学校的男人,不会袖手旁观的。你现在面对的可能是第三次世界大战,一旦打起来,一个孩子就像一滴水,被卷入到战争的海里……”舍脑说这句话时,他的脸色依旧苍白。
跟他分手时,我突然盯着他脚上的皮鞋说:“你的皮鞋……很亮!”
他看了看自己脚上的皮鞋说:“每天早上,皮鞋都要擦亮后再穿上出门的!”
“我能试试吗?”我提出了一个要求。
他的表情很怪,就那样呆呆地看着我:“为什么要穿我的皮鞋?”
我清楚地告诉他:“我从来没穿过皮鞋!”
他脱下了皮鞋,用脚朝我面前推了一下。
我脚伸进舍脑的皮鞋一瞬间,他弯腰抓住我的脚踝,让我的脚离他的眼睛更近一些:“你的脚有冻疮?”我说:“北大荒孩子的脚大多都有冻疮,即使我们的脚没有冻疮,也会有严重的鼻炎!”他松开我的脚踝,像是不理解地哦哦哦地哦了几声。我说,我要穿上你的皮鞋试试,因为我只在书上知道皮鞋,还没穿过皮鞋。舍脑又哦哦哦地哦了好几声。我的脚试探地钻进了皮鞋,像是钻进了一间很大的很结实的房间。
“你把我的皮鞋脱下来吧!我真的要走了!”舍脑说。
“你有急事?”
“玛丽在等我!”
“听上去,像是一个女人?”
“不,一个高中女生!”
“你们学校可以谈恋爱?”
“要打仗了。我可能要上前线,也许会死掉!在死之前,我向一个女孩子表达我的爱慕,这是我最想做的一件事情!不做这件事,一生会很遗憾的!”
那一刻,我被舍脑的话温暖了。我觉得自己特别可怜,一没有书读,二吃不饱肚子,看看这个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叫舍脑的德国人,有读不完的书,不愁吃不愁穿,才可以做那些我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也是在那一刻,我怀疑自己究竟在哪里见到了舍脑。是在北大荒的草地上,还是在我家的篱笆上挂满了红辣椒的小院里?但是,我又明明记得他弯腰看着我的眼睛,用手刮了一下我的脸。在他的手滑过我的脸颊时,我的眼睛闭上了。我还听到他说了一句:“小屁孩,等你懂这些的时候,还要等很多年啊!另外,我想说的是,我没想到中国的孩子,还吃不饱肚子!”
舍脑舒展开他白白的细长的手,里面有一粒用闪着银光的锡纸包裹着的东西:“给你的!”
我问:“什么?”
“吕贝克巧克力!”
他走了。他虽然穿着那么大的那么重的皮鞋,走路的时候却一点声音都没有。他的一头金发在北大荒的草地上飞舞。
我根本就不舍得吃有着很怪名字的吕贝克巧克力,让它储存在我的四季里,天热了,它融化了,天冷了,它又凝固变硬。最终,它只剩下了闪着银光的锡纸。
我真的分不清这是现实还是梦境,不知道是幻想还是确有其事,我躺在北大荒的草地里,蓝色的天空幕布上,有几只麻雀在移动,在跳跃,在鸣叫,让我幻想的车轮高速旋转,不能停下来。
学校开始天天贴大字报了,那些大字报就是在造谣,在人身攻击。人们在编造谎言的时候,却偏偏说自己在追求真理。
爸爸的头发被别人剃成了鬼头,没多久,又长出了头发,他自己又把自己的头剪成鬼头。爸爸说,他自己不剪,别人也会给他剪。别人剪,会故意扎破他的头皮,因为他是鬼。他知道怎么剪才是鬼头,越丑,就越是鬼头。我觉得爸爸真的成了另一个世界的人,他变得越来越不像我的爸爸了。爸爸怎么会心甘情愿当一个鬼呢?
为了躲避内心的伤感,我必须走进那条街道。有时候,一个还承受不了命运压力的孩子,为了摆脱现实的残酷,却闯入了一个更加残酷的世界。
这是圣彼得堡的涅瓦大街吗?还是它旁边的一条小街道?那里的木制房子上的油漆都剥落了,电线杆子歪了。我站在这条街上做什么?在等人吗?我为什么觉得一个叫安德烈的俄国年轻人要经过这条小街?他该经过这条街了。
我第一次在书中见他时,他刚从这座叫圣彼得堡的城市去德国的柏林留学。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他要终止自己的学业。因为战火,他一时不能回到俄国。
等到他历尽艰辛回到圣彼得堡的时候,他过去的恋人丽妲已经嫁给别人了。当安德烈看见丽妲怀着别人的孩子站在他面前时,安德烈的两只手深深插在自己的头发里,嘴巴里只会发出“啊!啊!啊……”的声音。他一个人朝着那条街道跑去。
那正是我等待他的那条街道。我一个北大荒的孩子,要跟他说什么?就在我还没看见他的时候,在昏黄的路灯下,却看见一排遭到细菌伤害变得永远失明的士兵从我面前经过。后面的人伸出手臂,搭在前面的士兵肩膀上,朝前走去。他们无论走到哪里,走到医院,走到车站,走到故乡,都是走向黑暗。
我呆呆地目送着他们的身影,被黑夜融化。
真的冷啊!
我看见了安德烈踉踉跄跄地朝我走来,他的嘴巴里还是发出“啊!啊!啊……”的声音。这时,他走不动了,他的脚像是被什么物体绊住了,他不停地甩着脚,不停地喊着:“走开,走开,给我走开啊……”
我要去帮助这个书中绝望的人。当我走近他时,我才发现,安德烈的鞋面上正有一群老鼠走过,一只肥硕的老鼠站在安德烈的鞋上,抬头望着他,像是对他说:“好一个绝望的人啊!”
我冲上去,抓住那只肥硕的老鼠,把它抛向黑夜。再弯腰去抓另一只老鼠,抛向远处。我用脚踢老鼠,用手抓住它们使劲地摔到地上。
我冲着安德烈喊道:“你不要这样,你站直了,朝前走啊!你为什么要哭啊?一只老鼠都让你走不动了吗……”
安德烈躺倒在地上,就像那根歪在地上的电线杆子躺下了,他的嘴里还一直喃喃自语:“走开啊!走开啊!给我走开啊……”
我冲他吼道:“你站起来吧,你脚下什么都没有啊!你可以朝前走了!”
安德烈没有听见我的话,他也根本不知道我的存在,只是重复着那句绝望的话:“走开啊!走开啊!给我走开啊……”
我愣住了。突然明白,我是一个生活在北大荒的孩子,根本就挽救不了一个书中的绝望的异国人。
……
那天,妈妈跟我说:“你瘦了!”
我说:“没事!”
妈妈说:“看来,今年冬天,战争要真的打起来了!”
我说:“没事!”
妈妈说:“怎么能没事呢?”
我说:“真的没事!”
在书中闯荡过的我,自己变得很不像一个孩子。
妈妈又说:“你弟弟和妹妹都说你在偷偷看一本书,那本书你没还吗?你还要继续惹事情吗?我们家的事情已经不少了,你该懂事了……”
我让妈妈在院子里等一下,我跑到别人家的猪圈防雨棚的藏书处,拿了书跑回来,然后当着妈妈的面,划了一根火柴,把书烧了。
妈妈问:“谁的书,你就给烧了?”
“我捡的!”
我手里拎着燃烧的书,快烧到手时,我把它扔到了地上。纸很快就变成了纸灰。但是,我感觉书中的字在火接近它们的时候,它们排成了队,跑成一条线,涌进我的大脑。这些文字,在我的大脑里找到了家吗?
……
在一个冬天的黄昏,我看见了一个人的背影,它比我熟悉的背影要长,要宽大许多。当他转过身来时,我发现他是德国人舍脑。他一眼就认出了我。他的一头金发有些银白了,像一个历经沧桑的人,也像一个顽皮的大人刚刚从雪堆里拱出来,蘸了一头的雪。
我担心他无声地消失,所以,我第一句问的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直在关心的事情:“你要是活到现在,战争又打起来了,你会帮助哪一个……国家?”
“我反对战争!”
我听见他在许多年前的声音传来。那时,天已经黑了,他的声音如同一件沉重的实物,砸在黑夜里,落在我脚下冻硬的地上。
我眼中模糊,竟然无法从书中回到现实,尽管我是躺在发霉的草垛上,眼中的冬日不知道是在升起还是落下。
这时,我听见远处妈妈的声音:“儿子!快回家吃饭了!”我摇摇晃晃从草垛里站起身来,却迎头看见德国的舍脑和玛丽,还有俄国的安德烈和丽妲站在不远处,一起微笑着看我。
我带着哭腔问他们:“你们到底认不认识我啊?”……
(补记)一九六九年, 我十二岁时读到了俄国作家费定的《城与年》,里面的城市和人物走进了我在北大荒的童年生活。里面有俄国青年安得烈和丽妲,还有德国青年舍脑和玛丽。那些活在书中的人物和城市,颠覆了我的北大荒和我狭小的视野。它也让我知道了世界和未来的写作。它影响了我,也决定了我的成长。所以,我把想要写的东西告诉现在的孩子。那个冬天,我在真实地长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