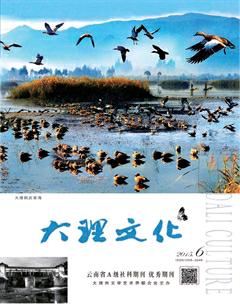遵循办刊宗旨,坚持正确导向
编者按:
本刊作为“以发现、培养大理文学艺术人才为己任,以发掘、弘扬大理优秀历史文化为目的”的文化期刊,始终遵循办刊宗旨,坚持正确导向,同时立足于“人才立刊,作品强刊,特色兴刊”的鲜明理念,不断保持开拓创新和与时俱进的良好势头,使刊物进一步贴近实际、贴近生活和贴近读者,充分传递了优秀期刊的正能量。云南省新闻出版广电局报刊审读专家杨正瑀女士,对本刊2014年全年期刊栏目作品进行了既有深度又有见地的点评,让本刊全体编务人员倍感温暖和深受鼓舞,增强了进一步办好期刊的信心与决心。
由大理州委宣传部主管,大理州文联主办的《大理文化》创办至今已35年。读了2014年全年的《大理文化》,感觉是神游了一遍大理的文学、文化海洋。
大理是一块具有深厚历史文化积淀的土地,我国唐代所建的南诏国,宋代所建的大理国国都都设在大理。大理是曾经的古丝绸之路上的一颗璀璨的明珠,早已享有“亚洲文化十字路口的文化古都”的美誉。大理是一块多民族,多元文化和谐共融的土地,因此,植根于这样一方沃土的《大理文化》,其历史民族文化气息十分浓郁。
有112个页码的月刊《大理文化》,坚持以培养大理民族作家、繁荣民族文学创作,出版民族文学精品、弘扬丰富灿烂的民族文化为宗旨,所发作品注重思想性与艺术性相结合。这本刊物有七个主要栏目,这些栏目将“文学”版块与“文化”版块融汇起来,每个版块的每个栏目都各自散发出文化馨香。文学类栏目有“开篇佳作”、“小说平台”、“散文空间”、“诗歌广场”;文化栏目有“大理旅游”、“大理记忆”、“大理讲坛”。另外还有几个非常设栏目:“文学评论”、“大理艺苑”、“大理书斋”等。《大理文化》所发表的作品,不管是小说、诗歌、散文还是文化类的文章,导向都十分明确,都没有脱离社会主义文艺路线、方针、政策的大方向。《大理文化》中的作品,或地域的,或民俗的,或乡村,或城市的;或小说,或诗歌,或散文,无不具有积极向上的精神和很强的生活气息。“开篇佳作”和“小说平台”所编选的小说格调健康,接近现实,有较强的新鲜感和一定的可读性。如2014年第7期大理本土作家杨友泉的《走出谢庄》是一篇反映乡村青年成长与蜕变的小说。故事的几个主角,为了实现走出谢庄,走进龙城的美好梦想,不仅失去了乡村爱情,还付出了迷失白我的沉重代价。这篇小说叙述技巧娴熟,虽然是写三个农村青年的爱情纠葛,但语言简洁干净。类似的小说还有第5期尹心洁的《灯火阑珊处》、第8期杨训波的《罗老汉进城》等等。这些小说,显示了作者关注现实、扎根现实的严谨创作态度。
大理是一块多民族的土地。因此,《大理文化》的“散文空间”栏目里的散文就显得清新白然,多姿多彩。如第2期李达伟的《一些目光》讲述了包括他白己在内的一些卑微的生命所承受的生老病死,那些看似原始、古老甚至是迷信的行为成为了滇西北村寨与神共存的标志,让灵魂在生命中得到净化。这个栏目第6期里的《草木记》,第3期里的《我的青春我的诺邓》,第9期《家住古道边》等等。读这些散文,可以看到作者在写作中都带着深厚的情感,都是作者真实生活的表述,因此就尤为感人。
《大理文化》诗歌栏目所发的诗歌,没有空洞无聊的无病呻吟。这些诗歌很接地气:要么是深入社会,深入生活的激情感悟:要么是表述作者对大自然寄予的深情。如第10期许文舟的组诗《故乡书简》中《卖牛的父亲》:“我想起姐姐出嫁/那天早晨/躲在唢呐后面父亲/像个胆小的孩子/木然地看着欢喜的人群……牛低头吃着/父亲则在一旁沉默/父亲的五个指头/变成五个梳子/从牛的背梳到胸/从牛的脸/梳到胃……”像这样不饰雕琢,平实无华,但却感人至深的诗,在《大理文化》的“诗歌广场”中,比比皆是!
《大理文化》的文学作品,不管是小说、散文,还是诗歌,都不低俗,不媚俗,内容健康向上。
“文化板块”中的“大理旅游”栏目中的文章,反映在大理的“吃、住、行、游”的过程,把国家级著名历史文化名城大理的美貌,尽显读者眼前。这个栏目中的文章,每一篇都引人人胜,写出了自然风光美丽多姿,人文风情璀璨夺目的大理。
“大理记忆”栏目所发作品,都是写作者个人亲身经历的对大理的记忆,尽可能地用文字保存已经逝去或即将逝去的事物,使“过去”变得清晰。对“大理记忆”栏目里的文章,我们这个时代的人,读来觉得亲切感人。如第4期《步行到大理》,第6期《我的1966》、第9期《下关琐记》,等等。这些经过时间沉淀的旧时光,像一杯酽酽的浓茶,慢慢品味,沁人心脾!
值得一提的是“大理讲坛”。这个栏目里的文章的写作者,都具有较深的历史文化功底。他们通过文本的形式,讲述大理古代、近代、现代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以及民族、宗教等相关内容。例如第8期张旗的《鸡足山人文历史其人其事》,不仅钩沉整理鸡足山的人文历史,挖掘阐释它的人文内涵,使鸡足山幽静、深邃、险峻、奇异的白然景观,折射出独特的人文异彩:同时写出了曾两次登临鸡足山,寓居大觉寺、水月庵、钵盂庵,时间长达五六个月的明代著名思想家、文学家、有着铮铮铁骨的傲慢清官,“自由烈士”李贽浪漫而悲壮的为官之道。读这样的文章,人的心身都得到净化!
《大理文化》的编辑们,能严肃认真对待所编发作品的,表现在对白己编发作品后面的“编辑手记”,也就是对作品的点评。如对第6期刘绍良的《我在乡野》,编辑的点评是:“在喧哗与躁动的年代,大地上那些具体、细小、卑微、密实的事物,已经越来越难以进入作家关注的视野,甚至很少有人会对它们产生兴趣,以至于一种远离事物、细节、常识、现场的写作,正在成为当下的写作方向,写作也因此正在演变成为一种无视大地、无视众生以及抛弃故乡和抛弃感官的语言运动……优秀的作家要有自己的根据地。刘绍良是一个果农,他的写作根据地当然是在乡野。从某种程度上说,他的散文是一种多维度交织的散文,一种有大地声音的散文,一种有灵魂深度的散文。”第4期“诗歌广场”的编辑对这一期入编的分别代表着七种不同风格的七位诗人一一作了点评。《大理文化》的编辑们这种严谨的对待作家作品的态度是值得称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