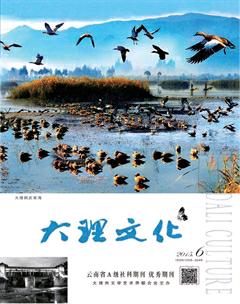那条叫“九峰路”的小巷
我又看见它了。
在这个宁静的夜晚,在这个春日沉沉的睡梦里,我看见祥云县城那条陈旧的小巷,又像水波一样在我心里不停地来回荡漾……
涟漪轻轻拍打心房。是的,已经很多年过去了,我曾经走过无数条街,繁华的,躁动的;经过无数条巷道,偏僻的,古朴的,但都不及“九峰路”——一条仄长的小巷,能给我一种心灵的归属感。
我的整个学生时代都是在“九峰路”度过的。
在那个早巳逝去的岁月里,有关“九峰路”的记忆已经定格为一组旧照片:每天天还没亮,就有人在小巷里经过,骑摩托车的,骑三轮车的,骑白行车的,步行的。年轻人骑摩托车时总是来去匆匆,而上了年纪的中年人骑白行车时却不快不慢,显得很稳重。至于那些孩子,每次上学经过小巷时,总是蹦蹦跳跳,一路踩着快乐。在所有经过小巷的行人中,只有那些老年人的步履才是悠闲的,他们经过小巷时,好像在一块一块地数着地上的石板……
说起来,“九峰路”和我们一家人是有缘分的。
1990年,父亲从部队转业回来后就分配到社保局T作,随后我们一家也就搬到了社保局的老式院子里住。而社保局就在“九峰路”中段。站在院子大门口,往南,可以看到与“九峰路”垂直的龙翔路,往北,可以看到文苑路,当然,龙翔路是后来规划的名字,老一辈人还是习惯叫新大街;文苑路也是后来规划的,以前,那一带还是大片大片的田地,也是我们放学后捉蚂蚱、编花环的天然乐园。现在,各个小区的高楼别墅拔地而起,成了繁华的闹市区,已经再也看不到过去起伏的麦浪,闻不到熟悉的泥土香了。
“九峰路”的青石板混杂着碎石的路面,斑驳不平,沿街的店铺也是看得见年岁的,更多的是老居民住户,青瓦灰墙,木门上的老记号已经很难辨认了,连里面端坐的人也大多是“白胡子红拐杖”。雨过天晴,走在小方格的青石板路面,头顶从墙院内伸出来的树枝上,偶尔会有冰凉的水滴,轻轻地落在鼻尖,耳畔鸟鸣悦耳,倒也别有一番情趣。不过,还是要留神,不然一不小心,踩到路面上翘起的石板上,就会被飞溅一身泥水。
几十年过去了,以前巷道两边的很多店面都已经换了又换。很多住户也已经搬走,可是让我印象最深的始终是那几家。
最南边有一个叫“零距离”的小酒吧,在小县城流行休闲吧的年代,“零距离”算是走在前面的。每到傍晚从门口经过,总能听到或轻柔或动感的流行音乐,于是我会站在那里跟着哼两句,但却从未进去过。直到上了大学,“零距离”也成了学生们放假回家同学聚会、休闲会友的好去处,我便也“名正言顺”地敢告诉父母“去零距离玩一下”。
“零距离”过来一段,是丽家卖香钱纸火的店。我对这两家店印象深是因为年幼时每次从门前经过,都不敢往里看那些寿衣、花圈之类的东西,心里总有一种冷冷的恐惧感。其实慢慢长大才体会到,那些所谓让我恐惧的东西,其实只是用来寄托生者对逝者怀念的一种方式。
在“九峰路”中段社保局的斜对面,有一个让我打心底敬佩的男人。他不是在事业上有多么辉煌,也不是多么的“高大上”,恰恰相反,他患有驼背,整个身体一直成90度佝偻着。听说早些年他老婆因为嫌弃他,更过不了苦日子,丢下一岁大的孩子跑了,后来他靠着每天在路口摆地摊卖光碟磁带之类的杂货,养活着自己和一个孩子。每天天不亮我出门上学时,大概都能遇上他。每次我在后面看着他一步一步拖着几乎与地面平行的身体,吃力地推着小推车去摆摊,心里总是有一种心酸的感觉,但更多的是对他的敬佩。后来,听说他儿子考上了大学,我心里顿时替他感到欣慰。多年不见,我不知道现在这个特殊家庭过得可好,无论如何,在我心里,驼背男人永远是一个高大挺拔的了不起的大男人。
从“九峰路”往北走,是当地人熟知的仓圣阁。仓圣阁比不远处的钟鼓楼少了些奢华和堂皇,但多了些朴素和宁静,是云南省境内唯一一个主要纪念造字圣人仓颉而建的楼阁。阁为青砖灰瓦,三层三重檐琉璃戗角木结构建筑。一楼供奉“文昌帝君”,东西各设一门相通,四周各留一圆窗相通;三楼供奉的就是造字圣人仓颉。一楼东面右侧立一石碑,所撰文字均为介绍。为纪念“造字圣人仓颉”的巨大贡献,圣人的故里陕西省白水县建有仓颉墓、仓颉庙,在河南新郑县城南仓颉造字的地方称作“凤凰衔书台”,宋朝时还在那里建了一座庙,取名“凤台寺”,在山东寿光县还修建了一个仓圣公园。但在西南偏僻的一个小县城里,特地为“造字圣人仓颉”建造一个楼阁,可见祥云历朝历代对文化的重视。最北端,便是我的两个母校——祥云县城东城区完小和祥城镇第一初级中学。那时上小学,别的同学家离学校远,需要走很远的路程,甚至父母接送,可我最白豪的就是爸爸只需要站在社保局大门口看着,三分钟我就能跑到学校,因为这个,同学们都特别羡慕我。后来升了初中,上学的路还是这条,只不过到了小学对面的初中。现在想起来,小时候能住在“九峰路”,真是一件极其幸福的事。它陪伴我走过了快乐的学生时代,承载了我所有年少的欢乐与忧愁。
这么多年过去了,这条名叫“九峰路”的小巷依然那么热闹拥挤,如果是雨天,路面上总会聚集起一些暂时排不出去的水,很恼人,因此步行总要小心翼翼地睁大眼掂着脚才行。不熟悉的人对这里的印象定然不会好,车多、人多、路窄。然而,小巷的居民以及熟知它的人,尤其是上了年纪的老人,对这条路是很有感情的。这里保留着他们亘古不变的生活习惯。懒散,悠然,称心。每一天,从天亮开始,他们便按部就班地行进在多年如一日的轨迹之上,吃饭穿衣,闲话家常,你来我往。早餐是豆浆油条烧饵块,中午的闲暇时光是象棋扑克拉家常,远远地总能听见几个老头卖弄地说着远近奇闻,而当说到国家大事时,必然要引起一场争论
“九峰路”就是这样一条平平常常的老巷道,尽管它不被人注意,但它每天早上总会以一种从容的淡定迎接着东方的黎明。
2008年,我大学毕业参加工作。2010年,我结婚了,搬离了那个盛满了我美好回忆的社保局大院,随后父母也搬了家,但父亲还在那里上班,我们便也偶尔回去看看。可今年,父亲退休了,似乎一下子就剪断了我们和这条住了二十多年的小巷之间的联系,心里不免有些失落与惆怅。但我依然会在傍晚时分,牵着我的女儿,带她一次一次地走过那条小巷,告诉她我童年的趣事,让她感受那里的和谐与质朴。
二十多年了,小巷没有什么变化。对于很多城市来讲,古城和老街都是保留整个城市风骨与韵味的所在,但是近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很多原生态的老街和古巷都面临着拆迁改建,市井的叫卖变成了机器的轰鸣,砖瓦木楼变成了林立的钢筋水泥,老街、古建和寄居其中的市井文化和我们正在渐行渐远。
我不知道这一条叫“九峰路”的小巷将来会不会消失。说实话,我真的不希望它变,因为那里镌刻着我的美好时光。
编辑手记:
在孟学祥《时间背后的乡村》一文中,作者的入笔从一棵和父亲生命息息相关的老梨树开始写,逐渐展开的物象后,是一个人、一个家庭、一个村庄的历史。不能游离于时间之外的乡村,让作者感到了茫然和孤独,对故土的忧虑表现得很突出,这样的情结在年轻作者周丽娟的《那条叫“九峰路”的小巷》中也有所体现。让我们不得不思考,面对社会的变迁,我们如何守住心中的那一片故土,用什么来寄寓乡愁。易春兰的《听说,你要回去了,要去大理了》,从文章的标题、内容、情感,以一个大理本地人的身份和熟络来写,确如一个老友的临行叮嘱。大理,的确是一个让人“记得住乡愁”的地方。《清风不等月明》写母亲,文章一开头就直接书写母亲离世后的酸楚,让读者迅速进入了作者的情绪之中,关于母亲的生平只是寥寥数语,更多的在写母亲最后的时日和丧事,语言老练,情感表达充沛,让人忍不住一次次热泪盈眶。忆苏的《从立春到谷雨》像几篇随手而就的日记,是对一段时间的生活记录,清雅自然的语言,把她在春天这个季节里的人生体验写得圆满和美好。
——仓颉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