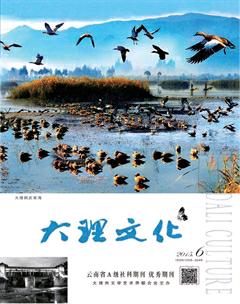山歌儿
马金莲
打锣锣,烙馍馍,
鸡儿叫,狗儿咬,
舅舅来,吃啥哩?
吃白面,舍不得;
吃黑面,羞得很;
吃荞面,肚子胀;
吃豆面,豆腥味;
宰公鸡,叫鸣哩;
宰母鸡,下蛋哩;
宰鸭子,看门哩;
……
我们齐声唱歌,因为我们看见,对面的土路上,那个推自行车的人,向着我们的村庄走来。那是我们的舅舅。那是碎舅舅熟悉的身影。
我们村庄的地形是一个狭长的扇面状,西边的人口是扇子的把儿,东边脚下依次铺开的平坦土地,是扇子的面。绵延起伏的远山,以蓝天为背景,划出一道道波纹,恰似扇子轻轻一挥,扇出一缕缕清风的波痕。
西南那边的山口,悠长狭窄的土路上,一个人影缓缓走来,下了山,再沿从西向东的大路往我们村庄的方向走来,那个人推着白行车,一身青衣,头上是白白的小帽子。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断定,碎舅舅来了。
碎舅舅姓李,在他们那个村里,李家是大户。
我母亲是大户人家出身。却嫁给了当时最穷的贫下中农。
我父母成亲时已经到了七十年代的末尾,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还没有实施。
土地承包到各家各户之前,我们家里的情况只能用一个字形容:穷。
那是一种如水洗了一样的贫困。
而远在三十里外的李家庄,光景远比我们好。李家庄居民一律姓李,是一个老先人传下来的子孙。李家历来家教严,风气纯朴,当年定成分时,李家庄没有一个地主,都是贫雇农,贫下中农,中农,最坏的也只是划成了富农。
舅舅家理应定为地主的,是大家集体庇护了这个够得上地主条件的人家,都是一个李家,一笔写不出两个李字,他们不愿意上演骨肉相残的苦戏。后来,我们的外爷爷李缠头,在社教中安排在了劳改的砖厂里,大家就对李缠头这一支血脉后人更是呵护关照,母亲记事起家里就一直比较好,日子苦巴,可远远没有撒马庄马家人困难。
母亲说她来到这个家里,虽然早就有了充分的心理准备,还是被这家的贫穷吓着了
我母亲的嫁妆极为丰厚,是他们那个年代李家庄人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当木匠的大舅舅亲白动手,给小妹子打家具。一对漆成大红色的大木箱,每个箱子的四个角上都包了黄铜色的梅花,前面画上三幅图画,一个箱子上的三幅画分别是喜鹊登梅,鸳鸯凫水,燕子闹春。另一个箱子上的三幅画依次是杏花图,双鱼嬉水,梨花图。我很小的时候就看见这些图画了,总是觉得好看,却看不懂是啥名堂。现在看得懂了,箱子早就旧得不堪,画面黯淡,褪色,是经历日月后的沧桑迹象,倒是不及童年记忆里那些画面的鲜艳色泽。
从母亲的嫁妆上,我们可以看出大舅舅是个心思细密的人,对他妹子的嫁妆也很重视,啥都做得细致精巧,结实耐用。两个箱子,十几年来一直盛装衣物,外面油漆剥落,箱子的样式结构却完好如初,没有丝毫散架的迹象。除了箱子,母亲的嫁妆还有一大堆零碎,一对粉盒,木雕的,桃木的木质纹理赫然可见,做工小巧精致,状如核桃,里外磨制得光滑细腻,捏在手心,一股淡淡的温润感油然而生。母亲的脂粉就装在里面。那时使用的是一种称作银粉的硬块脂粉,包在纸里,买回来装进粉盒,粉盒就永远散发一股幽幽的脂粉香。我小时候最大的愿望就是赶紧长大,早一天出嫁,要母亲将她的粉盒当作嫁妆,陪送给我。小时候,母亲的粉盒总是搁在高处,不允许我们把玩。粉盒里就盛了一个女子的梦想,幽幽的粉香,细腻的桃木质地,细巧的花纹,梦境五颜六色的,绚烂而质朴。等到我真的长大出嫁,早就不兴粉盒之类的小玩意,都是穿金戴银,嫁妆远远比当年的母亲丰厚昂贵,母亲的粉盒早就不知丢到哪儿去了。
大舅舅做给他妹子的还有梳子,篦子,簪子,鞋楦子……一大堆杂七杂八的东西,都是一个新媳妇生活里居家过日子的物件。今天看来,没有一样是值钱的。可那时,母亲说他大哥为此忙乎了好一阵子。
一对木箱子算得上是最阔气的嫁妆。还有二舅舅的那份哩。二舅舅是毛毛客,农活稍闲就坐下给人缝制皮衣皮裤皮帽子,以赚取一点手工费。母亲出嫁的时候,二舅舅的手艺已经在李家庄方圆有了名气。二舅舅倾尽所能,给他的妹子缝制了一个翻羊毛的“干衣”。这种衣裳我记事那些年里还流行,老人穿,男人穿,青色的面子,里面是二毛羔皮。这种皮子穿着暖和体面,是难得的上好衣物。二舅舅其实明白他妹子不可能舍得穿,就缝得宽大一些,早就准备好给妹夫穿了。果然这上衣后来真让我们父亲穿了,一穿好多年。二舅舅还给母亲缝了个小巧贴身的羊毛背心,这是真正给母亲的,父亲就是想穿也套不到身上。记得到一九九四年的时候母亲还穿着它。
母亲是很体面地嫁到撒马庄马家的。可是,父亲这边的贫穷还是叫她吃惊不已,难以接受。
父亲是个腼腆的小伙子。其实他们早就见过面,那是七八岁的时候。他们算得上是青梅竹马了。
小时候,母亲随她的母亲,来撒马庄走亲戚。我们外奶奶的娘家就是太爷这一门。细究起来,却又不是真正的亲娘家,是一个马家的后代。可能追溯到他们的祖父母那里,就能攀得上具体的血脉关系。
是女人总得有娘家。外奶奶没有娘家,就认了太爷这一门做娘家。
说起外奶奶认娘家,有一段叫人嗟叹的往事。
外奶奶小名七女。她在家里姊妹中排行老七。七女的父母一口气生出七个女子,看看年过半百,才最后生出个儿子来,真的是老来得子,喜坏了老两口。看看儿子将近一岁,就在一家人商量给儿子过周岁的那个冬天,地摇了。那是一场罕见的大浩劫。外奶奶说她们的父母睡在老院右边的窑里,她们姊妹在左首的土窑里,入夜不久,为了省油灯,大家早早就睡了。
大地摇开始了。七女从睡梦里惊醒过来。世界黑乎乎的。摸不着身边的姐姐们,油灯早不知去向。四周似乎全是土,大块的黄土几乎要将她埋起来。她在土里踹,踹姐姐,踹被子。
一阵接一阵天旋地转的震颤从身下传来。天地就要颠倒,星星在头顶上眨巴着寒咻咻的眼。
她才预感到出事了。摸到压在土下的姐姐,身子软软的,喊,她们就是不吭声。隐隐听到村庄里四处传来的哭声,狗叫声,羊叫声。外奶奶回忆说羊的叫声在半夜听来,那个碜人,死鬼一样。
七女摸出的姐姐都是死人。不是断胳膊,就是少腿。手上摸出一把一把的血水,湿乎乎的,她就四处乱抹,在泥土和血水中往外拉姐姐的身子。
有一个还活着!七女一摸她头上的辫子,断定是四姐,哭喊:四姐,四姐!
四姐一阵挣扎,说快跑,七女你快跑,地摇了。
四姐就昏过去了。七女抱住她喊,任凭她喊破嗓子,四姐就是不再应声,反倒渐渐冰冷下去。
借着星星的微光,她隐隐看清楚,土窑的顶子早就不知去向,四下全是黄土,院子倒塌成一片残骸。她们姊妹睡觉的土炕好像从窑里挪到了当院子,炕还好好的,她的光腿子还盖在被子里。父母歇息的窑洞黑乎乎地张开来,像一张大口。她哭喊着奔过去找寻父母。窑顶塌了,黄土压得死死的,她刨不开。
黑狗挣脱了绳索,跑过来,跟在她身后嗷嗷吼叫。一阵眩晕,她差点栽倒。残余的土院墙哗啦啦倒下一堵,又一堵。她还在土崖下的黄土堆里刨,她确信父母就压在下面。黑狗扯住她的后衣襟,死死往后扯,,她绊倒了,跌得满脸满眼泥土,爬起来哭喊着刨,黑狗愣是将她拖出一大截子。等她爬起来还要去寻找,刷啦啦窑又塌了,黄土埋得更厚。她惊呆了,坐在院子里的炕上哭。一直哭到后半夜,才昏昏沉沉睡过去。
外奶奶说她看见了奇异的景象。
名叫七女的女子,独白坐在倒塌的土炕上,身边是六个尸身残缺的姐姐。她抬头望着夜空,博大辽阔的夜空,深邃,幽冷,那些星星,仿佛没有看见人间发生的浩劫,兀自一颗颗闪烁着,发出微微寒光。余震还在持续,没有人告诉她怎样躲避灾难,四姐叫她跑,可她咋跑,黑漆漆的夜里,跑到哪儿去哩。唯一可以相依为命的黑狗也蹿出墙的豁口,不知去向。
恍惚中,她看见,遥遥的夜空里,一道亮光在西边打开,依稀有一扇门打开,好多人在排队,往门里涌去。一个老人在门口手握拐棍,一下一下点拨着,就有人不断被拨出来,滚落而下。人头黑压压的,连起来,像搓成的一条黑色毛绳在游动。
她望着那奇怪的景象,一直看到睡着。
那时,七女刚刚六岁。
我查阅了相关资料,那年正是一九二零年,那场浩劫就是震惊全国的海原大地震。
西海固人在这场地震中遭受的是灭顶之灾。打击是致命的。
天亮之后外奶奶看见了自己的父母。窑门塌了,自中间断裂,她从土堆上爬进去,刨开土,看见父母睡在炕上,颜面如生,周岁的兄弟睡在母亲怀里,他们三个人是在睡梦里离世的,身子冰凉后还保持着睡着的姿势。
村庄的人大半遇难。活下来的仅一小部分,其中还有一部分变成了残废,缺胳膊少腿儿,歪鼻子瞎眼,啥样的都有。大家埋葬了亡人。在塌废的原址上重新挖窑,盘炕,开始过日子。
七女是家里唯一的幸存者。我太爷的大哥收留了她。太爷一家死的人是:大嫂子,二哥三哥四哥五哥和他们的妻儿。大哥是外出贩卖皮子,才躲过了浩劫。
外奶奶一家亲人的坟园就在撒马庄的下庄子,每当舅舅他们来了,头一件事就是小净,去下庄子坟园给老人上坟。
有些人埋在窑里,埋得太深,挖不出来,也就不再掏,把那一块地方当作坟园,以后上坟的时候就跪在老窑的门前点香,念古兰经文。
我们家玉米园子下面那片陡坡,据说就是当年太爷们葬身的地方,那里有一排窑洞,弟兄五人,每家住一眼窑。太爷年小,随大哥大嫂子过。他们还有一个小兄弟,属少亡,埋在玉米园子的上面那片坟园里,坟头已经塌平。
我们的祖爷爷当时睡在一个装粮食的窑里,那个窑塌得不严重,只是土台阶上搁置的一个大瓦罐,装着满满一罐蜂蜜,地摇时瓦罐滚下来,端端跌在祖爷爷的心口窝里,祖爷爷就这样没命了。
名叫七女的外奶奶认了我们的太爷做巴巴。外奶奶就是在太爷家里长大,并出嫁的。
外奶奶记着太爷弟兄的恩情,把这里当亲亲的娘家看,有空就来走动。
我母亲小时候随着外奶奶来过我们家。她说那时她根本就看不上我们的父亲。问缘由,母亲嘴巴一撇,说没见过那么窝囊的娃娃,一点没有儿子娃娃的模样。
也就是这时候,奶奶问七八岁的女子,你给我家麻蛋当媳妇吗?
父亲居然有一个这样随意的名字。母亲说她听见谁喊麻蛋她就来气。好像他真会成了自己的碎女婿,就极力想摆脱他,不想看见他。
这个名叫麻蛋的少年长得分外瘦弱,高个头,瘦脸颊,走路悄没声儿。母亲说她们坐在奶奶的炕上拉闲,他悄悄进来,低着头,去窑里拿了啥,又小心翼翼低头出去了,始终不敢抬头看看炕上的亲戚。奶奶拉住他,说炕上这是你姑姑,李家庄的,给说个赛俩目。麻蛋涨红了脸,憋了半天,就是听不到从他口里说出赛俩目来。
奶奶放儿子出去,和外奶奶扯磨,说来说去,就说到了娃娃长大以后的事情上。两个人说碎女长大了就是麻蛋现成的媳妇儿。说完,她们嘀嘀咕咕笑,就是没有顾及一边碎女的感受,碎女又羞又气,从此对那个男娃娃怀了一种说不清的想法。
少年碎女这一回去,就再也没有到奶奶家来过,说起那个害羞的少年,满脸鄙夷,就是看不上他的胆小。
我父母的亲事最终还是成了。
提亲的是太爷。外奶奶来浪娘家,和太爷坐在上房炕上,仍旧说起娃娃们的事情,太爷说碎女长大了吧,这女子这些年咋不来浪娘家,要不就给麻蛋当个媳妇儿。外奶奶很是乐意,这等于把女儿嫁给了娘家侄儿,她乐意。
母亲一开始就抱着抵触情绪。真要把她嫁给那个窝头窝脑的男娃娃,这是她担心了好多年,终究无法躲过的事情。还是少女的母亲肯定极为郁闷。别人都为她准备嫁妆,热火朝天地忙,她自己没事人一样,冷眼看着忙碌的人。
母亲对于撒马庄的印象坏极了。她记起稍大些的时候,李家庄隔三岔五来几个讨饭的娃娃,都那么大了,还光着屁股,穿不起裤子。连女子娃娃都光着屁股。毛头娃娃到门上来,拥挤成好一堆,讨要吃喝,要是不打发,他们就不走,赖在门口,惹得狗汪汪叫,不断扑咬,愣是甩得铁绳哗啦啦响。外奶奶给每个人打发一点馍馍,摸着他们的光头问你们是哪个庄里的?娃娃们异口同声答:撒马庄的。
后面又来一拨,再问,还是撒马庄的。大家猜测,撒马庄一庄人都那么穷啊,咋都在要饭哩。
外奶奶心里难安,拾掇一点面食,背上去撒马庄看她的巴巴,真担心巴巴一家挨饿。
我太爷一家日子确实不好过,要饭的娃娃里就有他的小儿子小女儿。
其时正是母亲聘给父亲之后。母亲的郁闷程度可想而知。她存了心眼,听到门外狗咬,料定又有娃娃要饭来了,跑在别人前头开门去看,给几个光屁股娃娃一大块馍馍,求他们答应一件事,要是有人问你们打哪儿来的,就说是温塘的,马家湾的,刘家沟的,总之不要说是撒马庄的。
为了叫娃娃们改口,母亲费了好多馍馍,她真恨那些屁仔娃娃,恨那个叫麻蛋的窝囊少年,甚至恨撒马庄。母亲说她那时候就一个想法,撒马庄把自己给毁了,她这辈子算是完了。
母亲的前景黯淡极了,她看不见希望的光芒。撒马庄恶臭的名声,一贫如洗的家境,加上童年记忆里那个娃娃的窝囊印象,叫她前去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和那个娃娃做两口子,过活一辈子,真的是很让人伤心的事。尤其在一个少女想来,事情就更加糟糕。这可不是啥小事,是大事,一个女子一辈子可只有一次,是比天还大的大事。
母亲她能不忧心如焚吗。
母亲把前来掀脸的花儿娘给撵跑了。花儿娘是远近出了名的掀脸高手。手艺好,可她嘴不好,对着母亲一张闷闷不乐的脸品评,说要当新媳妇了,就得笑笑的,这样紫涨着可没有新媳妇应有的喜庆,婆家不待见的。经她手底拾掇出的脸盘,没有不透着喜庆色的。
我母亲当时一把扯断花儿娘手里的红线绳子,腾地跳下炕,取出炉火上煮得咕嘟嘟作响的两个鸡蛋,狠劲磕,磕破了,极麻利地剥下皮,放进嘴里,也没见怎么咀嚼,就吞咽下去了。
花儿娘给大姑娘掀脸无数,阅人无数,就是没看出来这个女子会是个厉害角色。
我母亲的举动惊骇了所有前来吃宴席的女人。她们悄悄议论着这莫名的变故。我的外奶奶出现了。外奶奶三十五岁上第一个男人病故,四十一岁那年第二个丈夫离世,她是一路踏着风雨走过来的,她啥场面没见过,对于小女子的任性和倔强,她早清清楚楚,我母亲对白己这门婚事的心思,当然也瞒不过她的眼睛。
事情到了这个节骨眼上,就是女子再不情愿,都为时过迟,有她这当娘的在,女子心思再花,也翻不出她的手掌心。
外奶奶毫不惊慌,微笑着说:这女子叫我娇惯完了。只一句话,就把所有的风雨遮掩过去了。
外奶奶不动声色地打发花儿娘出门,还按照老来的规程给人家送了谢意。
事实上母亲的脸只是草草扯出个大模样,嘴角鼻翼耳朵碗里的细嫩汗毛远没有拾掇干净,看母亲暗白垂泪又愤愤不平的神气,这脸无论如何没法再掀。外奶奶扔一个头巾给女子,看着她将头巾搭上,遮掩住有些毛糙的脸盘,外奶奶才出门忙别的去了。
外奶奶临出门,攀住门帮子,丢下一声重重的叹息,走了。这叹息像一枚熟得过透的果子,落在碎女心上,落得无声无息,却顿然破裂,浓烈的汁水四溅开来,我母亲闻到了酸涩的味道。
这门亲事,媒人换作谁都好推辞,偏偏是我们的太爷,外奶奶的娘家巴巴。外奶奶没有转圜的余地,何况她一开始就没打算推辞。
我母亲就带着一张没有掀干净的女儿脸上路了。大舅舅二舅舅押送着陪送的嫁妆浩浩荡荡踏上了李家庄通往撒马庄的土路。母亲头蒙黑色盖头,骑在最前头的一头黑色叫驴背上,由拉驴的娃娃牵着,沿土路走向撒马庄。
那时候还实行哭嫁的老规矩,女儿家嫁人都得哭哭啼啼上马,哭哭啼啼离开生养自己的娘家。不哭不行,不管你心里多么高兴,急于离开这个枯燥的地方去那个向往已久的夫家,可是,这会儿都得哭哭,真哭还是假哭都不要紧,反正有盖头蒙头,外人看不清。
我母亲却哭得一塌糊涂,她是真正的伤心,真正地不愿意离开娘家。借着这个机会,她将半年来窝在心里的委屈全都发泄出来,哭声凄惨,感人。惹得好多女人也抹起泪来,她们感叹说女子娃娃就是命苦,长大了就得离开白己的家,到旁人家受灾受难去。
哭嫁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你尽管放开嗓子哭,可就是不能哭诉,不能咿咿呀呀地诉说,那是死人出丧的一套哭法,成亲是好事,喜事,好事成双的事,要是哪个女子嘴里哕哕嗦嗦诉说一大堆,那会叫人笑掉大牙的。还有,哭的时候不能声音过大,放得过开,是轻轻巧巧凄凄婉婉的哭,能惹人怜爱,叫人跟着落泪。总之,就是得哭,可要哭得好看一点,动人一点,优美一点。是山里人在苦闷的日子里想出来的,增加生活滋味的一种方法吧,这法子现在不多见了,现在的女子大方,放得开,谁还会像个青涩的果子,做出羞涩的模样哭天抹泪哩。
我母亲哭着上了驴背。是被大舅舅抱上去的。就在这哭声上出了点岔子。外奶奶原本担心她这犟女子反抗,想不到她倒安安稳稳穿了嫁衣,蒙上盖头,安安稳稳上了驴背,就在外奶奶一颗提着的心刚要放在腔子里时,驴背上出阁的女子,哭声忽然大起来,像骤然升高的音符,在唏嘘送别的人群里炸响开来。这哭声没有节制,没有顾虑,完全是放肆的,无所顾忌的。新媳妇美好的形象在哭声中被撕得七零八落,惨不忍睹。一个本该凄婉优美地上路的女子,居然将哭声弄得像泼妇,像哭丧,这真的是大煞风景的事情。
外奶奶生活里的那些风雨坎坷不是白白见过的,她稍一愣神,第一个清醒过来,冲着拉驴娃娃喊,走,上路!抽出娃娃手里的皮鞭子,狠狠抽一下叫驴,叫驴带着伤痛,惶然迈步上路。母亲含糊不清的哭诉就被跄然奔跑的驴子带远了。
深冬的天气,路上奇冷,骑在驴背上不能活动,腿脚冷得厉害。大舅舅赶上前,撩起白己的大衣襟,抱住妹子的脚给取暖。这边暖暖,跑到另一边再暖暖。母亲一直在哭,期期艾艾的哭声,撒了一路。陪嫁的是母亲的大姐,大姐一惯性子绵软,语气轻柔,在这种场合下终于沉不住气,努力追赶前面的叫驴,试图提醒妹子不能再哭了,已经走过一大半路了,再哭,就不吉利了。可惜她骑的是一匹黑草驴,脚程远没有叫驴快当,就焦急得不行,压着嗓子喊停下停下,不能再哭了不能再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