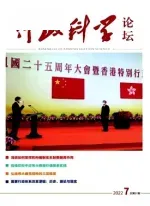我国宪法宣誓制度的架构及其责任解析
谭 波
(河南工业大学 法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1;中国社会科学院 法学研究所,北京 100720)
中国共产党十八届四中全会的报告《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在强调宪法地位与作用时重点提到了“宪法程序”问题。如果我们观察当前党的宪法政策文件中的最新提法,就不难发现,比如《决定》提到的“完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宪法监督制度,健全宪法解释程序机制”,“加强备案审查制度和能力建设”,“完善党对立法工作中重大问题决策的程序”,“完善法律草案表决程序,对重要条款可以单独表决”,“实践条件还不成熟、需要先行先试的,要按照法定程序作出授权”。“程序”[1]一词的反复出现足以说明,我国当前的程序建设尤其是权力运行程序还存在着诸多可以弥补的漏洞,制度建设任重道远。以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程序建构设想来看,宪法宣誓制度便是其中一例。“凡经人大及其常委会选举或者决定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正式就职时公开向宪法宣誓”,很明显,这是一项实体操作与程序结合的制度。但如果按照既定的常规思路来建设,则其硬性约束力可能为软性约束力所取代。以下我们可以通过对世界范围内宪法约束制度的探讨,来分析与预测我国下一步宪法约束制度的建构程序。
一、宪法宣誓程序建构的缘起及缺憾
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的起草说明曾提到“这是世界上大多数有成文宪法的国家所采取的一种制度。在142 个有成文宪法的国家中,规定相关国家公职人员必须宣誓拥护或效忠宪法的有97 个”。随后指出,“关于宪法宣誓的主体、内容、程序,各国做法不尽相同,一般都在有关人员开始履行职务之前或就职时举行宣誓”。在这种数字比例的影响下,国家决定“凡经人大及其常委会选举或者决定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正式就职时公开向宪法宣誓”,并在后面提及这样做“有利于彰显宪法权威,增强公职人员宪法观念,激励公职人员忠于和维护宪法,也有利于在全社会增强宪法意识、树立宪法权威”。2015年7 月1 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实行宪法宣誓制度的决定(草案)》。
整个权力约束程序的建构过程似乎天衣无缝,但仔细想来,是不是真是这样经过一种论证或数字搜集过程就足以造就我们成功的程序机制了呢?宪法的规定很清楚,即“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那么除了国家机关中的由人大及其常委会选举或决定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外,其他人在未来的宪法宣誓程序中,是不是就无所作为或不能作为了?或者说作为了以后,即使违反也不会追究相应的宪法责任了?当然不是。
通常情况下,我们在增加或修缮一种宪法程序时,必须把这一问题的来龙去脉彻底搞清楚,这里应该秉持一种社会学及历史学的观点,同时通过认真总结归纳把责任与程序落实连接起来,以责任保程序、以程序控权力、以权力护权利则为最终目的。从宪法宣誓程序来看,其本意不存在什么立论问题,它也符合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君子一言,驷马难追”的古训,但我们要明白的是,这一宪法宣誓程序绝不能简单地照搬,有必要明确我们的宪法宣誓究竟是在什么样的文化背景下建构的,与之相似的国际惯例如何操作,在我国这样的背景下如何建构起为人信服的宣誓程序机制。
二、宪法宣誓程序的制度元素架构
第一个问题,当然回到了开始时提出的那个疑问,即目前宪法宣誓到底在多少国家有,它们建构状况如何。为了保证整个结论的严肃性,我严格查阅了2012 年出版的《世界各国宪法》,得出的结论大致是,目前在五大洲193 个国家中,不成文宪法的国家大致有英国、瑞典、新西兰、以色列等少数几国;而在这180 多个有成文宪法的国家中,具有宪法宣誓或准宪法宣誓程序的有167 个。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有些政教尚未完全分离的国家,实际上存在向古兰经等宗教经典宣誓的做法,但有些也规定在宪法中。而这种广泛的统计实际上也不排除议员等代议机构成员本身所做的宣誓。而早先,在德国魏玛宪法之中,甚至有军人的宣誓(这里暂且不提)。在现代世界各大洲中,欧洲国家较早步入近代文明阶段,其相应的现代宪法文明及程序建构也较为先进。在44 个国家中,有36 个国家建构了宪法宣誓制度,占到4/5。欧洲国家的宪法宣誓制度建构相对完整,一般有明确的宣誓主体、宣誓对象、职责重点所在,而不是不加区别地统一所有誓词,而这于我们这个宪法宣誓制度建构刚刚起步的我国而言,恰恰是需要首先考虑的。因此,在宪法中首先明确宪法宣誓的各项程序要素,是该项程序制度建立的首要任务。适当的时候,还可以通过宪法授权的方式交给相应的委任性规范制度来设置。一些国家还细分了立法宣誓、行政宣誓和司法宣誓制度,针对不同的宪法主体有不同的程序要求,它们分别表现在宣誓的时间和空间上。由于各国不同的宗教背景和诸多的君主制国度存在的现状,我们对该洲国家宪法宣誓程序制度的学习也暂止于此。但从其宣誓对象来看,它们的宪法宣誓程序制度基本上都已经达到了政教分离的目标,仅是以“上帝的名义”,而绝非对上帝而行的宣誓,因为这牵涉到宪法责任的后期承担,不是仅有道德的谴责,而恰恰是要向“人民主权”背景下的国民承担国家责任。这是宪法宣誓目前在现在欧洲各国的程序意义所在。
反观我国,目前,在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的提法之前,我国有关宪法宣誓的制度规定主要有2012 年12 月19 日最高人民法院印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宣誓规定(试行)》(法发〔2012〕27号),所述较详,但这仅限于法官职业群体。2013年3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式上发表讲话:“我深知,担任国家主席这一崇高职务,使命光荣,责任重大。我将忠实履行宪法赋予的职责,忠于祖国,忠于人民,恪尽职守,夙夜在公,为民服务,为国尽力,自觉接受人民监督,决不辜负各位代表和全国各族人民的信任和重托。”但这也只能看作是国家主席在就任这一职位前的个人表达。“要建立宣誓仪式的程序规则,其内容包括由谁来主持宣誓仪式,谁来参加宣誓仪式”“让庄严的程序来增加宣誓者和公众对宪法的敬畏感,形成对法治的信仰”[2]。这实际上也是程序完成其初步使命的过程。2015 年7 月,经过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讨论后,宪法宣誓的誓词和宣誓人员范围被确定,宪法宣誓的组织者和仪式环节也被确定,这也只是按照上述思路完成了宪法宣誓程序的第一步。
三、宪法宣誓程序之观念确立:相近文化的比较
在亚洲,东方法治文化的一种倾向在于更加重视实体,略轻程序。这不仅表现在中国古代的法制文化中,同时也彰显于其他诸多的亚洲国家之中。从数量上来看,亚洲46 个国家有38 个具备宪法宣誓制度,占据比例与欧洲国家不相上下。
从国家性质来看,亚洲的其他几个社会主义国家也并没有相应的宪法宣誓制度,在这一点上与中国保持一致。然而,这其实并不是程序制度设置的障碍。因为,程序本身具有相应的共通性,其技术性较强,所需要的只不过是克服或弱化原本的文化观念障碍,淡化其宗教背景或者意识形态背景。如果我们假设社会主义国家都主张唯物主义,而宪法宣誓本身是在宣扬唯心,那么我们对于这样的程序制度设置可能就存有芥蒂。但如果我们从强化宪法观念、强调宪法心理内化的视角来看,这种程序制度设置就不成问题,也就是构成我们所说的“观念宪法”(其来源于现实宪法而被固化于成文宪法,而又可反作用于现实宪法,并促进成文宪法进一步的修缮[3])。“从设立国家宪法日到建立宪法宣誓制度,一个重要目的在于让依宪执政的思维内化于所有国家公职人员心中”[4]。
因此,正确对待宪法程序观念是建构宪法程序制度的第二步,有制度而不破除旧有观念,将导致宪法程序制度的实际死亡。如果我们突破意识形态的鸿沟,并且客观看待宪法宣誓与宗教的关系,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也就是,我们完全可以在文化上接受这样的一种制度设置。
值得一提的是,在剔除西亚伊斯兰宣誓模式的情况下,南亚的印系国家如印度、斯里兰卡、孟加拉等国家成为我们重点关注的对象。不同职位有着不同的宣誓誓词,这对于东方历来崇尚等级观念的国家而言比较具有适用性,也易于操作。有些宪法宣誓的誓言被单独置于宪法附件,既独立醒目,又起到了与正文内容加以区分的作用。值得效仿的东南亚国家还有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后者的誓词中虽然也含有对宗教偶像的宣誓,但整体仍不乏层次性与现代性。尤其是新加坡的宣誓程序,区分了总统就职誓词和代总统职权的人就职誓词(两者可归为一类)、效忠誓词、国会议员就职誓词、总理就职誓词、部长及政务次长就职誓词、公共服务委员会主席及成员就职誓词、少数族群权利总统理事会主席及成员守密誓词、总统咨议会主席或成员守密誓词和首席大法官、法官及司法专员就职誓词等八种不同的对象与情况,可谓程序建构已经达到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哲学视角的要求。而且,有些誓词的内容已经到了十分具体的地步,如“除非因履行职责的必需,不直接或间接向未授权的人披露此等事项”,这种誓词已经隐含了某种宪法义务的建构。而在以色列等一些国家,宪法宣誓的未完成实际上成为议员等国家公职人员具备权利资格的障碍。“当国会议长要求国会议员宣誓效忠而该议员拒绝时,该议员将不得享有国会议员的权利,直至其完成宣誓为止”,这说明宪法宣誓的意义绝对不局限于仪式,它已经可以成为特殊权利能力获取的程序要件,甚至是重要的生效要件,这在我国未来的宪法程序建构中也应加以明确。
四、违反宪法宣誓之责任的追究与落实
(一)宪法宣誓的形式意义与责任
宪法宣誓本身只是一种形式构架,“面向宪法宣誓到底具备什么意义,能起到什么作用,这不取决于宪法宣誓仪式举办得多么隆重和严肃”[5],重要的还是要强化其后续的责任。“要建立起对公职人员背弃誓言、违反宪法的法律约束和惩戒制度,只有这样,宪法的权威才能真正树立”[2]。如前文所示,新加坡的某些公职人员如果并非由于职责的需要,直接或间接地向未授权的人披露了需要保密的事项,那么他(她)所承担的宪法责任是明显的,这种宪法责任当然也可被归结为是他(她)违反宪法誓言的一种惩处。在我国,《宪法》第五十三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保守国家秘密……”一旦违反这种“保守国家秘密”的要求,其承担的责任完全可能是两种或多种责任的竞合,而这其实也应和了我国宪法宣誓责任机制建构的需要。如2014 年在给周永康违法违纪行为定性的问题上,有关文件使用了“严重违反党的”“保密纪律”,“泄露党和国家机密”等的词语,我国2010 年修改后的《保守国家秘密法》规定,“机密级国家秘密是重要的国家秘密,泄露会使国家安全和利益遭受严重的损害”,而“国家事务重大决策中的秘密事项”在国家秘密的列示中被列为首条。在违反宪法和法律义务的问题上,其按照刑法的“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承担的刑事责任,实际上也是一种宪法责任的延伸,而如果造成相应的损失,是否还要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则是未来在建构该种宪法宣誓制度类型中需要着重考虑的一个问题。
(二)政治责任与宪法责任的合与分
在我国,宪法的实施实际上是通过政治化实施和法律实施两种渠道在进行[7]。从法律责任的角度来讲当然也应有相应的两类渠道。当下政治责任的追究有强化之势,而政治责任的追究又包括党的追究和政治追究两种不同渠道[8],同时,“自我追究也属于政治责任追究的方式,比如官员对履职情况和言行进行自我评价,如未能认真履行职责或言行违背民意而进行的道歉可理解为自我追究的一种方式”[9]。这里其实也可理解为是对宪法宣誓誓言的违背而进行的道歉,但这种政治责任的承担并不能成为宪法责任追究。在世界范围内,许多国家也有相应的宪法宣誓程序违背的责任机制。如前文提到的印系国家,其中印度和孟加拉国的宪法均明文规定,如果没有经过宪法宣誓程序而直接就任的议员,要承担被罚款的责任,这是一种典型的宪法责任追究,其中孟加拉国宪法的条文叙述得更为明确,即“作为对共和国欠款的偿付(a debt due to the Republic of the Philippines)”。
(三)宪法宣誓责任发展方向的开放性
对宪法宣誓誓词违背的多元性决定了其未来的责任发展应该具有更大的包容性,其中可能涉及政治责任、经济责任或者保密责任。2014 年8 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反间谍法》,并同时废止了原来的《国家安全法》,等于以前者的“新瓶”取代了后者的“旧酒”。2015 年7 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又审议了新的《国家安全法》,国家安全的概念已经扩大,提到“国家安全是指国家政权、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人民福祉、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其他重大利益相对处于没有危险和不受内外威胁的状态,以及保障这种可持续安全状态的能力”。新的草案在赋予公民支持、协助国家安全工作受法律保护等权利的同时,也强化了公民和组织维护国家安全的责任和义务。这样,在未来的国家宣誓制度中,这种宣誓程序的责任机制很可能也需要根据不同层次和群体将其分别上升到维护国家安全的高度,比如保密宣誓可能涉及的保密纪律等。如此将表明宪法宣誓追责机制的内容是开放的,完全可能根据未来实际的需要而厘定其相应的法律责任。需要明确的是,不应该只是通过具体部门法的责任形式来统摄宪法责任,而是应该慢慢推行宪法责任,尤其要使狭义宪法责任的单立化,以此来推进我国宪法责任意识的强化和宪法权威的全面树立。
[1]《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辅导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7,8,11.
[2]范嘉欣.以“宪法宣誓”明确法治责任[N].江西日报,2014-12-04(B3).
[3]刘茂林.宪法研究导论(第2 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52.
[4]徐扬.用宪法宣誓制度捍卫宪法尊严[EB/OL].(2014-12-13)[2015-10-16].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4-12/03/c_1113497180.htm.
[5]叶竹盛.仪式的意义[J].南风窗,2014(23):8.
[6]翟国强.中国宪法实施的双轨制[J].法学研究,2014(3):82-94.
[7]刘俊生.政府官员的政治责任追究[J].新视野,2003(1):45-47.
[8]刘广登.宪法责任论[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7:1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