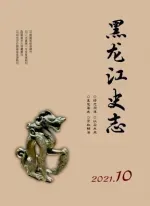陈寅恪之独立自由精神浅论
王靖玮
(贵州大学人文学院 贵州 贵阳 550000)
作为二十世纪人格最峻洁、学术成就最卓著的一代史学大师,陈寅恪已然成为一个时代的象征。而上世纪以来的“陈寅恪热”,更使得这位在十年动乱中一度淡出国人视野的学者,再次成为学术圈内外谈论的重要话题。陈寅恪学术研究的宏大视野(如时间、空间的突破与古今中外的比较)、精密研究方法(如“三重证据法”)、高度学术敏感(如“预流”说)等等,自然值得不断深入阐发,以期促进当下的学术研究水平。而把握其人生、学术一以贯之的思想,则同样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
对陈寅恪精神的把握,最关键的要点有二,曰独立、自由。“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贯穿于陈寅恪终生学术研究的最核心宗旨,也是其一生用舍行藏进退出处的根本原则。无论在学术研究,还是知识人的人格培养方面,这种精神都具有典范的价值,已内化为中国学术研究精义的重要部分。
一
独立与自由,是近代以来尤其是新文化运动以来,整个民族的集体追求,但落实到切实践履,陈寅恪当是这个词语的最好诠释。形之于文字,则为其于1929年所写的《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在碑铭中,他写道:“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宜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1]文中所论述的对象是同为近代国学大师的王国维。王国维(1877-1927),字静安,号观堂,浙江海宁人。1927年6月3日,王自沉于颐和园的昆明湖鱼藻轩。一代大师自沉,一时间议论纷纭,或以为与王曾效力清廷,北伐军即将入京,恐难免祸,因惧怕遭受屈辱,乃仓皇自尽;或以为系与罗振玉有隙,兼晚年丧子,心怀郁郁,不能自解,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但作为王国维的同事与友人,陈寅恪对此事给出了自己的解释,并进一步申说道:“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无论这种解释是否符合历史的真相,但他把王国维的死提到民族与文化的高度,给这一事件赋予了丰富的精神意蕴,也获得了学术界大多数人的认可。当然,“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与其说在论述王国维的自沉,不如说是陈寅恪自己对人生与价值的深刻思考,有着切身的思想认同,将其视为自己为人治学的根本宗旨。
关于独立自由精神的阐释,在陈寅恪的论著中,是屡见不鲜的。1953年,也就是在撰写王国维《碑铭》二十四年之后,在《论再生缘》这一长文中,他再次明确提出:“撰述长篇之排律骈体,内容繁复,如弹词之体者,苟无灵活自由之思想,以运用贯通于其间,则千言万语,尽成堆砌之死句,即有真情实感,亦堕世俗之见矣。不独梁氏如是,其他如邱心如辈,亦莫不如是。再生缘一书,在弹词体中,所以独胜者,实由于端生之自由活泼思想,能运用其对偶韵律之词语,有以致之也。故无自由之思想,则无优美之文学,举此一例,可概其余。此易见之真理,世人竟不知之,可谓愚不可及矣。”[2]认为《再生缘》之所以能从一向被界定为庸俗且不能登大雅之堂的弹唱文学中脱颖而出,显示出足以抗衡主流文学的品位与价值,“自由思想”才是其根本,并得出“无自由之思想,则无优美之文学”这一精辟的论断。同样,在晚年苦心结撰的皇皇巨著《柳如是别传》中,作者面对风雨如磐的社会局势,以及目盲老病的身体状况,将一腔心血融入文字,写道:“夫三户亡秦之志,九章哀郢之辞,即发自当日之士大夫,犹应珍惜引申,以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何况出于婉婪倚门之少女,绸缪鼓瑟之小妇,而又为当时迂腐者所深诋,后世轻薄者所厚诬之人哉!”[3]柳如是虽为明末声闻煊赫的秦淮名伎,但无论在当时或是后世,影响总归是十分微弱,以一史学大师,为何在艰难备尝的晚年竟然放弃所擅长的中古史,而选择这么一个人物来写一部大部头的著作,若非深深体会了其对独立自由思想至死不渝的坚守,是难以解释这一论题选择的。因为《柳如是别传》一书的核心思想,即在“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当然,更为后世所津津乐道的,还是他的《对科学院的答复》。1953年10月,国家历史研究委员会奉命在中国科学院设立三个历史研究所,拟由郭沫若、陈寅恪、范文澜分别出任一所(上古史研究所)、二所(中古史研究所)及三所(近代史研究所)所长。11月中旬,陈的学生,时为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的汪篯南下广州请陈寅恪北上。暌违的师徒并未在此问题上得出一致的见解,不欢而散,并留下了这一纸答复。
《答复》中说:“我认为研究学术,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所以我说‘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俗谛’在当时即指三民主义而言。必须脱掉‘俗谛之桎梏’,真理才能发挥,受‘俗谛之桎梏’,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学说有无错误,这是可以商量的,我对于王国维即是如此。王国维的学说中,也有错的,如关于蒙古史上的一些问题,我认为就可以商量。我的学说也有错误,也可以商量,个人之间的争吵,不必芥蒂。我、你都应该如此。我写王国维诗,中间骂了梁任公,给梁任公看,梁任公只笑了笑,不以为芥蒂。我对胡适也骂过,但对于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我认为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说‘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我认为王国维之死,不关与罗振玉之恩怨,不关满清之灭亡,其一死乃以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且须以生死力争。正如词文所示,‘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贤所同殉之精义,其岂庸鄙之敢望’。一切都是小事,惟此是大事。碑文中所持之宗旨,至今并未改易。”[4]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面对的是代表国家威权的知识界的最高层,能够写出这样的文字,需要何等的勇气!若非将独立自由精神视为个体存在的基础,视为高于生存、高于权势的永恒价值,是不可能做到的,所以才说“一切都是小事,惟此是大事”。
二
独立自由精神在陈寅恪八十年的人生、学术活动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分而言之,则可以从明辨是非、择善固执、以道抗势、自出新意四个方面稍加论述。
1.明辨是非
《孟子》说:“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是非判断是人存在的基本判断。对于日常生活中的是非,因有约定俗成的伦理道德或国家法律为衡量标准,通常较为容易评判。而学术研究中的是非,则常常易被潮流所裹挟,若无高度的自觉,有自己的独立思考,则难以立定脚跟,如中国近代的辨伪之风。
虽然自孟子就提倡“学贵有疑”,历代学者对先代典籍早有辨别和议论,如宋代王安石、朱子等人疑《周礼》《尚书》,到清初的阎若璩的《尚书古文疏证》更是使辨伪之学达到了一定的高度,之后姚际恒、崔述益加发皇,到二十世纪初与西方的实证主义合流,形成了一个声势浩大的辨伪学派,如以顾颉刚为首的“古史辨”派。于是一时间许多曾为世所尊崇的典籍,很快被价值颠覆,如《古文尚书》,如关于三皇五帝夏商的传说,都被认为是后世凭空的臆造。
但是,陈寅恪并没有在学界的潮流中迷失,在为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所写的审查报告中,他指出:“以中国今日之考据学,已足辨别古书之真伪。然其伪者,不过相对问题,而最要在能审定伪材料之时代及作者,而利用之。盖伪材料亦有时与真材料同一可贵。如某种伪材料,若径认为其所依托之时代及作者之真产物,固不可也。但能考出其作伪时代及作者,即据以说明此时代及作者之思想,则变为一真材料矣。”[5]认为即使是后代的伪书,同样具有研究的价值,而不能毫无辨别地一概抛弃。如今传《列子》一书,是魏晋人所假托,并非先秦思想,但是以之来考察魏晋时期的思想,却是具有很大价值的。在明辨了这一学术是非之后,他更进而提出了研读古书的基本要求,即“理解的同情”,说:“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盖古人著书立说,皆有所为而发。故其所处之环境,所受之背景,非完全明了,则其学说不易评论,而古代哲学家去今数千年,其时代之真相,极难推知。吾人今日可依据之材料,仅为当时所遗存最小之一部,欲借此残余断片,以窥测其全部结构,必须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始可以真了解。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者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否则数千年前之陈言旧说,与今日之情势迥殊,何一不可以可笑可怪之目乎?”这一真知灼见自一提出,就被学界普遍接受,成为史学研究的基本前提。而之所以能明辨是非并提出这一见解,则正和其一贯坚持的独立自由精神密切相关。
2.择善固执
择善固执是儒家道德修养的重要方面。《中庸》云:“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6]“择善固执”即是选择“善”,不受外界的干扰,一直坚持下去,与独立自由有着内质的相通性。
陈寅恪生活的年代,正值“三千余年一大变局”(李鸿章语)。政治上,旧有的政治体制土崩瓦解,新的国家建构正在探寻;经济上,小农经济逐渐破坏,资本主义方兴未艾;文化上,传统文化受到国内外的各种挑战,“全盘西化”之说一度甚嚣尘上。陈寅恪生长于官宦之家,祖父陈宝箴曾官居湖南巡抚,在戊戌变法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其父陈三立为“同光派”的领袖,一门显赫,在当时享有极高的声誉。但并非是说家世决定了陈寅恪的人生学术态度,虽然二者之间不无关联。
对于自己的学术思想,在1933年为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所作的审查报告中,陈寅恪如是说:“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湘乡南皮之间。”[7]关于这句话的阐释,历来众说纷纭。作为当事人,冯友兰先生说这句话是陈先生在叙述“自身之学术工作、思想情况”,而“其言简明扼要,为研究寅恪先生之最原始材料。”但陈寅恪的学生邓广铭提出异议,认为“那几句自述只是一种托词”,甚而说“如果真有人在研究陈先生的思想及其学行时,只根据这几句自述而专向咸丰、同治之世和湘乡、南皮之间去追寻探索其踪迹与着落,那将会是南辕而北辙的。”其他诸如汪荣祖、桑兵等都有辨析,而在种种解释中,更为客观、平情的大概要推程千帆。在《闲堂书简》中,他说“陈先生说‘寅恪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汪荣祖竟然认为这是指他专攻中古史,即魏晋六朝、隋唐五代。这不但与事实不合,也完全不解陈先生的微旨。‘不今不古’这句话是出在《太玄经》,另外有句话同它相配的是‘童牛角马’,意思是自我嘲讽,觉得自己的学问既不完全符合中国的传统,也不是完全跟着现代学术走,而是斟酌古今,自成一家。表面上是自嘲,其实是自负。根据他平生的实践,确实也做到了这一点,即不古不今,亦古亦今,贯通中西,继往开来。”[8]
所谓“不古不今”,这一看似不可理解的话语,其实正和陈寅恪平生所最珍视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一脉相承。程千帆所说“表面上是自嘲,其实也是自负”,可谓深解个中意味。因为二十世纪初期正是中外文化交流碰撞最激烈的时期,既有竭力固守传统文化而深闭固拒者,如叶德辉等,也有痛斥旧有文化为有百害而无一益者,如钱玄同等。在传统与进步之争中,固然双方阵营中都不乏有真知灼见者,但更多的是并无真切体会的附和。这在固守独立自由精神的陈寅恪看来,都是难以接受的,他自有其判断的标准。因此无论是在为人还是为学,都可以看到陈寅恪身上的“不古不今”,而正是这种“不古不今”,塑造了一座学术与人格的高峰。
3.以道抗势
道即道义,势即权势。“道”“势”之辨,是儒家思想中一个重要的命题。孟子就明确说:“古之贤王好善而忘势,古之贤士何独不然?乐其道而忘人之势,故王公不致敬尽礼,则不得亟见之。见且犹不得亟,而况得而臣之乎?”[9]当然,孟子以道自任,倡导仁政,游说列国,所面对的势主要来自政治威权,而作为学者,陈寅恪所面对的“势”,不仅有国内政权,还有国外势力,与学界的“势”。
陈寅恪与国内政权的态度,前引《对科学院的答复》已有充分的显示,为了保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他竟然对中共的最高领导提出条件,要求“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而且,“不止我一人要如此,我要全部的人都如此”。这还只是第一条。第二条是要毛泽东或刘少奇给他开证明,“以作挡箭牌”,并且“最高当局也应该和我有同样的看法,应从我说”。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中,这是何等的不可思议!
鸦片战争后的一百年,中国倍受外国侵略者陵辱,而尤以日本为剧。1941年,受香港大学中国文学系主任许地山所邀,陈寅恪往任职客座教授,讲授隋唐史。1941年底香港沦陷,学校停课,生活物资奇缺,由于陈寅恪在日本享有很高的声望,日军十分礼遇,希望以充裕的物资博得陈寅恪的好感,但他拒不接受日人馈赠。香港日本政权欲以高薪聘请其任香港东亚学院院长,也被拒绝。1942年,他携妻女逃离香港,至桂林,任教于广西大学。
对于学术界的权威,陈寅恪也从来实事求是,当仁不让。在《对科学院的答复》中,他回忆早年的治学生涯说:“学说有无错误,这是可以商量的,我对于王国维即是如此。王国维的学说中,也有错的,如关于蒙古史上的一些问题,我认为就可以商量。我的学说也有错误,也可以商量,个人之间的争吵,不必芥蒂。我、你都应该如此。我写王国维诗,中间骂了梁任公,给梁任公看,梁任公只笑了笑,不以为芥蒂。我对胡适也骂过。”[10]王国维、梁启超、胡适,是近世学术界公认的大师,但陈寅恪从不在学术是非面前稍有迁就。尤其是王国维、梁启超在世时,陈虽名列清华四大导师之列,但以界内声誉、学术著述及影响力来说,都远有不及,而能不为“势”动,是极其不易的。
4.自出新意
陈寅恪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还表现在他的学术创新上,而绝不是拾人唾余,人云亦云。在清华学校任教时,上课前,他对学生说:“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也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
另一件在当时备受争议的事是他为清华大学中文系国文科1932年夏考拟定的考题。他所出题目,一为作文《梦游清华园记》,一为对子“孙行者”。以对对子为题,在南北学界颇引起了一阵风波,“以此招致纷纷非议”。“试事终,下第者大噪。”甚而学术界内也多有议论,表示难以理解,如傅斯年就特致函询问。但陈寅恪并不因为外界的议论而稍有妥协,而是坚持自己的见解,据理力争。在回复傅斯年的信中,他说:“清华对子问题乃弟最有深意之处,因考国文不能不考文法,而中国文法在缅藏语系比较研究未发展前,不能不就与中国语言特点最有关之对子以代替文法,盖借此可以知声韵、平仄、语辞、单复词藏贫富,为国文程度测验最简之法,若马眉叔之谬种尚在中国文法界有势力,正须摧陷廓清,代以藏缅比较之学。中国对子与中国语之特点最有关,盖所谓文法者,即就其语言之特点归纳一通则之谓,今印欧系格义式马氏文通之文法,既不能用,舍与中国语特点最有关之对子,而更用何最简之法以测验学生国文文法乎?”他还特意表示:“以公当知此意,其余之人,皆弟所不屑与之言比较语言文法学者,故亦暂不谈也。此说甚长,弟拟清华开学时演说,其词另载于报纸,弟意本欲藉此以说明此意于中国学界,使人略明中国语言地位,将马氏文通之谬说一扫,而改良中学之课程。明年若清华仍由弟出试题,则不但仍出对子,且只出对子一种,盖即以对子作国文文法测验也。”[11]文中的“马眉叔”为清末的著名学者马建忠,所著《马氏文通》是中国第一部较系统的语法著作,影响很大。但其书以西方语法为本,强解中国文言,颇多扞格之处,反不如传统的对对子,立足中国语言文法的特性,更能见出考生的中文修养。从对这件事的处理中,可见陈寅恪对独立自主的深刻认识和笃实践履。
1964年,也就是陈寅恪辞世前五年,此时他已经受到冲击,再难继续学术研究,开始考虑身后之事,终将平生著述托付给晚年最知心的弟子蒋天枢,并写下《赠蒋秉南序》,说:“默念平生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似可告慰友朋。至若追踪昔贤,幽居疏属之南,汾水之曲,守先哲之遗范,托未契于后生者,则有如方丈蓬莱,渺不可即,徒寄之梦寐,存乎遐想而已。呜呼!此岂寅少时所自待及异日他人所望于寅恪者哉?虽然,欧阳永叔少学韩昌黎之文,晚撰《五代史记》,作义儿冯道诸传,贬斥势力,尊崇气节,遂一匡五代之浇漓,反之淳正。故天水一朝之文化,竟为我民族遗留之珍宝。孰谓空文于治道学术无裨益耶?蒋子秉南远来问疾,聊师古人朋友赠言之意,草此奉贻,庶可共相策勉云尔。”[12]这份带有“遗嘱”性质的文字,可以看成陈寅恪对独立自由精神的最后阐发。
综上可知,独立自由精神绝非陈寅恪一时的观点,而是有着高度的价值认同,并以毫不妥协的言行彻始彻终地贯穿于其一生的作人与治学之中。而“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也成为陈寅恪一生最贴切的光辉写照。独立自由精神中蕴含的丰厚思想资源,对于当下的学界,不啻一座振聋发聩的警钟。
[1]陈寅恪.寒柳堂集[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
[2]陈寅恪.柳如是别传(上)[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
[3]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M].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7.
[4]陈寅恪著.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2 编[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
[5]陈寅恪.书信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6]傅杰编校.王国维论学集[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8.
[7]王云五,朱经农主编.礼记[M].商务印书馆,1947.
[8]程千帆.闲堂书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9]朱熹著.四书章句集注·孟子集注·卷十三.北京:中华书局,1935.
注释:
[1]傅杰编校.王国维论学集.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8.p507.
[2]陈寅恪.寒柳堂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p73.
[3]陈寅恪.柳如是别传(上).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p4.
[4]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7.p110.
[5]陈寅恪著.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2 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p280
[6]王云五,朱经农主编.礼记.商务印书馆,1947.p187
[7]陈寅恪著.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2 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p285
[8] 程千帆 .闲堂书简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p330.
[9]朱熹著.四书章句集注·孟子集注·卷十三.北京:中华书局,1935.p181
[10]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7.p110.
[11]陈寅恪.书信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p42.
[12]陈寅恪.寒柳堂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p1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