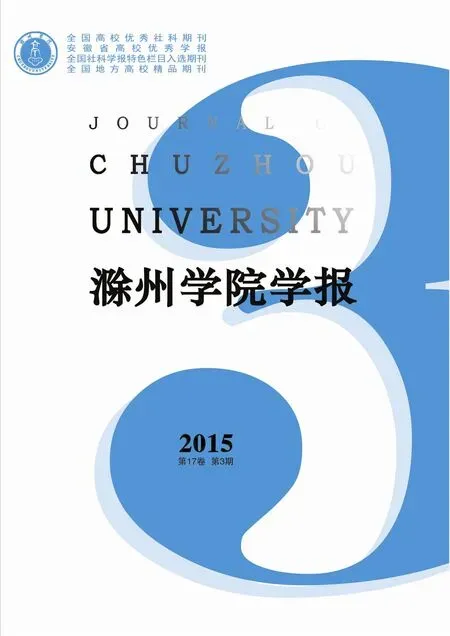朱天心小说中的边缘主妇形象
傅燕婷
90年代台北在消费主义的商业大潮中呈现为一片荒芜的后现代景观。在后现代“人与人之间的共同情操和感情纽带已经变得涣散和衰弱。给人提供共同身份证明和感情交流的基本因素——家庭、教区、教会和团体已经削弱了。”[1]206“上帝死了”,社会的羁绊已经绷断。进入后工业社会,人伫立在“一个他从未创造的世界上,孤独而恐惧”[1]200,“社会世界只能具有在‘恐惧和颤栗’中生活的特点”。[1]205
现代都市过分注重物质的追求而忽视了情感的交流使人的精神无处可栖,产生无所归依的疏离感和无法摆脱的荒诞感、空虚感。穆时英在《公墓·自序》中如此描写现代都市人们的生活状态:“每一个人,除非他是毫无感觉的人,在心的深底里都蕴藏着一种寂寞感,一种没法排除的寂寞感。每一个人,都是部分的,或者全部的都不能被人家了解的,而且精神也隔绝了的。每一个人都能感觉到这些。生活的苦味越是尝得多,感觉越是灵敏的人,那种寂寞就越加深深地钻到了骨髓里。”[2]人们在都市中生活犹如一个有机的人与一座无机的蒸汽机竞走。于是以往“精神上的储蓄猛地崩坠下来,失去了一切概念,一切信仰;一切标准,规律,价值模糊起来”[3]“人是精神地互相隔离了的,寂寞地生活着的”[4]这样就是都市女性所蕴含的生命实感。
在社会转型和变化期,女性可以更明显地反映出社会变化的内涵。朱天心常常借由女性命运的变化,来表现后现代都市环境中受人情稀薄和空间挤压出现个人精神世界幽闭症的都市人类。香港作家西西将一向被贱视的家务重塑金身,寄寓家务无小事,在《飞毡》中将普通家庭主妇命名为“家务卿”。西西试图给一向以黄脸婆印象的家庭妇女以去污,自我赋权命名。朱天心的《鹤妻》《袋鼠族物语》以动物寓言的方式,关注那些平日常出没于超级市场的普通家庭主妇们。鹤妻、袋鼠族在荒原般的都市丛林中,如母兽一般靠着穷凶极恶的购物方式努力经营着自己的巢穴。
一、绝世寻路的袋鼠妈妈
《袋鼠族物语》讲述的是受过高等教育,拥有年幼孩子(2岁左右)的年轻妈妈们(27岁左右),经济上仰赖丈夫,没有工作、社交、自我,在多姿多彩的社会中与幼子相依为命,过着遗世独立的苍凉生活。她们失去了社会性该有的群体关系,因被孩子捆绑而失去了互谈心事的朋友,最后甚至走向自杀的悲剧。朱天心将这类年轻妈妈称为袋鼠族女子,母袋鼠象征着母亲如同袋鼠一样,将小孩细心地呵护于哺育袋中,深怕其受到伤害。她们是一群患得患失、失去生活和自我的中产阶级全职母亲。朱天心以动物寓言的方式描述了一群都市女性在做了母亲后如何在现代商品社会重压下灭亡的过程。西蒙·波伏娃在论述现代社会女性处境时说“中产阶级的上层妇女和贵族妇女,毫不犹豫的准备彻底牺牲掉她们作为一个人的独立性,她们压抑一切思想,一切批判性判断,一切本能冲动;她们对公认的见解随声附和,人云亦云,她们把理想与男性法典强加给她们的货色混为一谈。”[5]父系社会对女人的防范和控制,是传统男权的女性价值尺度在文学中的折射,另一方面,它又作为一种文化现象长存于人类历史之中,逐渐成为人类常规文化心理。袋鼠妈妈们已经将带小孩、做家务作为一种常态的行为规范铭刻在心中,时时以丈夫和孩子为中心,逐渐失去了生活、朋友乃至自己。于是她“没有生活”,“没有朋友”,于是她“想死”,最后她走上了不归路。
母袋鼠们因为没有工作朋友生活就自杀,看起来有些突兀,自杀应该有更大的理由,只要作为母亲都会为了孩子而十分坚强,除非无路可走,出现如丈夫外遇、经济困难等。朱天心这样写,有其自身的原因,她曾经在接受采访时提到三年的专职育婴生活,让她语文能力退化,在家带孩子兼写作,被认为“闺秀作家”不食人间烟火。因此让远离社会没有生活朋友的袋鼠妈妈们自杀,可以看做是朱天心自己成为袋鼠族的强烈感受,认为没有自我,简直与死无异。
为了完善女袋鼠从没有生活到没有朋友,最后走向自杀的过程,朱天心采用了一种特殊的叙事策略——拼贴。戏仿、拼贴和黑色幽默是后现代主义文学创作的三种方法。拼贴的特征在于从整体上审视它是全新的,但组成它的每个部分却是原有的,作者的工作便是将这些原有的不同部分尽量巧妙地整合在一个段落、篇章或整个文本当中,使其呈现出与原有面貌大不相同的气质。《袋鼠族物语》引用李延年的《佳人曲》进行拆解拼贴,《佳人曲》中诗句以括弧形式并列在袋鼠族故事各段标题后,形成意义上的互文对应。以下是《袋鼠族物语》故事段落标题与《佳人曲》拼贴对照表:

表1
《佳人曲》由西汉李延年所作,意在向汉武帝推荐自己的妹妹李夫人,汉武帝听得如痴如醉遂招李氏进宫成为其妃嫔之一,然好景不长,李氏在产后失调后,萎顿病榻,汉武帝前去探望,李氏却锦被蒙头,李氏姐妹埋怨,李氏道“凡是以容貌取悦于人,色衰则爱弛;倘以憔悴的容貌与皇上见面,以前那些美好的印象,都会一扫而光,还能期望他念念不忘地照顾我的儿子和兄弟吗?”。在汉武帝与李氏的关系中,更多的是一种男权与女貌之间的交易关系。在古代男权社会,女性被当做一种物品,处于被看,被凝视,像物品一样被获取的地位,只有成为“佳人”,拥有美色才有生活的保障。女性在李延年的男性叙述中是没有主体性的。千年之后的现代女子依然受着男权文化的宰制,受家庭所束缚,没有生活,没有自我。无论是被观看而得宠幸或被遗忘而疏离人群,女性丧失主体性的形象,在相隔千年的时空仍然遥相呼应。法国女性主义者埃美娜·西苏曾说“所有父权制——包括语言、资本主义、一神论——只表达了一个性别,只是男性利比多机制的投射。女人在父权制中是缺席与缄默的,女人不是被动与否定便是不存在”。
二、艰难猎狩的洞窟女性
《鹤妻》同样以家庭主妇为主题,从商品购买的角度揭示家庭主妇在家庭中边缘地位,深刻表现了家庭主妇的寂寞感受。《鹤妻》篇名借用日本民间故事,故事内容类似中国民间传说中的海螺姑娘,穷青年救了一只受伤的白鹤,鹤化为女子与其一起生活,鹤用嘴拔羽毛织布来维系家中的生活的故事。朱天心用这个篇名是来讲述“洞窟经验,在先民时代,男人负责狩猎,女人在洞窟中将狩猎所获储存起来”。[6]《鹤妻》中的小薰大量囤积家庭生活用品,借购买的举动来与社会互动,同时也抚平内心的焦虑和恐慌。小说透过一个丧妻一个月丈夫的视角,从家中堆叠的商品,让我们看到一个深陷物质文明,却被孤独重压的家庭主妇。厨房柜子里堆满了各式各样的泡面、罐头,卧室抽屉里一大堆卫生纸、内衣、新鞋。小孩三岁半已经买好了他青春期的衣服。在这个物质文明丰饶的现代都市文明里,内心的荒芜却只能依靠物质来弥补罅隙。妻子如母兽般穷凶极恶经营巢穴的寂寞形象映在丈夫的脑海中,是无尽的怅然与震惊。鹤妻小薰处于台湾经济迅速转型期,物价迅速上涨,因此害怕物价上涨恐慌而囤积了大量生活用品。从小说的叙述可以了解到台湾男袜发展史,近五年家电史、女性内衣史、毛巾史、洗衣粉史、这使得全文也明显带有后现代消费文化中,人们内心虚无,通过购物来填补内心罅隙的色彩。
走进家庭之后的女性,大多会面临母亲职责的挑战,传统的母亲欣然接受母职。但由于社会变迁现代化思维早已深入人心,母亲角色便在一连串的潜移默化中,进行着微妙的变化。朱天心小说中的母亲形象并没有跟随女性主义的立场,对母亲职责提出强烈反对意见,只是写出了女性面对传统文化对母亲职责信念的无奈。朱天心曾在张大春的《谈笑书声》节目中说,她母亲看了《鹤妻》后看到哭。足可见,看似简单的购物做饭母职经验,对母亲们来说是相当不易。传统的男性赚钱养家,女性操劳持家观念,使得男性较少地承担了“母职”。于是在妻子死后一个月,丈夫开始对家里进行探险,才发现妻子艰难持家的一面。于是万分感慨对家的隔世之感。夫妻间看似亲密无比,却形同路人,缺乏精神的交流。两人传达意见所用的字数至多不会超过三、五字,“中饭吃什么”“客饭”。
在经过对家里的一番探险后,丈夫终于明白了妻子在物质文明和消费社会挤压下,自己又疏于与其沟通交流后,内心的挣扎和焦虑。自责自己让妻子放野牛似地自谋生存,还满心以为自己是一个一手擎天遮风避雨的雄性。最后丈夫拉开家中的落地门,看到核战后的荒原,“她站在一个失了四面墙壁的百货公司大楼里四顾张皇着,不时仰天发出哀鸣声,我完全猜测不出她的心情与状况,只确定自己于她是全无助益的”。“因此疲倦地掉下了绝望的眼泪”。妻子已俨然成了日本民间传说中的不断拔自己羽毛的鹤妻。
《袋鼠族物语》中的袋鼠妈妈以丈夫和孩子为中心,在疏离了家人、朋友、社会后,绝望地走向自杀。《鹤妻》中的小薰以商品购买的方式来与社会沟通,在自己的巢穴中自舔伤口、独自布置着令自己欢愉的情景。这些在生活中啃噬寂寞、咀嚼苦闷的家庭主妇形象,透过朱天心的叙写让读者察觉到在现代都市中,原来有这么一群女性心灵已枯竭,却仍在生活中苟延残喘。
[1] (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M].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1989.
[2] 穆时英.公墓[C].穆时英小说全集.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718.
[3] 穆时英.白金女体塑像[C].穆时英小说全集.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98:720.
[4] 穆时英.PIERROT[C].穆时英小说全集.长春:时代文艺出版,1998:518.
[5] (法)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M].陶铁柱译.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706.
[6] 陈培文.朱天心的生命风景与时代课题[D].台南:国立成功大学,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