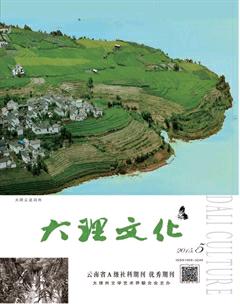喜洲忆旧
晓雪
1935年元旦(农历甲戌年冬月二十六日),我生在云南大理洱海边一个所有人家全部姓杨的白族村庄——喜洲镇城北村。
喜洲,是云南最古老的历史文化名镇。据考古发现,新石器时代,即有先民在这里定居,从事渔业、狩猎、采集等生产劳动。早在公元前109年(西汉元封二年),汉武帝就在这里设置了叶榆县。隋代史万岁南征曾驻兵于此,故称史城。南诏时叫大厘城。唐大历十四年(公元779年),南诏第八代王异牟寻建都喜洲。公元937年,喜洲人段思平建立了大理国。所以唐宋时期,喜洲便成为南诏、大理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之一。喜洲背靠苍山,面对洱海,风景优美,气候宜人,物华天宝,人杰地灵。隋唐以来在历史上有功名的喜洲人数以千计。喜洲人既重视读书,又善于经商;既努力学习汉族博大精深的文化典籍,又保持白族白己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既坚持继承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古老的优秀传统,又以开明、开放的眼光和胸怀积极学习外来的新知识、新事物、新文化,敢于开风气之先。20世纪初,曾任孙中山秘书、参与起草《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宪法》、《天坛宪法》(草案)的喜洲籍著名法学家张耀曾就在日本创办《云南》杂志,宣传科学民主、现代文明。1936年,一批喜洲知识分子又在上海创办了16开本的《新喜洲》杂志,主张改良社会,提倡科学文明,呼吁要建设新喜洲。不久,喜洲就建起了云南农村的第一座水电站,创办了私立五台中学、淑川女子中学、喜洲师范学校、苍逸图书馆、喜洲医院以及酒精厂、碾米厂等等。明代因得罪皇帝被充军到云南的四川才子杨升庵,看透封建社会政治腐败、不愿做官削发为僧的书画家担当等都在喜洲受到热烈欢迎和盛情款待。徐悲鸿到大理,喜洲有识之士把他请到喜洲来举办个人画展,让这位大艺术家在四十年代初就在洱海边的喜洲古镇留下了深远的影响。抗日战争初期,武汉的华中大学(现在的华中师范大学)来到昆明,正愁找不到落脚之处,喜洲开明人士,立即赴昆,将华中大学全校迁至喜洲。从1939年3月至1946年夏天,华中大学在喜洲镇整整七年,对促进喜洲的文化教育和经济发展,改变喜洲的社会风气,提高喜洲人的文化素质,都起了很大的作用。当时在华大任教的著名学者教授罗常培、韦卓民、游国恩、包鹭宾、傅懋绩等人在喜洲写出了一系列的《西南边疆问题研究报告》,在美国哈佛燕京学社出版后,使喜洲和云南名扬海内外。后来旅居美国的著名人类学家许娘光和他的妻子维拉,在华大任教期间,潜心致力于喜洲社会的调查研究,并在喜洲完成了他的成名作《在祖先的庇萌下》。这部著作1948年、1971年在美国用英文一版再版,引起世界学术界高度重视,认为它“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基本的社会体制作了非常有价值的分析”,“对于人们更深地了解中国的家庭生活做出了新的重大贡献。”
正是由于当年华中大学教授游国恩先生的邀请,我国现当代文学大师老舍才在1941年8月末来到喜洲讲学,并在他的散文中描绘了喜洲给他留下的美好印象。老舍先生这样写道:“喜洲镇却是个奇迹。我想不起,在国内什么偏僻的地方,见过这么体面的市镇。进到镇里,仿佛是到了英国的剑桥,街旁到处流着活水,一出门便可以洗菜洗衣,而污浊立即随流而逝。街道很整齐,商店很多。有图书馆,馆前立大理石的牌坊,字是贴金的。有警察局,有像王宫式的深宅大院,都是雕梁画栋。有许多祠堂,也都金碧辉煌。”
我出生时,父亲在外地做小生意。因为是长子、长孙,祖父高兴得把外祖父请来喝酒。两位亲家在频频碰杯时反复商量给我取名字。杨氏门中我们这一辈的名字统一规定有一个“文”字,如我的堂兄堂姐们的名字是文模、文纬、文斗、文浩、文莲、文章等等。所以祖父和外祖父最后为我选了一个“翰”字,叫“文翰”。大概两位老人也希望我长大后舞文弄墨搞文学吧!
我不到三岁,祖父就去世了。只记得他有一个红鼻子,可能是因为喜欢喝酒的缘故,我叫他“汉借爷”(白族话,意思是好看的爷爷),以区别于外祖父“爷爷”。家里穷,只租亲戚家的房子住,父亲帮外祖父家在外地做小生意,所以我从小寄居在喜洲镇彩云街外祖父家。
我的母亲赵碧玉(1913-1944)不识字,却聪慧过人,她心算比别人打算盘还迅速而准确。以心灵手巧、描花刺绣和烹调技术超群出众而远近闻名。我伯父、三叔常年在外地,最小的四叔杨朝栋和与他同岁的伯父的大女儿杨文莲留在家里,还有我的祖父祖母,都需要她伺候照顾。外祖父母家,两个舅舅在昆明读书,大姨妈、大姨爹早逝,表姐董芳兰、表兄董志汉同我一起寄养在外祖家,也要她照看。她从城北村到彩云街,每天婆家娘家两头跑,龙街狗街还要去摆地摊,所以在我九岁那一年(1944年7月4日),就因劳累过度、产后得病又吃错了药,而早早离开了人间。
外祖母尹银和(1891-1979)是喜洲尹家的大家闺秀,虽不识字,却有很好的记忆力,既熟悉《二十四孝》、《赵五娘寻夫》、《梁山伯与祝英台》、《陈世美不认前妻》、《穆桂英挂帅》之类传统戏剧和白族大本曲中演唱的各种故事,也会讲各种各样的民间神话传说。她为人厚道,心地善良,助人为乐,特别疼爱寄养在她膝下的外孙、外孙女。我从记事的时候起,就同她睡一张床,直到考上五台中学去住校为止。《蝴蝶泉》、《望夫云》、《飞虎山》、《段赤城》、《杜朝选》、《美人石》、《播歌女》、《大黑天神》等等后来我写成叙事诗的是她一遍又一遍地给我讲过的。儿时我常常在外祖母讲述的传说故事中进入美妙的梦境。外祖父赵廉相(1886-1947)则是一位有传统文化修养,能写会画,又见过大世面的人。19岁就因为在岳父家的大商号做事,香港、上海、武汉、四川、湖南等许多地方都曾留下他的足迹。但我出生前,他已因他服务的商号倒闭而回到家乡,叫外祖母拿出些金银首饰变卖后买了几亩田地,在白家的花园里栽花种竹,过着陶渊明式的生活。在白家新建的房屋的粉墙上有他亲笔画的兰草、松树、竹子、梅花,还“偶题”了这样的文字:“公退之暇,披鹤氅衣,带华阳巾,手执周易一卷,焚香默坐,消遣世虑,江山之外,第见风帆鸥鹭烟云竹树而已。…‘待其酒力醒,茶烟歇,送夕阳,迎素月,亦滴居之胜概也。”在二门外的墙壁上,他书写了王维的《酬张少府》:“晚年惟好静,万事不关心。白顾无长策,空知返归林。松风吹解带,山月照弹琴。君尚穷通理,渔歌入浦深。”以表达他晚年回乡闲居的心情。
外祖父每天早上都要到东房后面的小花园里侍弄他的那些小盆景:兰花、菊花、缅桂花、丁香花、玫瑰花、茶花。太阳照到花园里,他就靠在躺椅上用白族腔调朗读一本本的线装书:《诗经》、《离骚》、唐诗、宋词。下午,他就在北房他的小楼上写字、画画。我上小学时,就跟他学写小楷、大楷,临摹颜真卿、钱南园的字帖,临摹《介子图画谱》。外祖父曾把着我的手,教我怎么握笔。他说:一定要写好字,要从小练起。而练字、写书法,最好就是先练习颜字体。所以我除完成学校规定的大小楷作业外,还在放学回来和星期天、寒暑假坚持练习写爽舒畅的晚风,看着晚霞辉映下的田畴,外祖父总爱边走边用白族腔调哼着陶渊明、王维等人的诗,哼着“渡头馀落日,墟里上孤烟……”,哼着“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白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哼着“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他勉励我们要从小珍惜时间,努力学习,长大后做一个有作为、有益于国家社会的人,就给我们朗读和讲解汉乐府《长歌行》:“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讲解陶渊明的“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这些诗句我八、九岁时就会背诵,至今没有忘记。
到喜洲南门外大慈寺一带散步,每天都要经过坡头村的“让解桥”。外祖父给我们讲明代两位喜洲籍进士在这座小桥上“让解”的故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明朝的科举制度规定,每三年在各省的省城举行一起考试,叫乡试,乡试考中的为“举人”,举人的第一名叫“解元”。每次乡试录取的解元只有一名,当时云南贵州两省统一在昆明举行乡试,两省只取一名解元。考上后才同其他举人一起,由地方政府送到京城去参加下年春天的“会试”。明弘治戌午年(公元1498年),喜洲两位品学兼优的学子,一个是中和邑的杨宗尧(1476-1551),一个是大界巷的杨士云(1477-1544年),两人都准备到昆明参加云贵乡试并夺魁。一天早上,两人在喜洲南寨门外坡头村旁的小桥上不期而遇,谈起都将去昆明参加云贵乡试,并力争考上第一名“解元”。两人是好朋友,常在一起互相切磋,彼此知根知底,学识修养不相上下。如果两人这一年同时去应考,只能有一人考上解元,另一人必然降为一般的举人。两人在桥上谦让起来,最后杨士云坚持让比他长一岁的杨宗尧先去考。他这一年放弃了,没有去。杨宗尧果然考上云贵乡试该科第一名,中了“解元”。第二年进京参加“会试”、“殿试”,中了进士。他把皇帝钦赐的宫花转赠给杨士云。三年后,杨士云参加下一科辛酉年(1501年)云贵乡试,也中了解元,接着又在京城会试、殿试中高中进士,被正德皇帝钦点为翰林院“翰林学士”,成为全国十八学士之一。他又将皇帝钦赐的宫花回赠给杨宗尧。从此,坡头村的这座小石桥就叫“让解桥”,两位学子互相谦让、互相激励、共同为家乡增光,为国家做贡献的崇高风范和传统美德,六百年来在喜洲白族民间广为传颂。
外祖父是1947年秋天去世的。外祖母生了三个女儿之后再生了三个儿子。三个女儿都早已先后去世。我大舅赵柱不到十岁就因去洱海游泳,为抢救一个同学而牺牲。二舅赵橹和三舅赵楷在外地上学和工作。所以他卧病在床的日子,只有我们几个外孙、外孙女守候在身边。他病中回顾他的一生,写了一副对联,临终交给我,要我书写后挂在他的灵堂两侧。他含着眼泪对我说:“阿爷这回怕是起不来了!”我连说:“不会的,不会的……”但也忍不住抽泣起来。两天后,外祖父就去世了。对联是这样写的:
想当年白手成家,踪迹遍蜀港申湘,跋涉山川,历尽艰辛真苦矣:
愿异曰魂归天山,正气同日星河岳,逍遥宇宙,脱离尘世始安然。
两位舅舅奔丧回家时,这副对联已由我书写好挂在灵堂两边的柱子上。这副对联概括了他的一生,也表达了他豁达开朗的精神境界和生死观。
我1940年五岁时入学,到1946年高小毕业考入喜洲五台中学,正是武汉的华中大学迁到喜洲办学的年代。当时喜洲只不过是一个有两三千人的小镇,没有什么大的建筑,华大的校址就由大慈寺、张公祠、奇观堂三处合成。师生员T及家属上千人分散住在另外几个祠堂和一些大户人家的宅院里。记得我们小学对面的玉皇阁、一排新铺面是男生宿舍,染衣巷、市户里几家有钱人新盖的房子是女生宿舍,北栅门外的尹氏宗祠和杨氏宗祠是教职员和家属宿舍,几个洋人教授好像是住在城南的一座古庙里。喜洲小学打破男女界限,实行男女同校就是从华大来了以后开始的。华大男女同学手挽着手,一路说说笑笑,大大方方地在街上行走,我外祖母曾很不满意地说:“像什么话?伤风败俗!”后来也就见怪不怪,不再说什么了。一进喜洲“正义门”,两边墙上“驱逐日寇,还我河山”八个一人多高的大字和大街小巷、乡村祠堂里的抗日标语,如“好男才当兵,好铁才打钉”、“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等等,都是华大师生们写的。华大宣传了抗战思想、现代文明,也促进了喜洲社会经济的繁荣和文化教育的发展。小小的喜洲突然来了这么多讲外省话、外国话的人,绸布店、裁缝店、饭店生意兴隆,蔬菜、水果、鱼肉市场不断扩大,一些新的蔬菜品种,如被喜洲人称为“洋花菜”“洋辣子”的花菜、蕃茄也大量种植上市。邮局、银行、书店、医院、新式的理发店应运而生。华中大学的到来使新创办的喜洲私立五台中学一开始就有一批高水平的教师,教学水平在全省名列前茅。华大三四年级学生都要到五台中学实习,由于当时T作难找,有些华大毕业生也到五台中学当老师。有的甚至只能先教小学。我在小学五、六年级时的班主任和语文算术老师许清波、陈月英夫妇就是华中大学中文系的毕业生。
华中大学校长韦卓民的事迹在喜洲老百姓中广为流传。广东珠海人韦卓民,先后留学英、美、德,是英国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硕士,德国哲学研究所研究生,美国哈佛大学哲学博士,耶鲁大学哲学荣誉博士,是一位学贯中西的著名学者和杰出教育家。他用英文写作的有关中国传统文化的论文,常被西方学者引用;他翻译的西方哲学经典,被认为“是汉译中最忠实可信的”。1924年他回国时36岁,恰逢华中大学建校便被聘为副校长兼文理学院院长,并代理文学系系主任。1929年41岁时被选为校长。学校迁到喜洲后,国民政府曾邀请他去重庆担任教育部长,他不为心动,婉言谢绝,坚持留在喜洲,在条件艰苦,经费困难的情况下一心一意努力办好华中大学。他把多次应邀赴英、美讲学的丰厚报酬,全部捐给学校,白己的生活却极其简朴,同学生吃一样的伙食,穿一件旧西服,两只手拐破了就补上两块皮子,胸前衣服破了,就请裁缝用布条补缀上“华大”两字。记得有一天晚饭后,我和老表陪外祖父散步到大慈寺门口,正好碰见他同几个学生出来,有一个学生是我二舅赵橹的中学同学,认识我外祖父,便向韦校长介绍:“这是彩云街的赵廉相先生,早年去过香港、上海、长沙、武汉……”韦校长立即停下来同我外祖父热情握手,站在大慈寺门口的一棵柏树下,问他“您在云大读书的儿子学什么,每个假期都回来吗?”亲切交谈了好一会。这样一位平易近人、德高望重、为抗日战争和教育事业作出重要贡献的爱国高级知识分子.1950年竞被戴上“帝国主义文化侵略代理人”的帽子,在后来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受尽折磨,到1976年含冤去世。1979年,华中师范大学党委为韦卓民校长平了反,后来又为他在校园里塑了像,召开了“韦卓民国际学术研讨会”。韦校长生前说过:“抗日战争中的中国教育是一部史诗,将为中国人民子子孙孙永志不忘。”在喜洲的华中大学同在昆明的西南联合大学一样,无疑是这部史诗的重要篇章。
华中大学在喜洲整整七年,促进了喜洲的文明新风,师生们同老百姓亲如一家,处得很好。有一次,同学中有几个华大教授的儿子,闲谈中嘲笑喜洲子弟,我同他们争吵起来,并动手打了一架,老师来了才止住。了解情况后,一位华大教授还专门到学校,向我们表示歉意。两位教授(一男一女)搞社会调查,在一个星期天的下午,还到过我们家。外祖父在小花园里接待了他们,向他们详细介绍了喜洲民家族(即白族)的历史文化,风俗习惯、民族传统,同回族、纳西族、藏族等兄弟民族的关系和所受汉族的影响。两位喝着我外祖父亲白烤、泡得香喷喷的茶,同他交谈了整整一个下午。后来知道那两位教授就是许烺光、维拉夫妇。
1944年华大中文系毕业的浙江籍学生许清波、陈月英夫妇,是我在喜洲读高小时的老师,陈月英当过我一学期的班主任,并教算术课,许清波教过我一学期的国文课。他们1944年秋季到任,1945年秋日本投降,华中大学准备迂回武汉,他们也想随母校回武汉。但在准备迁校的一年间(1945年秋至1946年夏),他们仍安心认真地坚守在小学的教学岗位上。他们似乎特别留恋喜洲,舍不得我们这些小孩子。两位还到彩云街我外祖父家访问过,同我外祖父、外祖母交谈。学校组织高小学生游览蝴蝶泉、万花溪,他们也一起去。记得有一次在万花溪边,看着近处满山遍岭的山茶花杜鹃花和远处碧蓝碧蓝、波光闪闪的洱海,听着脚下晶莹清澈、淙淙流淌的溪水,许老师说:“我是浙江人,到过许多风景如画的江南水乡和全国许多好地方,我感到最美、最好、最清爽舒适、最醉心迷人的就是苍山洱海怀抱中的大理坝子,就是你们喜洲,你们生长在这么美好的福地,真是有福气啊!”许老师这番话,使我们这些孩子从小就有了作为喜洲人大理人的白豪感和幸福感。1954年夏天,我作为武汉大学学生参加武汉市人民抗击百年不遇特大洪水的防汛斗争,在奋战了四十几个昼夜之后患了痢疾,住进了武汉市第三医院。病情缓解后,有一天晚饭后出院散步。走出医院不远,见有一个小院子,门口挂着“华中师院教师宿舍”的牌子。我走进去随便看看,想不到凉台上竟站着八年不见的许清波老师!我喊:“许老师!许老师!”他没有反应过来。我走进去同他握手,他还是没有认出来:“你是……”我说:“我是大理喜洲你的学生杨文翰。”他想了一会,才惊喜地说:“想起来了,想起来了,你就是住在彩云街外祖父家的那个学生,那个书法比赛第一名的杨文翰!太好了!太好了!快坐,快坐!”八年不见,他戴副眼镜,文质彬彬的样子没有变,我从十一岁的高小生长成十九岁的大二学生,他当然认不出来了。他立即把他夫人陈月英老师也叫出来,给我倒茶。两位老师对我能来到武汉大学读书感到很高兴。他们谈起当年在喜洲读书、教书的日子,谈起对大理喜洲、对苍山洱海、对白族父老乡亲的美好印象,充满了无限怀念的感情。
我二舅赵橹(1922-2000)是20世纪40年代云南文坛上思想进步、创作活跃、颇有影响的白族青年作家,他在云南大学文史系读书期间(1943-1947年)是费孝通、楚图南、刘文典、徐嘉瑞等学术前辈和著名教授的得意门生,边读书边在几个中学兼课,并参与创办和编辑《海鸥周刊》、《青春》、《诗与散文》等刊物。大学毕业后,他在教书的同时又主编《云南论坛》、《笔丛文艺丛刊》等专刊。他积极投身“一二·一”学生运动,并以土弩、方戈、方卜、晶心等笔名,先后在他主编的刊物及其他报刊上,发表了大量的诗歌、小说、散文、杂文和时事评论,揭露社会黑暗,痛斥贪污腐败,反映人民疾苦,呼唤民主白由。后因特务追捕,便在组织安排下于1949年初夏奔赴川康边境参加了川康游击队,任金江第二支队政治部副主任。1955年反胡风运动和1957年反有派斗争中两次受到错误处理。蒙冤25年后,于1980年调回昆明新成立的云南省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做研究员,又创作了一批小说、散文和诗歌,并先后出版了《论白族神话与密教》、《白文<山花碑>译释》、《论白族龙文化》、《李白诗读》等四部学术著作。
二舅留在家里的许多古今中外的文学书籍成为我寒暑假和课外时间的精神食粮。所以我上高小时就读到了《水浒传》、《三国演义》、萧军的《八月的乡村》、萧红的《生死场》,读到了鲁迅、茅盾、巴金、蒋光赤的小说和艾青《大堰河,我的保姆》、《黎明的通知》、田间的《给战斗者》等诗歌,看到了《新喜洲》、《诗创造》等刊物。但我读高小时,对绘画、书法的兴趣更浓,作文在同学中并不突出,每次得分在80分左右,算中上水平,没有得到过老师的表扬。只有一次例外。
1945年12月1日,昆明发生了国民党反动派镇压学生运动,杀害潘琰、于再、李鲁连、张华昌四烈士的“一二·一”惨案。消息很快传到喜洲。有一天,教我们国文和美术的杨木荣老师,上课时先给我们讲时事,讲最近在昆明发生的“一二·一”运动,讲国民党如何黑暗、腐败,激起了昆明大中学生和广大民众的反抗和游行,讲四位年轻的学生和教师如何被杀害。杨老师激动地说:反动派的镇压反而唤起了更多的民众,反饥饿、反迫害、要白由、要民主的烈火是扑不灭的,反动派越是残酷镇压,民众反抗的烈火越要烧得更旺!烈士的血不会白流!接着,杨老师就转身在黑板上面出了报纸上刊登的四烈士的像,要同学们一个一个照着画。我想象着昆明大中学生哥哥姐姐们“一个人倒下去,千万人站起来”的悲壮场面,想起杨老师给我们讲过的雪莱的诗句:“既然冬天已经来了,春天还会远吗?”便在画完四烈士的速写头像后,在图画本上写了这样几句诗:
杀害了四烈士,
唤起了千万人,
烈士的血不会白流!
工农已经醒悟,
奴隶已经怒吼,
烈士的血不会白流!
任你黑夜漫长,
曙光就在前头,
烈士的血不会白流!
诗的题目就叫《烈士的血不会白流》。这几句诗很简单,也很一般,却白然而朴素地表达出我当时的真情实感。杨老师看后很满意,第一次在我的本子上批了100分,并写道:四烈士的像画得很好,这首诗也是你写得最好的一篇作文。这就是我童年时代意外地受到老师表扬的一篇作文,也是我学写的第一首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