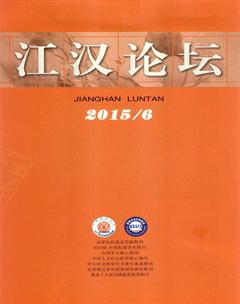《庄子》技术寓言的自由境界及其美学意蕴解析
万勇华
摘要:《庄子》书中包含了大量意趣盎然的技术寓言,这些寓言涉及许多种类和领域的技术活动。其中,有些活动是庄子赞赏的,有些活动则是庄子反对的。庄子赞赏的那些活动的操作主体大都拥有超乎寻常的技艺。他们在各自的技术活动中,达到了高度自由的境界,展现了极其超越的品格。《庄子》的技术寓言虽然没有从正面的角度直接论述美学理论问题,但却包含着丰富的美学意蕴,显示了独特的艺术价值。
关键词:技术寓言;自由境界:美学意蕴
中图分类号:B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5)06-0040-05
一、 《庄子》技术寓言的整体透视
《庄子》一书,既是一部语言优美的文学名著,也是一部思想深刻的哲学经典。在书中,庄子运用天才的文学手法,讲述了一系列生动有趣、富有哲理的技术寓言,其中有些是大家经常提及、耳熟能详的,如庖丁解牛(《养生主》)、轮扁斫轮(《天道》)、匠石斫垩(《徐无鬼》)、大马捶钩(《知北游》)、丈人圃畦(《天地》)、邯郸学步(《秋水》)、宋史真画、伯昏施射(《田子方》)等,还有一些则是人们很少提起、不太熟悉的,如大冶铸金(《大宗师》)、封人为禾(《则阳》)、宋人卖药方(《逍遥游》)、朱坪漫学屠龙(《列御寇》)、纪渻子养斗鸡(《达生》)、季咸相壶子(《应帝王》)、宋元君卜神龟、任公子钓大鱼(《外物》)、伯乐治马、陶者治埴、匠者治木(《马蹄》)等。
归纳起来,上述寓言主要涉及到三类技术活动:第一类是技术交易活动,如宋人卖药方;第二类是技术学习活动,如邯郸学步、朱坪漫学屠龙;第三类是技术操作活动,如庖丁解牛、轮扁斫轮、大马捶钩等。相对而言,第一类活动最少见,只有一则故事讲到;第二类活动也不多见,仅有两则提到:第三类活动最常见,绝大部分寓言都谈到。如果进一步考察第三类技术活动,可以发现它实际上涵盖五大领域的操作:一是日常生活领域,如宰牛、驯马、驾车、撑船、射箭、捕蝉、钓鱼、游泳、斗鸡等;二是手工业领域,如金工铸造铁器(大冶铸金)、轮工制作车轮(轮扁斫轮)、陶工制造陶器(陶者治埴)、木工制作木器(匠者治木)等:三是农业领域,如封人为禾、丈人圃畦分别谈到了农业耕作和灌溉活动;四是艺术领域,如宋史真画、黄帝奏乐分别记述了绘画创作和音乐演奏活动:五是巫术领域,如季咸相壶子、宋元君卜神龟分别讲述了看相和占卜活动。很显然,前两大领域(日常生活层面和手工业层面)囊括的活动形式非常多,而后三大领域(农业层面、艺术层面和巫术层面)包含的活动形式则比较少。
从技术主体看,以上寓言大致关系到三类操作者:第一类是自然界中的动物,如“搏矢”的山中野猴;第二类是虚构的理想人物,如“施射”的伯昏无人:第三类是现实社会中的人,属于此类的操作者特别多。他们当中有的是赫赫有名的帝王,如演奏《咸池》之乐的黄帝;有的是家喻户晓的技工,如驯马的伯乐、画图的工倕;有的具有完整的姓名,如看相的季咸、御车的东野稷、学屠龙的朱坪漫、养斗鸡的纪倕子;有的只有名而无姓,如斫轮的轮扁、斫垩的匠石、为璩的梓庆:有的以地域表示,如卖药方的宋人、钓鱼的臧地丈人:有的以职业指代,如铸金的大冶、治埴的陶者、治木的匠者;有的以外貌指示,如承蜩的痀偻者。尽管上述操作者的具体情况不尽相同,但有一点上却表现出了一致性,那就是他们的技术活动都是由自身独立完成的,而不是与他人合作完成的。
从技术客体看,以上寓言着重谈到了两类操作对象:第一类是有生命之物,如封人耕作的庄稼、木匠加工的树木、庖丁屠宰的牛、伯乐训练的马、痀偻者捕捉的蝉、纪噱子驯养的斗鸡、季咸看相的壶子等。在这当中,庄稼和树木为植物,生命等级比较低;牛、马、鸡、鱼、蝉为动物,生命等级相对高一些;而壶子为得道之人,乃是最高级的生命物;第二类是无生命之物,如丈夫游泳的河水、陶工使用的粘土、匠石削除的白泥、丈人灌溉的园地、宋元君占卜的龟壳等。
从技术中介看,以上寓言不外乎关联着两类操作器物:第一类是具体的物质工具.如庖丁解牛之刀、大冶铸金之锤、匠石斫垩之斧头、轮扁斫轮之椎凿、痀偻承蜩之竹竿、封人耕作之农具。这类工具都是非常简单的手工工具,相对于现代的智能机械要低级得多;第二类是个人的身体器官,如季咸看相主要用眼,邯郸学步侧重用脚,工倕画图仅用灵活的手指,而丈夫游水则要运用身体的诸多部位。就此而言,他们的身体器官就是他们的操作工具。
对于上述寓言中涉及的技术活动,庄子表现出了截然对立的态度:一是坚决反对,如邯郸学步、朱坪漫学屠龙、季咸相壶子、山狙搏矢、东野御车、陶者治埴、匠者治木、伯乐治马等。这些活动要么偏重外在的模仿,丧失自我的真性(邯郸学步);要么花费巨大的代价,缺乏现实的功用(朱坪漫学屠龙);要么卖弄个人的聪明,落得逃跑的下场(季咸相壶子);要么炫耀自己的技巧,招致杀身的灾祸(山狙搏矢);要么超过体力的极限,导致失败的结局(东野御车);要么违背事物的本性,戕害对象的生命(陶者治埴、匠者治木、伯乐治马);要么破坏人性的纯朴,扰乱精神的安定,造成大道的失落。诸如此类的活动一概遭到庄子的批判:二是高度赞赏,如庖丁解牛、轮扁斫轮、匠石斫垩、大马捶钩、梓庆为璩、工倕旋矩、痀偻承蜩、宋史真画、黄帝奏乐、任公子钓大鱼、纪渻子养斗鸡等。这些活动或者展现了自然之道,或者彰显了本然之性,因而获得庄子的肯定。
二、技术活动的自由境界及其原因分析
如果撇开庄子坚决反对的技术活动而专门考察那些受到赞赏的技术活动,可以发现这些活动的操作者大都身怀绝技,如庖丁解牛“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轮扁斫轮“不徐不疾,得之于手而应于心”,津人操舟“视渊若陵,视舟之覆犹其车却也”,匠石“运斤成风,尽垩而鼻不伤”。这些人物在展示绝技的过程中,达到了高度自由的境界,显示了极其超越的品格。
仔细探究上述能人巧者走向技术自由境界的原因,不难看出下面三点格外重要:
一是反复实践,勤奋操练。庖丁在刚开始解牛时,眼里看到的都是一头头完整的牛(“所见无非全牛”);三年之后,眼里就不再看到整体的牛了(“未尝见全牛”);到了现在,已经彻底摒弃感官的作用而直接运用心神与牛接触(“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假如说在前两个阶段中,庖丁还是仅仅依赖感觉器官(“目视”)认识牛的外部躯干,使用粗暴生硬的方式(“折”、“割”)解牛,那么到了目前这个阶段,他则完全凭借理性直觉(“神遇”)洞察牛的内部构架,采用圆融无碍的方式(“无厚人有间”)解牛,所以他现在手里的这把刀才能使用19年,解牛数千头,而刀刃还像刚磨过的一样锋利无比(“若新发于硎”)。正是年复一年的亲身实践造就了庖丁过人的解牛技术。轮扁最初制轮的时候,总是拿捏不好分寸,要么榫眼过宽以至榫头松滑而不牢固(“徐则甘而不固”),要么榫眼过窄以至榫头滞涩而难以安人(“疾则苦而不入”)。后来经过数十年的不懈操作(“行年七十而老斫轮”),终于达到了不徐不疾、得心应手的地步。大马工匠在20岁时就爱好锻造钩子,经过几十载的反复实践,最终练就了超乎常人的技艺——即便80岁时打造出来的钩子依然没有丝毫的误差(“年八十矣,而不失豪芒”)。而驼背老人炉火纯青的捕蝉技术,主要归功于他的刻苦练习:“五六月,累丸二而不坠,则失者锱铢;累三而不坠,则失者十一;累五而不坠,犹掇之也。”文中“锱铢”原本是古人使用的非常小的重量单位,用在此处比喻捕蝉失手次数很少。“掇”即拾取的意思,喻示着捕蝉成功率极高。如果说迭放泥丸由两颗(“累丸二”)到三颗(“累三”)再到五颗(“累五”),从正面表明了练习难度在逐步增加,那么捕蝉失手概率由很小(“失者锱铢”)到更小(“失者十一”)再到极小(“犹掇之也”),则从反面彰显了捕蝉技术在不断提高。及至最后阶段,驼背老人站在那儿,身体就像断树桩一样纹丝不动(“处身也,若厥株拘”),控制手臂就像枯树枝一样协调自如(“执臂也,若槁木之枝”)。这种近似木偶的捕蝉身体动作完全是其苦练的结果。
二是依循大道,默会理数。在《养生主》中,文惠君目睹庖丁的解牛技艺,首先给予了高度的赞赏(“善哉”),进而提出了“技盖至此乎”的问题。对此,庖丁回答说:“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此处的“技”可以纳入人为之“术”的范畴,“道”则表示自然的法则。对庖丁而言,他不再满足于一般的小技(“进乎技”),而是钟情于玄妙的大道(“所好者道”)。他已从平庸的人为之“术”走向神奇的自然之“道”。具体说来,庖丁所追求的“道”就是“依乎天理,批大郤,导大窾,因其固然”。文中的“天理”、“固然”可以理解为事物本身所具有的法则、条理,相应地“依乎天理”、“因其固然”即是要求在行为过程中依循这种条理与法则。假如没有依照、遵循对象的“天理”、“固然”,那么“批大卸”、“导大裒”的解牛活动肯定无法轻松地展开。正因为依从、因循了对象所内含的“天理”、“固然”,庖丁才能在“批大郤”、“导大窾”的解牛过程中达到游刃有余的境地。《达生》篇中,孔子观赏吕梁山水,看到一个男子在十分湍急的水中悠闲地畅游,于是走过去问他:“蹈水有道乎?”吕梁男子尽管起初予以否认(“吾无道”),可是随即做了正面回应:“吾始乎故,长乎性,成乎命。与齐俱人,与汩俱出,从水之道而无私焉。此吾所以蹈之也。”这里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从水之道而无私”。如果说“水之道”表达的是水流变化的趋势、规律的含义,那么“私”则关联着人的意图、目的。在吕梁男子看来,蹈水者唯有消除主观意图而完全顺从水流规律,才能超越与对象二分的状态而达致物我合一的境界,所谓和漩涡一起没人,和涌流一起浮出(“与齐俱入,与汩俱出”)即是形象地说明了这个道理。《天道》篇中,轮扁在反思自己的制轮活动时,讲到“不徐不疾,得之于手而应于心,口不能言,有数存焉于其间”。此处的“数”可以解释为内在之理的意思。这种内在之理既无法告知他人(“臣不能以喻臣之子”),也难以为他人所领受(“臣之子亦不能受之于臣”)。然而,制轮过程中的这种“数”或“理”虽然无以言表(“口不能言”),但却可以用心默会(“应于心”)。而一旦做到这一点,就能够展现出行为节奏的恰到好处(“不徐不疾”)和心手之间的默契配合(“得之于手而应于心”)。
三是凝聚精神,修养心灵。在《达生》篇中,孔子这样评价驼背老人:“用志不分,乃凝于神。其痀偻丈人之谓乎!”正是心意专注、精神凝聚的心理状态,使得驼背老人的捕蝉技术达到令人惊奇的境界。这种心理状态与技术境界间的紧密关联性,用驼背老人自己的话说就是虽然天地广大.万物繁多,但我只关注蝉的翅膀。我不回头不侧身,不因其他繁杂事物而转移我对蝉翼的注意力,哪里还会捉不到蝉呢!在《知北游》中,大马捶钩者解释自己“不失豪芒”的绝技时直言:“于物无视也,非钩无察也。是用之者,假不用者也以长得其用”。所谓“于物无视也,非钩无察也”意指对于钩子以外的其他事物一概视而不见,漠不关心。可见,这位工匠的绝技与其全神贯注、心无旁骛的精神状态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类似的情形也出现在津人身上。他在操舟时,注意力高度集中,即使眼前出现船覆车倒的险情,也无法扰乱他的内心(“覆却万方陈乎前而不得人其舍”)。正因为如此,他才能始终从容自若地驾船(“恶往而不暇”)。作为《田子方》中虚构出来的理想人物,伯昏无人经过长期的心灵修养,达到了生死得失无动于衷的人生境界,因此即便他登上高山,踏上危石,背临万丈深渊,脚掌后部垂在悬崖之外(“登高山,履危石,临深渊,背逡巡,足二分垂在外”),依然能够神闲气定地展示“不射之射”。而之前炫耀射技高超的列御寇此刻吓得趴在地上,冷汗一直流到脚跟(“汗留至踵”)。究其缘由是因为他的心灵缺乏修养,精神受到束缚。通过两者对比,说明心灵修养对于射箭技术的重大影响。
概括起来,以上三点构成了能人巧者达到自由境界的必备条件。在这当中,第一点尤为重要。没有它,个体不可能拥有高超的技艺,也就谈不上由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没有它,个体无法准确地把握事物的内在规律,更不会遵循事物的内在规律行事;没有它,个体无法排除外在功名的干扰和内在情欲的纠缠,难以保持虚静专注的精神状态。除此之外,后两点也很重要。如果个体违背事物的客观规律,盲目地进行技术操作,那就很难达到很高的技术水平;类似地,如果个体片面追求世俗的功名利禄,浮躁地开展技术活动,那也很难取得良好的技术效果。至此,不妨说,第一点乃是个体走向自由境界的根本途径,而后两点则是个体走向自由境界的基本前提和关键方法。三者相互依存,密不可分。需要指出的是以上三点并非明确呈现在所有技术寓言中。有的可能只是涉及其中的一点,如“津人操舟”主要强调全神贯注的道理:有的也许只是谈及其中的两点,如“轮扁斫轮”着重说明长期操作和把握规律的思想:有的甚至没有论及以上任何一点,如“匠石斫垩”、“丈人钓鱼”仅用简洁的语言描述了主体精湛的技艺表现。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没有提到的要点无足轻重、缺乏关联。恰当的理解应当是每个故事侧重阐述的方面不尽相同而已。其实,稍作分析即可发现,那些没被提及的要点往往隐约而微地包含在寓言中。以“匠石斫垩”为例,匠石“运斤成风,尽垩而鼻不伤”的神技绝对不是与生俱来、轻易获得的,肯定是通过长期刻苦的操作、掌握斧头运用的规律、排除所有世俗的干扰逐步练就出来的。只不过,这些方面在文中都被省略掉了。
三、技术寓言的美学意蕴
《庄子》的技术寓言虽然没有从正面直接论述美学理论问题,但却散发着醇厚的审美气息,显示了独特的艺术价值。
仔细分析庄子讲述的表达自由思想的那些技术寓言,可以发现“庖丁解牛”蕴涵的美学意味最为浓烈,最具代表性。本来庖丁从事的解牛工作是一项繁重复杂、充满血腥味道的技术活动,但是通过他的精彩演绎,却升华成了富有审美特质的艺术活动。具体说来,这种艺术性主要表现在两个阶段:一是解牛活动进行中,“手之所触,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砉然响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庖丁在解牛过程中运用了身体的诸多部位,每一部位既有相应的动作要求,相互之间又能配合得十分默契,因而产生了类似舞蹈的效果。伴随他的动作发出的声音,不仅表现出有序的节奏,而且显示了良好的韵律,由此形成类似乐曲的效果。上述两种效果通过庖丁“游刃有余”的技术操作,实现了和谐统一,最终达到了类似经典乐舞的大美境界。二是解牛活动结束后,庖丁“提刀而立,为之四顾,为之踌躇满志”。“踌躇”形容飘飘然陶醉状,“满志”表明志得意满的样子。面对解开的牛体,庖丁的内心荡漾着满足、得意之情,精神上也获得了自由愉悦的审美感受。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庖丁在解牛过程中自觉地按照“美的规律”进行操作——他在准确把握劳动对象内在法则的基础上,充分施展非凡的劳动技艺,从而使得自己本身力量对象化的同时,也从劳动对象中直观看到了自身的实践本领,进而肯定了自我的创造才能。
如果说“庖丁解牛”主要是从手工劳动的角度体现出了丰富的美学内涵,那么“宋史真画”则是着重从艺术实践的角度揭示出了不同心理状态对于审美创作的重要影响。《田子方》云:“宋元君将画图,众史皆至,受揖而立;舐笔和墨,在外者半。有一史后至者,值值然不趋,受揖不立,因之舍。公使人视之,则解衣般礴赢。君日:‘可矣,是真画者也。”文中“众史”一听君主召唤,便争先恐后,早早赶来;他们在君主面前“受揖而立”,毕恭毕敬,显示出奴性十足的情态;他们“舐笔和墨”,装模作样,急不可待地表现自己。“众史”这样做的目的纯粹是为了巴结权贵,谋取名利。怀着此种世俗的心理作画,肯定难以绘出真正的佳作来。与之不同,“一史”最后到来,他既没有在走向国君时加快步伐(“值值然不趋”),也没有在接受揖礼后马上就位(“受揖不立”),而是随即回到住所,解开衣服,赤身露体地盘腿而坐(“解衣般礴赢”)。表面看来,这种行为有悖世俗礼法,显得放荡不羁,然就实质而言,恰恰透露出了“一史”的率真自然、随性自由。正因为“一史”摆脱了世俗礼法的束缚,摒弃了功名利禄的追求,所以精神上处于虚静专注的状态,这就为他开展艺术创作提供了良好的心理前提。因此,尽管“一史”未画一笔,未描一色,但是有了上述心理状态,接下来进行绘画创作,自然就会思维活跃、灵感飞扬,想象力和创造力得到充分的发挥,从而能够顺理成章地创造出优秀的作品来。宋元君最后肯定他为“真画者”,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作出的评判。
相形于“宋史真画”的轻描淡写、简洁明了,“黄帝奏乐”这则寓言对于艺术实践过程的描绘可谓浓墨重彩、惟妙惟肖。《天运》篇云:“北门成问于黄帝日:‘帝张咸池之乐于洞庭之野,吾始闻之惧,复闻之怠,卒闻之惑;荡荡默默,乃不自得。帝日:‘汝殆其然哉!吾奏之以人,征之以天,行之以礼义,建之以大清。四时迭起,万物循生;一盛一衰,文武伦经:一清一浊,阴阳调和,流光其声;蛰虫始作,吾惊之以雷霆;其卒无尾,其始无首;一死一生,一偾一起;所常无穷,而一不可待。汝故惧也。吾又奏之以阴阳之和,烛之以日月之明:其声能短能长,能柔能刚;变化齐一,不主故常:在谷满谷,在阬满阬;涂郤守神,以物为量。其声挥绰,其名高明。是故鬼神守其幽,日月星辰行其纪。吾止之于有穷,流之于无止。予欲虑之而不能知也,望之而不能见也,逐之而不能及也;傥然立于四虚之道,倚于槁梧而吟。目知穷乎所欲见,力屈乎所欲逐,吾既不及已夫!形充空虚,乃至委蛇。汝委蛇,故怠。吾又奏之以无怠之声,调之以自然之命,故若混逐丛生,林乐而无形:布挥而不曳,幽昏而无声;动于无方,居于窈冥;或谓之死,或谓之生;或谓之实,或谓之荣;行流散徙,不主常声。世疑之,稽于圣人。圣也者,达于情而遂于命者也。天机不张而五官皆备,此之谓天乐,无言而心说。故有焱氏为之颂日:‘听之不闻其声,视之不见其形,充满天地,苞裹六极。汝欲听之而无接焉,而故惑也。乐也者,始于惧,惧故祟;吾又次之以怠,怠故遁;卒之于惑,惑故愚;愚故道,道可载而与之俱也。
文中黄帝运用匪夷所思的演奏技术,将一首古代著名的《咸池》乐曲演绎成了美妙绝伦的“天乐”,使得北门成竟然产生了三种奇异的审美心理,而这心理恰好合乎黄帝的期许。面对北门成的茫然不解,黄帝娓娓道出了其中的缘由。首先,在乐曲展开时,黄帝“奏之以人,征之以天,行之以礼义,建之以大清”,既表现了人事的主题和礼义的内涵,又抒发了大道和天理,还反映了天地万物阴阳四时的运行情况(“四时迭起,万物循生;一盛一衰,文武伦经;一清一浊,阴阳调和,流光其声”)。这样的音乐不仅内容丰富多彩,而且形式变幻莫测。它结束时不见尾声,开始时不见源头;忽而休止,忽而起奏,忽而降低,忽而升高(“其卒无尾,其始无首:一死一生,一偾一起”)。正因为这一切变化无穷,难以预料,所以听者才会产生惊惧不安的心理(“惧”)。接下来,黄帝“又奏之以阴阳之和,烛之以日月之明”,纯粹表现阴阳二气的和谐和日月光辉的普照。这样的乐曲不仅“变化齐一,不主故常”,而且声音“能短能长,能柔能刚”;悠扬嘹亮,高亢明朗(“其声挥绰,其名高明”),从而显示出了巨大的能量和作用——既可以“在谷满谷,在院满阬”,又能够“涂邰守神,以物为量”,甚至还能让“鬼神守其幽,日月星辰行其纪”。面对这样的音乐,无论人们怎样用尽感官、理智和精力都无法把握它的真谛(“目知穷乎所欲见,力屈乎所欲逐”),因此只好放弃追求,顺应万物变化(“委蛇”),于是心情逐渐松弛下来(“怠”)。最后,黄帝“又奏之以无怠之声,调之以自然之命”,完全展现无怠的乐声和自然的节奏。此时的乐曲一方面体现出了似有若无的特点(“若混逐丛生,林乐而无形:布挥而不曳,幽昏而无声”),另一方面又展现了非同寻常的品格(“动于无方,居于窈冥:行流散徙,不主常声”)。这样的音乐虽然听不到它的声音,看不见它的形迹,但却充盈着天地之间,囊括了上下四方,让人满心喜悦。当听者试图洞察其中的奥秘时,却又无法深刻地领会,所以感觉迷惑了(“惑”)。以上庄子描述的由惧而怠而惑的心理过程无形中揭示了一个深刻的美学原理:人的审美心理与音乐的形式结构、人的审美境界与音乐的内容表现是紧密联系的,两者之间达成了一种“异质同构”的效果。可以说,有什么样的形式结构和内容表现就会产生相应的审美心理和审美境界,而不同的形式结构和内容表现通常会形成相异的审美心理和审美境界。最后,必须点明的是庄子所谓的“天乐”实际上隐喻着不可言说的大道,因此闻“天乐”的心理过程本质上亦是体道的心理过程。庄子讲述北门成闻“天乐”的用意不是告诉人们如何欣赏美妙的乐曲,其真正目的在于引导人们通过层层推进的音乐审美体验获得对于形上之道的审美体悟,最终达到与道合一(“道可载而与之俱也”)的审美超越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