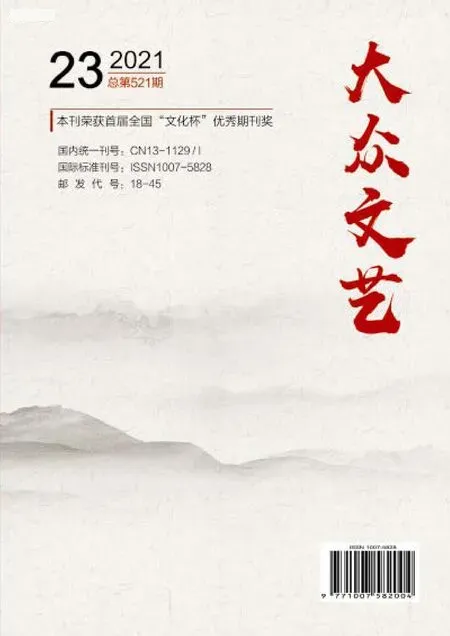湖北地区远古舞蹈初探
周 仪 (武汉音乐学院舞蹈系 430000)
在历史上最为遥远的远古时期,舞蹈艺术伴随着人类的进化和社会的发展,历经了一段漫长的孕育与萌芽。目前虽没有直接的考古及文献依据能够证明这一时期湖北地区舞蹈艺术的确切存在及样貌,但从艺术发展的一般规律及影响舞蹈艺术发生发展的环境因素中,依然能够探寻到舞蹈艺术孕育与萌芽的可能。
一、旧石器时代湖北地区舞蹈艺术的孕育
1.孕育的母体——“人”
舞蹈属人体动作行为。虽说不是有了人就有了舞蹈,但是舞蹈艺术的产生一定是以人的出现及其生命活力的存在为前提的。
从目前已出土的考古资料来看,至迟从旧石器时代早期起,湖北境内就已经有了人类的生存和繁衍。比如“郧县猿人”头骨化石、“郧县猿人”牙齿化石、“郧西猿人”牙齿化石、大冶石龙头文化遗址、“长阳人”化石、宜都九道沟石器文化遗址、丹江口石鼓后山遗址、江陵鸡公山遗址、房县樟脑洞遗址等,分别是旧石器时代早期、中期、晚期湖北地区人类留下的历史生活足迹。1
虽然现有的考古及文献依据尚不能证明在这些历史生活足迹中已经包含有舞蹈艺术活动,但是从舞蹈艺术的本质特征及发展规律来看,“人”的出现至少为舞蹈艺术的孕育提供了必备的条件——物质载体,即所谓的“母体”。
2.孕育的条件——人类的进化和社会的发展
如前所述,舞蹈艺术的产生以人的存在为前提,但不是有了人就有了舞蹈。舞蹈艺术的产生是人类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而文化的发展会反映在人类自身的进化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之中。
从考古资料来看,旧石器时代湖北地区考古遗迹的发掘主要是人类化石、石器和动物化石。其中人类化石和石器的出土反映出这一时期湖北地区人类自身的进化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比如“郧县人”的生存年代为距今80万年至100万年前,属旧石器时代早期。这一时期出土的石器主要有石核、石片、砍砸器、刮削器、尖状器等,石器制作方法以打制为主,较为粗糙。到“长阳人”生存的旧石器时代中期,出土石器出现了明显的修理台面技术,砍砸器和刮削器数量更多,且在石器的边或刃上有单、双、三之分,充分反映出石器制作工艺的时代进步。此后到了旧石器时代晚期,出土的石器从数量的增多、到材料的优化选择、再到种类的丰富和制作工艺的精美,进一步体现出这一时期人类自身的进化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2
不仅如此,考古工作者们在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址——“江陵鸡公山遗址”中还发现了当时人类居住的圆形窝棚基础的遗迹——五个由砾石围成的圆形石圈和脚窝痕迹,并在其南部发现有两个石核和石片分布的富集区,且伴有较多的石锤、石钻,经考证很可能是石器加工场所。可见,旧石器时代晚期湖北地区人类的居住环境和生活方式已发生很大变化,其生产能力、社会生产状况和生活关系的进化与发展均在一定程度上为舞蹈艺术的孕育提供了条件。
二、新石器时代湖北地区舞蹈艺术的萌芽
经历了旧石器时代漫长的历史孕育,湖北地区的舞蹈艺术在新石器时代繁荣的氏族社会生活中获得了诸多有益于自身发展的因素,最终以“击节歌舞”的综合形态及原始宗教的文化意味萌发在社会生活、特别是宗教生活中。
1.萌芽的基础——繁荣的氏族社会生活
氏族社会是人类社会早期的一种社会关系形态,主要特征表现为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稳定的聚落生活组织,以集体意识为导向的共同劳动、共同消费模式,以族群繁衍为目的的族外通婚及原始宗教习俗等。大量的考古资料表明,至迟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开始,湖北地区的人类就已经进入到氏族社会生活阶段。发展到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其氏族社会生活已经非常繁荣。总体来看,繁荣的氏族社会生活为这一时期湖北地区舞蹈艺术的萌芽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首先,从社会生活形态来看,湖北地区人类的聚落生活至迟在新石器时代早期就已出现,发展到中晚期其规模和数量呈扩大化趋势,且在总体布局上体现出居住区的核心性以及不同区域的布局关系。3一方面,聚落规模与数量的扩大化发展意味着族群的繁荣昌盛,为舞蹈艺术的萌芽奠定了深厚的群众基础;另一方面,聚落生活的方式反映出氏族社会成员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稳定的集体生活观念和族群意识,由此产生的氏族成员之间、氏族部落之间、人与神之间情感交流的需要,也为舞蹈艺术的萌芽提供了内在的动力之源。
其次,从社会生产方式来看,新石器时代氏族社会成员已经懂得因地制宜地进行农业种植、狩猎、渔猎、手工业等各种生产,集体劳动,分工协作。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中专业性生产作坊的出现,进一步反映着社会生产能力的提高和社会生产关系的和谐有序。4这些均能够为舞蹈艺术的萌芽提供内容和形式上的依据。比如集体劳动的生活为舞蹈艺术的萌芽提供了表现的内容,其劳动的节奏、呼号及动作也为舞蹈艺术的萌芽提供了表现的方式等等。
第三,从科技和艺术水平来看,新石器时代湖北地区的人类在制陶、建筑、纺织、治玉、冶铜、数学等方面已取得初步成就,比如制陶方面快轮成型技术、磨光技术、窑外渗碳技术的运用;建筑方面材料的精致、设计与施工水平的提高;纺织方面纺轮表面的速度标记;治玉方面的切割、雕琢、钻孔、抛光等工艺技术的运用;从陶响球表面所绘制的等腰三角形反映出的几何概念等等。5与科技水平发展相呼应的,是艺术性的创造。比如,彩陶上的纹饰、陶塑的造型、陶响球的节奏声响以及玉器的造型等等。科技的发展与艺术性的创造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一时期湖北地区人类的智力创造与审美意识,为证明这一时期舞蹈艺术的萌芽提供了依据。
除此之外,在这一时期的墓葬中还发现特定的丧葬习俗和常见的随葬品,比如大多为单人葬、一次葬,少见合葬和二次葬;葬式有仰身直肢葬、屈肢葬,少见俯身直肢葬;成人墓大多有随葬品,常见有生产工具、生活用品和玉器装饰品,儿童墓一般无随葬品等。6丧葬习俗不仅能够反映出当时的生活习俗,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氏族社会原始宗教意识的存在。自古以来舞蹈一直都是宗教仪式中最普遍运用的娱神手段,丧葬习俗和宗教仪式中情感表达的需要也为舞蹈艺术的萌芽提供了条件。
2.萌芽的表现——“击节歌舞”的综合形态与原始宗教意味
新石器时代湖北地区舞蹈艺术的萌芽并非以独立的表演形态呈现,而是寄身于“击节歌舞”的综合形态之中,蕴含有原始宗教的意味。
首先,从考古发掘的乐器类文物资料来看,湖北地区的新石器文化遗址中出土有一些陶响器、陶响球、陶埙、陶哨、陶铃类乐器或疑似乐器。比如黄冈牛角山陶响器、枝江关山庙陶响器、京山朱家嘴陶响球、枣阳雕龙碑陶响球、蕲春易家山陶响球、麻城栗山岗陶埙、黄梅陶哨、天门石家河陶铃等。这些可以发出声音或节奏声响的陶质器物一方面反映了人类在“戛击鸣球”中表现出来的最初的节奏意识和音响意识,另一方面也为了解远古时期“乐”的发生与“击节歌舞”的形态提供了印证。从“乐舞相和”的角度来看,这时的“乐”已包含有“舞”的内涵。
其次,从考古发掘的礼器类文物资料来看,湖北地区的新石器文化遗址中出土有各种石制、玉质类礼器,比如城背溪文化时期的太阳人石雕;石家河文化时期的圆柱形、长方形、三棱形等人头像、虎头像、盘龙等。这些礼器无论是用于祭祀还是丧葬,均带有明显的原始宗教色彩。从“巫舞一体”的角度来看,此类礼器的出土透露出远古乐舞的原始宗教意味。
第三,在湖北地区新石器时代的考古遗迹中,还发现有大溪文化时期的屈肢透雕人像和石家河文化时期的抱鱼坐偶、跨立人像,这三种人物形象分别呈现出新石器时代湖北地区人类跪、坐、立的形态状貌及其生活特征。从舞蹈艺术发展的角度来看,远古舞蹈简单、粗糙,服饰道具形态大多为现实生活的朴素反映,所以这两种人物形象能够为我们了解远古舞蹈的人物形象提供一些参考。
综合以上考古资料,虽不能直接证明这一时期湖北地区舞蹈艺术的存在及样貌,但从“乐舞相和”“巫舞一体”的角度来看,新石器时代湖北地区舞蹈艺术的存在是毋庸置疑的,只是除却“击节歌舞”以外,有关其舞蹈发展的其他信息尚需更多考古方面的材料依据。相信随着考古工作的进一步深入,终能探寻到越来越清晰的历史面貌。
三、有关湖北地区远古舞蹈的当代遗存
由于历史的久远和舞蹈艺术动态易逝的本体局限,今天能掌握到的研究远古舞蹈的资料十分有限。不过庆幸的是,舞蹈艺术作为人类社会文化传承的独特形态之一,其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和艺术传统在历史流变中得以相对稳定的保留和传承下来。因此,在考古资料以外,当代遗存中有关远古舞蹈的神话传说与民间舞蹈,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为我们研究和了解湖北地区的远古舞蹈提供启示和参考。
1.当代遗存的神话传说
其一:有关“神农氏”的传说。神农是远古时代以始作农具而闻名的氏族部落首领。传说神农始创农耕,植五谷,疗民疾,尝百草,训禽兽,创编织,演历时,兴贸易,揉木为耒,断木为耜,使人类从游牧转入农耕,由野蛮走向文明。历史文献中对其人其事多有记载,比如《荆州记》云:“神农生于厉乡……县北界有重山,山有一穴,云是神农所生,又有周围一顷二十亩地,外有九重堑,中有九井。相传神农既育,九井自穿,汲一井则众井动,即此地为神农社,年常祠之。” 经史学家考证,湖北西北部汉水中游曾是神农氏部落的活动中心。厉山(湖北随州北)为神农劳动生息之地。7在《通典》和《路史·后纪三》中均记载了神农氏部落的乐舞《下谋》,亦曰《扶持》《扶犁》,是以歌颂神农氏发明农业工具犁、教民种田功绩为主要表现内容的乐舞。史籍文献中有关神农的远古传说及其相关乐舞活动可以为我们了解湖北地区远古舞蹈的发展提供参考。
其二:有关“尧舜禹与三苗之争”的传说。尧、舜、禹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继黄帝之后的三位氏族部落首领。三苗又称有苗、苗民、南蛮,是由多民族组成的一个部落联盟,今湖北江汉地区是其生息腹地。关于“尧与三苗之战”,《吕氏春秋》中记载:“尧战于丹水之浦以服南蛮,舜却苗民,更易其俗”。这里的“更易其俗”虽未说明用何种方式,但借由“移风易俗,莫善于乐”的儒家观点来看,其中应该包含有乐舞。关于“舜与三苗之战”,《韩非子·五蠹》中记载:“(舜)乃修教三年,执干戚舞,有苗乃服。”这里的“干戚舞”是指古代的武舞,干戚为道具,其中干为盾,戚为斧。显然舜是借干戚之舞的英武气势,来达到威慑三苗的目的。由此可见,早在远古时代,湖北地区特别是江汉地区就已经受到了华夏族乐舞文化的影响。
2.当代遗存的民间舞蹈
与民间传说相比,带有原始文化遗存的民间舞蹈以其更鲜活生动的形象和姿态透露着湖北地区远古舞蹈的独特风韵。
首先,从远古舞蹈“击节歌舞”的综合表演形态来看,今天湖北地区仍有一些民间舞蹈保留着这种综合性的表演传统。比如,湖北鄂西南地区的《打丧鼓》就是以“击鼓”“领唱”“和舞”为主要表演形式的舞蹈;流传于鄂中南地区的《三棒鼓》也以“边击鼓、边歌舞”为主要形式特色。
其次,从远古舞蹈浓郁的原始宗教文化内涵来看,湖北地区很多民间舞蹈中都保留和传承有图腾崇拜、祖先崇拜、巫术祭祀等宗教思想和巫术色彩。比如湖北郧县的《凤凰灯》就是以“凤凰”为主要表现形式,以凤凰出巢、游园、寻牡丹、戏牡丹等为主要表现内容的图腾类假形舞蹈,体现出鲜明的“崇凤”情结;鄂西土家族的《摆手舞》以八部大王(也有供奉彭公爵主、田好汉、向老官人)为祭祀对象,表达着祖先崇拜的原始宗教情感;而流传在湖北境内的《端公舞》《八宝铜铃》等民间舞蹈亦带有浓郁的巫术祭祀色彩。
第三,从当代湖北地区民间舞蹈的表演形式和类别来看,普遍流传着许多拟兽类的假形舞蹈。比如,《麒狮舞》《独角兽》《赶象》等,这些舞蹈中的假形形象并不属于典型的图腾物,在热烈欢乐的节庆活动中,舞蹈以引领、众合的表演方式,世代相传。借由今天这类舞蹈的表演风格,可以想象远古先民“百兽率舞”的古朴风韵。
综上所述,本文以考古资料为依据,以神话传说和民间舞蹈遗存资料为参考,对湖北地区远古舞蹈的发展及特色进行了分析和论证。首先,本文以湖北地区出土的旧石器时代考古资料为依据,通过分析湖北地区人类社会的发展状况得出:旧石器时代湖北地区人类的存在及其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发展为舞蹈艺术的孕育提供了条件。其次,本文以湖北地区出土的新石器时代考古资料为依据,通过分析其社会形态、生产方式、科技与艺术水平以及丧葬习俗等内容得出:新石器时代湖北地区的舞蹈艺术在繁荣的氏族社会生活中获得了诸多有益于自身发展的因素,最终以“击节歌舞”的综合形态和原始宗教的文化意味萌发在社会生活、特别是宗教生活中。第三,本文以神话传说和民间舞蹈遗存资料为依据,对远古时期湖北地区舞蹈艺术发展的形态状貌与文化内涵进行了印证分析和补充。
注释:
1.参见张正明著.《湖北通史·先秦卷》[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41-77页.
2.参见张正明著.《湖北通史·先秦卷》[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41-77页.
3.参见张正明著.《湖北通史·先秦卷》[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05-109页.
4.参见张正明著.《湖北通史·先秦卷》[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98-105页.
5.参见张正明著.《湖北通史·先秦卷》[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09-131页.
6.参见张正明著.《湖北通史·先秦卷》[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31-132页.
7.《炎帝神农氏族源于随州考》.http://www.huaxia.com/zt/jl/06-030/2006/00487737.html
[1]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编辑部编.《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湖北卷(上、下)》[M].北京:中国ISBN中心出版,1995.
[2]杨匡民,李幼平著.《荆楚歌乐舞》[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
[3]王子初主编.《中国音乐文物大系·湖北卷》[M].郑州:大象出版社,1996.
[4]张正明著.《湖北通史·先秦卷》[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