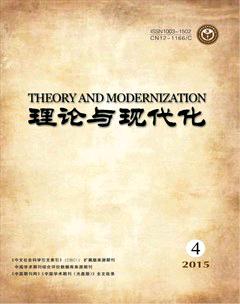都市民间中的本土现代性:当代津味小说的文化选择
丁琪
一、“本土现代性”的文化视野
天津在近代曾是九国租界,有史料记载亦有现实遗迹,相对其他城市天津作家也许更有资格谈论西方文化和现代性,然而津味作家的文化选择却是在国际化视野下致力于发现更好的“自己”。不像海派作家那样重新结构“洋化”的都市现代性,他们大多选择了都市民间视角——从都市底层、边缘、传统家族日常生活的内部,重新塑造了带有中国乡土文化气息的都市现代性。这些作品以素朴的世俗文化底子和家庭生活的慢节奏强调了这样一个事实:后发展国家的现代化过程表面看是西方文化侵略和殖民的后果,但实际更是东方传统文化在亡国灭种危机下的自主选择,甚至是都市民间顺势而动、因势利导过程中认知逻辑和精神信仰不断调整累积的思想结晶。
津味作家崛起时以都市地域文化自我标榜,但实际上对现代性的深刻领悟才是成功的关键。20世纪80年代的流行思想倾向是把现代性看成是资本主义的附属物,认为它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和启蒙运动的展开而形成的一个历史进程和相应的价值取向。由此形成把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性对立的地域文学表述,以西方现代性价值观作为内参照挖掘民族文化利弊,所谓“激浊扬清,去伪存真”,在文化价值取向上无可挑剔,但在思维上仍是一种现代性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割裂思想。而津味小说的创作者大多长期生活在天津本土都市环境中,对都市文化与现代性的辩证关系有着更为切身的独特领悟。在他们的视野中,“都市文化”不仅是表面的车水马龙、霓虹闪烁,更是一种日常生活方式的历史接续,“现代性”不是西方文化的独有标识,而是一种符合线性时间观念和发展逻辑的文化变动属性,它有内部差异性,化约为国家经验与地方特性。
这种文化变动属性在中国都市起源中的政治喻意和商贸交易动机中初露端倪,其后在漫长的封建帝国严酷的社会环境所培育的“生存伦理”中生根发芽,生出优先于封建伦理道德的自我奋斗、穷则思变、变则通久等从个人意志到家国治理层面的思想支脉,在近代传统儒家伦理遭遇西方文化的猛烈撞击后显示出其现实适应性,自觉渗透到民族传统文化中成为一种文化结构因子,从而推动传统都市文化艰难曲折的现代转型。天津作为中国现代化的一个发祥地,成为观察这一文化结构调整的最佳地点。津味作家要表达的就是这个城市的这种独特“韵味”:天津本土码头文化和传统民族文化在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时刻如何以自己的精神信仰和行为逻辑经受动荡并从容地跨进现代化大门。
二、都市民间的观察视角
津味小说成功与否考验的是作家对传统与地域文化的审美发现能力,如果借鉴历史上的风俗画经验,把故乡当作生命的原乡来歌咏,似乎与沈从文、废名等开创的传统地域小说并无二致,也无法突出天津的都市特色;如果延续上个世纪30~40年代的天津报人小说专写都市黑幕,似乎又被狭隘的追求所制约,影响了创作的深广情怀和阔达境界。津味小说摒弃了这两种创作倾向,以天津的市井百态和日常生活的细节方式描述了本土现代性的驱动过程,发现了地域生活的现代性审美价值。从逻辑层面讲都市民间也是本土现代性生长最为适宜的土壤,民间处在国家权力控制相对薄弱的领域,给自由、边缘、体制外的思想观念预留了空间,同时处于都市而不是乡野的文化前沿位置使它不断接触外来的刺激保证了变化的可能。民间的传统风貌和都市的前沿特征交融混合,形成了一个藏污纳垢、鱼龙混杂的独特审美空间,延伸着津味作家对中国本土现代性的开阔想象。
津味小说的都市民间是包涵特定物理空间和文化内涵的浑融整体,它有公共空间与私密空间两个场域。家庭之外的公共空间包括车站、码头、大桥、老城厢、“三不管”,这里活跃着一技之长的能人、奇人,终日无所事事、以协调事由来找饭辙的闲人,还有相士、赌徒、妓女、青皮混混等,这种三教九流的刻画在上世纪30年代津派作家中就曾流行一时,但那时由于思想格调不高没有形成影响力,当代津味作家提升了这种底层小人物的书写品质,主要源于他们发现了这种生存状态的历史文化基因具有一种本土现代性意义,即发现了天津本土码头文化因子的审美现代性。
以水文化为特征的码头文化可以说是天津地道的本土文化,代表着这座城市的原生品格。九河下梢的地理位置赋予了天津不同于北京的独特市民文化心理,皇城里的北京人尊崇的是传统,是礼数;而对于向河与海讨生活的天津人来讲,关注的则是变化和潮起潮落,必须顺应外在环境的变化协调自己的生活。天津人的开放性、自由精神和极强的适应能力具有本土现代性意义。这在冯骥才书写的刷子李、苏七块、神鞭傻二等人的传奇故事中体现出来,无论你如何身怀绝技、武功盖世,但老祖宗的绝活是“变”,“不改不成,改就成了”,这是《神鞭》反复强化的因时而变的主题,这既是本土草根精神的绵延,更是内忧外患的大时代所激发出的现代性。津味小说发现了这种地域文化的现代性内涵并对它进行了审美再创造。
三、家族文化的现代性关照
津味小说还在都市民间的相对私密空间范畴,展现了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结构内部的自发性调整,创造了成熟的当代家族文学。中国传统以“三纲五常”为伦理支撑的大家庭为生存发展所做的屈伸、表现出的强韧以及对惯性的改变都表现出一种积极的现代性意义,这主要以林希的“津沽世家”系列小说为代表。《天津卫的金枝玉叶》、《桃儿杏儿》、《小的儿》、《家贼》、《醉月婶娘》等作品以系统的血缘姻亲谱系、相似的人物性格命运和结局等构成互文关系,共同讲述了侯氏家族伴随民族危亡和买办文化的侵蚀而大厦将倾的悲剧性命运。如果止于这种亲历性的家族记忆,林希的作品似乎与传统的家族小说《红楼梦》或者与新文学中的《家》、《春》、《秋》等并没有实质区别,可贵的是林希的小说内置了“传统家族文化现代性关照”的独特视角使其在文化价值观上不流于俗套。
作者注意到了中国传统儒家文化虽然在国家治理层面失去了统治效力,但是在民间、在家庭生活内部它有一种绝处逢生的自我调适和救赎能力,它表现为家庭成员在国破家亡之际自主摒弃那种僵化的等级制度、门户意识和纲常伦理,默认和遵循一种生存发展逻辑和大局观念,从而摒弃了一些不合时宜的东西并保存了传统文化最为核心的灵魂,实现了化蛹成蝶的蜕变。“母亲”施展长房媳妇的权威不是为了维持家庭表面的和谐稳定,而是暗中保护着家里不断出现的新生事物和革命青年;醉月婶娘那样的传统女子也开始关心国家大事,喜欢新派人物和新文艺,她在绝望中的反抗已经表现出中国传统闺阁女性在文化视野、爱情观念和社会参与意识上的觉醒和行动;“父亲”本是洋场里的花花公子,但在民族战争的关键时刻不失气节,拒收公司的巨额贿赂,断然辞去了大阪公司襄理的职位,也给“爷爷”做出榜样,使他带动美孚油行全体中国员工罢工一小时,以抗议该公司的变相侵华行为。这些侯门子弟并没有被买办文化所腐化,在民族危亡时刻都表现出了传统文化富贵不淫、威武不屈的精神操守和民族大义。该变则变,不该变的则誓死捍卫,家族的优秀文化正是在这种规则秩序的自我调整中世代传承。
总之,无论是都市底层为生存之需“剪掉辫子留其神”的文化隐喻,还是津沽世家在式微之路上坚持的精神操守,津味小说都是要以都市民间的市井图来印证中国传统文化根脉没有被现代化进程斩断,相反它自身长期被压抑的另一面被外来因素激活并释放出生机和活力,它不同于西方文化的现代性内涵,代表着中国文化的原点以及辐射过程中遭遇阻力的曲折转向。津味小说以这种文化观念纠正着以往对传统文化与现代性的刻板认识,并保留了中国都市现代转型的复杂经验和强大主体意识,而不是沦陷在文化殖民的误区中与曾经被瓜分的城市一起做了宗主国的玩偶。津味小说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进入当代文学史并与京味、海派并驾齐驱。
(作者系天津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文学博士。本文为“天津社会科学院重点研究(应急)课题”,编号:14YYJ-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