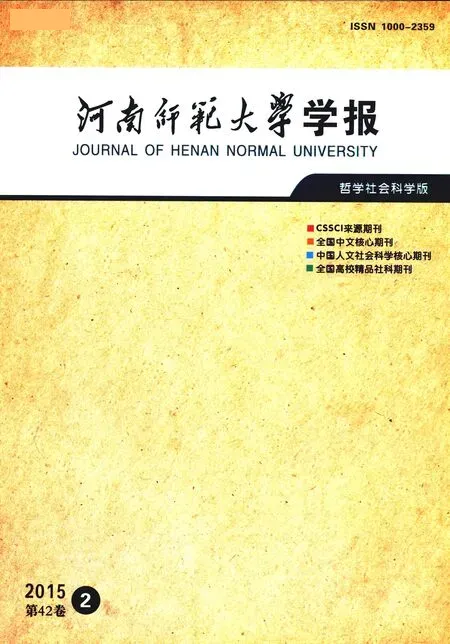类型学视角下的方言“子”尾研究
郝红艳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留学生院,广东 广州510421)
近年来,类型学的研究方法越来越受到汉语方言学界的重视。基于汉语方言丰富的语料,借助类型学的研究视野,对汉语方言“个性特点”的探寻,通过提取参项,阐述参项之间的蕴涵关系[1],探讨方言的共性,为汉语方言研究开辟了崭新的道路。“方言作为同一语言的地域变异,从历史方面说,方言是语言分化的结果,从共时方面说,方言受到共同语的制约,又同周边方言发生相互的交流”[2]。对各种方言进行比较的类型学研究,能让我们从句法、语义、语用功能及认知、心理等不同角度去诠释方言之间存在的共性以及形成差异的成因。
词缀是汉语形态构词成分中的一种附着语素,常常附着在词根的前面或后面或嵌在其它语素的中间。它只表示附加意义或语法意义,而不表示词汇意义,是一种不自由语素。在汉语方言中,“子”尾是普遍存在的一个重要构形后缀。由于“子”尾与词根的结合面不同,所以,普通话与各方言的子尾词或相当于子尾词的词在使用范围上、存在数量上有很大差异,其读音和功能各具特征,千差万别。本文借用类型学研究的视角,对汉语不同方言的“子”尾的读音、构词、语法功能和语法意义进行考察,展示其分布特征,探讨汉语方言“子”尾的共性与差异以及成因①就现代普通话来说,“子”是古汉语中的实词逐渐虚化而来的,鉴别“子”尾的主要标准是轻声。根据王力(1996)[3]的考察,有六种“子”字不是词尾:1.“男子”“女子”;2.作为尊称的“夫子”“君子”;3.禽兽虫类的初生者“虎子”“龙子”;4.指鸟卵“鸡子”;5.指某种行业的人“舟子”;6.指圆形的小东西“棋子”。本文考察的汉语方言中的“子”尾词不包括以上六种。文中所采用的语料来自公开发表的论文和笔者自己的实地调查,恕不一一列出。。
一、汉语方言中“子”尾的语音类型
“子”的中古音是上声,精母止韵。在现代汉语方言中,“子”的声韵都有所演变,声调类型、语音形式等在不同方言区有不同表现,具体情况可以参考下表:

?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方言中的“子”在声调上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重读,有声调,南方方言中“子”字属于此类;一类是轻读,“子”字读音为轻声,在北方方言中较为多见,吴语和客家话的个别地区也有将“子”字读为轻声的。从“子”的声韵演变上来看,北方官话、中原官话、粤语、湘语等地区方言中的“子”字声母读为舌尖音的,如[ts][t□],是对中古音的保留。晋语及附近地区方言中的“子”字声母读为舌尖中音,如[t][l],是对上古音的一种保留。值得注意的是,同一方言区内,“子”字读音的语音形式并不统一,出现声韵调多样的现象。比如晋语区内“子”同时存在[ts][z][t][l]和零声母等多种声母形式,[□][□][ou]等多种韵母形式,这实际上反映了方言在演变过程中一定的历史渊源关系。
二、“子”尾的构词范围
与普通话相比,方言中“子”尾的构词范围不尽相同。有的方言中“子”尾的能产性较普通话弱,构词范围与普通话不同。例如吴方言太湖片的浙江嵊州崇仁话中,有的词普通话用“子”后缀,崇仁话却不用,如用单音节词表示:兔(兔子)、金(金子)、茄(茄子)等等;用双音节词表示,大栗(栗子)、道地(院子)、柿红(柿子);有的词普通话不用“子”后缀,崇仁话却用“子”尾词表示,如:钢种锅子(铝锅)、束子/万子/筒子(麻将牌)、(蜡)角子(硬币),等等[4]。
有的方言中“子”尾的能产性很强,构词范围比普通话有所扩大。以江淮官话中苏北的沭阳话为例,普通话带后缀“儿”的,沭阳话都带后缀“子”,如:树叶子、笔尖子、话把子、一会子、人影子,等等;普通话有些不带后缀“儿”、“子”的词,沭阳话也可以加“子”尾,如:手指头子、嘴头子、手脖子、明年子、白天子、蝴蝶子、吴集子(地名)、马场子(地名),等等。沭阳方言中的“子”可以作为后缀用于以下各类词,远远多于普通话“子”尾范围:
1.用于指人名词,大体有几种情况:缀于一般名词语素,表称谓,如:外甥子、妗子(舅妈)等;用于人名后,主要用于乳名中,如:小玉子、大成子等;缀于形容词语素,如:侉子(北方人)、蛮子(南方人)等;用于动词语素后,如:骗子、叫花子(乞丐)。
2.用于名物词。有与身体器官有关的,如:耳眼子(耳孔)、吞子(喉咙)、拳头溜子等;有用于动物名中的,如:黄狼子(黄鼠狼)、骚獠子(公猪)、叫蝈子(蝈蝈)等;还可附在动词语素后构成名词:坠子(耳环)、戳子(印章)等;用于村镇名称中:吴集子、西圩子、马场子等;其他一般事物,如:金镏子(戒指)、家天子(家院)、年根子(年底)等。
3.用于代词中,如:哪块子(哪里)、多会子/多晚子(什么时候)、这会子(这会儿)、这样子、哪样子(什么样)。
4.用于熟语里的,如:半吊子(二百五)、二衣子(两性人)、尥蹶子(不听话的人)、麻木狗子(轻狂的人)、一叠三来子(叠坐)、人王子(家中受宠的孩子)等。
5.用于数量短语后,如一摊子、一团子、一滴子、一页子等。
6.用于数词后。只有单音节的数词才能附加“子”尾,“一”到“十”以及“零”和“几”都可以附加“子”尾,其他多音节的数词和序数词如“三十、一百、第一”等都不能带“子”尾。如:“五子比四子大。”“跟六子倒过来望就是九子。”还可指子女辈或同辈的排行,如“二子”。但排行第一的没有“一子”或“小一子”的说法。另外带有数字的扑克牌也可以用“数字+子”来表示,如:“我手上有三张八子。”
三、子尾的语法功能
普通话的“子”我们一般称之为词缀或语缀,位于词尾,而方言中的“子”位置不限于词尾,有时可以位于词或短语中,用来修饰另一个中心词,结合很紧不能扩展,往往又造成新词[5]。如:湖南汨罗话中的绳子衣、对子眼、蚕子屎、绷子床、碟子菜;河南浚县话中有嘴片Z、桌Z腿、挖耳勺Z、面条Z棵、筷Z笼、椅Z垫儿”等词语;山西汾西话中有羊肚子手巾、窝囊子人、坷垃子炭、溜沟子货等短语词;台湾闽南话有歌仔戏、邱仔懵舍、桌仔跤、蝶仔花、绒仔布的用法。
在方言中,“子”尾同某些虚成分的功能一样,不仅可以粘附在语素、词上,也可以粘附在短语上,活动范围是多层面的[6]。
1.语素层面
“子”附加在名词性语素之后。普通话的“子”尾主要附加在名词性语素之后,并且主要是单音节名词性语素之后,如:桌子、勺子、嫂子、哨子、房子、猴子、秃子等等。在汉语方言中,不仅可以用在单音节名词性语素之后,还可用于双音节或多音节名词性语素之后。其中名词性成分是非词根语素,需要加上“子”尾才能成词,“子”在这里有成词的作用。如,安徽濉溪话的麸子、口子、条把子、疙疤子、憋虎子妈妈顶子、雾拉毛子,山西长治话的孺子、胰子、妗子、冷蛋子、粪泊子。在有的方言中,由于“子”尾的语音形式不同,造成书写形式也不同,如,河南浚县话的桌Z、鼻Z、筐Z、筷Z、茄Z、虱Z、脖Z,河南安阳话的对的(对联)、油的(蝈蝈)、茄的、袋的、胰的(肥皂),广东海丰话的“师仔(徒弟)、薪仔(竹片)、番仔(异族)等等。
2.词的层面
在汉语方言中,“子”尾还可以附加在名词、动词、形容词、数词、量词之后,有名词化的作用。
(1)“子”尾附加在名词之后,包括双音节、多音节、重叠式。如,河北魏县话中的蜜蜂子、梅豆子、眉头子、汗褂子、鸡蛋清子、门插子、豁牙子,河南安阳话中的酒瓶的、澡堂的、结巴的、王老五的,安徽濉溪话的酱油子、丝瓜子、老汤子、孩头子(小孩)、星星子、狗狗子,江西南昌话中的外甥子、顶针子、角角子、筋筋子、舷舷子,山西吉县话中的门槛子、草帽子、窗窗子、篮篮子等等。
(2)“子”尾附加在形容词之后,包括单音节、重叠式。如,江西南昌话中的这重子、几远子、那厚子、乖乖子、细细子、碎碎子,河南安阳话的瘸的、秃的、聋的、傻的,广东广州话的呖仔(能干的男孩)、精仔、靓仔,福建永定下洋话的聪明子、新鲜子、麻烦子、安乐子等等。福建永定下洋话中可以加“子”尾的还有四种形容词重叠式,如:AA式香香子、净净子、饱饱子;ABAB式啰嗦啰嗦子、拗蛮拗蛮子(相当好);AABB式古古怪怪子、高高大大子;A里AB式马里马虎子、遢里邋遢子,等。
(3)“子”尾附加在动词之后,包括单音节、重叠式。如,安徽濉溪话的飞子(发票/收据)、跋子(拖鞋)、抽子(抽屉)、抽桌撑子(衣架),广东海丰话的刷仔、锯仔、夹仔、筛仔、纽仔、结仔,山西临汾话的扯扯子、沤沤子,湖南道州话的捞崽(小偷)、死崽(呆板的人)、打崽(吃药后出生的孩子)、下堂崽(随母亲改嫁的人),等等。
(4)“子”尾附加在数词之后,主要用于排行、扑克牌中,一般只有单音节的数词才能附加“子”尾,“一”到“十”以及“零”和“几”都可以附加“子”尾,其它多音节的数词和序数词如“二十七、一百、第一、第五”等都不能带“子”尾。如,河南安阳话中的老五的、五的、尖的(A),福建龙岩话中的一仔、四仔、十仔,江苏盐城话中的一子、六子、零子等等。
(5)“子”尾附加在量词之后。如,江苏泗洪话中的批子、窖子、攮子、提子、出子、抬子,河南商丘话中的本子、团子、根子、摞子,福建龙岩话中的粒仔(疙瘩)、片仔、盒仔、间仔,福建永春话中的刻仔(台阶)、架仔(架子)、窟仔(小水坑),等等。
3.短语层面
“子”尾可附在短语的后面增添某种语法意义(修饰性或结构性意义),有些并可改变短语的语法功能。“子”尾可以加在数量短语后面,如,辽宁大连长海话中的一桌子、一箱子、一车子,河南浚县话中的一摞Z、一道Z、一篮Z、一脖Z,江西南昌话中的几块子钱、三四岁子、四五十斤子、两句子、个把子月等等。
“子”尾还可以加在其他类型的短语之后。如,广州话中的光头仔(光头的男孩)、大眼仔(大眼睛的孩子),台湾闽南话的踅圆箍仔(绕圈子)、插花仔、抽阄仔、幌头仔。河南浚县话的“子”变韵可以附在动宾短语之后,像转椅Z、烂眼Z、背锅Z、推刀Z、疙料眼Z、捻捻转Z。安徽濉溪话的“子”尾可附在数词和重叠量词构成的数量词组后面,像一毫毫子、一撩撩子、一宁宁子等。形式上是数量词组作“ABB”式重叠后再加“子”尾,是一种发生在词组上的重叠加缀。
方言中的“子”尾还可以构成某种短语结构,表示特别的意义。江苏泗洪话中“子”尾和前面的动词或名词一起构成“V几V子”结构,进入这个格式的“V”是动作性动词或者是名动兼类的名词,并且这些词可以借用为临时量词,用来说明动作或者物的量。如,串几串子、伙几伙子、堆几堆子、回几回子、下几下子等用法。江西黎川话中“子”尾和前面的动词或名词一起构成“V仔V儿”结构,表示漫不经心地重复行为,如,扇仔扇儿、摇仔摇儿、滴仔滴儿等。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粘附在语素、词、短语上的“子”尾的语法功能主要有:作为构词语素,有成词作用,有些语素不能单独成词,只有跟“子”结合在一起才能构成名词。作为名词性词尾,突显“子”尾词的名词性特征,有些词的“子”尾可以带也可以不带,但带上“子”尾后名词性的特征会得到突显。改变词义,有些词加上“子”尾后语义有所改变。改变词性,汉语方言中,“子”尾还可以跟少数形容词、动词或者数词结合,组合后成为名词,改变了原来词语的词性,使动词、形容词、数词名词化。
四、“子”尾的语法意义
从汉语史上看,“子”作为后缀产生在东汉,发展于魏晋,唐宋时期作为“子”名词词缀普遍使用起来。例如:师云:“诸和尚子,打钟打鼓,上来觅什么?”(《雪峰录》上)师云:“此间有个老鼠子,今在浴室里。”(《雪峰录》下)师云:“饭袋子,身如椰儿,大开与么大口。”(《云门广录》卷下)口语化较强的《朱子语类》也有大量“子”尾词的例子。日本江户时代著名禅学僧无著道忠在其《禅录用语》子字部中,收录“子”作后缀的语词共38个,其中就有18个为三音节以上,近所见子尾词的百分之五十[7]。除了词根为双音节、多音节名词的子尾词外,这些书籍中还使用附在数量结构之后的“子”尾词,如一壁子、一边子、一饼子、一策子、一点子,等等。这些“子”尾词仍在当今各方言中使用,可以说现代汉语方言中“子”尾的丰富用法,是古汉语的共时遗留。
方言中的“子”尾附加在词或短语上,增添了语法意义,表示一定的感情色彩。1.表憎恶。例如山西临汾话中:坏坏(名词,中性)——坏坏子(名词,厌恶的感情色彩)、盆盆(中性)——盆盆子(厌恶、不喜爱的感情色彩)等;福建厦门话中,“仔”尾词表示对从事某种职业的蔑称,如,作田仔(农民)、乞食仔(乞丐)、讨海仔(渔民)、看命仔(算命先生),等。2.表喜爱。例如湖南道州话中狗崽、妹猪崽、黄鸟崽、鲤鱼崽,表示对动物的爱称,不能用于虎、狼、鼠、蛇、虫这些动物之后。3.表语气缓和。福建永定话中AA式做状语时,“子”尾可加可不加。不加“子”尾,语气比较直率,加上“子”尾语气比较客气:慢慢走——慢慢子走、轻轻放——轻轻子放。4.表小称。有些“子”尾还具有减势功能,表示小或少,在第一个量词前可以加“小”或“细”等表小的形容词,如安徽濉溪话中的一小点点子、一小毫毫子、一小粒粒子、一小页页子,山东沂水话中的几筐筐子、几棵棵子,其小称形态属于词组“一筐”和“几棵”,而不属于量词。
方言中的“子”尾有时与普通话表示的语法意义有明显的差异。比如广州话中的“仔”虽然用在词尾,但词义并没有完全虚化。它不仅可以作为名词的标志,而且还有“小”的词汇意义,或者表年龄小,或者表形体小,或者表级别低。广州话中的“仔”既可以表示轻蔑、厌恶的感情,如:兵仔、孤寒仔(小气鬼),也可以表示亲昵、喜爱的感情,如:细路仔、金鱼仔。
五、结语
通过对“子”尾的考察,可以发现方言中“子”尾的读音不尽相同、构词范围在不同方言中有宽有窄、语法功能和意义具有个性特点。从语音上看,南部方言(粤、闽、客家)是重读,跟南部方言没有轻声的语音系统有关,北部方言“子”轻读居多。从使用范围上看,南部方言(粤、闽、客家)基本上维持着上古汉语的情况,很少或完全不用词尾“儿”或“子”。吴方言除个别地方(如杭州)外,一般只用词尾“子”字,不用“儿”字,“子”的应用范围也比较窄些。官话中,江淮官话的“子”尾构词范围最广,语言形式尤其丰富,带有南方方言的特点。“子”尾在汉语方言中的差异化表现,也体现了方言区之间的不同。从地理分布上来看,一方面,不同的“子”尾都有一定的通行范围,这个范围与当前的方言分区有一定的联系,体现了“子”尾的使用具有一定的地域性。另一方面,每一种“子”尾又不局限于在同一方言区内使用,同一个方言区内经常出现多种“子”尾的形式,一定程度反映了不同方言间的相互渗透。
同时,通过对“子”尾词的考察,也发现汉语方言中“子”尾虽然在语音形式、构词特征、语法功能以及语义特征彼此略有差异,但它们作为名词词尾标志的本质属性是一致的:各方言中的“子”同现代汉语中的虚成分一样,是粘附性的虚成分,不仅可以粘附在语素、词上,也可以粘附在短语上。而且,各方言中的“子”尾从历史来源上看也具有一致性,都来源于古汉语词尾化的“子”,是古汉语的共时遗留。
总之,对各方言中“子”尾的现状、特征以及形成这些状况的源由有了准确而全面的了解后,对于我们以类型学视角把握“子”尾的历史演变及其与其它方言的源流关系,考察“子”尾在方言共处中与其它方言所发生的相互渗透状况提供了有益参考。
[1]李蓝.现代汉语方言差比句的语序类型 [J].方言,2003(3).
[2]李如龙.论汉语方言的类型学研究[J].暨南学报(哲社版),1996(2).
[3]王力.汉语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1996:223.
[4]张晓瑜.嵊州崇仁话词缀浅析[G]//寿永明.绍兴方言研究.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5:156-173.
[5]辛永芬.河南浚县方言的子变韵[J].方言,2006(3).
[6]施其生.论广州方言虚成分的分类[J].语言研究,1995(1).
[7]梁晓虹.禅宗典籍中“子”的用法[J].古汉语研究,1998(2).
——针对对外汉语语素教学构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