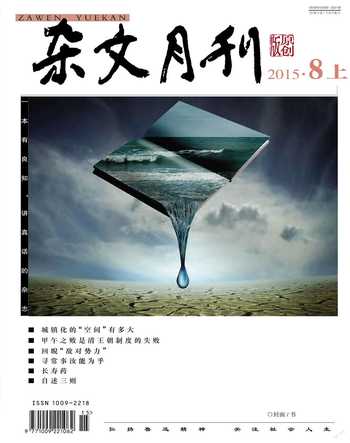“名”之思
秋水
有人把读名著比作喝咖啡。咖啡品牌多,雀巢、克莱士、麦斯威尔、上岛、星巴克……都响当当的,虽说归结起来无非都是一杯咖啡而已。但不同品牌的咖啡,都有自己的fanss拥趸,盖人们不同的口味、意境、情调追求致然。读书亦是,不同人读书的口味不同,从时间上分唐界宋、古今中外,从品类上散文诗歌、稗官野史、小说逸闻,从作者上各仰其名,择益而读。这种阅读,有如探幽,“入之愈深,其进愈难,而其见愈奇”(王安石《游褒禅山记》)。
年轻时恰逢文革,无书可读,就把旧的外国小说翻出来读,什么《欧也妮·葛朗台》《莎士比亚十四行诗》《老人与海》《死魂灵》《红与黑》……读这些名著,很开眼界,但因其都是些“批判对象”,要躲着读。也有些如《金光大道》《在田野上前进》之类的“进步书籍”。久之,便有一点感想:评价一部作品的优劣,是不能以它所描绘的事物大小和重要性来估量的,读书不能一概重名——无论“著”名,抑或“人”名。
许多文学作品往往从小处着手,展现辉煌。席勒擅写神化的人物,比之歌德笔下浑身污垢的下层社会人物,艺术描绘上不免显得容易些,从这点上,读歌德的作品更接地气。在无名氏的《天方夜谭》中,所出场的人物都是与阿里巴巴有瓜葛的乞丐、强盗、穷人和穷人的女儿、“老爷”,没有一个官员,只有两个铁笼子作为官方的象征,一个关着强盗,一个关着“老爷”。作者选取的角度很新奇,他站在贫穷人的一边,借穷人的眼光,去看统治者——好人和坏人共同的老爷。每每回忆这些作品,其中情节和人物都清晰如昨。近年读莫言的《红高粱》,所描写的农民、土地、故事,都不是“重大题材”,但透过这些故事,这些形象,表现了人的命运是如何与社会的命运紧紧联系起来的,那种黄土地上的人与人、人与土地的情结,演绎着一个民族的进化史。
所谓“名著”之名,往往名重一点,并不是面面俱名。作者“名气”之名亦然。《史记》里有句话:“人以颜状为貌者,则貌有衰落矣,惟用荣名为饰,则称誉无极也。”“名著”是相对的,“名气”亦非一成不变,有时就如过眼烟云。写《盐铁论》的古人桓宽,有个很生动的比方:毛嫱天下之娇人,她要靠香泽脂粉而后容;周公天下之至圣人,他要靠贤士学问而后通。“名”只是一种“气场”,要看实际的东西。
岁月倏忽,不觉霜雪盈顶,仍未改昼寝夜读之陋习。有时去书店看看,感觉书比过去多多了,琳琅满目。天雨,在家上网找书,书目更多,不输恒沙。有许多冠以“知名诗人某某”“著名作家某某”之作。所谓“著”,著名,显著也,即名声显赫,可以解释为“很多人知道的”,“很多人听说的”,但往往并不尽然。如一位自诩“某书法家协会副会长”的“名家”,在大商场门前设摊卖字,當场挥毫,不料其落笔便错,一幅字里面竟能有好几个错别字,而其润格,并不说明错别字不算钱。还听说有的“名家”作品竟是抄袭来的,为不是很“名”的原作者诉上公堂,变了斯文扫地。
市场经济下,商人的思维方式介入作品创作,遂出现了炒作之“名”。36年前,英国有一位“著名”儿童文学作家,在他的《蒙面舞会》出版发行前几天,他用纯金铸成一只20公分长的兔子,并用六块宝石加以装饰,在一位证人的陪同下埋在英国的某个地方,然后宣称在他的新书里有这只金兔埋藏之所的暗示,只要买来这本书,就有机会获取金兔。一时间,英国到处被挖得坑坑洼洼,最后被48岁的肯·托马斯挖到。而这次“活动”使他的书一下子畅销一百多万册。但这种纯功利性的写作加炒作,还谈得上什么品尝和阅读?
“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李杜当初未梦想什么“知名度”,“惟此两夫子,家居率荒凉”(韩愈)。其“名”之所成,积历史与造化之功,非一日之寒,诚如华山之险,泰山之雄,黄山之奇,峨眉之秀……
“有怎么样的人,就有怎么样的思想。假如他们生来是庸俗的,奴性的,那么便是天才也会经由他们的灵魂而变得庸俗、奴性;而英雄扭断铁索时的解放的呼声,也等于替以后的几代签下了卖身契。”(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这话值得我们深长思之,思索克利斯朵夫何以“痛诋艺术上的拜物教,说什么偶像,什么古典的大师,都用不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