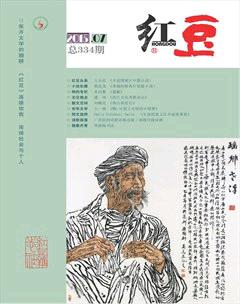遮蔽
朱以撒,男,1953年生,福建泉州人。现为福建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福建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书法家协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作家书画院副院长。在国内报刊发表大量散文、随笔作品。出版散文集《古典幽梦》《腕下消息》等多部。作品入选众多选本并获奖。书法作品广有流传和影响。
车子在北方这个小县城边缘奔驰,和夏日里所见已经远远不同。路边密集且舒展的杨树,已经退去所有的绿意,一叶不挂,把杨树背后的村子暴露出来。枝头上的黝黑空巢一下子变得醒目高悬,它的方位、形制在目击时被确定无遗。一年里头,这些村子、这些空巢都被碧绿的叶片遮挡着,让人从旁边走过,浑然无觉。叶片是渐渐长大的,初始有如星点,而后每一日伸张,形成一张绿色的屏障,几里,几十里,把人们窥视的好奇心挡在外边。夏日里经过,我揣度连成一道的杨树背后,藏着奇妙的玄机,会是很空旷、深邃,根本不会想到是一些实在的村子,每日鸡飞狗咬的,充满了世俗的气味。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都是有所遮蔽的,或是自然之物,或是人工设置,总之不让人一眼洞穿。如果没有冬日的到来,树叶掉得这么彻底,村子里的真相永远看不到,里边的人安然地过着寻常的日子。随着秋日以来一片又一片绿叶转黄、枯焦落下,空白越来越明显。谁都没有办法弥补这些空白处——遮蔽不见了,一个个村子让人看到了。只有等待这个漫长的冬季过去,春日缓缓到来,叶片由小及大,他们村子里的秘密才又重新得到了守护。
在很多时候,每一个人都喜欢有所保留,不愿罄露。记得我第一次见到尼龙蚊帐时,心里大吃一惊——它和旧日的麻蚊帐最大的不同就是薄且透明,可以清楚地看到里边睡觉的那个人的身体。而麻蚊帐让人看不清,睡起来就特别自在。这和一个人着不着衣裳是一样的,由于有衣裳的遮蔽,人们的心理、生理都会更加坦然。实在的墙体是一个家庭的遮蔽——目力再好的人也无法穿透一堵薄薄的墙。如果一个个家庭的墙都是透明的,那么在这种透明中,每一个家庭成员都会生出许多的不安。夜幕是白日的遮蔽,夜幕拉开的时候,目力逐渐受到挑战,最终宣告目力的失败,在漆黑中无能为力。人们不得不动用了火,即便一灯如豆,也使人能够清晰地看到眼前的人,看到他的眉目神情。人们在追求光明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光电专家应运而生,有能力把暗夜的迷雾驱散,使人们不再有日落而息的心态。光亮越发达的城市,遮蔽消失了,许多人要在这些光亮的场域里,劳作或者娱乐。只有那些循自然之道的人,才可能探究夜色独有的情调——柔和的、朦胧的,隔纱窥月的,雾里看花的,使置身其中的人的心理起了微妙的变化。就像暗夜里在荒野上赶路的人,恍恍惚惚疑真疑幻,那些草木摇曳之状,鸟鸣虫唧之声,都被无限地放大了,朝着诡异的方向。于是心弦收紧脚下生风,深浅不计,慌乱中踢飞了石块,忽忽过了茅店社林,过了乱坟岗子,看到村头水电站昏黄的灯光。此时背上已经沁出了汗水。惊悸之美——事后我回味不已,是因为这些暗夜、暗影,使我品咂了清明白日所没有的快感。
华滋的水土,总是有相续不断的水果推出,让这个南方城市的人们大饱口福。动作熟练的人们,撬开它们的外壳进入实质,感受内部的甜蜜和黏稠。对于一些形制硕大之物——西瓜、榴莲、菠萝、椰子,人们必须在购买前判断出内部的质量,然后决定取舍。西瓜是寻常之物,人们用左手托起,放在耳边,用右手拍拍,或者指头弹弹,倾听内部的回音,判断出生熟程度。对于榴莲就不能如此,这种植物的前世肯定遭受大劫,以至于它的后代对这个世界有着强烈的抵御意识——浑身是刺,摸不得拍不得,无从考察内部的真实,只能凭运气,把它绑回家再见分晓。就是皮层很薄的石榴,如果没有让它咧开嘴,谁也想不到里边隐藏着如此多的晶莹颗粒,闪动着珠玉辉光。这使我第一次见到时惊喜异常——一个孩童全然不懂,一枚外表不起眼的石榴,它的内部会是如此精彩,这些珠玉有秩序地堆垒在一道,任何力量把它们解开了,都无法还原到早先的那种镶嵌状。这是我对一枚水果最初始的感觉——内部的默契、神秘,不可究诘。由此可以延伸到任何一种果实,在或厚或薄的外表下,有着各自的精彩——不同的汁液,不同的气味,没有一种天生天养的果实会混同在一起。这使我在遭逢一枚从未见过的果实时,都充满了对它内部的好奇冲动。我不会急于打开这些陌生的形态,而是揣摩再三。往往在它们内部豁然开朗时,才知道我的猜度往往错了。
多水的南方,水把许多物体浸泡在里边,让人看不到深邃处的动静。我在海边行走,感到巨大液体内涌动着无定的力量——没有什么可以阻止它们的进退,如此的柔软,又如此的坚韧,让每一位进入水中的人,心与水一样,不停地荡漾。一些海边居民在退潮时用镢头在淤泥中刨出一堆堆木块,晒干了做劈柴使。时日久了让人感到蹊跷,觉得这些木块应该是一艘船的某个部位,只是已久不在波涛上行走,而是深藏于波涛之下了。此后费很大气力,这艘宋代古船终于从黑暗处起身,使人看到粗壮的锚、漫长的桅杆、恢宏的船体。政府为它建了一个巨大的馆,把它供在里边。在淤泥的覆盖下,还有多少沉船和沉船里的宝贝,永远见不到天日?并不是每一个事物都可能从暗中走出,被阳光铺满。在我认识的人中,金先生是个沉沦的人,他的家庭成分、个人身份,意味着连报考大学的机会也没有。他只有不断地买书,想象着要像大学生那般拥有很多的书。高考恢复后我上了大学,曾经遇到金先生,他很细致地向我打听大学课程的方方面面,魏晋文学史要讲几节课呢?元代的说经话本、诸宫调可能你们都很陌生吧,能读到多少呢?明代传奇读过了,是不是明杂剧就简略许多?我把自己知道的说给他听——一位长期徘徊在大学门外的人对于大学里的动静是很感兴趣的,千百次地想象着它的美好。那时金先生已经五十多岁了,觉得自己就是泥淖中的曳尾龟,浑身泥泽,永远爬不出来。他每日裤管一腿高一腿低地在杂乱的工地上奔走,监督着民工们的施工进度。这个年龄,繁忙的工作和繁重的家庭生活已经使他心力交瘁。从外表看,寻常日子的辛苦,已使他眉目低敛步履匆忙,似乎对任何人事都没有瞻顾的心思。只是,一丁点儿对于大学的言说都让他敏感、警觉,竖起耳朵听,并且会追问不停。他放光的双目终了黯淡下来。
四十年前,有一位女知青来生产队找我。我们在村头的樟树下,为着一家县办工厂招工而兴奋交谈,直到暮霭下来,两个人的脸都有些看不清了才分开。这些称为知青的人,在一个知青点生活、劳作,彼此文化水平相距未远,交流起来声气相投,互为知音。十年八年过去,知青点曲终人散,有的当了兵,有的进了工厂,有的又回到旧日的城市开始新的生活。我和知青点的所有人不同,考上大学,后来成了一名大学教师。生活的维度朝着专业的方向发展,单枪匹马,自得其乐,渐渐深入下去。我身边都是一些各有专长的同事,各怀隋璧,各骋其能。我们交谈的,也就大多是纸本上的风雅了。那些曾经辛劳的乡野生活,渐渐地淡薄甚至忘却了。我在家乡一条街的拐弯处遇上她,当时都感到惊奇,觉得应该说很多话。在对于各自近况都打听之后,慢慢就觉得言说的话题相差许多了,彼此已是熟悉的陌生人。正如《一代宗师》里的那个老潘对叶问说:“其实小姐她不知你,你不知她。”毕竟相隔太久,发展的方向朝着相异的方向延伸,关注点全然没有一点瓜葛,不知何所云,云何所。我发现如此漫长的时日过去,她的文化水准还停留在当时阶段,小学生的表达。她对学习毫无兴趣,觉得庸常日子足以应对。我只能小心翼翼地措词,有意带一些知青时的粗鲁、粗糙的表达方式,以免让她察觉出我言说中的书生气味。是什么让我们不能像旧日那般畅快地谈吐?我只能说是时日,时日的风尘把我们谈吐的通道遮蔽了,使我无法回到旧日的我,连同那些旧日的表达。
父亲八十多岁时,又重拾了年轻时的书法爱好,每日写上一段时间,作为消遣。一个人老了,相跟着也就眼花了,手抖了。格子折好了却看不清楚,写得忽大忽小,时紧时松。父亲喜欢写多字数诗词,以此来挑战自己持久的耐力。百十个字下来,气力费尽,忽然一滴口水控制不住,忽地落下,使字迹上的墨汁洇化成团。一个人年龄大起来,连使唤一杆轻柔的羊毫都那么力不从心。青年时的父亲神情俊朗动作敏捷,一幅字写下来,干净利落。如今,这个称为“病”的幽灵,潜伏在他身体内部,让他感到浑身上下的不适,有时甚至僵硬地钉在一处,动弹不得。病赶不走,还在体内越发坐大了。这样就使一个人的形态、神态不似本来,而扭转成另一种样子。病很像风,风是看不到的,但是人们看到了紧张摇曳的草木,听到了潮水急促地拍岸的声响,就知道风到了。所谓的病体就是这样,肢体语言本来是正常的,如同我们的正常言说,而后来不正常了,显得古怪、滑稽了,让人看了怜悯——不正常的力量太大,就把正常遮蔽。一个人终其一生,顺顺畅畅无疾而终的毕竟鲜有,更多的为一些病症纠缠,智力上的、体力上的,难以摆脱,只能在生存过程中极力抗争。母亲最终是全然不知这个世界上的人事的——一个往昔思路清晰的人如此这般,是我一直想不通的,因为那些使之转变的因素我如何都看不到,只是看着母亲一年年地衰退下去,无法阻挡。父亲如今还是坚持自己理财,他的记忆渐渐有些退化,但是拒绝妹妹的帮助。他认为一个人如果连管理自己的钱都做不了,那真是废了。这些钱代表一些数字,父亲根据这些数字进行分配,饮食起居所用、人情世故所用,还有心血来潮时所用。数字的分配、增减是一场智力上的游戏,有助于他大脑的磨炼。大笔的钱、小笔的钱,在加减乘除的过程中使自己的思维理性起来,不敢迷糊。过年时父亲的钱会多一些,子女给他一些钱,他塞入口袋里,或随手搁哪里,有时就找不到了,有时就被保姆抽走了——尽管有证据证明这些不足,父亲还是要自己理财,认为自己完全有这个能力。我觉得还是随父亲去,让他在数字的计算中感到自信——这个小城的人情礼数特别多,父亲那些算对了的、或者算错了的数字,进进出出,会让他更真切地琢磨、追究,亲人不要因为好意遮蔽了他的这种追求倾向。
最近我获得一株香樟树。当时动用了吊车还有七八个工人,才把它挪到院子右侧的角落上。而它的左侧是一株朴树,我想让它们相互映衬,达到平衡。这株香樟树已有几次的挪移经历,每一次挪移,为了成活,总是要锯去一些枝杈,使它生长的状态全然不是天生的那种,而是荒腔走板了。到了我这里算是尘埃落定。一个人和一株流浪的树在一起也是事先没有想到的,我希望此后它就兀立不动,从此渐渐恢复元气,枝叶舒展。
总是有一层皮表,包裹着人和物,使内部在暗中存在,给人们探究时设置了一些难度。往往是人的探魅欲望,执着地要去打开,得出一个真切的解释才罢休。其实,这个世界最吸引人的,还是那些恍兮惚惚,惚兮恍兮的部分,它让我们有许多纠结,不忍舍去。
责任编辑 卢悦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