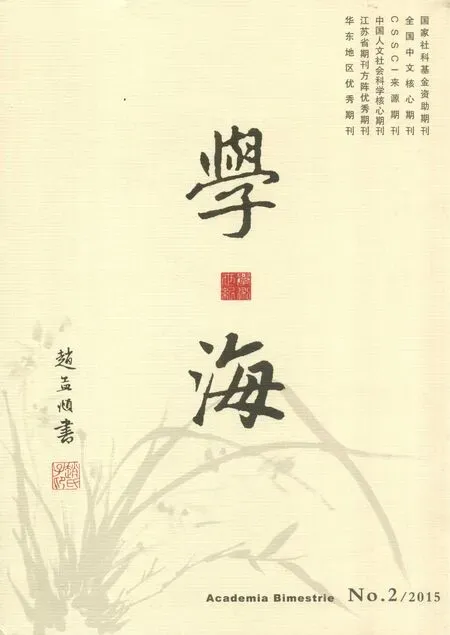如何以科学原则强化马克思主义学术话语权*
吴建国
如何以科学原则强化马克思主义学术话语权*
吴建国
依据科学原则给出马克思主义理论解读话语体系(中国版),是争夺学术话语权的关键。但学界因为概念指意沿用“苏联版”,而形成“概念避讳、问题悬置”;因没看清其“科学、技术、价值”三层架构关系,而形成“问题虚置”;因论证方法仍仅用差异比较,不用相同比较,而酿成“推论障碍”。这些用“科学原则”才能揭示的流弊,生出许多“理论盲区”,影响“三大自信”的社会形成。须依科学原则,在基本概念的确指中研究概念再分,这是理论进化的基础;在基本原理的凝练中研究其三层互动架构体系,不能停滞于管窥性马克思主义解读;在具体应用中坚持其科学普适性,不可将美国社会错置在马克思主义科学预见之外。
马克思 话语权 科学原则
如今马克思主义理论,一方面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方式固定在文献中;另一方面在中外各种方式竞争性解读中,“马克思主义”实指具有学术话语权的解读版本。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实是参与学术话语权的争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前提、基础是,依据科学原则建构出马克思主义理论解读话语体系(下称中国版),这也是争夺学术话语权的关键。
毋庸讳言,当今中国尽管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主阵地,尽管在邓小平理论引导下在批判“苏联马克思主义(苏联版)、西方流派”的过程中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版”建设,但理论研究尚没真正突破“苏联版”的底层禁锢,尚没在理论解读中形成真正的科学方法创新;这让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领域产生许多不必要的“概念避讳”与“问题悬置”,影响了“三大自信”的社会形成。针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流弊,中国社科院侯惠勤教授新文从科学原则出发提出马克思主义学术话语建设的方法论:“必须对现有学科进行前提性批判,确定学科研究对象;确立哲学社会科学学术判断的客观坐标,建立相应的核心学术话语;把价值评价建立在科学论证的基础上,确立哲学社会科学学术研究的基本方法和学术评价标准。这既是马克思开拓的学术话语权之路,也是我们今天重建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话语权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①本文试为解说,以科学原则解读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于推进“中国版”建设,对于获取马克思主义学术话语权,何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从科学原则认知马克思主义理论建构特点
马克思主义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因为它是以科学原则建构的理论体系。说清楚这一点,是树立理论自信的基础。而在此科学原则系列中,有两个基本原则:其一,以客在的原因解释人类所经验到的现象,以实践方法去“归一”各种人类建构的竞争性解释理论(规律体系),这就是唯物主义原则;其二,以现实的相互作用,去解释历史变化的形成动力,这就是辩证法原则。马克思以科学原则改造了哲学社会科学的学术话语(或称“范式”),使马克思主义拥有自然科学同样的科学特征,从而拥有无法扼杀的学术话语权争夺能力,“西方”无奈地将之比喻为无孔不入的“幽灵”。如侯惠勤教授所言:“马克思创建学术话语权,关键在于祛除哲学社会科学的主观随意性,树立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客观坐标,创建特有的核心话语,建立社会科学评判的科学标准。”②正因如此,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着重强调,马克思是“科学家”,发现了类似达尔文进化论那般的“规律”③;列宁、斯大林也特别强调它是“科学”④;邓小平在苏东剧变时强调“是科学”而颠扑不破⑤。西方著名学者贝尔纳等也都指认是“科学家”⑥,麦克莱伦等也发现马克思理论并不会随苏联死掉,领悟“对苏联的灭亡马克思会既不惊奇,也不失望”⑦。
依科学原则建构的马克思主义,不使用任何“应该”(道德条件)作为建构依据,所以即使西方学者也发现马克思不做道德辩护;它使用可以重复经验到的现象、经验(或称“事实”)为材料,形成逻辑自洽的、可以实践检验的规律体系(如剩余价值、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等等),并推论出科学预见(科学社会主义)。正是理论建构的科学原则,赋予马克思主义首要特征——科学特征。恩格斯强调:“社会主义自从成为科学以来,就要求人们把它当做科学来对待,就是说,要求人们去研究它。”⑧任何丧失科学特征的马克思主义解读文本,因首要特征被“阉割”,也必丧失掌握学术话语权的能力。为此,“马克思创立学术话语权,首先是对现行的学科范式进行前提性的梳理和批判,从中寻找自己的学术立足点,为建立自己新的学科体系奠定基础。这种前提性批判的任务有二:一是破除虚构的、想象的价值预设,进行科学的学术发问;二是奠立现实的、无可回避的事实前提,确立学术研究对象及其话语方式。”⑨
要讲清楚,马克思所采用的科学原则,就是自然科学的建构原则;但与孔德的“社会科学(规律体系)”建构方法有本质不同。孔德范式是采用统计、模型、经济人假定等方法,把社会中人的能动性因素滤除后的规律研究,而马克思范式是采用把社会中人的能动性因素增设为主要变量的规律研究。如果说孔德范式的社会科学研究特点,是把社会科学塞入到传统自然科学之中;那么马克思范式的社会科学特点,就是把社会科学拓展到传统自然科学之上。如侯惠勤教授所言:“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实际上也就是涵盖了政治、法律、经济、文化、国际关系、社会交往、生态等及其趋势在内的真正宏观社会学”⑩。相较而言,孔德范式本质上不是真正的“社会科学”。
以科学原则揭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流弊

然而,纵观我国30多年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教科书修订,“中国版”虽然不断发展,但至今仍然没有完成,仍然存在许多用“科学原则”才能揭示的流弊;这导致一方面难以彻底替代苏联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难以在中外夺取马克思主义实际的学术话语权。
其一,概念指意方面,仍然基本沿用“苏联版”的概念解释,形成许多“概念避讳、问题悬置”。概念明晰、概念再分,是理论进步的基础,然而“中国版”研究工作却少有公认建树。例如,对“无产阶级”概念,既没有将“产”明晰为指意“私有财产、资本(生产资料)”中何者,也没有概念再分为“自愿无产阶级、被迫无产阶级”;从而影响到对“工人阶级与无产阶级”、“无产阶级专政与无产阶级执政”、“财产剥削与资本剥削”等等核心概念关系的科学解读。更没有区分清楚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属性、科学地位”、社会主义的“制度标准、道路同向”、共产主义按需分配的“富裕供给、竞争供给”等等概念。这也就影响了深化马克思主义逻辑推演的可能,让“中国版”研究形成许多“理论盲区”。


以科学原则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版”建设
“中国版”建设的核心是,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文献研究为基础,借鉴“苏联版”经验教训,吸取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合理观点,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基本概念,重新抽取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规律),形成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解读话语体系(规律体系),以回答“什么是马克思主义”问题。“中国版”建设必然是在世界学术话语平台上进行的,最终成果是为全世界重写一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教材。“中国化”研究的核心是,研究如何将“中国版”马克思主义应用于中国现实国情条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等领域的国家建设,它回答的是“怎样运用马克思主义”问题。

其一,在马克思主义基本概念的确指中,依科学原则研究概念再分。概念指意的具体化(确指、再分),是理论进化的基础。现实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对许多问题解释感到力不从心,多是因为“概念多义”导致“问题漂移”,或者“概念意会”导致“解释诗化”。如不把“剥削”区分为身份权利剥削(如奴隶主对奴隶剥削等)、财产权利剥削(如地主收取地租等)、资本权利剥削(承担商品生产过程风险而获利润),就难说清社会进步的阶段表现和“资本剥削是其最后形态”。如不把“公有制”区分为平权集体制(均股均权)、国有制(平权集体制的最大化)、不平权集体制(公司制)、国控混合制(国家控股的公司制)、非国控集体制(非国家控股的公司制)等等,就难以解读“苏联制度”与“美国制度”,都是走向马克思所预言“社会公有制”的可能过渡技术方案。如不把“共产党人”指意为“自觉无产阶级(共产主义者)”,就难以解读清楚“工人阶级(穷人)中有被迫无产阶级”、“工人阶级参政、无产阶级执政、无产阶级专政”等概念相关问题。
其二,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凝练中,依科学原则研究理论架构。尽管“苏联版”存在许多问题,但它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括之上的体系建构;尽管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也不失可借鉴的观点,但它们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个别角度或个别理论的“管窥”。学术性“解构”是必要的,但不做宏大叙事的“建构”是不能解决根本问题的。须在科学原则下,如同从牛顿、达尔文文献中凝练出基本原理那样,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文献中凝练出一组基本原理组成的有机结构体系。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只有一部”的整体性研究,不能停滞于“实践马克思主义、生态马克思主义、市场马克思主义等等”管窥性马克思主义解读。就是说,科学原则下,对待牛顿、达尔文著作不能如对待“圣经”那般引章摘句地使用,对待马克思著作也不能。
其三,在马克思主义具体应用中,依科学原则坚持其科学普适性。马克思依科学原则建构的理论体系,必然具有科学普适性;在马克思主义面前无例外,也必然适用于对美国社会历史、现实、未来的解读。只要理解了现代公司制、税收制(遗产税、房产税、消费税等)、普选制、发行纸币权、国债、赤字财政、高福利制、强势工会等等方面变化实质,就会看到美国制度也许没达到“社会主义制度”初级标准,但美国社会也已经按马克思所指道路步步前行。至于中国(发展中国家代表)、美国(发达国家代表)在技术方案上的“同向性差异”,是由于现实的“社会生产力(人均)”水平不同,其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现实水平不同,即“国情不同”所致。伊拉克、阿富汗、埃及等等发展中国家“仿美国”的惨痛,恰恰力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科学性。把美国设置为“例外”是苏联版的论证思维特点,不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自身局限。遵守科学原则,改变论证思维方法,把美国社会变化纳入马克思主义科学预言“之内”,才能实际获取学术话语权。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76-777页。
④联共(布)中央特设委员会编:《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共中央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390页。

⑥[英]J.D.贝尔纳:《马克思与科学》,《山东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2005年第2期。
⑦[英]戴维·麦克莱伦:《卡尔·马克思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432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8页。


〔责任编辑:吴 明〕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马克思主义科学性与制度自信关系研究”(项目号:14BZX015)的阶段性成果。
吴建国,1965年生,科技哲学博士,南京邮电大学教授,wujg699@126.com。南京,210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