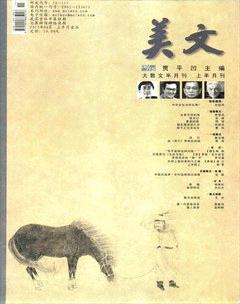君子之交淡如水
曹然


田仲济与吴奔星两先生同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学科的奠基人,数十年间交往密切,被学林传为佳话。近读《田仲济纪念文集》,看到吴奔星先生打鼾的逸闻,发在微博上,不想因此与吴先生公子心海先生相识,田、吴两先生后人都在南京,也是缘分。晚辈惊喜惶恐之余,遂起整理二老交往历史之想法。余生也晚,未曾亲见大师风采,文才又不逮先贤,难以描摹二公友谊之深厚,实在惭愧。
田先生与吴先生有着极为相似的家庭背景。1907年,田仲济出生于山东潍县(今潍坊市),父亲是一名私塾老师。六年后,吴奔星出生在湖南安化吴家湾,他的父母都在一所教会小学教书。田仲济与吴奔星不仅同为小知识分子家庭出身,且都受到了新式小学教育,还目睹了同样的社会黑暗——田仲济九岁时,幼弟芸宽患疑难病症,由于无力延请名医,更无条件去外地大医院诊治,最后死去,状态令人痛心。田仲济目睹弟弟的惨状,深受刺激。十七年后,刚考入北平师范大学国文系的吴奔星也遭遇了大哥兰阶在家乡为庸医所害而去世的不幸,这种伤痛很快就反映在了他当时的诗歌中。
上世纪三十年代初,还在上海中国公学读书的田仲济刚与张鹤眺、李竹如、胡也频等左翼作家相识,聆听了冯雪峰关于文学的讲话;吴奔星则在北师大的风雨操场被鲁迅的演讲所震撼。1936年,吴奔星在北平创立《小雅》诗刊,提出了“国防诗歌”的口号,一时间名满文坛。同时期,田仲济在济南创办《青年文化》半月刊,用鲁迅风的杂文参与了左翼文学运动。抗战爆发后,两人都辗转大后方。田仲济在重庆的中国乡村建设学院任教,出版了《发微集》《情虚集》等杂文集;吴奔星先后在桂林师范学院、贵阳师范学院任教,抗战末期也到陪都,出版了《雾霭》《春焰》等诗集。如吴奔星所言,他们都是“在新文学的哺育下成长并将毕生精力奉献给新文学祭坛的虔诚的信仰者”。值得一提的是,田仲济的表妹夫梁宗岱与吴奔星同为现代诗派成员;而且田、吴两先生均与茅盾、臧克家、李何林等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朋友圈交集很多,两人又同为文艺界抗敌协会成员,同在《文艺先锋》等期刊发表文章。我们有理由相信,两位先生此时虽不熟识,但肯定互有耳闻,神交已久,有一面之缘也未可知。
新中国成立后,吴先生曾在武汉大学与南京师范学院任教,后受政治运动冲击,以右派之身发配徐州师范学院,一呆就是二十余年;田先生以齐鲁大学中文系主任的身份,在院系调整时亦受打击,留在了山东师范学院,之后又因为写作杂文受到了种种不公正对待。两位先生虽然都离开了一流学府,并被迫离开了热爱的文学创作事业,但他们并没有就此消沉,反而凭借自身的努力,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不仅开创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这一全新的学科,还让徐州师大、山东师大成为了现代文学研究的重镇,为该学科的发展培养了一批批杰出人才。试问今天的现代文学研究界,谁没受过田仲济、吴奔星等老先生的影响?
自五十年代开始,由于共同的研究方向,以及共同经历的磨难,两位先生开始了密切的交往。笔者并不知晓二人最初相识之时间,或许是五六十年代的教材编写会议上?抑或是两人分别走访老友而得以见面?抑或是有书信往来?田先生旧藏信函,“文革”中悉数被毁,先生不写日记也不愿撰写回忆录,这个问题只能暂时存疑了。
“文革”后,两位先生的交往极为密切,这是学界所共知的。他们共同担任了中国茅盾研究会和《茅盾研究丛书》的顾问,共同参加了《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中国现代文学辞典》等书的审稿工作,共同发起创立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并担任领导职务……他们共事的经历举不胜举,二人的名字常同时出现在各种会议的专家名单上,也同时出现在茅盾、唐弢等先生的纪念文集中。那时,一年中田先生与吴先生见面的次数,怕是比与他子女相见的次数还更多呢!
丁尔纲先生在《王瑶先生与全国首届现代文学学术研讨会》《往事悠悠忆田老》《忆吴奔星先生》等文中提到了吴先生打鼾的趣事。那是1979年1月,现代文学研究学科的奠基人们齐聚北京简陋的东四旅馆,出席《中国现代文学参考资料》审稿会。此时田先生与吴先生已经相识,但田先生或许还不知道吴先生打鼾的威力。那时“创业艰苦”,丁尔纲与二老同居一室,得见“吴老打呼已臻声震屋瓦的高水平”,以至于“田老两夜没睡好”,只好与华忱之先生换屋,“华先生耳背,故与吴先生相安无事”。丁先生受此启发,此后每次办相关研讨会,都将吴、华二老安排在一起,两先生“因此成了关系最密切的会友。”有意思的是,此时吴先生还顶着右派的帽子,“然而他吃得香,睡得甜,开会发言,一切照旧”,而王瑶、田仲济诸先生也不以吴老的右派身份为意,当时还是乍暖还寒时候,老先生们的坦荡是多么难能可贵。
君子之交淡如水,田仲济先生与吴奔星先生交往半个世纪,表达感情却十分含蓄。1993年4月,田仲济杂文研讨会在济南开幕,吴先生因故不能与会,托研究生给田先生带了一本民国二十九年(1940)初版的《新型文艺教程》,还在扉页上写了一句话:“因事不能与会,这本珍藏旧书给田先生做纪念。”当时山东大学马瑞芳教授在场,田先生还得意地问马教授:“你见过我这本书吗?”
别说马教授了,田先生的亲友弟子也多未曾见过这本先生的早期著作。《新型文艺教程》1940年由华中图书公司出版的初版本,田先生自己都没有留存(也许原有,但毁于“文革”)。这本书究竟是吴先生多年旧藏,还是在八九十年代有心淘来,笔者不得而知。该书对田先生意义重大,两位先生的友谊,从中可见一斑。
提到这本《新型文艺教程》,又不能不提到二老共同的挚友李何林先生。李何林与吴奔星是北伐时就一起投入革命洪流的老战友,也是田仲济初入文坛时的伯乐,曾给《新型文艺教程》作序,盛赞该书为第一本用故事的手法和软性的文笔写成的文艺理论和知识书籍。有人说田老是杂文家,吴老是诗人,所以田老比吴老说话更直率尖刻。这是事实,臧克家、臧云远等先生就曾给田先生起过一个“田石头”的外号。不过要论直率,李何老比田老更胜一筹。“文革”甫一结束,李老就大谈三十年代两个口号之争,田老认为“四条汉子”在“文革”中受苦受难,现在旧事重提不适宜,然而李老意志坚决,田老也只能随他的性格去了。田老晚年为艾以主编的《现代作家书信集珍》写了《李何林至田仲济信》的注释,对李老的极强的自尊心有很好的分析。每当我看到田老谈李老自尊的这段文字,就不由得想起长辈们的回忆——田老晚年也是自尊心极强的人,开会走路颤巍巍却坚持不让人扶。无论是李老坚持要和四条汉子“把问题讲清楚”,还是田老在“文革”初期因为直言“四条汉子有错误但绝不是叛徒”而被打倒,他们的观点虽然不同,但性格真是非常相似的。
吴老与李老交往更久,也常有意见相左之时。李何林在《五四时代新文学所受无产阶级思想的影响》一文中讨论鲁迅小说《药》中“乌鸦”之细节,曾引起轩然大波,吴奔星在《文学作品研究》中就对李何林的说法表示了反对。然而吴老对李老的尊重却不因学术之争有半点减损。
君子之交淡如水,田仲济与吴奔星两先生的这段书缘,令笔者想起二老与臧克家先生之间的一些往事。1986年4月,臧克家诗歌研讨会在济南举行,适逢臧老八十大寿,全国学界文坛名流济济一堂,纷纷为臧先生祝寿。然而就在这片祝寿声中,大会主持者田仲济先生发言了:“今天在这里举行的是关于臧克家诗歌的学术研讨会,而不是来给他祝寿只说好话的。大家要以学术研究的态度,对他的诗歌进行实事求是的评价,优长说优长,缺陷说缺陷……”先生此言一出,当时就有人觉得田老太不会说话。然而,同样是在这片祝寿声中,吴奔星先生也没有高声颂寿,反而是对臧老提出了新的期望和良好的祝愿——要知道,同为诗人,吴老直到89岁高龄还在写诗,他是多么热诚地在鼓励臧老坚持创作啊!
在那次研讨会上,田仲济先生的学生吕家乡提交了论文《臧克家的叙事诗、报告长诗和讽刺诗》,“对于所论的作品不满多于肯定”。吕教授当时“真有些惴惴,怕惹得臧老不快”,没想到田先生却告诉他:“臧老看了你的论文,觉得你的看法有道理”,“你对他有批评,还能让他满意,不容易”。1988年,吕家乡到南京参加臧克家顾问、吴奔星主编的《中国新诗鉴赏大辞典》的定稿会议。吕教授以为“自己能够受邀大概是吴奔星先生的照顾”,而吴先生却告诉他:“你不要感谢我,是臧老点名要你来的,臧老说看过你写的几篇论文,你对他的诗有赞扬、有批评,臧老觉得你言之有据、学风踏实!”2000年,已经年过八旬的吴老为《世纪诗星——臧克家传》作序时,在高度评价臧老诗歌成就的同时,依旧坚持鲁迅知人论世的观点,提倡学者“对他(臧克家)一生的业绩作出实事求是的科学评价”。
臧老对于两位老友及吕家乡等晚辈学者的批评鞭策鼓励是无比感激的。1979年,他曾在《甘苦寸心知——关于<罪恶的黑手>》一文中不无夸张地自责道:“学诗五十六年来,长长短短写下的诗,论行数,岂仅三万,谈篇数,何止一千。自己觉得,能经得住时间考验,为别人所记忆、尚可一读的,至多也不过二十首左右。”八十大寿之后,他的创作更为勤奋。他说:”如果人老了,什么都不干,天天计算还有几年活头,这样可能死得更早。即使能长命百岁,整天让人侍候着,当老太爷,这样活着更不如死了。”田老去世之后,臧老在纪念文章《仲济,曾记否》中,还特别提到了那次诗歌研讨会。难怪吴奔星先生说:“我向他(臧克家)学习的不仅是诗品,还有更突出的人品。”老一辈文人的友情,是多么单纯而真挚!
2002年,田仲济先生去世,享年95岁。2004年,吴奔星先生去世,享年91岁。2007年田仲济先生诞辰百年之际,吴老送给田老的初版本《新型文艺教程》被田老后人捐赠给了中国现代文学馆。这本书,和这段友谊,都将永远留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