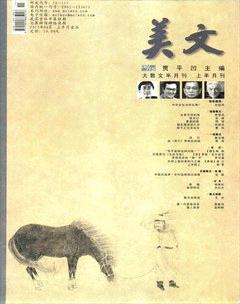不像村庄的村庄
安黎
绿叶争着当红花
威海市位于山东省的最东端。
太阳从东方升起,威海就是距离太阳最近的地方。日复一日,当晨曦泛白,射向中国大地的第一缕金色阳光,总能将威海的街巷镀亮。
150年前,威海只是一个小小的渔村。世代居住于此的渔民,划着小船,撒着渔网,在汹涌澎湃的大海里漂移捕捞,用以繁衍生息。大海是渔民的母亲,也是渔民的敌人——大海以其慷慨任凭渔民随意取舍,也以其凶悍常使渔民身处险境绝境。
沿海城市的繁荣,大都与远洋贸易密切相关,唯威海例外。威海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僻壤之地,摇身变为备受世界瞩目,最初靠的不是漂洋过海的商人,不是洋商品与土特产之间的交易,而是中国海军的成型与沉浮。
如果中国海军是一组恢弘的诗章,那么,第一行的诗句,就在威海吟咏而成。
帮我联络的是诗人北野,给我领路的是诗人李杰。威海的诗歌,比威海的波浪还要汹涌。诗人,并不比渔民寡少。
李杰带我去的第一个村庄,名叫外窑村。
外窑村归环翠区管辖,位于市郊的一面斜坡上,背依城市,面向大海。
外窑村与威海市的市区,间隔一道山梁。山梁的那边,高楼林立,灯红酒绿;山梁的这边,绿树繁茂,清静幽雅。在苍翠的松树簇拥中,外窑村显得格外妩媚亮丽。
一边是喧嚣,一边是静谧;一边在堆积着财富,一边在铺展着绿色,山里山外,别有洞天。
住在哪边会更幸福呢?我在问李杰,也在问自己。
李杰说不清楚,我亦道不明白。
我所知道的是,人总是这山看着那山高,总是在得到了这样的东西后,还想得到那样的东西。但上苍不可能满足人的所有欲望,它故意给人留下些许遗憾,留出某些空白,让人天天去妄想。在鱼和熊掌不能兼得的情况下,就看人更在乎什么,更看中什么。看中的与在乎的,也许才是最重要的。
李杰告诉我,他的表姐家就在外窑村。过去,市区的人要去外窑村,或外窑村的人要去市区,都要翻越一道山梁。弯弯曲曲的盘山小径,宛若一条蜷曲的绳索,缠绕着山脉臃肿的身躯,将两地拴在了一起。外窑村距离城区的直线距离并不远,但在落后的交通条件下,村里人若去一趟市区,一个单程,就得耗费大半天的时间。
前多年,一条宽阔的公路建成通车,使外窑村与市区的距离,缩短了一半。在山梁的腹部,开凿出了一条一眼望不到尽头的石洞,即所谓的隧道。隧道开通后,车来车往,昔日闭塞的外窑村,不再寂寞。据说,一到周末或节假日,市区的人闲得无聊,就来这里游逛。公路边,树底下,草丛间,不但多了纷乱的脚印,而且多了被遗弃的餐纸、餐盒、烟头、塑料袋以及手纸避孕套等。
人是污染的受害者,但同时也是污染之源。
外窑村颠覆了我对村庄的认知与概念。在我固有的记忆里,村庄似乎总是被绿绿的田野包围着,低矮的房舍,窄窄的巷道,苍茫的古树,颓唐的土墙,空阔的碾场,撒欢的牛羊,鸣叫的鸡狗,飘浮的炊烟……浪漫主义的虚脱想象,总能使实实在在的村庄,变得虚幻而朦胧,从而弥漫起一层诗意的薄雾。事实却是,村庄是贫乏的,是困顿的,是脏乱的,是混沌的,得过且过,捉襟见肘,充满了汗腥的气息,充斥着人粪和牛粪的味道。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只封存于泛黄的纸张里,而在现实中压根儿就寻觅不到。
外窑村名为一个村庄,但名不副实,实则为一座小区,只是这座小区没有置身于熙熙攘攘的闹市中,更像是一个隐者,游移于世态之外,离群索居,形单影只。
一栋一栋的六层楼房,沿着缓慢的坡地梯级修建,给人以层叠错落之感。黄漆涂墙,红瓦覆顶。背后的山坡,翠绿繁茂,面前的大海,蔚蓝无际。妩媚的小区仿佛一幅斑斓的油画,悬挂于半山腰中。
小区内的环境也格外典雅优美。六角形的石亭,大理石铺就的休闲空地,一排排的冬青蓬勃着嫩嫩的黄芽,一簇簇的花朵在微风里轻轻摇曳。居民楼显得颇有档次,就连楼梯,也一律律为石板铺就。
在山东游走,我发现很多很多办公楼与居民楼的楼梯,都铺着打磨得光溜溜的石板。从事建筑业的朋友曾对我说过,山东的石材闻名遐迩。石板楼梯,无疑印证了朋友的这一说辞。
但转眼一想,我又颇为纳闷:山东省的省名里,有一个“山”字,其意是不是想证明山东多山呢?我的地理知识极其有限,却也知道,山东的山算不上有多么的多,相反,比起其他省份,它的山脉甚为稀廖。山东是典型的平原省份,其平原总面积,在全国至少能排至前三位。一个缺山的省份,却以石材闻名,令人甚觉奇怪。墙面上的每一块砌石,地面上的每一块铺石,楼梯上的每一块卧石,没有一块是从天而降的陨石,毫无疑问,它们均来自于大山的腹部。环保专家算过这样一笔账:从山里取出一立方米的成型石材,就会使六立方米的山体遭殃。如此计算,每一栋高楼所用的石材,会使多大面积的山体开膛破肚呢?中国有多少座楼房,多少座广场,多少条街道,敢汇总吗?石头不是庄稼,今年收割了,明年继续春播秋收。石头是地球的细胞,属于一次性资源,消耗掉了,就永不复生。
楼房的气派,广场的阔绰,酒店的奢华,街道的光洁,无不建立在对山体大规模破坏之上的。山体一经开凿,一经破败,一经消失,气候随之产生异常,最终自食苦果的,还是人。人的贪婪,人的物欲,是挖给自己的坟墓。对物欲的追逐,对大自然的无尽索取,自以为是在酿造蜜汁,殊不知是在酿造毒液。
鼎盛的石材业,真该冷却冷却了——别再干那种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蠢事了!
过去,外窑村既是农村,又是渔村。1985年之前,村里拥有耕地300余亩,碾打的粮食能够自给自足。1985年之后,依照国家政策,丘陵地带以及坡度大于15度的坡地,一律退耕还林。于是外窑村就在坡地里,不再种植小麦和玉米,而是栽上了松树,并保留了少量的苹果林。
村民们手持一个农业户口本,但大部分人,再也不耕不种,不稼不穑。有人干建筑活,有人干个体经营,有人在镇办企业里上班,有人自己创业当老板。当然,还有少数人或在田里耕耘,或在海里捕捞。未被林木覆盖的田地既不平坦,也不肥沃,大多为沙石地。一畦畦的薄田,像一绺绺的布条,或一方方的手绢,晾晒于山岔里,遗落在斜坡间。倒是大海,苍茫无际,似乎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但近些年,海里虚脱了,没有了鱼,村里的渔船,已由过去的上百艘,猛然缩减为了目前的6艘。仅有的6艘船,如果单凭打渔收入,百分之百地亏损。那么,它们为何还要出海,为何还要漂浮于海面之上呢?其答案,则和我们在莱州了解到情况相类似,那就是寄望于国家的补贴。根据马力大小,国家给予每艘船一定数额的补贴,这些补贴,俨然成了渔民下海打渔的动力所在。
村支书兼村长夏斌说:6艘船中,有两艘350马力的大船。只有这两艘大船,还在兢兢业业地从事着捕捞。近海无鱼,就去远海。一出海,短则一星期,长则半个月。
夏斌又说:鱼很聪明,连海里的国界线都能辨识清楚。中国渔民的滥捕滥杀,鱼心知肚明。鱼越是稀少,渔民越是下手狠;渔民越是下手狠,鱼越是稀少。如此这般,构成了一个无法扭转的恶性循环。于是在大海里,鱼就和渔民们进行着猫捉老鼠的游戏。你追我跑,你退我往。中国的很多渔船时常游弋于中国海域和韩国海域的交界处,渔民们惊奇地发现,同一个大海,中国这边空空如也,而韩国那边却密密匝匝。鱼挤在韩国的海里,死活不肯到中国的海域来。当然,若发现中国的渔船遥遥远去,也会偷游到中国的海里来觅食。但一经发现中国的船只驶来,宛若摆摊的小贩远远地望见了城管的身影,鱼便慌不择路,箭一般地向韩国海域逃窜。
夏斌坐在某栋楼一层的单元房里,给我讲述着捕鱼,也讲述着外窑村的现状。
夏斌高个,身材颀长,脸庞红彤彤的。他生于1967年,威海一中毕业。
在江苏某大学当老师的同学回到威海,昨天中午,威海当地的同学聚在一起,招待这位从远方归来的同学。餐桌上,夏斌请他们饮的是矿泉水,滴酒未沾。
夏斌讲这些的意思,在于告诉我,他在严格地执行着山东省不许饮酒的有关规定。
夏斌读完高中后,回到村子,在一家村办建筑企业里当临时工,先后当过钳工、翻砂工、会计等。
1998年第一次村委会直选,他被选为村委委员。那时,村委会由五人组成。2001年再次选举,村委会缩至三人,夏斌退出。2007年,夏斌又一次被选为村委委员。2011年,他当选为村委会主任。
选举采用的办法为“两推一选”。“两推”,指的是“群众推”和“党员推”,即群众每户派出一名代表,代表本户投票推选出三名村委会主任候选人,党员则推选出三名支部书记的候选人。
外窑村共有1046位村民,常住人口870人,选民707人。正式选举那天,村民被几辆大轿车拉往不远处的海军大礼堂,进行正式投票。
选票上排列着四名候选人,从中选出一个主任,一个副主任,一个委员。选举采取不记名的方式,秘密填票,当场唱票,全程录像。区党委政工书记主持会议,派出所派出警察维持秩序。
一般而言,村委会选举在先,支部选举在后。支部的人选,需要等到村委会选举的结果出来之后才能定夺。村委会主任,是当然的支部书记。书记与主任必须一肩挑,这是山东省依据自身实际制定的“土政策”。
夏斌在村民选举和党员选举中,双双获胜,他成为支书兼村委会主任的不二人选。
夏斌的当选,得益于老支书的提携。老支书1950年出生,已年过六旬。老支书往支书的位置上一坐,就是20多年。夏斌任村委委员时,其实际角色,就是支书的秘书。秘书的日常工作,是替支书记跑腿写材料。
夏斌说:自己参选,未花一分钱。
夏斌的竞争对手很有实力。他1958年出生,比夏斌大了10多岁。1998年基层选举之前,在好多年里,他都担任着村委会主任。1998年由于山东省实行了支书与主任一肩挑的政策,他被迫降格成了村委会副主任。与夏斌同台竞选时,他还是时任的支部副书记。也就是说,这次选举,是村上的支部副书记和秘书之间的擂台赛。
夏斌的对手,仿佛命中注定只能在村里担任二把手似的。但他不信命,不服气,并不甘于永当绿叶,而是一心一意地想成为一朵红花。
提起这位对手,夏斌眉头紧锁,感叹道:别人也竞选,但竞选之后,对手变成了合作伙伴,所有人都得服从结果。但我们就不一样了。你和他竞争过,你就成了他的死敌。他天天都在挑战你,故意给你使绊子,处处抓你的把柄,想方设法要整倒你,你咋工作呀?
外窑村的人以夏姓为主。夏斌当选,一是得益于老书记的竭力举荐,二是得益于“自己人”众多。除了本族人的支持,夏斌在村子里也有不少亲戚,他的外公家就在本村。也就是说,他母亲的娘家人,都站在了他的身后。他的一个姐姐,也嫁给了本村。姐夫及姐夫的家人等,都转化成了他的人脉资源。外公在村中也有亲戚,姐夫在村中也有亲戚,亲戚套亲戚,于是,村中近乎一半的人,念及亲情,都成了他的票源。然而,他的对手并不比他弱多少。对手的岳父家,也在这个村子。对手的3个姐姐,也是肥水不流外人田,全都嫁给了本村。对手的岳父与姐姐,在村子里也有不少亲戚。于是,各自的亲戚们分列两个方阵,组成了立场鲜明的两个阵营。
夏斌当选后,深感村里的一把手并不是那么好当的。羁绊盘根,矛盾错节,村上的诸多事务,他都无法做主。
2008年,在老支书执政期间,村里原有的房屋被拆除,取而代之的,是这座花园般的漂亮小区。房子分给村民,入住了好几年,一直相安无事。但在夏斌接任支书村长后,住在顶层的数户村民,却反映起了房子存在漏水以及设计不合理等问题。申诉房屋质量缺陷的领头人,即为竞选落败者的姐姐。其姐姐组织了一帮自己的亲戚,去镇上上访,其中的一个诉求,就是应将顶层住户的房价降下来,把过去所缴纳的一部分房钱退还给业主。镇领导对小区的状况知根知底,因此,面对气势汹汹的上访者,他们应对自如。
镇领导说:退款可以,但你们得把属于你们家的阁楼,用水泥封死,不许以后再使用。
顶层住户的屋顶上,都耸立着一座阁楼。阁楼的室内面积约10平方米,产权归住户所有。分房时,阁楼属于免费赠予,依照房价计算,等于少收了每户5万元。仅阁楼一项,村上就给村民让利了200多万。
上访不了了之,但留给夏斌的心理阴影,却久久地挥之不去。
夏斌说上访是“醉翁之意不在酒”,那些人的真实目的,无非是想抹黑自己,为下届的选举鸣锣开道。
夏斌感叹:每次选举,都是一场硬仗。
外窑村现在拥有三家企业,一家名叫新港机械厂,另外两家是建筑企业。企业全都不怎么景气,个个半死不活的。新港机械厂规模很大,负担很重,单土地使用税,就是一笔不小的数目。每平方米缴纳8元,一亩地年需缴纳5千多元。
土地使用税,对我这样一个孤陋寡闻的人来说,还是第一次听说。
问起村民的福利情况,夏斌告诉我:20世纪80年代,外窑村就开始向村民发放福利,那时候,每位村民每年可以从村里领取50元钱。2009年之前,村里向年长的村民发放退休金,60岁以上的男性可领取2600元,女性可领取2400元。2009年之后,村民被全部纳入社保体系,65岁以上的男性和60岁以上的女性,每人需一次性地缴纳5万余元,村上负担一半,个人负担一半。如此,73岁的老人,每月便可领取1600元左右的养老金。45岁至60岁的男性和35岁至50岁的女性所缴纳的统筹金,也是二一添作五,村里和个人各缴纳一半。
村里的钱从何而来?
夏斌告诉我:资金的来源有多种渠道,有的来自于旧村改造的土地出让金,每亩8万元;有的来自于向邻村开发商的借贷——共贷了1500万,年息15%。仅每年的利息,就高达225万。向开发商还贷,采取了以物抵押的形式。村上把建好的两栋别墅,划拨给了开发商,以此来抵消开发商的贷款。
收了百元就“叛变”了
从外窑村回到市区,我参观了卧龙山书院。
卧龙山书院的院长,即为李杰。名誉院长,则由邵力华和北野担任。
书院位于一座小山的半山腰,与市区若即若离。喧嚣近在咫尺,但书院却躲于一隅,独享清静。一座小院,几间仿古建筑,翠竹点缀其间,别为雅致。书房内,字画满墙,宣纸铺案,墨汁飘香。仵从巨、刘家相、孙基林、高泉、苏更等,一批威海文艺界的名流的名字和照片,浮现于镜框之中的“特别顾问”和“顾问”一栏里。
书院占用的是李杰所在村的地盘,它与村委会相互连接,又独立成篇。
李杰的母亲——一个年过六旬的老太太,村妇联主任——坐在村委会办公室的连椅上,一副气定神闲的模样。办公室里,坐着五个年龄较大的男性,皆为村干部,其中挨门处,一个戴着老花镜的人坐在一张桌子后面,时而斜睨着我,时而心不在焉地盯着报纸。
李杰本为诗人,创办这家书院,昭示着他对艺术还怀有更大的雄心。
李杰接下来带我去的地方,是一个名叫戚家钦的村子。戚家钦村位于市区之内,满眼望去,只见楼房林立,不见庄稼蓬勃。
银行、超市、邮局、中学、医院、商贸市场等,遍布戚家钦的村里村外。村子现有居民312户,总人口758人。
戚家钦村归属于威海市高技术产业开发区怡园街道办事处,它的村部,是一栋五层楼房,楼外的出入口,挂了许多牌子,其中的一个牌子上,竖排着“戚家钦村居民委员会”的字样。
戚家钦村现任支书兼村委会主任名叫苗华庆,1964年生人。苗华庆的长相,有点儿像南方人,小巧玲珑的五官,小巧玲珑的骨架,与所谓“山东大汉”谬之千里。他的头部呈扁圆形,面色则宛若海边的砂石那般殷红。
戚家钦村的村委会,比较特别。自1947年新政权诞生,其领导班子,只经历了4次变动。1947年至1958年,为第一届;1958年至1991年,为第二届;1991年至1998年,为第三届;1998年至我采访时的2013年,为第四届。
苗华庆22岁时入党,23岁当上了村里的团支部书记。有意思的是,他当团委书记时,并不是一名团员——他从未加入过团组织。
苗华庆是1998年走上戚家钦村的领导岗位的。据苗华庆讲,他的前任很公正,很廉洁,只是负责村务时间过长,便对其有点儿厌倦,有几分腻味,于是经常性地提出要辞职。
苗华庆1981年高中毕业后,从未离开过村庄,先是在田里干农活,后在村办维修厂当修理工。在维修厂,他一干就是14年。1994年年底,他被他的前任赏识,抽调到村部,负责分管财务和工业。那时候,村上有八家企业。他一走马上任,就大刀阔斧地对企业进行了严厉整肃,一口气换掉了三家企业的负责人,在赢得掌声的同时,也得罪了一大批人。1998年,在实行村级选举之前,他有意参与竞选,却清晰地意识到自己已步入了一条死胡同,横在前面的,是一道一道严严实实的高墙。他得罪的三位厂长,每个人都不是孤立的个体,而是蜘蛛网中的一个枢纽。枢纽悸动一下,整个蜘蛛网都会颤抖。
三个被罢免的厂长,无疑都已成了他的死对头。三个死对头振臂一呼,半个村的人都会成为他的反对者,他若参选,可以预见的是,胜选的概率几乎为零。
那一年,34岁的苗华庆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内心极为郁闷。有人想见他,他躲着不见;有人给他打传呼,他装聋作哑不回复。他把自己隐匿了起来,苦思冥想着新的出口与出路。在迷惘彷徨之际,老支书找到他,安抚性地对他说:给你一个公司,你去当总经理吧!
在赴公司履职的前夕,老支书改变了主意,又找他谈话,让他接任村支书一职。
老支书是地地道道的戚家钦村人,却非地地道道的农民,而是乡工业办的工作人员。老支书回村上掌舵,那是受之于乡上的委派,而此时,他已66岁。
老支书的辞职申请得到了上级的批准,去意已决,却一直没有物色到中意的接班人。在无人接力的状况下,他不得不暂时滞留于村里,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急于脱身,又脱不了身,因急上火,在长达三个月的时间里,老支书的嗓子一直发炎,竟至于哑口无言,发不出一丝声来。
老支书唯一相中的人,就是苗华庆。老支书劝苗华庆接任,而苗华庆却犹豫不决。老支书说:我年龄这么大了,回到乡上,乡上还能给我安排一份轻松的工作,老来好有个依靠。这样耗在村上,连养老金都会耗掉的,这可咋整呀?老牛拉不动载重车,我这把老骨头,已没有力气拉动戚家钦了。
看到老支书期待的眼神,苗华庆咬了咬牙,然后点头道:行吧,那我就试一试!
老支书叮咛他:你当了支书,支部要团结。不团结,最终伤害的还是老百姓。
支部选举,30名党员,苗华庆得了28票。
苗华庆未给自己投票,如此算来,只有一位党员对他投了不赞成票。
苗华庆顺利地接过了老支书肩上的担子。
老支书是个老好人,一遇矛盾就回避,习惯于和稀泥。这样做的结果,反而使矛盾越积越多,越淀越厚。
有人劝苗华庆向老支书学习,做一个滑头,并说要当好一名村干部,上上策是“脚踩西瓜皮,手抓两把泥,能溜就溜,能抹就抹”。
但苗华庆天生就是一个急脾气,这从他说话的语速上能感受得到——他说起话来,快言快语,很像打机关枪——他一改老支书的工作方式,由和风细雨的按摩式,变为雷厉风行的手术式。
一届支书干下来,苗华庆焦头烂额,不愿再继续了。
新一届选举,山东省的政策发生了变化,不再实行书记与村委会主任相分离的办法,改为了书记与村长一肩挑。
也就是说,要当支部书记,就必须当村委会主任;要当村委会主任,还必须先当上支部书记。
支部书记的当选相对容易,因为那是在党员中进行选举;但当村委会主任,则必须直面村里的每一位村民。村民远没有党员那样好对付,他们的个性脾气以及利益诉求等,各有千秋,要顺利当选,并非易事。
在陡峭的山崖面前,苗华庆打起了退堂鼓。父亲和妻子纷纷劝他放弃,说村里人多嘴杂,出力流汗未必能落好;并说你如果拿出给村里干事劲头的一半,退回家中过自己的小日子,还能愁自家的日子不好过?
但也有不少人跑来劝他,让他竞选村委会主任。
几度摇摆之后,他还是报名参选了。
竞争者有好几位,个个志在必得,不计成本地疯狂拉票。然而,拉票过度,却适得其反,反倒容易引起村民的心理不适。
某位竞选者给村中的一位妇女送去一张银行卡,卡上存有一千元钱。那位妇女甩手不要,并冲着竞选者数落:我老头死了那么大的事,也未见你到我家里来,哪怕来给我说一句安慰的话也行啊!一投票,你咋就想起我来了?你的卡,我是不会要的!
别人在拉票,苗华庆却无动于衷。关心他的人,无不为他的漠然态度而着急。他和一帮朋友在饭店里聚餐,有人诘问他为何不拉票,难道是坐等着自己出局吗?苗华庆回答说:我拉票都拉了三年了!我这三年里所干的事,就是在为自己拉选票。
苗华庆对选举有着较为清醒的认识,他说:既然选举,就会有赞成票,也会有反对票。支持与赞成,都是选民的权利。一个国家的元首,得票率如果是百分之百,这个国家肯定不正常;如果一个村长的得票率是百分之百,那么这个村子肯定不正常。
这次竞选,前来投票的村民,挤满了村部的院落。
会场一片嘈杂,坐在小矮凳上的村民,神态各异,有人扭嘴,有人瞪眼,有人拍腿,有人吹口哨,他们以各自不同的方式,故意嘲弄自己排斥的竞选者。
现场有人喊:苗华庆,我给你投票,你可要给我办事啊!
苗华庆回应道:我如果当选,我在这里承诺,将全心全意为每一位村民办事。
苗华庆一家是村里的独家户,没有本家。村里以戚姓、陶姓和谷姓为主,兼有其他姓氏。三大姓氏相互抵触,相互挤兑,相互提防,你抱我的腿,我拽你的胳膊,你拆我的台,我挖你的墙脚,活生生地上演着现实版的“三国演义”……互斗的结果,反而使单打独奏的苗华庆“渔翁得利”。苗华庆尽管不能令所有人满意,但大多数人对他的当选,尚且能够接受。
可以想象,任何一个大姓的代言人当选,村里都不会那么安宁温馨。落选的两大姓,绝对不会让胜选者那么轻而易举地摘取桃子。恰恰是苗华庆,平衡了村里潜伏的矛盾,使选举前海浪般咆哮的村庄,海潮退却,祥和平静。
苗华庆最终当选,连他自己都不相信。
苗华庆现在的年薪是10万元。
但他说,从1998年至今,他只从村里领取到25万元的工资。平均下来,一年大约1万7千元。
苗华庆胜任村委会主任后,正值戚家钦由农村向城市的转型期。他的政绩,主要集中在能看得见的楼宇上。
村里贷款两千万元,与三个开发商并肩携手,共同开发。村里出地,开发商出钱。村里占有35%的股份,开发商占有65%的股份,合作建设村民小区以及商业与公益等配套设施。村民居住的小区,楼房已排排耸立,人均居住面积达50平方米。门面房建好后,作为村上的固定资产,对外招租,租金与开发商按比例分成。村里的厂房,也以每年三四十万元的价格,出租了出去。村里建起了公园,向村民免费开放;建起了老年公寓,供孤寡老人免费居住。耕地与水塘原有600余亩,以种粮食、栽果树和养鱼为主,但现在,已缩减至60余亩。每逢中国传统四大节日——春节、端午节、中秋节和重阳节——村里都会向村民发放米面油等物。所有村民,都参加了城镇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村里承担缴纳费用的70%,村民承担30%。对于考上大学的学生,悉数予以奖励,考上一本的奖励1万元,考上二本的奖励4千元。主要劳动力早已与耕种不沾边了,而是或打工,或开商店,或跑运输,或游手好闲。
我问:村里有这么多的资金积累,你如何能控制住自己,不将双手伸向集体的保险柜呢?
苗华庆给我讲起了故事。确实有村民给他送来烟酒,他不好意思当面回绝,就暂且收下了;但过了几天,他会买上一些别的东西,给那位村民送去。有一位老太太,姑娘在上海读书,为迁户口之事,苗华庆与派出所进行了反复协调,最终使老太太如愿以偿。为感激他,老太太怀揣一包5元钱的将军烟,蹑手蹑脚地敲开他办公室的门,将烟硬要塞给了他。他不要,老太太很是着急,说你赶快装起来,小心人家看见了。
在村民会上,他对村民们讲:你们以为我不爱钱?我也爱,但怕被抓去坐牢!那样的话,不但我自己将毁于一旦,而且还会连累到我的父母和兄弟姐妹。
苗华庆继续说:选举那会儿,有党员收了竞选者的一百元钱,就改变了立场,将票投给了送他钱的人,我知道后,就在会上讲这件事,说你一个共产党员,竟然这么不坚强,一百元就叛变了!
苗华庆是家里的老大,还有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父亲是退休工人,母亲是农民。他说他当村干部,要做到四个字,那就是“顶天立地”。上级为天,百姓为地。不顶天,天会塌下来砸死你;不立地,地会塌陷要你的命。天和地,都得敬奉好!
(《中国式选举——农村选举状况调查》一书,将由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