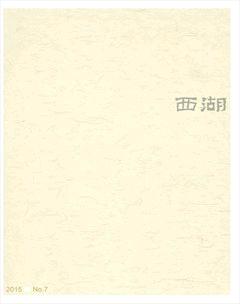“散文是对时代的全息观察和反映”
杨献平+姜广平
关于杨献平:
杨献平,河北沙河人,1973年生。1991年12月入伍至巴丹吉林沙漠,1998年—2000年为空军政治学院三系十三队学员。2011年调成都军区政治部文艺创作室。从1995年开始,先后在《天涯》、《人民文学》、《大家》、《中国作家》、《山花》、《诗刊》、《青年文学》、《芙蓉》、《啄木鸟》等期刊发表大量诗歌、散文、小说和文学批评作品。先后获得第三届冰心散文奖单篇作品奖、全军文艺优秀作品奖、首届林语堂散文奖、“在场主义散文奖”等数十项。已出版《沙漠之书》、《匈奴帝国》、《生死故乡》等十多部个人作品集和长篇小说,并主编《笔尖下的西藏》及《散文中国》系列书籍近三十部。其中,《沙漠之书》进入第六届鲁迅文学奖散文随笔奖评选前二十名。《生死故乡》出版后,在国内引起一定反响。现为中国作协会员,成都军区政治部文艺创作室专业作家。
导语:
有论者认为:杨献平的原生态散文最能打动人的地方在两个方面,一是独特而率性的文字细述,一是巨大的想象磁场和深邃的时空深广度。这些文字带着一股浓浓的青草味道,有着金属的质感,又有种让你无法抗拒的悦目与清朗。它们仿佛不事雕琢,浑然天成,看似粗粝,实则精细,宛若绚烂之后归于平淡的野花。这些文字的野花,生长在巴丹吉林沙漠,生长在太行深处的莲花谷,生长在万物生灵的最低处——即使这最低处的呈现,也依然有一种内在的到达。在缺乏浪漫想象力的时代,他的文本很好地诠释了什么是人类童年里的想象。
杨献平认为,散文是个人的一种姿态。当代散文已逐渐由九十年代到二十一世纪初期的“受关注”、“异军突起”转向边缘化、冷漠化,形成了远远落后于小说诗歌的一个相对冷僻的文学门类。杨献平认为,根本原因是散文写作者在求新的道路上矫枉过正,在自我审察与“惊醒”的过程中过于迟钝与麻木,并且以此来作为区分“族类”的基本杠杆,使得散文写作日益成为“一群人的剧场”,自我封闭,自我“过滤”得过于严密,而导致了新散文写作发展的难以为继。
一
姜广平(以下简称姜):我们还是先说原生态散文吧。这似乎是你的标签,重要标签。你也是这个流派下的标志性作家。虽然我看到你在书上说,你不愿意站到某个旗帜下,也不愿意被归类。但至少,你是散文原生态的首倡者。
杨献平(以下简称杨):关于“原生态散文”这个主张和提法,它有个背景。即,2000年到2006年左右,整个中国的散文写作一方面求新求异,另一方面追求形式、语言等各个层面的创新,基本上沦入了“向内转”、“玄怪异”的窠臼。在这样的一个氛围和环境当中,我想到的是,散文一方面是需要回到现实生活和我们这个时代的现场。这里面的问题是,我们的文学一直是滞后于时代本质的。这当然和文学需要沉淀的自身规律有关,更和写作者参悟时代本质的能力有关。另一方面,散文这一文体因其敞开性与大众性,它更应当去链接大地人群、生存烟火与精神灵魂,不应当把一个最具有普世意义的文体搞成“个人的精神宫殿”和“一群人的内宇宙解剖和展露”。基于这样的一个思考,仓促之间,提出了“原生态散文”这一理念。
其实,“原生态散文”与其说是理念,不如说是主张;与其说是另立流派和旗帜,不如说是对当时整个散文写作的一个呼吁。当然,说校正我觉得也可以。但是,一个毫无力量和“资源”的写作者,做这样的事情,是对批评家的僭越,也是自不量力的。幸亏,有一些朋友支持,我们一起在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原生态:散文十三家》一书。为了证实或者说呼吁,更为了引起一些注意,我为该书写了一篇万余字的后记,明确提出,散文应当具备“大地原声与现场精神,人间烟火与众生关怀”的品质。其实这几个关键词,也不是我首创,古人早就说到了这层意思。所幸的是,这本书在散文界还是引起了一定的关注。汪政、张清华、何平等批评家在对话中也提到了这本书,尤其是“原生态散文”这一主张。
姜:你当初为什么提出这样的文学概念呢?就“大地原声与现场精神,人间烟火与众生关怀”而言,其实所有文学种类都应该有着这样的理念啊!
杨:正如你所说,这个理念不仅是散文的,也是艺术的根本之道。我个人观察,这些年来,我们向西方学习得太久也太多了,到现在都没停止。甚至,我们的文艺与西方同步的能力远远超出了对自身传统的承继。艺术上的借鉴和兼容是非常必要的,也是通往巅峰与大师的必由之路;但过分地去摈弃一个东西,张扬一个东西,往往会畸形。尤其是在汉语这个特殊语境和文学传统当中,我们自身很多东西被我们自己割裂了,丢弃了,这也是一味“拿来”带来的负面效应。关于“大地原声与现场精神,人间烟火和众生关怀”,这一理念不仅深植于我们传统文学的血脉,也是文学的本质所在。重新提出和张扬这样一个理念,一是基于当时的散文写作氛围。这一点上面已有解释。二是强调回归传统。所幸的是,大致从2006年开始,中国的散文整体性地回到了传统甚至时代现场来了。这一点有目共睹。抒情、变异性的书写与呈现,怪癖和过度审丑的书写从大面积涌起到自觉地撤离,相信身在散文场中的人也是有所觉察的。
姜:现在,原生态散文的状态,与原生态散文刚刚提出伊始的状态相比,有了哪些变化呢?
杨:“原生态散文”从一开始就不排斥散文任何层面上的创新和想象力,尤其是采取多种方式发现和呈现当下时代之本质的高强度的“试验”与“创造”。“原生态散文”也绝不直接模仿和照搬现实生活,成为现实生活及其场景的“纸上陈列”。但是,最初的原生态散文,很多在文学的典型性和艺术性上做得不够,或者不够精致和独到。这也是一个问题。2006年之后,中国散文可以说整体性地回到了生活现场和时代现场,出现了不少好的作品。从这一点上来说,我觉得自己的直觉或者预言能力还是可以的。但对于“原生态散文”这个提法,我宁愿它从来没有过。因为,一切标签对于文学本身来说,都是毫无价值的。我愿意“原生态散文”的主张能成为一个共识,这个共识就是以才华和思想,能够真正书写并且建立起迥然相异于此前任何时代的、专属于我们这一时代的文学“万峰耸峙”与“江河并流”。
姜:新时期以来,散文也经历了很多发展与变化。什么新散文啦,文化散文啦,大散文啦,“在场主义”散文啦,这一点跟早先的小说界差不多。世纪之交,继先锋文学之后,小说界倒是一茬一茬的流派。现在的小说界倒是不再有什么提法了。散文流派其实倒是古已有之,与小说相比,散文更是文学正统。但当下谈散文流派的意义何在?
杨:中国散文有两个高峰,第一是司马迁的《史记》,它是史传,其实融合和调动了所有的文学经验和技术,当然,重要的还是司马迁那颗思接千载、承当万世的勇气和雄心,襟怀与思想。《史记》所开启的文学传统和文学精神,我觉得至今还是中国文学的一个标杆和参照。第二个是鲁迅、胡适这些人的启蒙主义写作和新白话文运动。前者是古代散文乃至文学的一个制高点和丰碑,它引领了数千年的史学传统和文学道统;后者则是开启民智,以文学方式介入大众,并以此推动现代主义和人文精神的由精英向泛众的深入,这是两个时代的不同处。但是两者之间的关系始终是相互衔接的,并没有因为时代巨变而断裂。
姜:严格地说,中国散文其实出现了四个高峰,一是先秦诸子时期灿若星辰的大师与先贤们的杰作,二是唐宋八大家,其后是晚明小品,再接着是五四时期。
杨:撇开一段时期的散文不谈,进入新时期以来,散文的发展尤其是出现新的迹象和气象,变化和新鲜,这要归功于小说家;如张承志、史铁生、张炜、贾平凹,以及周涛、马丽华等诗人,余秋雨等学者,以及林非、王宗仁等一些散文家的共同努力,才使得散文从模式化的散文写作中解脱出来。如果将这一功绩全部移植到后来的“新散文运动”那寥寥几个散文家头上,我觉得是有失公允的。关于这一点,我很多次讲过,也和几个大学做散文研究的朋友讨论过。我觉得这个说法非常荒谬,遵从者完全是毫无主见。后来的新散文运动,周晓枫、冯秋子、张锐锋、祝勇,包括并没有加入此行列,但已经非常不错的散文家和诗人钟鸣等人,这些人对散文的再度解放与创新做了前所未有的努力,尤其是他们的“实验”精神与“挣脱”、“自立”的非凡勇气和诸多“有声色”的“实践产品”,都是可圈可点,值得尊敬的。
姜:你如何看余秋雨的散文?
杨:余秋雨近年来招人烦,但他的《文化苦旅》一书对散文的再次“解放”和“拓展”功不可没。后来的散文流派还有“后散文”。谢大光做过一套以此命名的丛书。再就是陕西诗人和散文家黄海的“原散文”和我的“原生态散文”。其实我很赞赏“原散文”这个理念,它很科学,有理论可以支撑。周闻道的“在场主义”我起初不认同,觉得没有科学性和可阐释性的理论。他们开始做的时候,我也看过他们的相关理论文章,觉得不靠谱。也不参与他们的任何活动和评奖。六年后,我忽然明白,周闻道、张生全、沈荣均等眉山散文家们其实在做一件给散文“长脸”的事情,那就是,以民间的名义,设立一个大奖,这对于提升散文的地位、激发散文写作者的雄心,是非常有益的。2014年,与周闻道兄见面细聊,对于散文,我俩有一个共识,当前的散文写作,就是要调集各种手段、智力和能力书写我们这个时代及其各种生活和精神现场,进而深刻反映“此时我在”这一文学命题,这一点,应当成为散文作家的一个自觉的“使命”和发力的要点。
姜:你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谈到体制散文。最近评论家何平谈及上世纪的先锋文学,也用了“国家计划”背景下的“被设计的先锋文学”这样的说法,倒也是意味深长的。但什么是体制散文呢?什么又是非体制散文?散文的生态性,或者文学的本体性,可以被什么体制与非体制界定吗?
杨:散文没有体制和不体制的说法。那时候觉得,不在体制内就相对无拘无束一些,作品也自由主义一些。但事实上,文学没有体制不体制那一说,文学可能会受到体制的影响,但体制决不是限制文学的“千斤坠”。有一段时间,我想,如果一个写作者不考虑到发表,有藏诸名山、传之后世的淡泊,不那么在乎当世名利的话,体制还有效吗?这一点,杨显惠先生可能是目前国内唯一一人。他的《夹边沟纪事》、《定西孤儿院纪事》、《甘南纪事》肯定是会留下来的作品,而且价值也会越来越高。因此,体制内外的说法不成立,说自己是体制外的写作者,无非是一个标榜。羞于说自己是体制内的写作者,其实也没有必要。完全取决于作家对于文学的态度。一方面想要现世功利和好处,一方面又想与其他写作者作一个意识形态和身份上的区隔,这一心态,比比皆是。
二
姜:你多次谈到你对散文的理解,譬如你所理解的散文写作的“现场回归”。 还有你的《原生态:散文十三家》,既廓清了你的阅读轨迹,也表明了你的散文立场与评价标准。凡此,我们都可以看作是你的散文观。现在,我们就请你把你的散文观再一次系统地表述一下。
杨: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文学就是用来书写写作者所处时代,尤其是他对文学的理解,他的个人时代经验和时代在他个人身上的痕迹,把这样的一种“状态”“文学”地呈现出来,就是了不起的。所谓回到现场,就是回到我们所在的这个时代的所有场域,回到人和人群的生存状态、精神困境和思想要求上来。无论受众多少,《原生态:散文十三家》提出的散文主张可说适逢其时,还是比较成功的。我的散文观大致如此:紧贴“此时我在”这个时间和生命节点和空间,力所能及地,以人为全部参照点,进行触及时代真正本质和人心人性的发现和表达,应当是散文写作的一个要点所在。语言精准、新鲜度、自由精神、创造力、形式好,我觉得这是衡量散文的一个基本参照。
姜:你提到的当前的散文写作,已经形成一个大致如下的格局:一个是以已经成名的散文作家意识和喜好为主宰的“纯粹新散文”跟从式写作。这种情形,其实可以看作是这一类散文作家的集体无意识,也可以看成是这些散文家的文学操守。
杨:文学可以模仿,但是是在写作初期。写了一段时间,再模仿,无异于抄袭。据我观察,散文写作者目前甚众,但真正有自己的“道路”和“精神向度”的却寥寥无几。相当一部分写作者亦步亦趋,跟风走步,鹦鹉学舌,东施效颦。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就是缺乏思想,缺乏识见,缺乏自我感。他们以为某些被吹捧的才是最好的,某些报刊喜欢的才是主流和方向。这样的写作者是没有前途的。这一现象,也可以上升为当下全民集体无意识在文学层面的一个具体表现。
姜:你还谈到一个散文作家首先要奠定的是立场,是对散文乃至散文这一文体的深刻理解和把握,而这一切,是建立在对前人作品乃至当世作家创作的透彻认识和整体评估上。现在,你还持这样的观点吗?我总觉得,这样一来,对一个散文家而言,规定性的动作就多了点。这样的散文家能否成为大散文家,就值得怀疑了。
杨:一个写作者必然是文学的行家,或者杂家。一个写作者也是很好的批评家和文学观察者。闷头写也是好事,但要真正地洞彻和了悟文学,还是要有对前人和同代人作品的非凡透视能力。唯有这样,你才可以在写作上更宽裕和自由,更能站在前沿的位置,去环顾众多同道,并为自己的写作选定一个较好的角度,有一个相对较高的起点。这个不是规定,而是一种自觉的自我要求。文学被要求就会坏事。文学是最自由的东西,一旦把某个说法作为教条,那就距离毁灭不远了。
姜:恕我直言,在这本《原生态:散文十三家》里,走出来的不是很多。被人们广泛接受与认知的也没有多少人。当然,这可能与散文这一文体相关。
杨:诚如所言,《原生态:散文十三家》当中的作者,走出来、广为人知的,还真的没有几个。这和他们自身有关。他们有的转向小说,有的被工作拖累,有的洗手不干。但那本书里的许多文字还是非常漂亮的,放在整个当代散文当中,也不能说差。另一方面,其中的很多人能不能走得更好更深更远一些,现在还不好说。说不定哪一天,这些人忽然又横空出世。因为,文学不是一时之兴趣,而是一生之情结。
姜:这样,我们今天也就不得不重提散文写作的出路和方向问题。
杨:关于这一点,我也很迷茫。从当前的散文写作整体态势来看,散文还是处在没落时期,尽管有几个被叫好,吹捧的,其实也是很悬乎的。我们的媒体,读者,很多时候是不具备独立判断能力的,跟着跑的多,一权威说好了,马上跟上,连篇累牍,共吵共喊。风一过,又是一片沉寂。还是要以作品说话。作品永远是作家的立身之本。关于当下的散文出路,我觉得唯有去书写属于自己的文学地理,特别是时代之下的众生情状,人在此时代的心灵痕迹和精神诉求,才是比较好的一条通达之路。我认为,散文应当更宽泛一些,不要拘泥于任何人对散文的定义、对散文的要求,写自己熟悉的,喜欢的,观察和思考深刻的,与自己生命灵魂关联紧密的,永远不会有错。像小说一样探究人心人性,描绘时代之下的万民行状,像诗歌那样饱含隐喻和建构的热情,并且具备科学的直觉,自由、向善、亲切、低姿态、关怀的力量,我觉得这就是散文的主方向。
姜:一个传统的,也是人所共知的共识性话题,即“形散神不散”,你现在如何看待呢?散文界对此有颠覆性的理论,但我想问的是,这些颠覆性的理论,其影响力究竟有多大,有没有切实改变散文的文学生态?
杨:我并不觉得“形散神不散”的定论过时了,也不觉得这个定论有什么好。对于一个获得大家公认的文学理论,在纸上言说是可以的,因为它是文学理论,与创作实践永远有距离。文学理论不是教你如何去操作,而是理解文学门类的一种方法。如果把这些当真、并且奉若神明,或者踩在脚下,都是幼稚或者不懂得创作规律的表现。我的意见是,对所有的文学理论,都没有必要刻意颠覆。因为,文学理论是随着文学作品而走的,文学理论是文学作品的“副产出”,作家,只管用适合的,新鲜的,富有创造力的方法去做自己的事,写自己的作品就够了。事实上,很多试图颠覆已过时文学理论的做法都像是未成年的孩子顶撞父母,当时生气,事后还是要和解。对任何文学理论,适合我的则采纳之,有科学性与合理性的听从之,其他的,都可以放下,没必要过分计较。文学理论,从来不可影响文学的生态,但是,我们要警惕文学批评背后的非文学力量。
姜:非文学力量!这话说起来有点沉重,也很大。不一而足了。其实就像小说界,散文有一段时间也非常热衷于写个人的私生活。个性话语未尝不可。但散文写作的个人化、内心化和另类化倾向如果越过了边界,可能就丧失了散文的立场与本质。散文,在我看来,还是应该给人们以美的享受,让人在一种美的浸润中获得满足与愉悦。
杨:私生活也是散文应当着力的一种。私生活也是文学应当书写的领域。因为,个人私生活里也有各种外部的影响和痕迹。一个人处在一个社会一个时代,无论从哪个角度说,我们都是时代的产物,即使隐居,出家,这些也都是受时代影响的。当然,有些私生活写到了内心的卑暗处和人性恶、自私等等层面,我觉得是可以赞赏的。自我审视、自我点验和拷问,其实也很有震撼性。散文不唯提供美的享受与愉悦,散文更重要的是对时代的全息观察和反映,更重要的是对时代的发现、记录、“审察”与“提炼和提升”。如果每个写作者都从不同角度和现实场域,不同的艺术形式和精神要求这样做,我觉得才符合文艺基本的道统。
姜:还有个现象,不知道你是否注意到,很多散文家,其实第一身份并不是散文家,而首先是小说家或诗人。散文倒是作为他们写作的“边角料”存在着的。恰恰是这些边角料,反倒别有情趣,也成为他们重要的文学存在。
杨:事实正是如此。专业的往往有匠气。当工匠时间久了,就有了套路和模式。我个人还是喜欢那种剑走偏锋的,不经意之间的自然书写。在文艺这条路上,自然永远是一种葆有创造力的“老师”。所以,在上面,我表达了对张承志、贾平凹等小说家开拓散文的敬意。
三
姜:我发现,故乡是你散文的一个重要的主题。看来,文学母题的意义是庞大且厚重的;不管针对什么样的文体,那些永恒的文学母题,是所有作家都非常关注的。我发现你对故乡的感情有点特别,你在书上说,你觉得南太行无比丑陋;但一个作家,势必与自己的故乡血肉相连,同气连枝。这是作为作家的宿命。无论这个家乡是丑陋还是美丽。
杨:故乡对于男人,是根脉的事,是血液中的事,更是精神和灵魂的事。我的故乡在南太行山,偏僻,封闭,乡村人古来有之的本性和行为方式仍旧顽强保留,尽管现在有所改变,但在我成长时期,他们还是那样。少小时候在乡村的苦难,主要是屈辱,尤其是人和人之间那种不加任何掩饰的恶意和恶行,使得我长大之后,曾经有一段时间对它深恶痛绝,甚至多次告诫自己,宁可客死异乡也不会再回来。现在看起来,这一心态包含了相当的孩子气。我父亲去世之后,我觉得故乡,自己的生身之地,在自己身体和灵魂里越来越重,越来越布满各种亲热却又非常奇诡的光亮。这种光亮曾经使得我莫名其妙且又欲罢不能。人到中年,这种感觉尤其强烈。每次回家,路过父亲和爷爷奶奶的坟茔,我就悲哀地想,总有一天,我也会像父亲一样躺在那里的,而且是永恒的。因此,对于故乡的文学书写,我还是非常用力的。我想到的是,为我的亲人和乡亲们写点东西,即使不能作为一种广为人知的文学存在,至少可以留给自己的儿子;即使百无一用,当他也老了的时候,一定会从我的那些文字中寻找自己祖先的来龙去脉乃至整个南太行乡域曾经的那些生命状态。
姜:巴丹吉林对你的意义何在?你是不是在那里生活了很久?你的《巴丹吉林的个人生活》缘何而产生?我看到过有人问你:“巴丹吉林、额济纳这些地名,在你的精神版图上有着什么样的指向和意义?”
杨:巴丹吉林是一片浩大的、充满上古传奇的沙漠,古称流沙,其中有著名的弱水河和匈奴语名字沿用至今的“额济纳”。我十八岁参军到那里,除了在上海读书的几年,基本上都在那里度过,一直到2011年。我在巴丹吉林的时间比在老家南太行乡村还要长。每一块地域都有自己的自然属性与文化属性。而这些,却是无形中改变人的强大力量。我起初并不喜欢沙漠,我的理想是容身城市。沮丧一段时间后,却发现,沙漠是最适合我这样的人的地方。千里黄沙,苍茫瀚海,绿洲和河流静默其中。尽管风暴不断,个人前途迷茫而又苦痛,但作为一个出身农家的人,偌大的中国有一个收留我的地方,已经是上帝格外开恩了。
姜:看来,巴丹吉林对你有着故乡或原乡的意义了。
杨:我的文学梦很早就有,但参军后才真正开始。写诗,把自己写到骨肉枯干,体重不到90斤。1994年开始发表诗歌。1998年觉得自己的诗歌存在很大问题,便转写散文。我的诗歌和散文,基本上都是以巴丹吉林沙漠和军旅生活为背景的,其中还有对故乡南太行乡村的穿插。慢慢地,我觉察了巴丹吉林对我生命的意义和文学写作的价值。天如穹井,白云宛如丝绸,赤地千里,浩瀚汹涌,这种阔大与苍凉,非常适合我的性格,天长日久中,我的骨子和精神当中也忽然有了沙漠的这一元素和品性。我一向觉得,做人要大,作文也要大。做人要从大处观察世界,写文要从细微处感知并顿悟和提升。与此同时,我也发现,自己的文章,无论诗歌还是散文及零打碎敲的批评和小说,都有了一种与沙漠氛围非常切合的“气息”,那就是,悲壮、肃穆、深切、疼痛。现在,虽然我离开沙漠几年时间了,但这种“气息”仍在。这使我感到幸运,也觉得,巴丹吉林沙漠不仅是容留和损耗我青春的地方,也是塑造我个性和文学作品的根本所在。它俨然成为了我一个精神背景和文学地理,当然还有灵魂版图。
姜:坦率地说,你的这些经历,对我们沿海的人来说,显得非常陌生。而对我们这些沿海的常年足不出户的书斋中人来说,则更显得陌生了。你当初写作这些散文时,有没有考虑过我们这样的读者会很难接受这种异质文化的作品?
杨:有这样的隔阂。南北文化本来不同,西北更是独特,沿海人对于西北的概念大致是雪山大漠,草原戈壁,荒凉至极,苍茫雄浑。但在西北待惯了的人,他们对于西北之地的理解和看法却是另外一种。我也认为,搞艺术的人不去西北历练或者看看,作品就很难开阔起来。这些年来,我一直在强调地域文化对于写作者那种无可言状的影响力。写沙漠背景的文本之初,我根本没考虑到受众的问题。我觉得,写作者很多时候的写作是为某一个,某一群人而写的, 而不是为大众,也绝不会考虑什么影响和现实名利的东西。自觉自发地写作,自由自在地表达,唯我独尊的呈现,切入心灵的通达,我始终崇尚这样的一个状态。
姜:这里面于是就有一个问题,我们如何将异质文化的内涵转化为大家都能接受的文学作品及文学风格?我看到你的作品里经常体现出沉雄、苍凉和血性的意味,这使得你的散文异于一般的叙事状物。
杨:文学的本质是相通的,温暖,有力量,并不在于作品的“格调”。我也觉得这个时代最缺乏的是血性,是表现一种阔大的精神力量及其沉雄苍凉的人生况味。太多的温软腔调尽管时代需要,但刚性、豁达、明晰和大开大合的文学品质和精神境界也有存在的必要。
姜:我由此发现,你这么多年来,一直书写着一般人有点陌生的东西:《匈奴秘史》、《沙漠之书》、《梦想的边疆》、《丝绸路上的月光马蹄》等,都是在写我们非常陌生的历史与人文。这种写作,看来你是有着特别的情怀了。要不,你就是想帮我们追回那快要逝去的历史。你的写作,是不是想要有这样的担当?
杨:在一地热爱一地,进而了解一地,我觉得这应当是写作的天赋和写作必修的一门功课。西北有恩于我,是我开启真正人生、也是岳父母生活和我儿子出生之地,无论是文学上还是现实生活中,西北都与我割舍不开,同气连枝的。我写的那些文章,其实也是有报恩的成分在内。我的那些书,基本上涉及到了整个西北,也就是古之“小西域”、河西走廊、青藏高地、蒙古高原和湟水流域,但主要的场域还是河西走廊和阿拉善高原。追溯历史是让自己对一方地域了解得更为透彻和全面,利于自己的文学书写,也利于自己更好地认识所在的地域及其自然环境和文化蕴含。这对于写东西的人来说,是很有益处的。
姜:你最近出的一本散文集里,我看有很多历史的史料。你是不是想要寻求我们这个时代的史传散文的突破呢?像这样的史传特征,在《中国的匈奴》那篇作品里更其突出。
杨:实话说,我对历史文化散文没有兴趣,我愿意写现实生活和时代场域的东西。也觉得,历史文学散文写作,其实很徒劳,除了可以多一点版税以外,对于作家的文学成绩似乎没有多大的意义。我写匈奴体裁,也是热爱这个消失了的游牧军团,对他们史前时期在蒙古高原和大漠之中的生活、战争、习性和文化有强烈的兴趣,进而写了这样一本书。
姜:《行走沙漠二十年》是你2014年出的一本新书,同样锁定了沙漠。不过,行走沙漠的生存方式,是让我们肃然起敬的。我现在想,你这种行走方式,应该寄托了你的一种想头吧?
杨:这本书是一本纯粹的旅行书,无非是介绍了一些沙漠常识和个人在沙漠的各种体验,当然还涉及到阿拉善高原周边的一些地方,如河西走廊沿途的人文遗迹和自然风貌等等。书名是责编起的。做得很用心,也很辛苦。唯一不足的是,很多文章是长文拆开之后的小段落。从文章角度来说,可能有些不大好。
姜:我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莫言写高密东北乡,贾平凹写商州,他们已经建立起了自身的小说类文学地理版图。你的散文作品中则有着众多的地域描写与叙事。你是不是也想在散文里建立起你的散文类的文学地理版图呢?
杨:我依托的现实地理,一是巴丹吉林沙漠——阿拉善高原——西域,另一个就是故乡南太行乡村。这两个地域这些年分别在文学圈子有了一定承认和知名度,尽管很小,但对我个人来说,还是很欣慰的。对于文学创作来说,地域的依托必不可少,可地域很大程度上也是限制。我觉得,突破地域限制的唯一有效的方法,就是由自然人文转到现实中的人和人群,他们的生存状态,在现实中的诸多遭际,文化上的断裂之痛,精神上的迷茫之惑,灵魂中的复杂和奇诡,如此等等,才可能将地域性的文学提升到一个广阔的境地上来。现在,到西南之后,我一直在寻找一个完全从属于自己的文学地理,前后写过川藏线、西藏山南和阿坝州,但都是浅尝辄止,属于一知半解的多。这方面,需要很好地去加强。
姜:关于《生死故乡》,“故乡”前面加了“生死”二字。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乡村的消逝吗?
杨:当前的乡村,南北之间可能有很大的不同。我所了解的北方乡村,正处在一个剧烈的转型期。四五十年代的人相继故去之后,凝聚并且靠他们传承的乡村文化面临着巨大的断裂。六七十年代的人虽然有的当了爷爷,但由于掌握知识多、跟从时代的能力较强,多数选择了迁居城市。八九十年代的人虽然相当一部分在乡村生活,但乡村已经今非昔比,新的思想观念、意识潮流、行为方式、行为习惯、教育日常完全是全新的另一种;有的还能与传统的乡村接轨,有的干脆与乡村分道扬镳。乡村的崩溃首先是人的和文化的崩溃,在这种背景下,乡村正处在一个信仰混乱乃至丧失、价值观念大规模颠覆而又无从重建、城乡特征急剧消失的时期,使得当前的乡村出现了一些非常复杂的现象,令人无从捉摸。我想这可能是延续数千年的乡村农耕文化全面更新换代的非常时刻,衰亡与新生或者介于两者之间,我们这一代人熟稔的乡村已经面目全非。因此,当朋友建议我把书名定为《生死故乡》时候,我大为叫好。新旧乡村,生死之间。人的交替也是自然和现实生活的变迁。在这生死之间,就文学创作而言,对于乡村,我们的文学书写还有很多的大有可为,而不是像某些批评家信口胡诌的那样,乡村文学已经消亡之类的,纯粹是坐在虎皮上想老虎。
姜:《生死故乡》里,其实有很多小说笔法在,很多故事及有关性的描写,如果拾掇成小说,也非常有看点。当然,在我们这个古老的国度,小说本身一开始就是以散文的形态出现的。我想问的是,你现在选择散文,但我看你的情形,其实也完全可以选择小说这种文体立足文坛的,为什么放弃小说而抓住了散文呢?
杨:故事是打动人心的。抒情很多时候只是一时快意。对于南太行乡村,我写了很多文字,基本上都是抒情议论的多;说事,人,再发些感慨之类的。我对这样的写法非常失望和疲倦。在写的时候,选择了讲故事,或者纯叙述,尽量把自己从中剥离出来。不需要作者全知全能,喋喋不休,用一种视角把那些人典型化和艺术化地“树起来”就是最大的目的。因此,我选用了这一种写作方式。介于虚构与非虚构之间,纪实与想象并行推进,这样的效果我自己还感觉不错。其中一些,以小说的形式在刊物上发了,也算是对我的一个认同。其实我最理想的文体是小说,我一直对小说怀有莫名的敬畏。这些年,写的小说总数不超过十个。而且都是短篇,有些发表了,有些没有。我觉得我的小说能力还是比较弱一些,或许是长期写散文、诗歌和批评的缘故。我一直想有一个非常散漫与自由的时间,专门来做几年的小说。可是,手头的活儿非常多,要写的东西一个接着一个,很难让自己从其他文体中空闲出来。这很矛盾,也很痛苦。
姜:您个人的经历非常复杂,农民、打工者、军人、作家,这些身份的转换与转变,对你的散文写作有什么样的意义?
杨:除了农民和军人,其他的经验非常简短,有的几个月,有的几天,但也都是非常有意思的体验和经验;这对我文学写作,是非常有益的。农民出身,长期从军,这两点在我个人生命和秉性里是最为持久和隆重的。尽管进城很多年了,开始以为自己身上真的没有泥巴了,忽有一天,我发现自己还是一个农民;军人这个身份和历练,对我的意义也很大,我知道自己血液里有相当比重的铁的成分,自己的灵魂里有一些英雄主义的火苗和种子。一个男人,必须要血性足;一个男人,要有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要有一种纵马沙场、横刀江湖的豪气与决绝之心。农民的自卑和卑微,自知和朴素,军人的铁血梦想与正直坦率,这对我的文学写作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再者,我还有点书生的羸弱和某种顾影自怜。关于这些,我相信在自己文字中体现得更为真切一些。
姜:你的写作状态应该是非常自由的。《生死故乡》中,《张刘家往事》里慕向中一说村子里又有新事儿发生,我看你就收拾行装,几经辗转,回去了。这样的写作状态与生存状态,着实令人羡慕。我的意思是,只有这样的状态下的写作,才是从容的。写散文需要这样的心性与状态。这样的写作状态,与你的人生经历应该非常相关吧?或者说,这种写作状态已经就是你的人生状态。
杨:我喜欢一种随遇而安的写作状态,而不是事先想好。我觉得文学就是情之所至的产物,预先的规划肯定建立在自己特别想写、非常有感情的基础上,才寻得时机去完成的。对于故乡,我一次次体察和思考,有时候觉得她很清晰,有时候又很模糊,的确难以抓住她的关键部位。忽然有一天,我想,是不是能以外乡人的身份介入呢?这样的一个角度可能更客观和真实,一个对彼地熟稔的写作者故意把自己从中“摘”出来,以陌生的角度进入,效果可能更好,更有利于对人物的观察和呈现。文章写好之后,我觉得还不是很满意,有些地方仓促了一些,缺乏再深一步的“典型化”和“艺术化”。这也是《生死故乡》一书的缺憾所在。
四
姜:你对当下的散文总体上有什么样的评价?你对你的哪些同行有着非常深刻的感悟?
杨:关于当下的散文,在不同文章中,我说了很多。这里不想重复。就说两点,第一,这还是一个散文相当没落的时期,繁荣不等于货真价实,叫好不等于名副其实;第二,散文还是自己把自己逼到了胡同里,也是散文家自己把自己送到了越来越狭小的境域里面去了。关于同行,我觉得有些人做得很好,还有相当一部分还没建立起属于自己的“散文”。我看同行作品,找缺点比优点多,换句话说,从他们的作品当中,我可以学习的东西太少,而我可以指摘的问题又太多。
姜:除了散文同行,我们也可以谈一谈散文流派。你对先锋时期的散文成就如何评价?
杨:“先锋散文”,这个概念似乎不够科学,我觉得不能成立。中国的文学,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一直就是西方文学的忠实跟从者。几乎所有的先锋散文,都可以在西方那里找到摹本和鼻祖。这是一件很悲哀的事情。文艺最根本的要求是原创,我们连原创的能力都丧失了,还来谈什么先锋?这本身有点荒谬。倒是新近几年,有一些新的散文家,由于出身,特别是文化环境与以往的巨大不同,作品写得更为到位,并且带有先锋的意味。那些“拿来主义”痕迹很重的作品,我觉得充其量是二道贩子,不足以称之为先锋。当然,那些以先锋命名的散文,对于本土散文写作来说,也有很强、很及时的推动和示范作用。它们也是推动中国新时期散文解放,进一步从“无我”到“有我”,从集体到个人,从抒情到叙事,从精英化到大众化的主要力量。也是功不可没。现在反身来看,先锋散文中还真的出现了很多优秀的作品;尽管有拿来的嫌疑,但我个人还是对他们保持了浓重的敬意。
姜:你是如何走向文坛的?在你走向散文界的过程中,哪些作家作品给了你决定性的影响?
杨:我起初写诗,大致有五年的时间,后来写散文。对我有主要影响的作家主要有昌耀、张承志、贾平凹、史铁生、杨显惠,还有博尔赫斯、西蒙娜·薇依、阿尔贝·加缪、赫拉克利特、哈耶克等人和他们的作品。
姜:最近打算写什么作品?
杨:2015年,先后有五本书的样子。有写丝绸之路的,川藏的,也有些写南太行乡村的。下一步,想写的是近年来北方乡村的当下状态,包括民主选举、乡村权利结构的嬗变和调整,乡村风习和文化的更新与变异,乡村癌症病人最后人生时光中的亲情、利益和钱财博弈之间的人心人性,乡村各类从业人员的现实遭际和蹊跷命运等等。另一本是长篇小说,时间跨度可能长达五十年,涵盖面更宽泛一些,涉及改革开放初期乡村现状以及军队现代化信息化进程、时代沧桑巨变等等,主要书写具体人身上的时代痕迹、不同思想追求和现实遭遇。这本书酝酿了很久,起码有十几年。我想,这两年内,应当是下笔完成的时候了。其他方面,会由着性子继续写诗和散文随笔评论等,没有特别明确的计划。
(责任编辑:李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