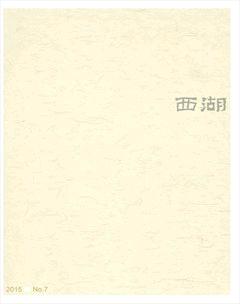生命的细节
蒋军辉
这些年来,我的人生百无聊赖,我对争权夺利蝇营狗苟没有兴趣,在经历了一些事情后,许多人许多事对我也早已不再重要。这几年的经历,改变了我对人的看法和对人生的态度。我重拾写作,我知道我也许写得不是很好,但它却可以让我拥有现实之外的另一种人生。对我来说,写作不过是一种生活方式,正如有人把打麻将当成生活的一部分一样。对于写出来的那些东西,我常常提不起拿出去发表的兴趣。
当生命中所有的喧嚣和繁华离去之后,人就会变得安静,如同艳阳下澄澈的湖,宽厚,安宁,大度,耐心。你会有足够的时间去打量你的人生你的生活还有你身边来来往往的人。时间的隧道被打开了,沿着隧道往回走,重温曾经经历过的风景,一切如同昨日。人生是一张单程车票,在积攒了一把年纪之后,你就会明白什么是世事沧桑,你的内心也会变得柔软,常常被一些生活的细节感动得一塌糊涂。
前段日子去了山区的一所小学,这所学校只有一位女教师,五十多岁了,在这所学校待了近三十年。在这近三十年里,她早上把学生接到学校,晚上把学生送回家,天天如此。每天九点多钟,她还要趁着下课给孩子们蒸中饭。那天早上,我看见她领着接来的十几个学生走进校园,就像一只老母鸡领着一群小鸡,那一刻,我的内心被温暖了,我发现自己其实很渺小。
往事被岁月风化成了记忆的碎片,逝去的时光沉入无边的黑暗,唯有记忆悬浮在水中,静待我们的打捞。夜深人静的时候,它会主动来敲门。我生活的这个地方,曾被称为“鱼米之乡”,现在,许多河里已经没有鱼,而我吃的大米,也来自东北。我现在住的这个小区,以前是块农田,是我曾经赤脚走过的地方。二十多年前,这里水沟纵横,蛙声阵阵,螃蟹横行,春天是一方方金黄的油菜花,夏天是一阵阵连绵起伏的稻浪,还有水池里的浮萍和刺菱。这一切,都被埋在了时间的深处,成了记忆的化石。现在,我住在一个钢筋水泥垒成的格子里,窗外是迷蒙的夜空,我不记得上一次仰望星空是在什么时候,至于日出,现在已经看不到了,因为钢筋水泥的积木已经遮住了地平线,粗暴,霸道,让人无可奈何。有一天,我的窗口飞来一只久违了的麻雀,她在花架上稍作停留,那一刻,我竟然被莫名其妙地感动了。这是生活的细节。
我们的生活不缺少令人感动的细节。每天下班回家,路过小区的花园,我都会看见一对老年夫妇,老太太坐在轮椅上,老头儿推着车,他们缓缓地沿着小区的路走着,没有话语,只有安详与恬静;有时天下雨,他们会穿上雨衣,那种透明的塑料雨衣,依然安详,与世无争,行走着他们人生最后的路。儿子的学校旁边,是一个公园,每次去接儿子,如果还早,我会去公园转转。有一天我看见了一对老人,男的显然左脚行动不便,女的左手扶着男的,右手牵着一根布条,布条的另一端系在男的左脚的脚踝上,女的拉一把,男的左脚就往前走一步,两个人走得极其默契,像两个摇摆的木偶。他们沧桑的脸上是一脸的冷漠,还有沉默。其实,每个人的人生就写在他们的脸上,只是旁人不容易读懂而已。我有时候会想,透过他们沉默的脸,这两对老人,他们有着怎样的人生,是像大海一样深沉,波涛起伏,还是像湖水一样清澈宁静?
我原来住的村子离现在的小区不远,只隔着一条马路。但我很少去那儿,因为我的人生被种种莫名其妙、不明所以、不知所措的忙碌所纠缠。那里对我来说近在咫尺,却远在天涯。我对那里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有一天我回去了一趟,居然惊讶地发现,许多我熟悉的老人,已经在这几年里陆续离开了人世。真是世事沧桑,让人讶异。随着老人们的离世,他们走过的人生,也和他们的躯壳一起,化为尘埃,埋没于土中。他们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痕迹留在愿意记住他们的人们的记忆里,最后,时间会把所有的痕迹抹去,如同一块抹布抹掉一堆残渣。
但是,每一个平凡的人生都是值得尊敬的。尽管它们最终将消逝在黑色的夜空里,了无踪迹。
每一个人生都是一部作品,现实的人生往往比小说更精彩。没事的时候,我就想,如果让我选择人生,我最想干的事是什么?思考的结果是,我想做一个民间记忆的打捞者,四处去流浪,去和一个个人聊天,记录一个个鲜活的人的记忆,他们的生活,他们的凄惶和得意,无奈和平淡,那是时代的碎片,也是一个民族的记忆,可以印证“历史”的真实与虚假。然后呢,然后把它写成小说,因为我只会写小说。